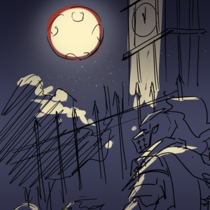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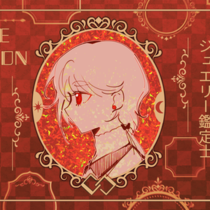




*同样一件事在两个不同的参与者眼里,看到的东西和注意的细节都不太一样。
*怎么会有人用能力学打台球的。
*怎么还有同事架着人用能力学台球的!
菲恩图斯轻巧自然地把那杯咖啡从叶斯廷的手边拿起来,稳妥地将它放置在远离叶斯廷惯用手的位置,并且把盖子盖好。叶斯廷坐在那儿目睹了完整的犯罪过程,默不作声地用视线对菲恩图斯表达了抗议。菲恩图斯假装没看见,又把咖啡杯推远了几寸。
“……”叶斯廷叹了口气,“菲恩,把咖啡给我。”
“我们只是来走访一下整合情报的,你猜我为什么会选这儿?”菲恩图斯意有所指地垂下视线看了眼叶斯廷的电脑,可惜他没来得及把叶斯廷的设备扣在办公室。“难得是个能放松些的地点,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的良苦用心?”
叶斯廷细致地体会了一下这份过于沉重的良苦用心,感觉到自己的胃脏随着这份来自前辈的关怀一起下沉,同样下沉的还有他的眉心。他叹了口气,决定自给自足——他伸出手去拿自己的咖啡杯——菲恩图斯显然是对桌子的大小以及叶斯廷的臂长有了一些细微的计算误差,导致咖啡杯脱离了他的庇护被叶斯廷重新攥回手里,并且更显然的是他对自己的臂长以及桌子的大小有更大的计算误差,当他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把咖啡杯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够不着。
叶斯廷假装没看见。“整合情报也是一种工作。已经到约定时间了,她在哪里?”
菲恩图斯在两次尝试之后放弃了把杯子拿回来(他的好胜心不允许他用站起来的方式去够到它),和叶斯廷一起作出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将视线投向门口,略略一抬下巴。
叶斯廷抬起头,从门口跨进来的那个红色身影让他有了那么几分自己还在指挥办公室的感觉。加舍尔迎上他们的视线,简洁地一颔首,步履轻捷地像一小团被风吹过来的烛火一样,落在桌边。
“…………………………”菲恩图斯眼看着这两个人在桌边排排坐,整齐划一地打开电脑,键盘声和手指滑动触控板的声音嗒嗒响。
“…………欺负先锋派遣队不需要用电脑是吧。”他有一种严重地被排挤了的感觉,于是把胳膊支上桌面,硬是在两台电脑间掏出一小块空隙,并且拿起自己的手机(界面是公司闲聊群)假装自己融入了他们,并且对加舍尔和叶斯廷投来的“你在做什么”的余光大大方方地视而不见。“你们俩认识?”
“……指挥办公室和情报收集办公室的合作非常密切,”叶斯廷的视线在菲恩图斯的手机界面上默默停留了几秒钟(看起来菲恩一点都不在意)又收了回来,他和加舍尔不约而同地挪了挪自己的电脑,给菲恩图斯腾出些空间来。“上次的坠楼事件也是他们作情报支持的。”
“是的,我也听莱特提过关于指挥办公室的……趣事。”加舍尔看了一眼叶斯廷手边的咖啡,暂且将电脑合上站起身,看向同样没有咖啡因支持的菲恩图斯。
“需要来点什么吗?我去买。”
“哪有劳驾女士的道理,请交给我吧。”菲恩图斯从善如流地揣起手机也站起身,终于找到了去拿走叶斯廷的咖啡杯的机会,然而入手空荡的重量让他的笑容略微一僵——叶斯廷保持着严肃地表情对着自己的电脑,坚定地没有分给菲恩图斯哪怕一点余光。
“……正好帮他带一杯。您的点单是?”
“好吧,一杯咖啡,谢谢。”加舍尔没有多余的推辞,又坐回自己的位置,听着菲恩图斯一边小声抱怨一边走向柜台,并没有顺手带走他已经拿起来的空杯。
叶斯廷将空杯略微捏扁一些,投进墙角的垃圾桶。他看起来精神并不是很好,想来大约是刚刚得到的各同事的反馈并不令人满意,加舍尔对此非常感同身受,同为加班过度的7/24待命员工在沉默的视线交换间达成了对彼此的惺惺相惜。
“……总之,等他回来再说吧。现在的有效情报很少。”估计我们这里也不会发现什么就是了。叶斯廷看了眼这个俱乐部,人流量在变大,可惜他实在不觉得从一群中午就用鸡尾酒和气泡水把自己灌得醺醺欲醉或骨质疏松的年轻人口中得到什么有效情报,只能期望去其他地方调查的同事们能带回些更有价值的……他没等到加舍尔的回应,于是瞥了她一眼。加舍尔似乎是在听着他的话发呆,但好像并没有想要开口的意思。
或许是有什么心事,好在他们大概也不需要做什么很繁重的工作。叶斯廷收回视线。他对加舍尔的心事多少也有一些猜想,毕竟希蒙纳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藏得很深。
“朋友们,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轻松的冥想时间,”菲恩图斯端着两杯咖啡光荣回归,恰到好处地打破持续时间不超过半分钟的寂静(感觉更像是突然钻进他俩之间抻开翅膀抖了抖),“我们可以开始谈谈案情了?”
“………………”
“真是坏消息。”菲恩图斯用食指的指节抵着自己的额角,三人间随着诸多无果情报的交换安静了下来,加舍尔也靠在椅背上——重量不仅仅来自于调查和情报的无疾而终,她胃里始终住着另一群蝴蝶*。
“人越来越多了。”叶斯廷终于挑起了案件之外的话头。他默不作声地又稍稍压下了一些自己的肩膀,大概是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小个一点(菲恩图斯和加舍尔同时觉得这是个徒劳的尝试,但这样子还怪好笑的),颇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们去楼上的单间吧,我看到这里有斯诺克可以打。”
“…………我觉得我们——”
“你想想,在这种地方打斯诺克的一定都是熟客,年轻人里的混子比你想象中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加舍尔看着菲恩图斯用那种非常热切的眼神紧盯着叶斯廷(一定要形容的话,就像狮鹫看到了鹰马兽之类的),后者艰难地躲避着这种充满了危险意味的视线,甚至脸色都变得更糟糕了一点。
“我们完全可以跟他们打赌然后来套情报!”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仿佛不是针对工作而是针对叶斯廷的死期,加舍尔可以从叶斯廷的脸上清晰地读出那种“糟糕了我最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的心理活动。
她胃里的蝴蝶静静地憩着*。
“我不觉得两个完全没接触过台球的初学者和一个三流玩家能打过这里的熟客……”叶斯廷举起咖啡杯挡住自己,艰难地最后地抵抗,然而两个人四道视线齐刷刷地带着那种要刺穿纸杯的热度凝视着他,隔着杯子都无法忽视。
“…………”
“……等等、等等,你们,不会……”
“又能满足你想工作的需求又能满足我们俩(重音)娱乐的需求,多两全其美的事情!”
菲恩图斯和加舍尔在电光火石之间靠某种不可言说的思维同步达成了绝佳的共识,加舍尔利落地一左一右扣上两台笔记本的屏幕抱在怀里,菲恩图斯则是热情地(强硬地)把咖啡杯从叶斯廷手里拿(扣)出来,毫不含糊地把他从椅子上拉(架)了起来。
“等一下我的意见……我的咖啡……!”
加舍尔踩上楼梯前回头看了一眼,有一小块破碎的灯光落在她刚才倚靠的桌沿,像一只金色的蝴蝶——不知道是谁走过,它消失了。
她回头走上台阶。
“…………说到能力,”菲恩图斯的声音轻了一些,他稍稍侧过身,方便他的话语更隐秘地落到加舍尔的耳边,“为什么加舍尔小姐你不选择记忆清除办公室?既然都是工作,更能活用自己能力的地方不是更好吗?”
加舍尔对这个问题有那么一瞬间的空白。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怀表在那里,染上体温之后静静地缓慢地融化。
“……有记忆清除的能力,不代表一定要去用。”
叶斯廷并没有刻意去听他们的谈话。他手里的球杆指向母球,杆子轻轻地推出,母球滚向台球桌的边缘,一枚红球和一枚蓝球先后被撞到,分头奔向两个不同的球袋,咕嘟两声。他的耳坠吸饱了灯光,滴下两束昏暗的折射光带。
先是加舍尔的视线投了过来,然后是菲恩图斯走近了台球桌。介于之前的一个小时叶斯廷把围在这张桌旁边的所有玩家都打得落花流水(当然,是指斯诺克),他们现在完全凭实力得到了这张桌子的使用权。菲恩图斯似乎是接着方才他和加舍尔的对话说着什么,在两杆失败之后干脆上手把台球当篮球抛进球袋,而加舍尔似乎并没有加入的意思。
叶斯廷回头看向加舍尔,后者正用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我有些好奇,”叶斯廷就这样听着她指向自己的发言,光线在他们之间划开一道分明的界限,加舍尔只是在影子里看着他,“如果您也有这样的能力,会怎么利用它呢?”
叶斯廷看了一眼菲恩图斯,从菲恩图斯方才简短的不着边际的关于记忆的发言里总结出了加舍尔问题的源头。
“……我吗?”叶斯廷并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被抛给他。他不曾经历过遗忘,从来不知道“事情会过去”是什么样的体验。
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永远都只是上一秒,上一刻。
“是的,”他看到那一小团烛火在影子里晃了晃,“不过我只是问问……”
“……”叶斯廷将球杆收过来,在思考的间隙中拿起滑石粉块轻轻地按上球杆的皮头。
“……我大概不会用,哪怕是‘正确’的用法。”他把滑石粉块放回台球桌的桌沿。
“我之前见过从记忆清除办公室出来的普通人。在记忆清除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意识恍惚和记忆断层。”他用指尖点了点太阳穴的位置。
“那时候的他们看起来就像芦苇一样。我……你知道我的能力,我很……排斥那样的情况。”他用两个停顿的时间斟酌了措辞,把其他什么单词换成了排斥。
“对我来说,人是由记忆和历史堆砌成的,失去记忆本身就是非常残酷的惩罚。”他重新架起球杆,一杆之后又是一枚红球落袋。
“也许有人觉得忘记过去是一种救……好事,他们也许也确实拥有了快乐,”他终于又看向加舍尔,这一次他用指尖点了点自己的眉心,“但这种‘快乐’真的是好的吗?”
“……”加舍尔下意识地略微抬头,像是叶斯廷点得是她的眉心。她又自己抬手摸了摸——在皮肤、血肉和骨骼后面,那块藏着她所有的认知、情绪、让她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她的蝴蝶从这里来。
“抱歉,看来我提起了一些令人不适的疑问。”她放下手,几步跨过黑白的分界,菲恩图斯为女士让出正前的位置,她拾起桌上的一枚红球,抛进球袋里。
叶斯廷即刻对做了错误示范的菲恩图斯投以“你看看你”的眼神,后者自信地抓起一枚黑球看起来随时准备再来一轮。
“……这还怎么认真打。”他认命地放下球杆,看向加舍尔手里那枚黄球。
“不用道歉,只是我自己也很忌惮这样的能力。”叶斯廷将球杆递给菲恩图斯,制止他进一步破坏球局的行为,然而加舍尔好像意会不到一般,趁机把那枚黄球投入了球洞。
……他叹了口气。
“你就差把‘我有心事’写在脸上了。”菲恩图斯和叶斯廷接在柜台前的长队后面,在长条的队伍后面增加了一个突兀的凸起。叶斯廷尽力伏低一点,让自己不要那么显眼。
“什么?”
“你。”菲恩图斯用胳膊肘顶顶他,尽量把声音压低点,加舍尔没有加入他们的排队,在俱乐部的门口等待他们。
“我?”
“是因为她刚才的话吗?”
叶斯廷犹豫了一下。菲恩图斯研究着他的表情,结论是从这家伙的脸上虽然看出有无很容易,但要细究起来却麻烦得很。
“不,我只是有点不好的预感。”叶斯廷叹了口气,默默地把手揣进口袋里。
“用你那可靠的大脑推理一下要发生什么怎么样?”菲恩图斯拍拍他的后背。他的好指挥尴尬弓着身,一半屈服于人群的密度,一半受制于肩上的压力,可惜压力的那半没办法就这样被拍散,人群也不会因此而溶解。
“…………”叶斯廷试图整理措辞,但却没办法从字典里翻出一个合适的单词来形容自己的感觉,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我只是觉得好像有蝴蝶在飞。*”
“也是,毕竟到季节了。”
“…………”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想跟你开玩笑真难。”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用以形容一种持续的紧张、压力、忧愁、想要逃跑的心情。

序
黑暗将他淹没,侵入他的口鼻,钻进他的血管,游走于他的神经,他喜欢这种深沉的迷离。他不睁开眼睛,光明也不来入侵他的世界。他知道那些潜藏在黑暗里的东西,就如同现在,他的皮肤仿佛感受到了冰冷的抚摸,香水的味道钻进他的鼻腔,伴随着熟悉的呼吸节奏,他躺在那里,仿佛一具尸体,等待着死后亲人们对他的爱抚。
他睁开眼睛,所有的幻想都随着窗外投入的月光而消失,冰冷的房间里没有如火的爱情,没有燃烧的欲望,只有一个被自己的欲念填满的男人和一具尸体,那个等待着爱抚的人不是他。尸体的皮肤冰冷而僵硬,失去了常人的柔软,摸起来如同鞣制的皮革,里面的血液不再流动,冷硬的嘴唇不会再勾勒柔软的微笑。尸体全身的皮肤都失去了血色只剩下冰冷的惨白,只有曾经的美貌依旧。他仍执着地亲吻过每一寸皮肤,幻想女人体内仍存在着如同过去般炽热的爱情。
他在等待着,等待着被她的回归救赎。
热切的渴望充盈着他的身躯,他脱下自己的衣服。
1
斯嘉丽·布什记得那种眼神,它曾来自不同的人,愤怒的父亲,哭泣的母亲,恐惧的丈夫,疑惑的手足。而这一切最终都归咎于同一个问题——
你是谁?
这对斯嘉丽来说不是什么需要思考的最究极的哲学问题,而是应当抽身而退的信号。但现在她可不能离开埃癸斯,即使这次用那眼神质询她的是埃癸斯的异种同事。阿黛尔·马丁,向往着魔女美丽的身姿的奇美拉,在上次案件中她的一百分小姐。虽然她有意和她展开一段甜蜜美好的关系——她的意思是同事关系,斯嘉丽可不是会在感情问题上莽撞的冒失鬼,但是对方的眼神警告了她,这不是个好的信号,她也最好不要轻易接近对方,毕竟这张脸她确实很喜欢,而且还没有用够。
白炽灯的冷光自天花板照下,镜子中的女人比起白种人肤色较深,波浪似的卷发天生呈现出一种红棕色,双眼眼角微微上翘,棕色的眼眸偶尔会折射出类似琥珀般的金色,右边的唇角下有一颗美人痣。她的指尖轻抹过唇边多余的口红,丰满的唇上艳丽的红色均匀了许多。斯嘉丽觉得这个女人应当有些吉普赛的血统,不然为什么最后会悲惨地曝尸街头,战争结束时就连街上的流浪汉都会有人收尸。她的手指伸进衣服里面调整了一下内衣的肩带和罩杯的位置,柔软的胸部因此更加凸显出聚拢的形状,但是没关系,她现在会让这张脸发挥该有的作用。
就如同现在,她推开洗手间的门与外面等候已久的男人擦肩而过。她眯起眼睛同对方点头微笑,男人的目光仿佛被她的视线紧紧缠绕,当她走远时她听到后面传来脑袋撞在木板上的沉闷声音,走路不看前面的下场。
不过眼下对她来说还有比看那些大脑空空的男人们为她神魂颠倒更重要的事。埃癸斯,处理超自然事件的隐形组织,也是斯嘉丽现在的庇护所。所以很不凑巧,现在是斯嘉丽的工作时间。她走向车厢中段的位置,并在一个座位上坐下,“不好意思,久等了。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没事,还有一段时间才到库迪列罗,”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对她暂时的离开表示谅解,他抬起头,稍长的刘海儿后金色的眼眸跟着她坐下的动作转动,同为异种的布莱克隶属于神奇生物管控司,刚见面时无精打采的样子让她的脑海中一瞬间闪过无数张面孔,这个地方拼命的人还真够多的,“我们刚谈到这起案件的那些网络传闻。”
传闻。这次发生在库迪列罗的案件没有什么直通埃癸斯的报案人,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网络上的那些都市传说般的传闻。比如复活的死人,比如失踪的尸体。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死而复生吗?”
布莱克摇摇头,“我不知道,或许死了的人会变成幽灵,尸体变成活尸或者僵尸,但那可不是真正的死而复生。再说死而复生并不是什么好事。”
“是吗,耶稣复活的时候人们可是欢天喜地的呢。”
“布什,你该不会在本部的时候也和别人开这种玩笑吧。”
“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她眨眨眼睛。
“我会的。”他耸耸肩,之后便继续低头回到手里的手机上,没有对斯嘉丽的示好照单全收,更像是只出于同事情谊包容了她的不尊敬与逾矩。他的大拇指自下而上地在已经裂开的手机屏上滑动。
看来至少这次的一同工作的同事不是什么不懂通融的老古板,虽然可能也并不好说话。斯嘉丽做好了一些关于可能会出现的意见相左的未来的心理准备。
“那你呢,”这次是布莱克反问她,“收集办公室的专家对这些信息有什么见解吗?”
“说实话那些照片很模糊,但是我从这些照片上占卜到了死人的信息,这些尸体仍然只是尸体。所以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后期合成的还是尸体真的被人动了手脚。”斯嘉丽轻哼了一声,占卜时从她的卡牌上散发出的死人气息让她不舒服。她并不喜欢和那些死物打交道,死亡带来的不祥让她汗毛直立,但是在埃癸斯工作总是避免不了这些事。金钱和自由总是有代价的。“也别那么看着我,”她径直迎上那双金色的眼睛,“占卜不是那么方便的东西,不能过于依赖,别总想着不劳而获。”
“经验之谈?”
“算是吧。我们的生命那么漫长,总是会有些有趣的小意外。”
“希望那些意外算是有趣吧。”布莱克将手机放回口袋,列车的广播已经开始播报即将抵达库迪列罗的信息。
2
8月的库迪列罗已经进入初秋,刺目但不炎热的阳光洒在这片不大且拥挤的小镇上,这里没什么高楼大厦,低矮的房屋紧紧地挤在起伏的低地里,狭窄的道路恐怕连车辆通行都成问题。吹过的风里裹挟着海盐与海产丰收的味道,随着捕捞季的来临小镇的旅游业也渐入旺季,四处都能看到操着不同口音与语言的游客,因此斯嘉丽与布莱克拎着行李箱站在车站等待的身影也并不算显眼。
斯嘉丽挂上电话,“当地警察(Policía Local)马上就来,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当地警察(Policía Local)?”
“也就是城市治安警察,在这种小地方就会设置这种治安警察,所以也被称为当地警察。看来你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啊,”斯嘉丽看到布莱克点了点头,“那你最好把蓝牙耳机戴上,等会儿让我来和对方说话,别让那些当地警察发现你不会说西语,如果对方发现来的是英国人会变得麻烦。你手机上有谷歌的实时翻译吧?”
“有。我这就把它调成西语翻译。”
斯嘉丽将手机放回外套的口袋,手扶在行李箱的拉杆上,这次来到西班牙她没有戴那顶有着薄纱的帽子,而是改戴了一顶无檐帽,她将眼前的墨镜摘下挂在领口,因为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当地警察已经朝他们走来。
“你们好(Hola),警官们,”当他们走来时斯嘉丽率先向他们打招呼,“我们是受阿斯图里亚斯大区派遣的国家警察,我是布什,这位是布莱克。”
她偷偷瞄了一眼身后的同事,好在布莱克不是语言天赋全无,他点点头也同对方打招呼,“你好(Hola)。”
“你们好,我是阿尔沃,这是科尔塔,”在他身后皮肤晒得几乎成古铜色的男人咧开嘴对他们露出一口白得发光的牙齿,蓝色的眼睛在墨镜摘下后看向斯嘉丽,看起来这位科尔塔铆足了劲打算给像是大城市来的美女同事一个好印象,但是斯嘉丽只是对他礼节性地微笑点头,而后将视线继续投向阿尔沃,“我是目前这起案件的负责人,感谢二位前来协助。你们预定酒店了吗?”
“是的,可以的话请先送我们去酒店,路上你可以和我们讲讲案件目前的进展,之后我们希望去案发现场看看。”
“当然。需要帮你拎行李吗?”
在他身后的科尔塔跃跃欲试。斯嘉丽挑了挑眉。
“不了,谢谢。”
两个陌生人来到了这里。
他从未见过他们,那两个家伙,一男一女……他甚至感受得出来他们不是人类。这里发生的事终于把埃癸斯的那群鬣狗引到了这里。
女人用西班牙语同走在她前面的警察交谈,当她行走时她扭动的臀部与身体使他目不转睛,忽然她身后的男人转过头,他急忙躲到墓碑后面。脚步声与谈话声渐渐远了,他才再次缓慢地探出头。他不发出任何声响,视线仍停留在女人曼妙的身姿上,小心地在树林的阴影中穿行。
为他们带路的当地警察停在一座墓碑前,墓碑前的石板已不翼而飞,泥土被堆在旁边,本来湿润的深层泥土已经晒干,黑黢黢的墓坑暴露在阳光下。女人微微向前探出身体,她胸前的布料被撑出的明显轮廓使他频频注目。他知道墓坑里本应钉死的棺木盖子变成了碎片,现在里面空空如也。
“这是最近失窃的墓,死者已经去世三十年,她的丈夫就葬在她旁边,”警察指了下他右手边的墓,“她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搬走了,目前还没有联系上。”
被掘的是艾蕾娜·胡安·德-阿瓦罗亚的墓,一个死了三十年的女人,她生前的模样也是十足的俊俏,她有着深邃的五官与标致的身材,当她行走时乌黑的秀发被微风抚摸,而费尔南多·阿瓦罗亚·卡斯特罗这个走运的家伙得到了那个美人的垂青。他们甚至死后也葬在了一起。
女人直起身,十字架形状的墓碑上一串白色的花环挂在上面,只是花瓣早已干枯。艾蕾娜,艾蕾娜,瞧瞧你,你会知道你死后连给你献花的儿女都已经远走他乡了吗。
“这是她丈夫的墓?”费尔南多安宁地永眠在妻子的旁边,完好的大理石板隔绝了外面的信息,他对妻子被打扰的安眠一无所知。
“是的,失窃的尸体无一例外都是女性。”
“目前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推测吗?”
“根据墓园的监控录像,曾在深夜拍摄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中等体型,但面部特征被遮挡,我们在镇内排查了一些可能的人选,但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至于其他的,现在正是旅游季,来这里的游客们……”
“……好吧,接下来我们会对这里进行一些调查,希望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回去帮我们准备好你们的调查结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电话联系你们。”
“好吧,那么二位注意安全。”那些当地警察对他们敬了个礼简单告别后便迈开脚步沿着小路离开这里走向墓园的大门,他们的警车停在墓园外面的停车场里。
现在就只剩下了这两个外地人,没有人类的气息做掩护他随时可能会被发现,他屏住呼吸,悄悄挪动脚步打算移动到离他们更远的地方。
“既然你这么想和我们亲近亲近为什么不到更近些的地方来呢?”
突然炸裂的声响好像连他的身体也彻底击碎,他颤抖着转动眼珠,发现一枚子弹嵌在碎裂的墓碑边缘,而自己已经被男人手中的手枪瞄准。
“不是我!这些被挖开的墓不是我干的!上帝作证——”
“在我受够你的破铜嗓子发出的尖叫前给我闭嘴,我当然知道不会是你干的,你个幽灵要一副骨架子做什么。”
离开酒店后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郊区的墓园查看被掘开的墓穴,从进入这里开始斯嘉丽便感受到了异样的视线与动静,于是她想办法支开了警察们,结果令她大失所望,跟着他们的只是个中年人模样的男性幽灵。从他的衣着打扮看来或许他死亡的时间甚至在近代之前,而且不知为什么斯嘉丽总觉得他这张惹人厌的脸非常眼熟……
幽灵的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他站在树荫底下,目光四处扫来扫去像是无处可放,但每隔一会儿总会落在斯嘉丽的身上。她听见身旁的布莱克发出咋舌声,毕竟幽灵的眼神过于露骨,任谁都会感觉到不适。但是这正中斯嘉丽的下怀。
“先说说你的名字吧。”斯嘉丽装作对他的视线毫无察觉。
“阿隆索·菲博,您好,女士。”他倒是对礼仪十分熟稔,可能他生前曾经担任过哪个贵族家里的佣人吧。
“你好,菲博。接下来我们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可以谨慎作答,我想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再对你解释我们的身份?”
“是的,埃癸斯的贵人们,我一定知无不言。”他行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礼,斯嘉丽更加确信此人生前所处的时代。
“感谢你的配合。那对于这些被盗的尸体你有看见过什么可疑的人吗?”
“虽然我偶然瞥见过犯人,但他的脸完全被遮住,看不清长相。”
“你对他有别的印象吗?”
“没有了,他真的……十分谨慎,没有任何能看出他原本模样的方法。”
“是吗,”斯嘉丽微微抬起下巴,阿隆索仍是那副低着头的恭敬模样,时不时地抬起头瞄她一眼,“听说这附近还有尸体复活之类的传闻,关于这个你都知道些什么?”
“这个……”那双老鼠似的窄小眼睛再次开始四处打量。
“怎么了?”
“虽然我知道,”他的喉结动了动,那双眼睛也不再转来转去,而是紧盯着斯嘉丽,而斯嘉丽也将他这幅觊觎的模样尽收眼底,布莱克迈步挡在她身前,但阿隆索并不在意他的威胁,似乎已经打定主意他们不会拿他怎么样,“小的惶恐,如果我能亲吻您的手背……”
布莱克皱紧眉头,拇指已经按下手枪的保险,“布什……”
但斯嘉丽将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将他举枪的手推下,“没事,布莱克,一个吻手礼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随后她便走向身处阴影中的阿隆索。
树荫底下没有日光的明亮与温暖,阴影笼罩着他们,当站到阿隆索身前时斯嘉丽伸出手臂,手背朝上等待他的靠近。幽灵的脚步在草地上拖拽出沙沙的声响,他的目光紧盯着斯嘉丽的脸庞,然而就在他即将抬手接住她的左手时斯嘉丽立刻如同捕猎一般转而死死掐住了阿隆索的脖子,她甚至不需要迈步便对这色欲熏心的白痴手到擒来,幽灵冰冷的体温传递给她的手掌。
“这几百年死性不改啊,阿隆索·菲博。”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钳制的阿隆索只能抓紧斯嘉丽的手臂,试图扒开她的手指,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尖细,几乎要断了气似的,“什……什么……”
“我一开始也没想起来你这号人,你现在不认识我了很正常,更何况我换了脸也换了名字。但是被你服侍的日子还是很愉快的,管家菲博。”
那张脸在阿隆索的眼中扭曲、变形,直到变为另一个女人的模样,久远的记忆终于在他的脑海中复苏,眼前的女人像是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他被这恶魔扼住了喉咙,无论他想要尖叫还是大声求饶都得不到丝毫的机会。
“你怎么总是摆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呢,你真以为你那点儿东西称得上‘筹码’?我是不介意在埃癸斯的报告上添上一句该幽灵因妨碍公务已被就地正法,你觉得如何?”
幽灵用尽全力挤出挣扎和求饶,只期望这狐狸能暂时放过他的小命,“不……不!饶了我!饶了我!!女士……夫人!!”
幽灵的身体被斯嘉丽推倒在地,树林形成的暗影下女人的面容变得模糊,奇美拉的面容随着摇曳的树影变幻,但她嘴里的牙齿却如同狐狸的利齿,弯起的笑眼不加掩饰地投射出威胁,“几百年前你没能把我送上火刑架,现在就该我了。你应该不想变成那样吧?”
3
整片天空因为太阳的西斜已经变成了怒放的紫罗兰色,不消片刻,当赤红的夕阳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之下,整个小镇就会为人造灯光所接管进入夜晚。斯嘉丽不记得上次吃西班牙菜是什么时候,她不喜欢番茄的味道,不管生的还是熟的,所以晚饭时她只点了一道橄榄油煎鳕鱼佐火腿薄片和芦笋,主食吃了几个柔软的小餐包。但是布莱克看起来并不挑食,在餐馆他一勺接一勺地将有着浓厚番茄风味的烩饭送入口中。
现在她坐在旅馆的公共阳台,晚风带走了她口中香烟升起的烟雾,即使她从口中呼出一团白色烟尘,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布莱克靠着阳台的栏杆站在她前面,从室内映照出的温暖的灯光让他苍白的皮肤看起来有些血色。
“别那么看着我啦,”斯嘉丽将自己的左手第不知多少次展示给同事,“真的什么都没发生,量他也不敢对埃癸斯的人怎么样。”
布莱克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只得放弃似的耸耸肩,“我觉得你也不是会为了工作做到那个份上的人。”
“看来你对我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菲博透露的那些信息让你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吗?”
“没什么想法,他的消息和他头盖骨里的东西一样没用,只能知道那些尸体中的一些被做成了活死人。那种会动的尸体,电影里一样的。”说着斯嘉丽活动着手指,试图模仿出电影中那些僵硬的活尸。
“……我没时间看电影。”
“真的你总见过吧。被某种魔法驱动的死物,听说有些魔女深谙此道。”
“我之前已经和悠铃发过消息了,差点她就下班了。精通或者了解这些魔法的魔女并不住在这附近。会不会是人类?”
斯嘉丽的眼睛转向自己的手指,像是陷入沉思,“研究死灵魔法的人类?加舍尔·罗勒给我发过这里的人员档案,当地只有一个鲁斯家族,但是档案里没说过鲁斯家族研究过死灵魔法。”
“档案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一个月前。”
这是个较近的日期,布莱克点点头,这方面看起来没什么可怀疑的。“其他的呢,如果不是死灵魔法还能用什么方法让尸体动起来?”
斯嘉丽摇摇头,将吸尽的烟头在桌上的烟灰缸里碾灭,红色的火星在灰烬中转瞬即逝, “我可不知道,毕竟我对这种东西一窍不通。但是既然当地有会魔法的人类为什么不去问问?”
“他叫什么名字?”
斯嘉丽将桌上的手机翻开,解锁屏幕点开通讯软件中聊天窗口里的文档,指尖滑动屏幕直到看到她想要的那个名字。她抬起头看向布莱克。
“何塞·鲁斯?”
阿隆索·菲博是这里仅剩的幽灵,他对小镇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就像他当年对教会所宣称的教义与塑造的世界深信不疑,无论整个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还是太阳,社会的权力如何运作,这都同他毫无关系。他能看到的只有沉甸甸的黄金白银,投怀送抱的女人。但这可不包括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
他就知道那女人不对劲!可是几百年前他明明眼睁睁地看着那张脸被火焰吞噬,细腻的皮肤在火焰的亲吻中变得焦黑,曾经婀娜的身体变得如同黑炭一般干瘪。可是今天出现的女人什么都知道!他怀疑起自己的记忆,难道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记忆已经在时间的冲刷下变得模糊。他在黑夜中坐在墓园里的某块墓碑上,月光穿透了他的身体,没人知道他不再具有实体的大脑如何运作,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些答案已经随着他的死亡永远地跟着他腐朽的尸身一同消失。被烧死的究竟是谁?
曾经担任管家的阿隆索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或许也不会有机会再思考这个问题。在他熟悉的黑暗中,那个身影再次穿行于墓园,这次他躲过了摄像头,幽灵最后的思考与他死后的见闻也将永远地消失在无人知晓的黑夜中。
从口袋里传来的震动让阿黛尔·马丁不胜其扰,上午八点五十分,她来到埃癸斯灾害司办公室刚刚坐下不到一分钟从工作群组接连发来的工作信息便一刻不停地催促她尽快投入到工作当中。真是活见鬼了!但她还是不得不任劳任怨地将手机从口袋里抽出,谁让她现在是整个办公室里最没资格休息的人。
她打开内部的工作系统,却发现全欧洲都在等着她的出勤,这些家伙就不能哪怕一天消停点?但作为曾经同为惹事的家伙中的一个她好像也无法对此加以置喙。
伦敦的就算了,最近出了一起杀人案,指不定要忙成什么样。看来英国脱欧是为了不给欧洲的治安拖后腿,其他地方的都是些小打小闹,反正最后不是哪个幽灵的家长里短就是人类疑神疑鬼,走个流程拉倒,接了还能去旅个游。
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在她看到西班牙发来的支援请求时再一次看到了那个名字,她尽力躲避却无法视而不见的名字。
斯嘉丽·布什。
她的手指在申请说明旁边犹豫不决却不知应不应该点进去。她的理智告诉她不应该和那狐狸精有任何纠缠,那家伙一定会把她拖进痛苦的感情深渊使她万劫不复,但是她的感情仍无法不受那熟悉的脸庞影响。不告而别的你,了无音讯的你,令我沉沦的你……阿黛尔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是很快命运就帮她解决了这个难题。申请从系统中突然消失,她抬起头看到一个起身正要离开的身影。
“安妮雅?”
有着一头银发,肤色略深的女孩转过头看向她,金色的眼睛向她投来疑问,“是?怎么了吗,阿黛尔?”
尤利塞斯·安妮雅的年纪在整个埃癸斯都是非常年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善良,心软且很好说话。如果她向她请求能不能转让这个任务的话……
她张开嘴,犹豫了一下,“……不,没事。任务顺利,玩得开心。”
虽然安妮雅对她的祝福一时摸不到头脑,但还是因为她展现出来的友善表现出了感谢与开心,“谢谢你,阿黛尔,那我走了。”
最后阿黛尔仍选择了顺从命运,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尤利塞斯·安妮雅的身影离开办公室踏上前往西班牙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