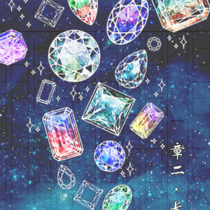


与所罗门这个张扬肆意的人一样,这位战队的老牌打野自从在维克康尼青训营起就秉承着一贯的激进派打法,虽然在战队配合上稍显吃亏,但观众却很吃这一套。
而他也确实很有资本,出道第三年连胜五场,直逼冠军赛。
维克康尼属于老牌战队,实力强劲,今年人员改动并未引起太大波澜,所罗门与他在青训营里就亲密无间的伙伴adc配合上不出问题,可要适应他想一出是一出的打法,对队友来说就稍显吃力。
维克康尼的教练加纳·冈特是退役下来的职业选手,和所罗门的惯用打法截然不同,他更偏向老成稳重的配合战,所罗门觉得他古板,他觉得所罗门过于个人英雄主义,两人处在互相看不顺眼的阶段。
甚至,加纳在盛怒的时候曾说出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狠话。
不过由于加纳·冈特看哪个队员都不顺眼,俱乐部并没把这话当回事。
雷伊作为ADC很能适应所罗门的冒进,他和这位“狼性”打野的配合亲密无间,是在青训营就与所罗门合作的队友,他几乎相当于所罗门的专属辅助,虽说走的Center路线,可日常比赛时把关注度放在打野身上是常有的事。
团队合作是所罗门的短板,而雷伊在这方面似乎也不太擅长,他俩刚出道那段时间,由于这两匹孤狼顾前不够后的独立式配合,再加上时不时在走位上的先遣操作,使得队伍里的辅助选手经常因为配合不当出现操作性的失误,这也就直接导致冈特教练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指导辅助适应他们的打法。
或许加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他们不顺眼的。
就这么磕磕绊绊地磨合了三年时间,辅助位逐渐适应所罗门鬼魅式的走位,已经能很好的在他冲出家门时缜密地在他身后扫除障碍,并且配合他收下人头。
可是很快又出现了新问题。
打野是需要游走的灵活性多变位置,而所罗门又惯用刺客型英雄,需要经常从野区赶往其他路线上帮助队友Gank敌方英雄,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罗门开始频繁地在下路游荡,即便雷伊只是在与敌方正常对线。
加纳针对他这个臭毛病训过很多回,可是就跟ADC身上有什么吸铁石似的,他清完野要去下路游走看看,收下敌方打野人头后也要在下路欢呼似的转上一圈——在做完这些后,他们总能收获到加纳铁青的脸和他毫不掩饰的白眼。
在加纳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并且把所罗门和雷伊分在了两个阵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
“所罗门。”他黑着脸说,“你跟我来。”
大家忐忑不安地摘下耳机,齐刷刷地看向面无表情的加纳和满不在乎的所罗门——这人甚至能在经过雷伊时,轻佻地冲他抛个媚眼。
教练办公室厚重的木门被掩上,很快,里面传来了毫不掩饰的怒吼与咆哮,队员们听出那是加纳的声音,看来这次的确是动了怒,他平常虽然也会在训练时时不时阴阳怪气地刺上他们一两句,可发这么大火仍然少见。
雷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几次想冲进去,都被队友们拦住。
加纳·冈特最忌有人挑战他的权威,如果雷伊这时候闯进去,吃苦头的就不单单是所罗门一个人了。
这时屋内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众人心里具是一惊,一个年轻气盛的明星选手和一个毒舌、刻薄的恶魔教练,会动起手来也不奇怪。
但仍然没人敢进去看看情况,而雷伊却挣脱队友紧握住他胳膊的手,毫不犹豫地拉开大门——
屋内一片狼藉,办公室里那张厚重的书桌歪倒在地,看来刚刚惊心动魄的响声正是它发出来的,加纳站在窗边,所罗门则站在书桌旁,低着头看不清神色,双手紧攥着,青筋暴起,不过看到他身上没什么明显伤痕,雷伊仍然松了口气。
“滚出去。”加纳背对着他们,头也不回的说。
所罗门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大步流星地跨过地上散乱的,原本被摆放在书桌上的零碎物件,在出门时牵起雷伊的手,拐进空无一人的厕所里,锁上了隔间的门。
雷伊抬手拥住大男孩初具规模的宽阔臂膀,像给某种大型犬类顺毛似的,无声地安慰他。
所罗门将脸埋进猫咪蓬松柔软的颈毛里,闷闷地说:“他发现了。”
雷伊张开嘴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叹口气:“太明显了......”
所罗门是个在比赛中容易兴奋的选手,向来是杀红了眼就不管不顾,管他什么战术打法,看见红色血条就往上冲,可是刚刚组内的对抗赛,他却在兴奋状态下一次次装作看不到似的,拒绝前往对面雷伊的所在路线配合队友击杀雷伊,这直接导致边路连下两塔,中路英雄在支援时中路失守。
“凭什么不让恋爱?”所罗门嘟嘟哝哝地说,“他自己之前不是也队内恋爱过?”
的确,加纳没退役时,玩的竟是辅助位,与他配合的是当时俱乐部唯一的女选手芙露尔,女打野,很难想象加纳这样刚愎自用的人会心甘情愿地给谁作陪,他们这些刚出道没几年的毛头小子都没真正见识过当时惊才绝艳的芙露尔,因为早在他们出道之前,这颗璀璨的明星就陨落了。
她死于先天病,并且,当时加纳已经和她订婚,两人只差两个月就要步入婚姻殿堂。
雷伊想起刚刚被所罗门拉走前看到的最后一幕,加纳逆光站在窗前,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戒熠熠生辉,他的腰挺得笔直,仿佛一颗风雨中的松柏,但他瘦弱的肩却无力地塌陷下去,仿佛上面担着重逾千斤的孤寂。
“总有一天,”所罗门说,“我要亲手把冠军奖杯捧到你面前,让他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因为恋爱影响训练。”
“好。”雷伊不禁微笑起来,“我相信你。”
当晚,雷伊从梦中惊醒,墙上的时针指向三点钟,他一摸自己身旁的床铺,是冰凉的。
他穿上拖鞋下楼,训练室里只有一台电脑是开着的,白色的光源映出一头张扬的红发,他默不作声,拉开椅子,开机,登录游戏。
所罗门没管他,或许,他已经料到这个发展。
他在用小号打匹配赛,队里是四个路人,此时比赛进入后期,对方中路仅剩一塔,边路各剩两塔,自己这边也不容乐观,因为路人队友无法配合所罗门这样不管不顾的猛冲式打法,容易跟着他冲上去攻击敌方,却丢失后方资源。
所罗门此刻很明显已经处于兴奋状态,呼吸声很重,眼睛里含了一团熊熊的火焰,在没有开灯的训练室里亮得吓人。所幸,尽管只有他一个人carry全场,但由于技术过硬,操作娴熟,他的电脑屏幕上仍然跳出了大大的“VICTORY”。
他摘下耳机,额头沁出了汗,像狗狗从水中上岸甩干身体那样甩了甩头。
“你怎么来了?”他的热情还未消退,脸上布满被汗水蒸腾、或是由于过度兴奋而发散出的红晕。
雷伊微微一笑:“我陪你。”
所罗门一怔,随即咧开嘴笑起来:“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
在青训营时,所罗门常常因为他的冒进打法吃苦头,或是被教练加训,雷伊和他是同期生,很早就注定要和他加入同一个队伍——维克康尼,俱乐部的王牌战队。
这两名未来的明星选手还没成为朋友之前其实没怎么说过话,只有那一回,所罗门又一次因为队友配合不了他而挨训,年轻的男孩心里憋了一股气,在训练室待到凌晨两点,正当他冲电脑里的角色发泄怒火时,旁边有人拉开椅子,他转过头,是队里向来稳扎稳打的ADC。
那时候他一肚子气,说话就难免有点冲:“你来干什么?”
雷伊没有恼怒,只是目光沉静,深蓝色的头发在黑暗里看起来像一潭死水,可是底下有多少凶险的暗礁、暗流未有人知。
“我陪你。”他说。







这里是艾尔芬号最终列车。在前往天堂与地狱之前,逝去的人们相会于此。或许他们能够弥补生前的缺憾,又或者能为来生结下新的缘分。无论出身贫寒还是高贵,无论出生在哪个国家,也无论出生在哪个年代,相聚于此的人们,总是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奇妙故事……
这里是艾尔芬号最终列车,在这列行驶在星空中的列车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鲁小狗走进餐车,想找点东西来吃,却一眼看到有个孩子坐在车窗旁抹眼泪。那孩子看起来只有十岁,抽抽搭搭地哭得甚是可怜。他的面前摆着培根和煎蛋,但小孩一点都没有享用的意思,只是不住地用手背擦眼泪。鲁小狗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他走过去,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找不到爸爸和妈妈……”
“他们,嗯……有可能不在这里。”鲁小狗不知怎么解释才能让这个孩子明白,只得支支吾吾地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他们说,我这样的坏孩子,是要去地狱的……”小孩哭着向小狗伸出手,那上面明晃晃地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带。鲁小狗吓了一跳,可是这么小的孩子,到底是犯了什么错,才会下地狱呢?
“为什么我会下地狱呢,”小孩子抽抽搭搭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只是把爸爸的杯子打碎了……爸爸,爸爸打了我,我好害怕,他还打妈妈,妈妈流了好多血……呜呜呜,妈妈那么好,一定会上天堂的,可是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大哥哥,我还能见到我妈妈吗?”
他用湿漉漉的蓝眼睛看着鲁小狗,拥有那样纯净的眼神的人,肯定不会是坏人,鲁小狗想。
“肯定是他们搞错了!”他义愤填膺地说,“走,我带你去找乘务员!”
他拉着小孩就要起身,小孩却拽住了他的袖子,摇了摇头,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他们不肯给我换……他们说,除非有人愿意跟我换,一个善良的,好心人……”他的目光落在鲁小狗耳边的蓝色丝带上,流露出期待的神色。
“啊,不,这个不能换的,”鲁小狗慌乱地摇了摇头,“我,我还不想下地狱,那个,你还是去找别人……”
“是吗?”小孩的表情陡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哭泣戛然而止,垮下的嘴角上扬,露出一个可以说是有些轻蔑的笑容,“你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
“等等,你——”
那个男孩,那个头戴护目镜的小男孩,就这样在鲁小狗震惊的目光之中跳下了座椅,独自走向了车厢的另一头。他的步伐轻快,系在手腕上的红色丝带也仿佛随之跳动……
他真的只是个小孩子吗?鲁小狗不禁这样想。那个无助地哭泣着的孩子,与刚刚那个冷漠眼神的孩子,真的是同一个人吗?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那孩子便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最终他也只能挠挠自己的头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伊芙坐在梳妆台前,长发柔顺地披散下来。拉里站在她身后,用梳子仔细帮她整理头发。他动作很轻,梳子碰到了头发打结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把它理顺。注意到伊芙轻轻地动了一下,他便问:“疼吗?”
伊芙笑着摇摇头,他才继续。他慢慢地让梳子穿过她的头发,呼吸都慢了下来,像对待一件易碎的艺术品。梳子像一截浮木,慢慢地从细密的河流上漂过,直到穿过发梢,落入孩子的手中。
“要我帮您编头发吗?虽然我可能没办法像您编得那么好。”
“好啊。”伊芙温和地说。于是拉里的手灵巧地穿过她的发丝,穿针引线般地编织起来。他用发卡固定住编好的头发,拿了面镜子放在伊芙脑后:“这样可以吗?”
“你的手真巧。”伊芙说。
“我经常帮我妈妈梳头发。”拉里笑了笑,又说:“您好像我妈妈啊。”
“想妈妈了吗?”
“嗯。”拉里垂下头,吸了吸鼻子。
伊芙摸了摸他的头,安抚道:“没关系,一定能再见面的。”
拉里抬起头,眼角似乎有些发红。他抬起自己的手臂,红色的丝带像血丝一样刺眼。
“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伊芙又摸了摸他的头,还想再说些什么,房间的门却在这时被人敲响了。
“是谁?”伊芙问。
“请问有没有见到一个叫拉里的孩子?”男人彬彬有礼的声音隔着门传了进来,“我在找他。”
拉里一听到这个声音,便躲到伊芙身后去了。伊芙打开门,龚子高站在门口,向拉里招手:“过来,拉里。你答应我什么来着?我们该去上课了。”
“我不想去。”拉里从伊芙身后探出头来,冲龚子高吐了吐舌头。
“来吧,等今天的功课结束了,我们一起去餐车吃布丁。”
拉里不情不愿地从伊芙身后走出来,依依不舍地跟她道别。在龚子高温和的注视下,他只好拖着脚步跟着这位校长先生去往“课堂”。
拉里有时会觉得这一切很好笑。在列车上的授课让他想到自己读过的儿童读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向往过那个像是童话世界般的学校,但死后世界仍要读书学习这一点实在是太超出想象,甚至有些荒诞。
如果仅仅是作为旁观者,他倒是会欣赏这种荒诞。然而当他坐在书桌前,咬着笔杆做习题的时候,他只觉得无聊透顶。龚子高很认真,也很耐心,这恰恰是好笑的部分。他容忍拉里的耍小脾气,故意捣乱,尽职尽责地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完美得就如同他佩戴的那条蓝色丝带。
拉里看着那条丝带,突然放下了笔。他说:“我受够了。”
“这道题对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的确很难,但我看得出来,你很聪明。你一定能解开的。”龚子高说。他没意识到拉里说的是什么,或者装作意识不到。
拉里摇头。
“我不认为您的课对我有什么帮助,”他说,“就算您再怎么教导我,也不可能把我的丝带变成蓝色。”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尽我所能,毕竟这也算是教育者的通病吧。”龚子高笑了笑。
“您是个好老师。但您似乎搞错了一点。”
拉里伸出手,给他看自己的红色丝带:“您真的认为,善和恶能简单地通过丝带来区分吗?红色就一定是恶人,而蓝色……”他看向龚子高的丝带,“就一定是善人吗?”
龚子高脸上的表情明显动摇了。拉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觉得有机可乘,便继续说道:“我想这世界上没有人是全然无辜的,即便是戴着蓝色丝带的人,也不可能说自己在这一生中从未犯过错。善恶到底是谁来评判?如果要蚂蚁评判,那碾死它们的人类无疑是恶,如果要家畜评判,那食用它们的人类无疑是恶。究竟是谁有权在死后判定我们的善恶?是神吗?若神认为众生平等,那人类岂不是个个罪恶滔天?我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是我们自己。您见过诺艾里吗?她才八岁,却拥有一条红丝带,只是因为她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自杀。您能说她是恶人吗?只是因为她认定自己有罪而已。”
龚子高说不出话来。他的视线在两人手腕上的丝带上来回移动,而拉里的话还没有结束:“我与您的区别就是,我认定自己有罪,而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如果我的推测属实,您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
龚子高做了一个深呼吸,用手抹了一把脸。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他说。
“无论如何,谢谢您的教导,再见。”拉里冲龚子高鞠了一躬,步伐轻快地走出了房间。他哼着一首曲调轻快的儿歌,回味着刚刚龚子高的表情。
太有趣了,他想,死后的世界真是出乎意料地有趣。
*关于善恶的讨论全是拉里胡编的,具体还是以企划设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