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正文请点外链,内含r18/暴力倾向
有语句不通和错字,未修正
请多多海纳
字数:全文5k6左右
链接:https://poipiku.com/10113287/10384636.html
「 自从那天起,过去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有吃有住,谁又会在乎过去了多久?
这样的靠在椅子上回忆道。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坐着不知道去向哪里的船,摇晃着、到达了从未来过的遥远国度,游荡在东京这样偌大的城市,面容特征大相径庭的异国人引来原住民们诧异的目光。当时无论怎么想翻开钱包都是身无分文的状态吧,就是这样如同远漂的船只一样…摇摇欲坠的晕倒在陌生的街口。
再次醒来时是一名长相清秀,稍微有些稚气和女相的男人,发辫上扎的白色飘带牵引着我的目光。他用沁湿的纱布敷到我的伤口上,明明素不相识,为何会去帮助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呢?我用着还算熟悉的英语跟他交流着,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一些足以留在这里的信息。
……但是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央求他把我流下,以打工的名义。」
从北欧漂泊到日本的人就这样名正言顺的留了下来。而因为语言问题,能打交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伯纳德迫不得已每日百无聊赖的蜗居在小小的十几平米的店铺。大家都有自己的归宿。店里打手的松永和还在上学的尺见都有自己最终的归宿,而伯纳德的归宿…就是碇海塬空无一人的出租屋。与其说归宿,更不如说是寄人篱下。因为工作的原因,碇海塬总是身处异乡僻壤。而那无人打开的房间正好供给伯纳德随意处置。朝九晚五的工作对于没什么本领、而且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说还算得上安逸。
天边挂上了一抹少女的红晕,已经到戌时了。忙了一天的尺见应付完最后一位客人开始收拾离开的物品。松永在点清今天所有的账后也徐徐离开了。
“走的晚的话别忘记关门。”松永提醒道。
“知道了,松永女士——”
伯纳德在楼上仓库回应道。也差不多该回到那个“家”了,他想着。按照平常的时候,他早就点好了仓库剩余的货物、锁上门、离开这小小的当铺了。稍微有些例外,在摸索腰间的钥匙时意识到了什么。
“啊…钥匙。”
他皱着眉头。
眼看着其他人挨个离开,自己却在原地不知所措。就算现在去追也晚了。如果再去找尺见或是松永,也太麻烦了吧。反正二楼有床,就这样草率地暂时安置一晚应该也没什么,虽然二楼推拿用的床铺有点小,但也算得上应付。
正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门外传来金属碰撞的嘈杂声音。
碇海塬拖着硕大的货箱和行李试图跨过自己垫设的和寺庙一样高的门槛,搬着货架上一件根本不算大的货物。伯纳德看着对方吃力的样子,稍微有些发笑。对方低着眉眼却先说到。
“这么晚还没回家吗?难道是有什么心事?”
被突如其来的问责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虽然口气有些严厉,像父亲一般的口吻,但最终传来的感情还是关心。如果心直口快的话或许会说“忘了把钥匙放哪了。”但是很明显…伯纳德还是思考了五秒,直说一定会显得自己有些愚蠢吧?难以启齿于吐露出简单的真相,反而说了一个打趣的俏皮话。
“我这不是在等你回来吗?”
碇海塬挑了挑眉毛,没有理会他这样的回复。站在门口的优势就是店内的情况一览无余,如果稍微瞟一眼左边的柜台,用眼旁的余光就能发现那串属于碇海塬,用红线绑有铜钱挂饰的钥匙串。只是恰好放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看破对方心眼的碇海塬没有直接说出事实。
「你怎么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说嘛。」
他选择回敬一句玩笑话。“莫非是想我了,因为睡觉的时候身边空无一人而感到「寂しい」?”
他用伯纳德听不懂的中文说着。
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是也被旁人稍微教了些许日语词汇,还是听出了“寂しい”这样的词。像是电影套路一样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碇先生一个人在外感到寂寞吗?我有大家陪着,感觉没有很寂寞呢。比起在之前那个地方,我果然更喜欢这里啊。”
气氛飘出了奇异的暧昧感。碇海塬别过头,用食指和大拇指服了服侧边的眼镜框。别在耳后和飘到脸前的细碎发丝也遮不住耳尖的红晕。
“你啊,给我把这些东西搬上去吧!让我这样的人来做这种粗活未免也是太为难了!”他命令着。
“搬完这些,就回去吧。如果还没吃饭,可以拿这些糕点垫垫肚子。”
碇海塬扬了扬手中带回来的特产,用了稍加柔和的语气说道。
搬完杂七杂八的货物,那刚染上的红晕也成为了落幕的余晖。人吉商店街的闭店时间大同小异,当竹门榭下班时,主营晚间的店铺都张灯结彩迎来新的客潮。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部分是穿着西装的上班族,中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又或是步行,穿着白色短袜和乐福鞋成群结队的走在街道上,扎堆商量着今晚去哪个家庭餐厅。棕色的乐福鞋与抹着松油的黑皮鞋交杂在一起,也有一些穿着木屐的店员拉拢着擦肩而过的访客们。嘈杂的人群各自描述着不同的人生,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这里为人吉迎来了新的生机。
心情像天边的云一样轻飘飘又悠然自在。
“昨天睡的还好吗?”伯纳德问着。
果然不好吧。他想到自己坐远途轮渡的时候上吐下泻的模样,从中国到日本的轮渡是三天起步,比起北欧到日本,这样的时间算近了。他在那满是商人,又或是有权有势之人间的轮船感到阵阵不适,要不是为了离开那个地方,伯纳德根本不想上船。
“如果是为了挣钱,累一点也没事。”
“这次的渡口是上海,我拿了一点艾粄带回来。”
他从包中抬出一个艾粄丢给伯纳德。包是中国特产的布包,虽然说不上好看,但质量显得还不错,灰绿色的斜挎包容量大的惊人,如果要塞五本书估计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到。艾粄被一层油纸膜包装着,外面又裹了一层全是中文的报纸片角。拆开包装繁杂的外衣后就是软糯粘牙的第一层,咬下去亦或是枣泥和豆沙,微甜不腻的口感让来自北欧常年吃腌制食品的伯纳德阵阵感叹。
“真是辛苦了…先生。”他低着头谄笑着。“这个…真是好吃!吃起来有点像大福…和三色团的混合体。”
“哼,这个是用艾草打成的汁液,还有糯米粉做出来的,好吃吧?”
“所以才会有绿绿的外衣,吃起来有一种清香,然后就是绵密的豆沙。”碇海塬解释着。
“那先生喜欢这个吗?”
……
两人就这样有说有笑的聊着闲碎的话题,用着平缓的速度走向家的方向。是那个温暖的、没有暴力和胁迫的“家”。
“又在中国看见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先生?”
伯纳德一边百无聊赖的塞着艾粄一边鼓着腮帮子问到。
碇海塬将视线移向伯纳德的脸庞上,注视了良久。对方此刻正专注于和粘牙的艾粄打架,像被攻击了一样与上牙膛和舌头混战着。反而忘记了回答他的问题,碇海塬差然的飘出一句:
“你这没有染黑的眉毛和睫毛………”
“还真是违和……哈哈哈。”
他笑着说到唐突的话语。伯纳德稍微有些不满于被嘲笑黑色头发和黄色睫毛的事情,他扭头生气的怒视对方的脸庞,那白皙的皮肤覆盖在颧骨上,对方的侧颜倒影在他的瞳孔之中。不符合脸部线条的眼镜架在稍显幼态的脸上,个子矮了一头的男子正捂着嘴偷偷笑着。…稍微有什么感觉入侵了。
就这样却再也说不出来什么话。本是聊的火热的氛围逐渐冷了下来,红色的余晖衬着两人的影子让氛围稍显暧昧,但又相对无言的朝着房子前进着。
也许是幸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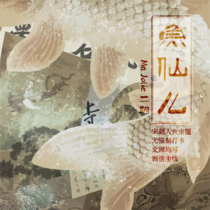

·IF线。作者与角色亲妈承诺死亡角色是自愿的。出场禽类均未受到胁迫。
————
Summary:英武的前傲罗珀加萨·海利伊特斯小姐不幸卷入爱丁堡的黑魔法集会。这一事件后来成为了她职称里的“前”字必须出现的理由。而英武的鹦鹉偏见先生在其葬礼上发表重要演说:“欢迎光临!热烈欢迎!你好!拜拜!下次再来!”——以上内容在本文占比极低,之所以写在这里只是因为作者喜欢这个笑话。
————
“啊!我懂了!我一定是从出生起就在想了——如果有的选的话,将来我要睡在能看到星星的地方。就和这里差不多,但最好不要这么安静。永远永远的睡下去。是的,永远——”
风自地平线外围阵阵地吹过来,云卷云舒漏出时隐时现的月亮。夜深处草皮凝住了透亮的露珠,潮乎乎地被少年少女用肩胛骨压覆。
旷野中毫无遮挡,完整开阔的星幕在他们面前展开。那幽深的琼宇有如绸缎流动,抽带着泼洒其上的金华银粉,脉脉越过高空,俯瞰向人间静默的山林与海。稀疏冷峭的天光,与这长夜一般幽寂,透过仰望的虹膜留下片缕残影。每当他们闭眼再睁开,一呼一吸的间隙,遍布寰宇的星便也同步完成了一次心跳般的悦动。
珀加萨扭动了两下身子,将手惬意垫平在脑袋后面,抬头望天的时候小腿还在不安分地寻找靠山,一会儿踏着自己裙摆边缘,送那印花的丝绵去与泥腥做伴,转眼又去故意地碰撞她血缘遥远的胞兄的膝盖。他体质寒凉,皮肤往往总是冷的,但并不抗拒与人的亲近,露在风里吹得泛白的膝盖头,也只要贴过去熨暖片刻,就会重新活络起来。珀加萨很享受这分易于取得的成就感。
“其实我还想象不出‘永远’。”她斩获温暖的战果,便暂放过表兄的腿,翻回正面伸手到虚空抓挠,指缝间雾状的光芒闪动明灭,叫她揉散后又傍着她的手指重聚。“一小部分故事吹捧它,好像人人都渴望它;另一部分故事讲它是悲切而且无奈的,得到它的人通常悔不当初。它是一种诅咒还是祝福?我问过爸爸妈妈,他们说这只能靠我自己去想。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会永远爱我。我也只能说——好吧,我也爱你们,这是永远不变的。”
“珀加萨,你已经想好墓志铭了吗?”
她的那位身体欠佳,话也不多的表兄——艾利亚斯·弗洛斯特就躺在她旁边,听得仿佛很认真,开口却是没头没尾的。他们之间时而会发生这种对话——毫不相干的两个句子同时登场,总该有一方被斥责礼仪缺乏,要么也是有人未曾用心聆听前文。然而,实际上,至少这两个孩子自己保有共识:他们说的确凿是同一件事情。每一次都是。当她谈及星辰,永恒与爱,她当然是在暗喻死亡;他没转任何弯地读懂了,因此直接问起她对墓碑的期望。其间逻辑分明如此顺畅。
珀加萨于是理所当然地接下话茬:“没有啊。我还没考虑太久呢,只是以防万一。万一我见不到永远了呢?也许我们最后都还是没找到它就死掉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那我最好还是留下点能和永远的爱比肩的东西,以免我来不及回馈同样多的爱,让比我活的更久的人赢过了我——也许我该在墓碑上写,’她只是先过去看看,收拾好屋子等你们过来’?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呃,对其他人的葬礼太迫不及待了?”
“可能稍微长了点儿。”艾利亚斯客观地评价道。“不过没关系。我想——就算没有永远那么长,你总还是有不短的时间可以慢慢改的。多想几种方案抓阄也不错。那样就连你自己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坟上写着什么了。”
“如果你想好了,随时告诉我。我会替你记住的。”
他转向珀加萨的方向,缓慢地眨动那双淡蓝的,如水泊般清浅的接近空无的眼睛。珀加萨觑见自己模糊的倒影,在男孩开闭的眼皮的缝隙里浮现,星辰拥围的面容渐渐凸现,含笑的唇角刻印在底片,如同正在完成一次正式而且庄重的照相。
“我可真的会构思很多很多句的!否则抽取的时候就没有惊喜了。那么你会记住它们多久呢,艾利亚斯?我是说——每一句,还包括向你说出那些句子的时候的我。时间,地点,我的样子,我说那句话时的语气……”她明知故问地笑着,半阖了眼任由想象力驰骋,远飞向天外宇宙,重叠交错的无数个明天,好像已当真在窗边,在小巷,在学校幽邃的走廊里,用她轻快的声线无数次地确认。“你会记得吗?每一次?”
“永远——当然。”艾利亚斯仍然平静地回答,侧过一点面庞,用他清澈专注的眼看了回去。“爱与承诺都会抵达永远。无论永远实际上有多长,总有些事物会比它更加顽固。”
“就像洗碗池里的水垢。”卧在他们头顶杂草堆里的冥王星忽而尖刻地说。“不管你想不想它,它总会比清洁剂的寿命更长一秒。”
珀加萨一下没能绷住嘴唇,淅淅沥沥的笑声迸落如珠,在一点外泄魔力的辅助下,弹射出好几簇星星状的幻光花火;而当艾利亚斯一本正经地讲起前一回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还是他的母亲,那些克制的轻笑旋即就摔碎成了不加收敛的大笑,她不得不捏住自己嘴巴,遮挡乳牙遗失后漏风的洞,以免被魔法部以未成年施法的理由追究——且不得不解释她只是笑得太厉害了。
后来珀加萨独自一人重回这片草野,恰逢礼拜日,英格兰境内应景地全面降温,风雨前夕湿重的雾霭如海浪般翻腾鼓涌。远处大伦敦郡则一如往常,水泥修砌的森林静默无言,街道楼栋披覆烟尘,染着煤炭烧灼的晦暗。
她站在群星匿迹的天幕之下,自白昼的末梢望向那座城市阔别已久的灰影,脑仁里忽然不合时宜地诞生了灵感。若是在墓碑上写一句“这姑娘已过完了她的白天,将要去看星星了”,似乎也还不赖。怎么那天夜晚她没想起,倒是十几年后突发了雅兴?可惜艾利亚斯并不在身畔。她相较而言并不怎么有能将临时起意的创作长久记忆的自信。
不过话说回来——她今日走出卡尔顿山的阴影,舍了追迹数月的目标,却忽而冒险地扎进伦敦附近的荒郊野岭,倒也并不是为了追忆往昔。
远在这麻瓜不感兴趣,而巫师与神奇动物尚未涉足的东南部平原的边角,她找到一栋弃用的教堂,还特地穿了修身的黑裙,手掬鸟儿纤细骨骸,只为将那镶嵌太阳花形黄水晶的——伯母的首饰盒充作的棺木,连同陪伴她度过少年期的小小亲友,亲自埋没到旷大草野的一隅。
这甚至算不上个庄重的告别。女巫在麻瓜的天主教公墓里安葬自己的小鸟,听来也实在荒谬可笑。可她一时半会回不了家,连自己将要埋骨何方都说不好,无暇做出比这更妥帖的安排,总是值得谅解的;况且听说沐在圣钟里的灵魂都能升上天堂,她一个前推几世纪还在被教廷追捕屠戮的女巫是注定没戏了,饲育的鸟儿恰在此地寿终正寝,倒说不定有些机会。它的娇媚的颊羽,圆溜溜的眼,织布机般的叻啦叻啦的吟叫声,还有最为得意的——那宛如热带青芒果的饱满靓丽的喙,是连被人叫做“上帝”的麻瓜男人也绝对没有理由诋毁的。如果他当真全知全能,就必会在一眼的判决间认可它生机勃勃的完美;否则,他就如传闻里那般枉负盛名了,根本比不过梅林的小拇指。
她没觉得天堂特别好,也很难断言天使是否算一种当地原生的鸟——没有任何一册典籍谈及它们如何繁育——但问过的麻瓜大多说自己想去,又信誓旦旦讲那是好人与善良的动物才被准入的地方。她便希望这只漂亮的巨嘴鸟,在陪她走完短短的一辈子后,如若死后还能有个归处,那归处会是温柔友善的灵魂所扎堆的甜梦乡。
她在墓园站到黄昏,天边溢散的残阳起初显出一种淡漠的苍白,犹如死鱼腐败的眼珠,溃烂后融化在废弃教堂的尖顶,又逐渐汪汪地流成了染红云霞的血水。
“永远缅怀、铭记,感恩虚荣在这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我们带来的欢乐……”
殷红若血的夕阳铺满原野,旋即一切都迅速褪色,夜幕沿着地平线侵袭而来,白日的鲜艳转瞬凋零。这场雨终究没能挣脱乌云凝铸的枷锁,空气因而加倍沉闷了。珀加萨在公墓独角戏的最后动情地吟诵起早已准备好的悼词。一轮将要沉没的日晕盛开在她眼窝里,与那昏黄的瞳仁交相辉映,闪烁着碎钻般晃荡的薄薄泪雾。她抽了抽鼻子,给住的最近的弗洛斯特家写了封信,托困境送过去,记上刚才想好的墓志铭,又在信里反过来拜托他们收留捎信的这只猫头鹰。至于留在家中的两只鹦鹉,她相信爸爸妈妈能替她照顾。
小时候,她曾格外期待主持亲朋好友的葬礼——倒不是说她当真盼望谁的猝然离世,而单纯只是中意尘埃落定的圆满结局。人们出生,与他人建立联系,做出一番事业,最终在爱着自己的人的簇拥下,怀抱花朵而安睡下去,来年肉体腐朽为肥料,滋养又一季新春的草长莺飞。她钟爱葬礼主持这个角色,乐衷向任何人介绍这名躺卧棺中,与她息息相关的死者曾走过的精彩一生,号召众人共同为他即将踏上的死后旅途献上祝福;没想到初回上岗却只送葬了自己的虚荣。
她也曾欢喜地构思过自己的葬礼。在她所足踏的这片繁星烂漫的草野,在某个假期曾扑入过的白沙攒聚的海滩,在大本钟沉沉振荡的嗡鸣声中,在伦敦的广场纷落如雪的鸽羽之下,在年复一年驰往霍格沃兹的列车车厢里……但凡突发奇想有了灵感,她便当即转头向身边的男孩,乐此不疲地诉说起关乎死亡的畅想。他未必表现得专心致志,有时压根儿在看别的方向。但她知道他会记得。这个男孩所应承的永远是值得信赖的。经由他的双目摄录的世界的切片,最终将连缀而为名为回忆的不朽。而她有信心成为其中占比不低的一块儿。
后来一些人果真先于她而死掉了。可她却还没来得及长到能主持葬礼的年纪。再后来她备考,毕业,工作,执起魔杖去捍卫身后贵重的一切,时间流逝忽而加快,连她笼在掌心呵护的幼鸟都不知不觉长成老者模样。她的墓志铭积累到了181条,关联着181个迥然各异的场景。时局日新月异地剧变,新旧势力碰撞,各家造着不同的神,却异口同声自诩正义,喊着高尚的口号戕害同胞。海利伊特斯从不培养黑巫师的传统迄今未曾打破,她却因此而不得不与家人分别——愈是夜深处,那光明正大亮起的灯火就愈是刺目。与每一个领了傲罗名号的人一样,最后,她毕竟只能孤身投入漫漫长夜,许愿自己英勇如曙光女神,能用杖间的微光将混乱的世道劈开一寸。即便她仍旧搞不明白事态如何恶化,人们伤害彼此的理由又是如何被包装渲染,唯独武器不应当指向同胞,友爱的拥抱永远比刺伤他人的刀尊贵,这一朴素的心愿从未被曲解遗忘。
在这条路上她更频繁地与死亡相逢,有时擦肩而过,有时眼睁睁望着他人迈过那条线去,偶尔想起儿时的约定,诞生了新的关乎碑文的主意,习惯性回头却只撞进他乡湿冷的空气,渐渐也便习惯孤独的滋味。孤独并不等同寂寞,曾充盈她人生的爱依旧在远处与她同行。而现今连陪她长大的鸟儿都开始离去,某种含糊的决意也终于有了雏形。
她好像从未害怕过,也好像其实是从某一刹那起才忽然充满了力气。离开教会墓园,用幻影移形回到爱丁堡的山谷,不过隔了半日,血腥味伴随酸液的恶臭,已然弥漫的铺天盖地。她望向眼前七零八落,卷着制服碎片的肢体,忽然一下回想起来,最初驱动她攥紧魔杖的那种情绪,逼迫她去战斗的原动力。啊,当她最初看到那只被恶咒洞穿的眼睛,当她听闻闺蜜与兄长的死讯,却受绊在外不能回去,那时升腾在她心中的情绪——海利伊特斯的遗憾,悲伤,以及紧随其后燎原般奔袭的愤怒,原来是早就注定会推动她直到这里。
直到她准备好,面对一场只能由她面对的战争,站在其中退无可退的位置。
昏迷咒的红光擦着鼻尖飞过,艾利亚斯被拉扯的一个趔趄,凑巧又避开急射向他的几道不明魔法。他在傍晚这昏昏沉沉的光照里尤其看不清楚,显然心思也没全在路上,不幸撞进傲罗执法现场,要不是被正在加班的珀加萨惊讶并眼疾手快地逮住,保不齐会和躺地上的黑巫师一并登上日报讣告。
“要是有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就好了。”死死拽着他袖口的珀加萨,单手拔杖回了道霹雳爆炸,一边找掩体,一边还不忘跟许久不见的熟人抱怨,倒像是挺开心捉到个唠嗑对象。“不过——听说连麻瓜自己的警察都很难配到。他们用的那棍子还不如魔杖方便呢。”
“砰!轰!哒哒哒哒!”她张合嘴巴发出不间断的拟声词,魔杖用拇指扣住,再架到另一手的食指关节上,虚虚瞄准持续射出魔咒,将露头的巫师像标靶一样逐个击倒在地。“漂亮!珀加萨!你的爆破咒真是运用的炉火纯青!”而后大声赞许自己,并立即因循声而来的攻击狼狈地缩回了头。
“你是说手枪?确实。英国警察大多数也并没有那个。”
那时艾利亚斯茫然地回答了她的问题,而并未真正理解他迷路到了多危险的地方,珀加萨也并未向他解释,换过几趟据点,连巷子里的垃圾桶都炸的粉碎后,便将他往坍塌的墙壁后面一推:“重点当然是我的魔咒射的比子弹更准!再见,艾利亚斯!你晚上有空来我家吃饭吗?虽然我暂时不回家不过你还是随时可以来的,以及代我向困境问好,哦,还有我妈妈——”
艾利亚斯没能回上这句话。他在被迫地扑过瓦砾堆时摔倒了,重新爬出来的时候战场已经转移到别处,巷子里空留下满地碎裂的石板,与流散在裂缝里的血痕。而这实质上也是他和珀加萨说上的最后一句话。再收到关于她的消息已是她失踪后的第三个月,通常魔法部会认为如此时局下,执行公务途中失联的傲罗与殉职无异,但她的家人并不需要抚恤,也拒绝在确认尸体前承认她的离去,这件事因而始终拖延,直到她破损的魔杖被和沾满酸液的衣角一并送回。
“嘎嘎!来了好多人!艾利亚斯!是的!嘎!好多人!好多!他们要见珀加萨!谁是珀加萨?你好!我是珀加萨!”
车轮冠在窗沿上蹦蹦哒哒,艳丽的脑袋前摇后晃,吐出大段不明所以的话。艾利亚斯看了它一眼,它似乎条件反射有些畏缩,而青年却一反常态,将轻抿的唇挑起来一点。
“继续。我不讨厌那个。”
他松开手指,让刚完成魔力灌注的小纸条们飞到半空,那些纸片如鱼儿般环绕游动,又似蜂巢般堆叠集群,舒张扩展,构成个层层绕绕的雪白星球。他勾手呼唤偏见过来,为纸条公平地赋予坚果的香气,叫它随自己喜好叨出一张。
窗边路过的宾客诧异于他的悠闲,许是认为在亲朋葬礼前摆弄纸模太过轻慢,或者叫他怪诞的作风恐吓,看过一眼便匆忙离开;但也有那窃窃私语的,偏要用恰巧能被他听见的音量,让流言有意地飘进他的耳朵:看那家伙,我就说他从小就很奇怪。他甚至没有在难过。
艾利亚斯不为所动,伸手向鹦鹉夹在喙内的纸条,硬是扯了出来。写字的位置破了个洞,但内容仍然能够识读。
—现在,我离永远更近一步了。
那是20岁的珀加萨在庆祝入职的晚宴上说的。所有与它相关的回忆,都还尚在艾利亚斯记忆深处乖顺地沉眠着。时间,地点,她的样子,她说那句话时的语气……如有必要,他甚至能将那一幕用魔法复现,好让珀加萨亲自参与自己的葬礼,并对所有来宾宣读她为自己准备多时的墓志铭。
“希望是你喜欢的。”他笑了笑,轻声地自言自语。眼见着终得自由的偏见啄开锁销,迫不及待展翅飞了出去。它早已看中那个有珀加萨的活照片的墓碑,绕过所有伸向高空试图阻拦的手,傲首挺胸站了上去。
“不过我想,你应当每张都很喜欢。每一次你都考虑的很认真呢。”
如果最后大家总要去往同一个方向,而他确信直至重逢前那些记忆都不会被淡忘,似乎分别也不是多么值得悲伤。
如她所说,她只不过是走的稍早了一步。
“欢迎光临!热烈欢迎!你好!拜拜!下次再来!”
偏见高扬的鸣叫刺穿了整个会场,艾利亚斯挥了挥魔杖,抽取纸条中的文字,将它用别种方式重新绘制。墨色黯淡下去,而另一重色彩却在墓园里构建,不断丰富细节,直至鲜活如昔。
他转身离开了这扇面向墓地的窗。在他身后,熟悉的声音气鼓鼓地响起:“偏见!这是我要留到明天吃的部分!而且你不能跳到桌上抢奶油蛋糕!有礼貌的小鸟应当学会道歉!”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