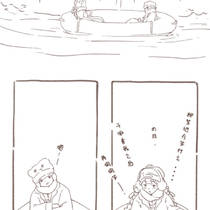标题是从一首歌那里抄来的,不见得好代这篇但很好听,遂推荐。
Window Pain-Xenia
https://music.163.com/song?id=31273947
主线无关联,人设弱关联,还有很大幅度的年龄改动(但不重要)。吸血鬼迟离与地缚灵王珲,没什么具体含义或剧情的互动,我都写au了让让我。
*
年轻的吸血鬼先生路过废墟。
好吧,他的确是一位吸血鬼,但究竟是否年轻,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就是活了太久的害处,一年与十年没什么变化,十年比百年没什么分别;时间一长——时间不长,你难免就对日期推移失去了概念。吸血鬼的相貌只有二十岁出头,大多数见到他的人便以为他真的刚过二十岁不久,他也就习惯了顺其自然、不做解释。要是有些更糊涂的称他为“好心的年轻人”,他还会高高兴兴地应上一句呢。
年轻的吸血鬼先生路过废墟。这不是他的工作,哪有吸血鬼需要工作呀?也不是他的任务,谁能给一个吸血鬼派发任务呢?这只是他最近用来打发时间的活动,大多数人将其命名为“旅行”。吸血鬼没有多少旅行的经验,就算有,他也不记得了。他为自己选了一双舒适耐用的靴子,一节长短正好的手杖;可他带不了遮风挡雨的屋檐,也带不了松软暖和的床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从废墟里找一间合适的屋子,除了帮他遮蔽有害无益的阳光,最好还能挡一挡叽叽喳喳的鸟鸣。罗宾们成天寻找蚯蚓,红隼只知道为领地争吵不停,他实在已经听腻啦。
年轻的吸血鬼先生路过废墟。这片废墟的年纪一定很大了,一片残留的天花板都难见到,堆积的瓦砾间只有昆虫被吃空的尸体。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要升起来了,要是连一面高墙都找不到,那可就真的有点难办了。正当吸血鬼这么想着、难得地皱着眉头走过一个转角时,一栋几近完好的房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伸手推了一下勉强卡在原处的木门,它们纹丝不动,甚至传回一种隐约的麻痹感。
吸血鬼当然知道这麻痹感代表什么:房子仍有主人,而他未受邀请。他绕过外墙,走向后院;篱笆的木头有一半已经腐烂,剩下的又有一半歪倒,只余一半还立着。从这些稀稀拉拉的木条之间,吸血鬼见到一个女孩,她专心致志地蹲在泥土里,脚边堆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枯叶。
吸血鬼举起手杖,在本该是院门的木桩上敲了敲。
“你好,不好意思,”他和颜悦色地说,“我能进去歇歇脚吗?”
女孩抬起头来。她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已经顺着鼻梁滑到了一个快要掉下来的高度,看起来有些滑稽。她盯着吸血鬼想了一会儿,表情显得很迟钝;过了片刻,她脸上露出一个尤其欣喜的微笑。
“当然,”女孩热情地说,“请进吧,先生!”
吸血鬼向前迈了一步。他的鞋底没法落在院内的土地上,麻痹感又传了回来。他抬头看向女孩,对方的表情一开始同他一样疑惑,但很快就变成了歉疚与失望。
“对不起,吸血鬼先生,”女孩说,“看来我的邀请不能算数——我仍旧不是这里的主人。”
她站起来,吸血鬼这才看到她逐渐透明的裙摆与淡得几乎看不出的双脚。难怪她会独自出现在废墟里,她只是一个亡魂,一个幽灵。吸血鬼并不怎么喜欢与亡魂打交道。为了从六尺之下的安眠处爬回来,亡魂们将自己变得很轻;不仅舍弃了肉体,还丢下了大半心灵。因为这样,它们会如晨雾般被人世的微风渐渐吹散,淡化成一段循环往复的影像,一句没头没尾的低语,一阵略带寒意的注视;你将很难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更不要说从中获得什么信息。吸血鬼叹了口气,问道:
“这家的主人在哪里?”
亡魂歪着脑袋看着他。那表情就仿佛她很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并因为熟知谜底而提前感到为难。“他们早就不在啦,”她说,“都死了,我的父亲、母亲,兄长和弟弟。那已经是一个国号、两次百年、三场冻雪又四轮圆月之前的事了。这里只剩我啦。”
吸血鬼挑起眉毛。他还没有遇到过能够这么清楚地数出时间的亡魂,不如说,他还没有遇到过能停留这么久还不消散的亡魂。她死的时候有多大,十二岁?十五岁,顶多了——再小的孩子会因为害怕吸血鬼而尖叫,再大的则会因为读了太多流行小说而随时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这之间的少年人能兼具两者的优点,不过分密切,却又有恰好的热心为他敞开家门。这个年纪的孩子是因什么死去,又为何成为亡魂的?
吸血鬼提起了兴趣,自然要想办法满足。他回忆着人类最喜欢的字眼,说:“在这里停留了这么久,你一定很爱这个家。”
女孩又露出疑惑的表情了。“我听说不是这样的,”她说,“我听说爱会给人远行的勇气。恨才会将人困在原地。”
“可你没有被困住,不是吗?只要你想,你随时能够……”
吸血鬼挥了一下手。亡魂是很轻的,没有什么墙壁、大门或者篱笆能挡住它们。可女孩摇了摇头。
“不,我不能。我没办法离开这里。看,” 她伸手向外戳了戳,没有实体的指腹在篱笆上方压出一个圆圆的面。“就像这样。”
吸血鬼向同一个位置伸出他苍白的指尖。一层屏障隔在它们之间;比玻璃还要透明,像空气一样无形,与围成篱笆的木片一般厚。它一直在这里,外侧、内侧,两者之间的分割线,巧妙得让吸血鬼觉得有些可笑。一个上锁的箱子,他想,钥匙就放在箱子里。他瞥了一眼天色,夜幕的颜色在变浅,群星因此黯淡。他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浪费了。
吸血鬼再次举起手杖,轻轻碰了碰帽檐。
“既然如此,很抱歉,我恐怕得走了。”他说,语气里一点歉意也没有,“要是从现在开始赶往最近的一个城镇,我还能在日出前敲开一扇戒心不足的大门,然后补充两口味道不错的甜点。下次再见了,亡魂小姐。”
亡魂点了点头。“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说,“要是我能请您进来坐坐就好了。”
“要是你忘记他们,一切就解决了。”吸血鬼说,用忍不住被逗乐的语气。“你会获得自由,我会获得阴影与屋檐。可你不会,是不是?”
亡魂这一次没有回答。吸血鬼转过身,重新绕过院墙,回到大门的方向,那是往城镇最快的一条路。亡魂留在院落里,她蹲回泥土里,两手搭在膝头,不厌其烦地细细观察跌落在地的落叶。与这栋房子离得远了,吸血鬼才意识到这路线给他带来一种影影绰绰的既视感,像是他曾在什么时候走过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活得够久,这样的错觉会变得十分常见。因此年轻的吸血鬼先生并不在意,他走出废墟。
年轻的吸血鬼先生路过废墟,废墟里有一段停留在一个国号、两次百年、三场冻雪又四轮圆月之前的记忆。年轻的吸血鬼先生将它留在原地,然后路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