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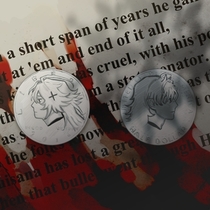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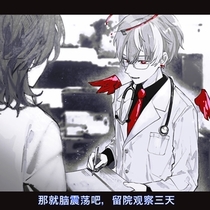




死亡有几万种方式。
刘改生想到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掐断当前的道路,改换一个来世,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但他从来不信那些东西,所以也不会升入所谓的天堂或理想乡;在前方等待的只有虚无,那是唯物主义者的专有地狱。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刘改生自己也不清楚。他的思绪像被猫扯过的毛线,全部都乱掉了。明明前十几年的人生都像无缝镶嵌的几何地砖,本以为今后也会像这样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直到触及死亡的墙壁;现在却突然在某处断裂开来,这样的残缺品只能被掀起更换,重构成另一种完全不美丽的秩序。
他不再进行多余的思考,动身前往学校。烈日当空,路面飘起摇曳的热气,树冠里上演夏蝉的大合唱。融化的柏油有些粘脚,但对他来说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牵绊。在家,房间的空气渗着抑郁;但外面更像凝滞的膏体,使一呼一吸都变得困难。好在快要结束了。他正如所愿,没人拦着就进了校门。被门口张贴的大红榜单稍微刺痛了一下,刘改生加快步速,来到熟悉的教学楼前。
走廊里还挺阴凉,不锈钢的楼梯扶手甚至有点冰冰的,给他打了个寒战。整个学校都空荡荡,不会有什么目击者。他走进教室,班级牌子还没摘掉,只是同学们的东西都已经搬空了。书桌膛再没有胡乱塞着的校服外套,空白的黑板也已经整理好姿态,准备迎接下一批新生。
他并不是想在最后来看这些。但一个只知道学习的人,他的世界里早已别无他物。刘改生打开窗户,顺着桌子就往上爬。他骑在窗台上往下看,被水泥地的反光晃得有点晕。跳楼,好自负的词语,明明根本没有跳的动作,只是坠落的过程罢了,却说得像什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一样。
越过窗户到达另一边,所有的烦恼和不甘立刻就能终结。后悔?后悔从不会折磨死人,只会折磨幸存者罢了。很快,他就能变成一圈白色的粉笔线,一滩无人认领的污渍——像校服上的鼻血印,迟早也会被洗掉,不留任何痕迹。
刘改生想起,可能是为了避免推敲理由出现麻烦,也可能只是不明不白地离开太过寂寞,他走之前还在餐桌上留了纸条。但等到真的要写,他除了“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就难以继续,最后破罐破摔留下一句“我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连名字都没签……要是能写得再好看点就好了。
“刘改生!!!”
在他犹豫的几分钟之间,出现了戏剧性又老套的情节。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幻听到同桌的声音呢?刘改生条件反射地一回头,发现她是真的站在那里,喊着自己的名字。
在这种怪异的对峙下,陈岳生闯到本应只有他自己的世界里来了。应该是跟家里联系过了吧……先找学校真是个好思路,不愧是她。刘改生一时间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以“你再过来我就跳了”相威胁未免太过丢人。一段僵持后,陈岳生带着怒气开了口。
“刘改生。”
像每个家长训斥小孩的标准开场白一样,被人用饱含情绪的语气念出全名是有魔力的。虽然一直以来,陈岳生也是这么叫他,但今天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我不是来劝你的,因为我现在很火大,我的情绪不允许我在这种情况放下身段来救你这种家伙。”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今天,我就是来这里骂你一顿!
“是,你没考好,你没考好还可以复读,但我赌你不敢,因为你是个懦夫,你连一次失败都受不了!也别说你目标太高我们不懂,你太聪明了,我们每分每秒都在经历的东西,你也不懂吧?
“现在说你想要一走了之,以为你很了解生死这回事是吧?那我告诉你,我哥陈海生,在我出生之前,在他四岁那年就死了,我压根就没见过他。一个比我大六岁的人,今年应该二十四了吧,我却连他的样子都没法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的所有这些,他已经没机会了。”
陈岳生说着,眼圈就红了,整个高中三年也没见过她这样。要在甜蜜的虚无和痛苦的存在中选择哪一边——他根本没考虑,只是突然很想安慰一下眼前在哭泣的人。他叹口气,从窗户上爬下,走到跟前,陈岳生还没消气,伸手搡了他一把;刘改生没反应过来,向后一摔倒在地上,脑袋也磕到,可能肿了。这才是要杀了他吧!他心有余悸地坐起,却看到同桌哭着哭着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刘改生,我不许你死,你必须和我们所有人一起,痛苦地活着。”
这是哪门子的诅咒啊,但刘改生还是嗯嗯应着点了点头。趁着对方揉眼睛看不见,他盯着陈岳生整整齐齐的刘海看了起来,想起某天课间看到她在喝酸奶,喝完利落地把纸盒子四角拆开,仔仔细细地压扁才丢掉,说这样方便回收还节省空间。后来他也学着这样做,感觉宇宙的熵增过程又减缓了一点点。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呢?刘改生不知道,他现在脑中浮现的尽是些奇怪的东西和搞不明白的事情,那是之前没注意到的,这个世界的其他一切。
刘改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听爸妈说,陈岳生跟他报了同一座城市,他才发觉自己连问都没问。但唯一的志愿落空,他简直就像一个叛徒逃离了北京,还企图连这个世界也一并逃离。
最后,他把头发剪短,也没复读,乖乖去上了中科大。陈岳生通过了好友申请,但是他们没有再说话,整整一个学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