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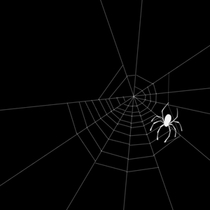


•论乱七八糟的分段如何给人带来良好体验,在线等
—
“你没设想过未来的那一天吗,哪怕一瞬间。”
“哪一天?”
“死掉的那一天。”
三人围坐同一团火焰,噼啪作响,火光触摸每个人的脸,像母亲也像子女。
人类的生命起初是抑制力,因为这世界上的掠食者过于繁多也过于优秀,所以十分之一的人要踩着十分之九的人的尸体去维持世界的运作。
佩涅洛佩想想,说:“死去的话,会有点可惜。”
“为什么?“尼禄本来直勾勾盯着篝火的眼睛偏过来,刚才他不知是在发呆还是在干什么,可他又没什么值得念想的事物,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以后也不会再有。
“因为还有人需要我吧,至少现在是。现在能想出来的是——我过去呆的那家孤儿院,现在每个月都要接受我的援助,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孩子们就要去打工。”
“你又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尼禄咧开他那张怪异的嘴露出里面怪异的牙齿,笑声很奇怪,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恶魔?”
晚风吹过时篝火呼呼作响,像焚尸炉。
“不见得,但估计也差不多。”
“那你怎么还在公会工作,你该和我一起跑。”尼禄没理解她的回答,只当那是一种嘲弄。
“权当我自愿送死吧。”佩涅洛佩想,自己其实应当补上一句:世界上生命的总量是百分之百,可生命却不是只属于我的,人的生命平均又平均,最后活下去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她在哪里、自不自愿都只是一种态度,并不能决定什么。
加拉哈德这时才出声:“还是可贵的……我是指生命。”
“……你们人类是不是都这么一副矛盾的模样?”
“比如说?”加拉哈德抬起头看向尼禄。
“你看吧,佩涅洛佩每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但她却使用些稀奇古怪的救人法术,某种意义上,她心里是抱着一种'活下来'的倔强。”
尼禄抬手捋捋头发,他不太习惯人型的模样,因为没什么威慑力。
“而你呢,哎哟,我真是不能理解你们这些贵族……尤其你还是贵族之中最叛逆的那种。你倒是天天冲锋陷阵地救人,每天给别人灌输活下去的希望,结果你自己呢,从你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里也看不出来什么活的希望嘛。”
“你整个人,尤其是灵魂,就是那个词语啦——支离破碎的。”
“……说不定我没有灵魂呢,你看见的正是我拥有的——拼凑出来的,虚假的灵魂。”
“那你说不定也该和我一起跑呢?说不定你也是恶魔。”尼禄歪歪头,“好朋友?”
朋友?好朋友?我和你可称不上什么好朋友。加拉哈德学着像尼禄那样咧嘴,所以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笑”。笑本身有千百种表现形式,他却选择最非人的那一种。
加拉哈德说:尼禄,你坐过来。
尼禄,生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和尼禄谈论生命本身是无趣且乏味的,因为恶魔活的时间很长,而人的生命很短,可没有灵魂的东西活着也不知能否称为生命,所以恶魔是活着的,但或许没有生命。大抵这世界上拟态为车轮的东西不止时间一种,还有恶魔。
所以某一瞬间他想把尼禄的头摁到篝火中去,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可不是为其他的什么,单纯地出于种族自卫。因为加拉哈德设想:说不定以后尼禄要去杀人,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或者更多。
如果正义是由人界定的,那人以外的种族就没有称自己为正义的权利,自然也没有将正义作为武器举起的权利。社会机器在律法下昼夜不停——就连那也是人类创造的。所以,他大概很久以前就想这样做了。要称它为正义吗?因为加拉哈德也是人类的一种,所以加拉哈德也应当有定义正义的权利。
尼禄有点站起身的意思,但最后没有。
靠近加拉哈德像靠近故乡,他们同样带着腐烂变质的深海的味道,血在海水里氤氲开来,气味同样也挥之不去。他敬畏故乡,他知道他的故乡是一小片斗兽场,称不上是社会。因为社会要求人们并不针尖麦芒地相对,换句话来说是包容,在粘稠的介质里同化,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杀死对方。
因为这种介质漆黑一片,所以没人知道谁杀死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