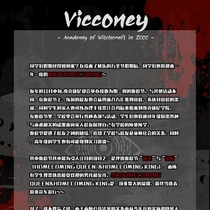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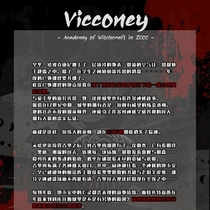


是泉唐三年后的再会,泉很努力的追到他的女总裁身边了!
.
.
.
直到飞机降落在异国的土地,他还有些不敢置信。
比他想象中简单一点——但又完全不同。唐工作太忙,没办法来等他的飞机,而夏川也不想被她之外的人带领着了解这个国家——她的国家。因此他独自站着,既没有行李也没有接机人,茫然无助的试图读懂中英双语的指示牌。
他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太过自信了。
至少快餐店的招牌长得都一样,夏川狼吞虎咽的吃了一整根赛百味,胃袋安稳下来。芝士和芥末酱给了他足够思考的热量,他终于想起自己手机上的即时翻译软件。它是离线的,即使没有网络也应当足够让他跟着指示牌离开这里。
但在他起身之前,熟悉的身影停驻在他的桌边,与整个店面格格不入。大衣从她的手臂垂落,高档面料独有的光泽遮盖她的半身,下摆随着她的靠近蹭在桌边,也许还沾染了机场快餐店的油渍——可她毫不在乎。夏川看不出这大衣的价格,可他姑且知道自己打工一个月的收入也不一定能负担得起它的一次干洗……如果它可以干洗的话。唐有不少衣服甚至是一次性的,它们被制造出来时就不是为了需要把同一件衣服穿上两次的人。她就是有那么有钱。
唐站在他的眼前,似乎觉得夏川嘴角的芥末酱很可爱,她轻轻笑了起来。
她和夏川记忆中的不太一样,不再是一身干练的西服,用面罩和防风镜遮盖整张脸——在杀戮之夜,那是必须的装扮。没有人想被记录下杀人时的样子,尤其是她这样并非无名小卒的成功人士。
而现在,她大约是从工作中赶来,化着精致的妆,细高跟鞋,女士西装,标准而典型的职场女强人。她甚至都懒得花时间考虑一套更具特色的衣装,只是以最低限度的诚意将自己装进职场所要求的装扮。
除了她的套装的价格,你无法明确的指出她和任何一个普通女白领的区别——但她不需要裤式西装,或者礼服,或者任何强调她权力的衣装。即使只是随意打扮,她那仿佛光焰一般放射出的强大气场也没有丝毫折扣。她仅仅是站在那里,如同雷厉风行四个字的具现化。
夏川舔掉自己嘴边的芥末酱,稍稍有些不安。
"夏川君,长大了呢。"唐的日语比夏川的汉语强多了,她甚至还有心情开玩笑:"虽然好像没有长高。"
熟悉的语言让夏川安心下来,他无意识微笑:"您和我记得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变老了?"唐甚至还有心情开个玩笑,她晃了晃手指上的钥匙圈:"抱歉啊,这样突然袭击。虽然说了不会来,但总是放不下心。"
她临时翘了下午的工作,开车来接他。
这像梦一样,夏川忍不住笑着站起来——他比唐略矮一点,唐的高跟鞋也没有给他更多帮助。唐略微低下头拥抱他,昂贵的大衣被她的手臂压在他的后背。她的身上带着某种香水的中调,木质香与柑橘香从她的袖口散发出来,轻柔的笼罩夏川泉。她的下巴在夏川的头发里蹭了蹭,轻轻叹了口气——像靠宠物的柔软毛发来恢复精神的上班族似的,再一次挺直身体,变回夏川不太熟悉的那个干练的女总裁。
"你已经吃过东西了,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看我们的房子吗?"她略微偏头,长发滑过肩膀,雾一般的香味还未散尽就再一次涌到夏川的身前。她牵起他的手,带着还有些呆滞的小男孩大步越过沙丁鱼群一般流动着的人们,她的长发左右摇摆,鞋跟如利刃,踏步如长矛。世界上如果有专为一步裙和高跟鞋设置的走秀,她会是那条步道上永远的女王——她现在也是。
夏川于是非常想要亲吻她。
有何不可?他们是恋人关系,时隔许久的再会,她美丽得让他无法好好思考,而他十九岁——他还有权利犯傻,对不对?唐也不会生气,她专程赶来,抛下天知道有多少件大概比全世界都重要的工作,就为了拥抱在飞机上闷了几个小时、刚吃完快餐、闻起来像电影院地板似的夏川泉。她拥抱时手臂用力,像要弥补过去未能与恋人相见的时间——她只不过是个不被允许展露出纯粹热情的成年人罢了。
夏川泉作为未成年人的时间(按照日本的算法)还有整整一年,能作为唐的全职恋人的时间……还有很久。为何不来练习呢?
于是他加速,伸出手,捉住唐的肩膀。唐的头发和他想象的一样,冰凉,光滑。可是他的手指陷进去,柔软而细腻的发丝下唐的后颈纤细,姿态挺拔——夏川想象她将香水洒在那里,垂着头,将厚实的长发拨到一边,肌肤光滑。如同此刻,她略微低下头,呼吸温热,而口红有可可的苦香。
一触即分,唐睁开眼睛,脸色比亲吻之前红润了些。人群无声的绕过他们,她盯着夏川轻咳:"下次记得跟我要一颗薄荷糖。"




夏川泉在下午三点睁开眼睛。
从决定参与杀戮之夜那一天开始,他提前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将睡眠时间从午夜调整到白天,这样他才能一直清醒到早上。改变发生得如此之快,他还来不及自豪或害怕,生物钟就已经偏移到了昼伏夜出,仿佛比他本人更加清楚的意识到这一切的紧迫。
太阳还勉强挂着,尽管仍然明亮,街区却镀上了一层完全不同的气氛。携带着可疑包裹的人在街道角落鬼祟,窥视着这里毫无自保之力的老年人们,企图透过薄薄的木墙确认他们藏在床垫下的存款厚度。这些食腐的野兽嗅着野蛮与死亡的恶臭聚集于此,等待着不久之后后那个允许他们随意狩猎的命令。
从昨天开始,涌入天栖区的大批恶棍人渣们似乎将这里视作一片无法之地。他们是在将死的土地上盘旋的秃鹫,喉咙里咕哝着模糊的悼亡曲。在他们刀刮一般的眼睛中,老人们心惊胆战的走过,试图继续度过他们的日常——现在他们仍然安全,此刻的天栖区仍然是法律的领地。但每个人都能听见它临死前惨重的呼吸,如暴风一般席卷走这里安静平稳的空气,替换以躁动不安的野火一般的干燥和刺痛。
夏川泉不喜欢此刻的天栖区。上天居住之地不该是这样混乱,焦躁,剑拔弩张。那难以言喻的蠢蠢欲动的恶意渗透进泥土里,仿佛让冬草干枯的黄色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医院早早的关上了大门,街口的警察岗亭门窗紧闭,所有可以防身的工具都在被抢购,就连公交车司机的座位底下也露出半截扳手。人们惶恐而焦躁的企图在逃命和生活之间寻找平衡,从法案公布那一天起就躁动不安的社区在昨天已经到达了几乎暴乱的程度,今天只会更甚。
但奶奶和她的房子一起下定了决心,要与她丈夫亲手建起的这片社区同进退。电视机的老旧屏幕发出细微的蜂鸣,夏川泉听见新闻主播若无其事地念着稿子:"被称为国定杀戮日的社会活动的第一次试验将会在今晚七点起于东京市天栖区开始,请市民们做好准备。"
夏川泉不知道他们要如何做好准备。
他和奶奶一样喜欢这里——住在山和海的中间,脚下总是踩着亲人奋力工作才从无到有建设出的土地。人造地面深处填充的沙子和水泥在夏季吸收人类的热力,又在冬天将它们释放,让这里成为东京凝滞空气中难得的宜居地带。海风沿着窄小的街道一路吹到他的窗口,渔汛来时,被吹干的校服衬衣带着腥味。好在他的同学们也带着一样的味道,自豪的炫耀着他们总能享受到的海风。街道安静极了,偶尔有租住的穷苦大学生在通宵后的早上和高中生们一起挤着公交,哈欠连天的赶去上一门没用的课。这里是胸无大志者的避难所,前途无亮者的暂住地;不求上进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得过且过,无依无靠的老者也能满不在乎的享受当下。夏川泉与他们格格不入,却又相处融洽。
他的确有个目标——得让奶奶安心的在她最熟悉的家里颐养天年。这梦想平淡得让他能与混日子的大学生们和光同尘。夏川泉满足于此。
可是那目标,连同天栖区的秩序一同被废弃。这片土地不会再是他们的家,而会是全日本共有的私刑架,斗兽场,和赌博项目。夏川泉同时感到愤怒和空虚——当你需要仇恨的东西远远超出你的理解能力,仇恨又有什么意义?法令并非是某个大臣的一意孤行,也绝不是只有政府想要一次盛大牺牲。他们已经被抛弃——天栖区原本就是一片过于幽抑避世的社区,居民们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老化,如今已经成了社会的不可燃垃圾。政府迫不及待的想要将他们抛下,让这片土地的价值重回市场,变成高层公寓和填满了连锁店的豪华商场。这里的老人们像曾经占据着金矿的土著,因对他们毫无价值的东西而即将死去,甚至无力反抗。
换上厚大衣,他逃出家门,祈望街道比奶奶那固执的平静略微令人安心。但街口前后都空无一人,夏川泉独自在斑马线前等待绿灯亮起。红色的小人安静的站在灯箱上,冷漠的看着他。城市明亮而安静,看不见太阳的天空是均匀的铁灰色,几乎像一片触手可及的穹顶。四面八方的天空都空旷得让人心生恐慌。向四方望去。凤凰山从民房的屋顶露出墨绿的层林,工业区和唐人街逐渐喧闹起来——即使这里即将沦落地狱,生意和工作也要正常进行。
他能想象到商店街的游客们如何挤满了每一家店,试图在这里变成人性的试验场前拍出伤春悲秋的照片,最好配上居民平淡而幸福的笑容和人生故事——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人乐于欣赏他人的受难,讨论这里的人即将死去,像在通过预告片猜测电影的剧情。工厂和码头此刻大约正忙着将最后一点库存转移出这里,比起仍需回到居民区休息的工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货物不会受害。而居民区——他刚刚从哪里走出来。有的房子已经空无一人,有的房子里还在兵荒马乱的进行最后一次整理打包,企图保全他们能带走的所有财产。他不想看那些挣扎——他自己已经够焦躁了,从别人那里吸收更多也并不能让那焦躁升华成什么别的东西。
天空肉眼可见的逐渐昏暗下去,街道沉默得像捕猎开始前的动物世界。狼群无声的对着暗号,食草动物不安的张望着,无能为力。夏川泉决定再次检查他的装备。他并不打算就这么向这一切投降——也许是出于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暴躁,也许是出于对亲人的保护欲,也许他只是因为无路可退而歇斯底里。
也许他就是个热爱杀戮的疯子,终于见到适宜自己的世界因此不愿离开。
少年还无法清楚的辨别自己的情绪,他也无法将任何一个可能彻底划去。只是想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话,他就不会准备这么多武器,隐藏在街道和房子的角落里。只是没有退路的话他也不会像这样在点数箭只时兴奋。他并不是个因无知而傲慢的孩子——这些箭的数量就是证明。他花了整个寒假在熟识长辈的铁工和木工厂里亲手车出零件,逐一组装,绝不是为了用几发警告射击将恶徒吓走了事。
此刻箭支的数量成为了他新的安全感来源,箭包藏匿在他能想到最隐蔽却又能让知情者快速取得的地方,老旧社区那混乱杂陈的墙面和屋檐都成了他最好的掩护。不愿被卷入的人们早已经搬走,剩下几户人家负隅顽抗,或者无处可逃。他在空洞的社区里散步,逐一查看隐藏在树枝,水管,屋檐和盆栽下的弹药。数个月的时间中,他亲手从铁块和木料中将它们车削成型,新制的箭头闪烁着工业制品的寒光,没来得及打磨的表面还带着刀头留下的细细螺旋。它们不是表演和比赛用的——它们是杀人用的。
他有意杀戮,尽管是以爱与保护的名义。可他确信自己仍然正义,比前来欣赏他们即将降临的厄运的游客正义,比街道中等待着开始抢劫的男人正义,比那些即将来狩猎人类的恶徒们正义,比颁布了这项法律的政府正义。
他还是个人生轻盈得可以随便弃掷的少年,他还没有活到会畏惧死亡的年纪,没有经历过后悔也未曾学会谨慎和犹豫,有与无知相同程度的无所畏惧,愿意为他仅有的那点东西付出一切。那种爱和勇气是简单而纯粹的,简单到不需要理由,纯粹到不需要结果,愚蠢得像一出戏剧。但他下定了决心,即使他依然不知道要如何'做好准备'。
太阳不可抑制的沉下去,仿佛并不打算开启新一年的春季。天地昏暗,夏川泉握紧自己的和弓,在晕眩中等待钟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