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我饿了 好嘞妈去给你把饭做 妈妈我渴了 好嘞妈去给你烧水喝 妈妈我冷了 刚做的棉袄穿上吧 我是妈妈的小棉袄 妈妈的心窝窝 现在我长大了 妈妈也老了 我要给妈妈最好的 妈是我的心窝窝 给她买点吃 再给她买点喝 有空常回家陪陪她 陪她唠唠嗑 做人儿女不忘父母的养育恩 乌鸦反哺我们要报答咱父母 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渴了 做人儿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妈妈她累了 妈妈她老了 家有一老如一宝要好好爱护她 现在我长大了 妈妈也老了 我要给妈妈最好的 妈是我的心窝窝 给她买点吃 再给她买点喝 有空常回家陪陪她 陪她唠唠嗑 做人儿女不忘父母的养育恩 乌鸦反哺我们要报答咱父母 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渴了 做人儿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妈妈她累了 妈妈她老了 家有一老如一宝要好好爱护她 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渴了 做人儿女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 妈妈她累了 妈妈她老了 家有一老如一宝要好好爱护她 家有一老如一宝要好好爱护她

马赫·布德曼很少能看见他的邻居,但最近他却很想见见这位——作家,或者从事什么别的文化人的工作的家伙,随便他是什么,反正马赫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这位有着黑人血统的年轻帮工很难找到一处舒适又便宜的住房,好在这座城市至少还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码头附近的破公寓也没什么不好的,这里有床让他睡觉,离他的工作地点比较近可以给他节省一些乘坐公共马车的费用,还有海景让他没事发个呆,不管是破旧的地板斑驳的墙壁还是时常出没的醉汉对他来说都是习以为常,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从他的天花板上时不时会传来巨大的声响。如果是白天他尚且可以忍受,但是到了夜晚需要休息的时候这声音可就不怎么能让人无视了。
这声音就这么持续了一个月然后在某一天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天马赫难得睡了个好觉。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兆头,或许楼上的那位搬走了也可能是幡然醒悟了,总之他不必再忍受那些噪音,安静的生活似乎回来了但却没有回归平静。回家之后一股莫名的腐臭味在房间里萦绕不去,但马赫不以为然,就好像楼上的声响一样,他认为这迟早都会消失的。他像往常一样擦洗地板——虽然这些咯吱作响的木头已然破旧不堪但至少要整洁一些,然而今天在某块木板上的一处黑色痕迹他却无论如何也擦不掉,他用拖布反复擦过那里直到那黑色也染上拖布表面他才意识到这些液体仍在某处流淌,他抬起头,同样掉了漆的天花板上那黑色的水滴正在从缝隙滴落。
——————
有人失踪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罗洛翻看过去一年的卷宗时里面的失踪案没有十个也有二十个,最后那些案件要么是老太太隔天走回来了要么不了了之,因此他也并不打算为此劳神费力,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办,要不是人手不够他也不会被支使到这么远的码头来。尤其是从这间屋子里散发出的熟悉的腐坏味道,他决定趁早把这起烂摊子丢给别人。
尽管道林并不想扯上这档子事,这个瘦削的男人从口袋里抽出手帕掩住口鼻穿过门堂走进这间杂乱得不像是人住的房子,然而当他看到现场的时候便已知道自己无法脱身。
“我知道你会接手的。”
他瞥了一眼探长胜券在握的脸,只能抬了抬自己的帽檐表示对于不得不趟这浑水的无可奈何,“如您所愿,顺便把门口那个碍事的记者也带走吧,我没那个闲功夫应付她。”
“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可不擅长对付这种能说会道的女人。”
我看你是根本就不想管。侦探腹诽了一句但也只能如此,“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就能拿她怎么样吗?”
“随便你,反正不要惹事。”就在道林打算跟上他的步伐探长那红色的长发忽然在空中扬起一个弧度,他竖起食指在私家侦探身前示意他闭上嘴乖乖去办事,直到看到翻了个白眼的道林满脸不情愿地挥挥手帕做了一个滑稽的“送客”姿势他才将手重新插回大衣口袋转身离去,“来吧,布德曼先生。”门口皮肤黝黑的报案人冲着道林点点头随后跟着罗洛一同离开了。
随着门口的人群也被警察们驱散,这里最后只剩下了道林。还有躺在浴缸里的那具尸体——那玩意儿曾是一条人鱼,鱼类尾巴的轮廓依稀可辨。尸体搭在浴缸边缘的胳膊上的肉烂掉了一大半,曾经缠绕在骨头上的肌肉纤维化成腥臭的液体顺着白骨滴落在地板上,这栋年久失修的公寓的地板和天花板年事已高,于是这些渗透地板和天花板的液体引起了报案人的注意。
不知道罗洛会不会告诉报案人这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幕对于普通人来说可够幻灭的,想想看,从曼妙美丽的生物变成腐烂的尸水和白骨。但是对于道林来说他需要知道的可不是这个,这座城市管不住手的有钱人大有人在,可是人鱼的主人哪去了呢?白色的浴缸边缘除了黑色,些许发黑的红色尚未完全被侵染。那红色在地板上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痕迹,最后落在不远处的洗手池上。他走过去扳动水龙头,水管发出声嘶力竭的抽水声后什么都没从里面出来。早已被水痕模糊了字迹的纸张堵住了水池的底部的孔洞,类似的纸片子在这个房子里随处可见。
他离开浴室走进客厅——同时也是卧室,这个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同样,那些写满了东西的纸张几乎铺满了地板,除了衣柜旁。他小心地跨过那些纸尽量踩在它们之间的缝隙里站到衣柜前,他脚下的空白恰好够他站在衣柜前。这个衣柜也同地板一样,道林一拉动它它便发出刺耳的声音以示抗议。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衣柜够空的了,没想到这家伙更是一贫如洗,散发着潮湿的旧木头味道的衣柜里只有沾染了血迹的湿衣服堆在里面。
道林关上衣柜,从床上拾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上面被不知什么人狂乱地勾抹成难以辨识的痕迹,从缝隙里娟秀的字体隐约可见。他将这张纸放回原位。
而在不远处的书桌前则是纸张最多的地方,除了四处乱飞的纸片子被团成一团的废稿堆得从纸篓里溢了出来,桌面上胡乱摆放着钢笔信纸和书籍等各种用具,而墨水瓶还没有盖上盖子,沾满了墨水的钢笔插在里面。他拿起桌面上的信纸,上面的字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的字迹但却有些生硬,就好像是在刻意模仿某人。这张信大致表达了对某人的感谢并对其发出了邀请,道林想看收件人是谁,但上面的名字不巧沾上了墨水,实际上类似的墨点在这张纸上也到处都是,其中“谢谢”的单词在纸张上隐约可见,道林猜想把这张纸垫在下面写字的人下笔一定很用力。
“嗨,您好,我可以进来吗?”
敲门声使他回过头去看门口,那个女记者仍然不死心地等在那里,看来罗洛真的什么都没和她说,还挺称职。他摘下帽子捋捋头发又重新戴上,不要惹事,罗洛的警告又响起来,去他妈的不要惹事,你又不给我发工资。
他站在原地并不打算走过去同她打招呼,“抱歉,这里是案发现场,无关人员禁止入内。”
记者扬起眉毛又眨眨眼睛,“无关人员?”她四周环顾一圈最后那双绿色的眼眸再次锁定在道林身上,“您是说我吗?”
“难道我在说别人?”
她将手放在胸前,张开嘴发出难以置信的感叹声,“呵!先生,我可是记者,我有义务报道社会事件,您怎么能说我是什么,‘无关人员’呢?”
“少和我扯!你们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嫌疑人更不是报案人,这些案子和你们有什么关……我不是让你不要进来吗!”
但是记者的高跟鞋已经踩上了地板,鞋跟使得地板发出岌岌可危的咯吱声,记者像是被吓了一跳但这并没能阻止她的脚步,“不要破坏现场,我知道。”她和道林一样注意自己的脚步尽量不要踩在纸张上,“现场在浴室里吧,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不可——”
“您确定?等会儿协会的清理工就要过来了,警察也没有拍照,您就不需要留个底什么的吗?”
就算道林再怎么不想和她打交道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是对的,罗洛态度已经很明确,无论人最后能不能找到都不会再插手,而他自己又能力有限,他长叹一口气一手扶额另一边随手向浴室指了一下。记者立刻发出欣喜的道谢声和着地板的求救声向浴室走去。
“谢谢您,今晚您就可以来本社取这些照片了。”得到素材的女记者向道林递出名片,但他并没有收下。
“照片也拍完了,你可以走了。”
记者并不生气,她也没有将名片收起来,“嗯哼,我是不知道您干嘛一直要赶我走,就算是警察也只是请我闭嘴而已,并不会拒绝我采访或者调查。”
“因为现在管这件事的是我,不是警察。”
“您说的很有道理,那您更应该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啊,”记者歪了歪头,挑衅似的勾起嘴角,“我知道您是那位平时乐善好施的善良侦探,如何,您想试试我的报纸的影响力和您的名声哪个更厉害吗?”
“你……”
“芙蕾雅·怀特。”
她再次递出手里的名片,道林将它一把夺过抓在手里几乎要把那张卡片捏碎,“道林,”女人得意的微笑让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些客套话,“合作愉快,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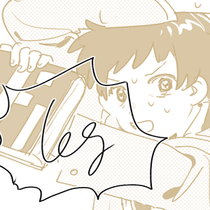


人鱼协会的清洁工从来都是那么有效率,有效率到让道林觉得没必要,好在这间屋子大变样之前道林抢救出了些许有用的东西。
“中央银行年贷,伯利辛根借贷,基尔南私人人鱼转租……”他把桌面上的借据和合同一张张捋过,终于确认了一件事——这个名为兰伯特·邓肯的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和疯子,几十万的债务,就为了一条人鱼。
现在这个数字恐怕还要翻个番。
“你该不会以为把自己的房子变成那样儿的人还能有什么理智吧?”芙蕾雅看着道林最后把这些加起来抵得上普通工薪家庭好几十年开销的纸片子小心折好收进外套内兜,他们现在在道林的事务所里,她坐在道林的对面,背光的侦探更显消瘦,这让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而迎着光的记者已经摘掉了她的帽子,比起道林她年轻的皮肤白皙细腻,淡淡的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他觉得那应该是一种他叫不上名字的香水,“那你怎么看?”
“现在是你采访我?”
“集思广益。”道林做了个请的手势。
“嗯……或许他是为了逃债。”
“怎么说?”
“很简单,这个疯子失手杀了他的人鱼,于是他就要面临协会——或者那个转租人的巨额债务。是我我就会逃。”
“可你也说了他是疯子,他怎么会判断出需要逃跑呢?”
芙蕾雅的眼睛微微睁大,她下意识地挪开自己的视线看向别处,“好吧,”她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你问倒我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或许这种精神疾病会间歇发作?”
实际上这个问题甚至把道林自己都问倒了,死掉的人鱼,消失的主人……他隐约觉得这和一年前的那起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却无论如何都抓不住那条连接它们的线。
他在迷茫中送走了芙蕾雅。
“等你的好消息,先生。记得不要把这个独家头条透给别人。”
那么现在他要先按顺序一个个地寻找线索,比如给兰伯特·邓肯发了这些纸片子的家伙们。
——————
毫无疑问贝尼迪克特·伯利辛根是个头脑灵活的商业奇才,他对市场走势有着敏锐的嗅觉,而他也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这也是他决定在人鱼行业一掷千金的原因。现在他就在享受他的回报,人鱼协会荣誉副会长的办公室如此宽敞明亮,光是坐在这个房间里他都能捞到不知比起他交的入会钱多多少倍的油水,以至于他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名下还挂着一个金融公司这件事。
提醒了他这件事的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他两颊凹陷但并不病弱,而那双紫色的双眸时常以一种观察似的目光扫过他和这个房间的摆设。贝尼迪克特有一个称不上是特异功能的能力,那就是他总能看出谁能让他捞一笔而谁是来找麻烦的,这个男人显然是后者。
“嗯,你说的没错,”他点点头打了个响指,房间里的女秘书为他们端上茶水,而后在胡契克的眼神暗示下离开了房间,“我确实有一个借贷的业务,专门为那些想要拥有——或暂时拥有一尾人鱼的人提供些许帮助。”
“所以你也给这个人借过钱吧,”男人从外套的内兜里拿出一沓皱巴巴的纸从里面抽出一张展平放在桌子上转过来推给他,“这是贵司开具的贷款合同。”
贝尼迪克特挑了挑眉,他将那张纸拿起看了眼最后的落款,上面明明白白地签着他和另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想要租一尾刚刚分化性别的亚熟期人鱼,我记得这个男人,兰伯特·邓肯。”
“他长什么样?”
现在男人的眼神里又写满了赤裸裸的探究欲,贝尼迪克特耸耸肩,“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最好不要去打牌?”
“什么?”
“当你身体前倾,微微侧头将耳朵靠近对方时通常都代表你迫切地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信息,”当男人猛地坐直身体为时已晚,贝尼迪克特摊开双手吹了声口哨又合上手掌,“情况变了,道林先生,该我询问你了。兰伯特·邓肯怎么了?”
“我正在找他。”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一些心虚话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
道林一拳砸在桌子上,他受够了这个男人的戏弄,“你这人到底什么毛病!你该不会是情报安全局的审讯员之类的吧?!”
“小玩笑而已嘛!冒犯了您我很抱歉,”他无所谓地耸耸肩,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看起来不太像很抱歉,“所以继续刚才的话题,邓肯怎么了。”
“他失踪了。”刚大吼完的的道林的声音听起来闷声闷气,满是不愉快。
“哇哦,那真是太遗憾了。”
“他是失踪了,不是死了。”
“我知道,我只是例行公事地感叹而已,那他的人鱼呢?”
“人鱼死了。”
“那真是太遗憾了。”这次贝尼迪克特的语气听起来认真了一些。
“……听起来你更在意人鱼一些。”
“毕竟那可是协会的重要财产,可是租赁人们总是不懂得爱惜,”他一边摇头一边啧啧做声,“不过我刚看到那个男人的时候就知道他养不久那条人鱼,毕竟他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
“你知道他很穷?”
“资产评估是一家合格的借贷公司应该做到的基础,他的一套房子已经抵押给了中央银行,我们没法动,所以他只能用人身劳动来抵债,如果逾期不还他就会成为我的——”
奴隶。道林在心里帮贝尼迪克特说出了那个碍于对方文明人身份没有说出来的词汇。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着急,如您所见我不缺那点钱,但是要是他本人跑了我还是很头痛的,”他抬了抬下巴,“先生,茶快凉了。”
当道林被滚烫的茶水烫了舌头时贝尼迪克特哈哈大笑。
——————
贝尼迪克特·伯利辛根的捉弄让道林的舌头又痛又麻,于是他婉拒了伊沃·基尔南的咖啡。
“好吧,”伊沃摆了摆手,他的助理带着咖啡壶离开了这个房间,“所以你是到我这里来找人的?”
尽管伊沃·基尔南不像伯利辛根那样不着调但看起来也绝不是好相处的那一类,不过道林更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尤其是他在被当成猴儿耍了之后。
“你见过他吗?”
“签完转租合同之后吗,”伊沃摇了摇头,“没有,我连他的人鱼现在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条人鱼死了。”
不苟言笑的商人怔了一瞬,但马上露出了然的神情,道林不知道他究竟清楚些什么,“所以您的意思是邓肯先杀死了我的人鱼又畏罪潜逃了是吗?”
这次轮到道林摇头,“不,他只是失踪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要自欺欺人了,先生。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说你道听途说了什么有意思的传闻?”
“只是一般的实事求是,我倒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笃定邓肯逃跑了。”
“下手没轻没重的家伙的惯用伎俩,”自打道林见到伊沃到现在这个商人终于嘴角微微上翘,他轻笑一声,这让道林感觉有些不舒服,“我总是能在各种奇妙的地方逮到他们,为了逃债他们真是开动了所有的脑筋,至于之后的故事……你应该不会想知道。”
“……追回人鱼的工作是您负责吗?”
“对。”
“这是协会默许的吗?”
“你指什么?”
“你全部的这些生意,或者说——业务。”
当伊沃那双蔚蓝的双眸直勾勾地望向道林像是要从他身上挖出些什么的时候,道林忽然明白了伯利辛根为什么总是能看穿他,他无意中也曾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这种刨根问底。
“为什么你会觉得乌奈还有那个伯利辛根什么都不知道,”伊沃调整了一下坐姿,他直视道林的眼睛,“侦探,我知道你的工作就是寻找真相,但是你要知道有的真相是会消失的,只因人们默许如此。”
——————
之后的好几天道林都一无所获,他从银行职员那里知道了邓肯大致的长相,金棕色的头发,和他相似的瘦削的脸颊,刮得乱七八糟的胡子,蓝色的眼睛。但是就算知道这些也毫无用处,捏着这些特征在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更糟糕的是另一边芙蕾雅已经开始催促他,她的头版头条早已等候多时。
这个什么活都没干的女人居然还敢像赶驴一样威胁他,又是无功而返的道林从邓肯居住过的公寓出来,这里已经被清洁工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楼下的报案人也已经搬走了,他得到了一笔举报酬金,足以让他脱离这栋破旧的小公寓,但是道林的噩梦还没有结束,他还得想一套说辞去应付芙蕾雅·怀特。
他就这么心不在焉地走在街上,忽的他的肩膀撞上一个和他的身高相差无几的男人,“喂!”他的肩膀被撞得生疼。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下巴上贴着创可贴的男人朝他挥了挥手大声道歉后便立刻转身加快脚步离开了这里。
道林一边拍着衣服上的褶皱一边习惯性地因为这起倒霉事皱起眉头,这种冒冒失失的男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少一些,他甚至连胡子都没刮好……这时银行职员的描述让他立刻抬起头望向男人离开的方向,但他的身后只有人来人往的街道,那头金发再也无法寻觅。他将手插回口袋,口袋里细腻的纸制品哗啦作响。
——————
过了一会儿那个令他难以应付的女声响了起来,“您好,芙蕾雅·怀特,哪位?”
“是我,道林,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怀特小姐,我们的合作要结束了。”
“……你说什么?!”
“就是字面意思,结、束,这段被您使唤的日子我过得非常不愉快,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再!见!”
“那我的头条怎——”
听筒落到电话机上的声音截断了女人的声音,即使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道林仿佛也能听到芙蕾雅·怀特歇斯底里的愤怒叫喊,一种报复和脱离苦海的快感让他感到浑身舒畅,他踢踏着舞步到衣架前摘下帽子戴在头顶,或许去喝点小酒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他的桌子上躺着一张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家伙写出来的纸条,或许有的真相就是那么简单。
——————
这就是真相,你好,先生。
兰伯特·邓肯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