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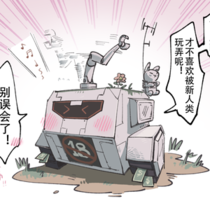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冬天。父亲近几个月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家里,但他没再露出过什么轻松的神色。弟妹已经被哄进了被窝,母亲反常地在客厅踱步,阿列克谢请了假,顶着一头寒意归来时只是对母亲摇头。
父亲已经一整天没回家了。
你回想起父亲上次攥着你的手。魔术,是的,你该学会这个。但那天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对着你很勉强地勾起嘴角。他根本没在笑,你想。
“你怎么了?”你说。
你没有得到回答。那天晚上父亲离开的时候,电视里播放着你并不关心的演说,你一向讨厌电视里那个家伙的脸。阿列克谢那个混蛋也反常地沉默了,你不喜欢这样。
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想。溜出门前,你发现今天没有人动过家里的台历,你随手把印着“25”的纸张撕下来,团成一团丢到了门外的垃圾桶。
人们似乎都习惯了把不灵光的器件送到你这里。
遗传自你的父亲,你的魔力储量并不出众,但足够精细,精细到能够胜任最细致的元器件连接。
对于人们来说,只要应该动起来的东西能动;不该动的东西安安心心待在正确的位置;天线能够正确地接收信号,这就足够了。没人在乎过程是怎样的,只要工具能重新完成自己的工作,谁又会去苛责什么呢?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工具,你也一样。
你坐在马路牙子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左手那块从废品堆里翻出来的电路板上。你的指尖冻得有些发红,日列兹诺戈尔斯克的冬天总是这样。燃烧的烟头几乎要烫伤你的右手。直到面前出现的那个着装过于整洁的男人打断了你的思绪。
他提到了你父亲的名字。
716ms的反应时间,再花费329ms以肩膀为支点带动整条手臂。忽略系统误差,总之在莫约一秒钟后,他的鼻梁以一种刁钻的角度迎上了你紧握到发白的指节。
你最终还是接受了那份学习机会,男人代表的势力——从目前来看并不包括他本人——近乎无底线的慷慨在你的脑子勾起名为“疑问”的线头:为什么是你?
再次见到他时,你已经得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歪鼻梁的男人挎着脸把工牌和一份自1991年封存至今的档案袋一同交于你。你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翕动的嘴唇吐出于此刻并无意义的字词,而你一直在摩挲那份档案的封口。
打击点应该往下一些,你想,太便宜他了。
你再次回到那座坟场时,口袋里放着那枚撞针。似乎是来自某个很有名的枪械原型机,你不记得黑市那个家伙对你说过什么了——你也不在乎,大概吧。你对枪械一窍不通,自从那场的终局后更是如此,但管它呢,只要能用就好。
清亮的视野中展现了你儿时不曾留意的景象,尽管机器尖锐如海啸的报警声早已停息,你依旧能看到那一丝微弱的魔力遗存。理顺线路一向是你擅长的。你拨开那些如烟雾一样逸散的魔力,这次的终点是一片模糊的身影——那个轮廓与你记忆中的影像逐渐契合,以及一颗卡在角落的,9mm子弹的弹壳。
你盯着那里看了许久,眼里闪烁的光点逐渐暗淡。

莫里斯说,你知道吗钟先生,我跟她的系统终端其实是连通的。
钟柏瑞一顿,他没回头,在不到两秒的惊愕后键盘被继续敲响。
钟柏瑞从来只用红轴,办公室的环境需要一种更安静的选择,否则他就要面对职场上的困境。
但自从他把这对另类的从者从英灵殿里薅出来后,他的键盘就被换成了噼里啪啦的青轴——不要疑惑,这不是他的主观选择。莫里斯在来到现世的第二天就黑掉了他的银行卡密码,导致他在没有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购置了一套崭新的青轴机械键盘,吵得要死,所以他从来不敢带去工作场合用。每晚在钟柏瑞休息后,那个迈不出屏幕的意识体就会使唤能迈出屏幕的人形机体为自己更换工作设备。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在屏幕里敲代码,外面的键盘也会跟着响,魔术的事情你少管。
钟柏瑞不止一次跟机体躲着那个意识体商量,现在她有名字了,她叫露娜。他说,露娜,他用红轴也可以工作,而我是被绿轴吵得真的睡不着觉,我劝不动那个祖宗,但我知道你一定能听进去我的话,对不对?露娜不说话,或者说目前为止,钟柏瑞还没见过她说话,但他能看见她眼睛里的镜头焦距缩放。
接下来的几天他难得地睡了个好觉。
他说,谢谢你,露娜,你真是帮大忙了,不像那个一意孤行又不听指令的家伙。钟柏瑞的黑眼圈终于消下去了,他开始时常和机体抱怨,更多是单方面倾诉,露娜总是笑而不语。
我知道你在听,钟先生。意识体被他关在电脑里了,因为他偷偷换了wifi,而他破解新的密码起码需要一段时间,几分钟到几小时,或者是几天不等,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情,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但起码能让他安稳地工作一会儿不受弹窗骚扰。
在听在听,那又怎么样?钟柏瑞被他逼烦了,他正在群内和同事进行激动人心的交接,他真是爱死这份工作了。人形的阴影从身后落到蹲坐在客厅茶几前的他身上。
所以这意味着,莫里斯说,你对她说的坏话我一直都知道。露娜的上半身轻轻弯下来,靠在他后背上,右手越过他的头顶,用指尖轻轻碰了电脑屏幕。莫里斯出狱了。
所以,莫里斯这样说着,出现在他的工作用电脑上,他在大笑。作为回报,现在我要把你的浏览器记录发到你的工作群里!
这是钟柏瑞大叫到被举报扰民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