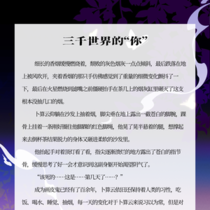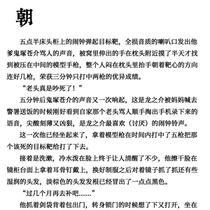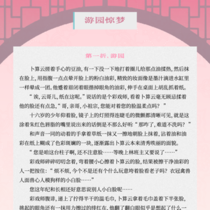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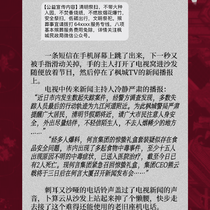

作者:莫特
评论:随意
————————
连绵的雨让整个城市被笼罩在潮湿的蒸汽下,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密集又聒噪。整个城市变得又湿又滑,屋檐下嘀嗒嘀嗒落着连成串的水晶珠子砸在地上,激起一阵阵混合草木和泥土气味的风。
卜算云坐在窗台撑着脸看着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彩色的雨伞笼罩着一个个身影不断碰撞又分开像被风吹乱的花,又像三流画家凌乱的调色盘涂满了各种各样混合的颜色。
他端着一杯奶茶咬着吸管,视线转移过来看着书桌前看资料的望海,男人低着头看着纸上的字,骨节分明的手修长白皙,干净整齐的指尖没规律地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左手转着笔时不时划上几划,垂着眼眸一脸沉思的样子让卜算云咬吸管的力度重了不少,他深吸了好几口,发出很大的咕叽咕叽声来吸引望海的注意力。
“阿云?”被声音吸引的人不出所料抬眼看了过来,满眼都是疑惑,“怎么了?”
卜算云最喜欢看他有些莫名的呆样子,松开已经变形的吸管歪着头笑了笑说:“没事哦~”
咕叽咕叽的吮吸声再一次充斥在二人之间,望海看着卜算云笑弯了的眼睛有些不知所措只好低下头继续计划着他的工作。
要瞒着地府的事情太多了,在望雾亭筹划的话被发现的可能性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偶尔他会借着鬼门稳定的时间到卜算云的房子里来。
这儿和望雾亭完全不一样,明亮敞亮完全不像是有鬼住在这里,唯一就是无论阴气多重也盖不了盛夏雨季的闷热潮湿,好在原本住在这里的“人”没有感觉也并不介意。
所以只有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被卜算云笑了好多年真装的望海鼻尖上冒出浅浅的汗珠,呼吸在沉重的空气中又重了几分,汗水最后被透着浅浅青筋的手背擦去。
窗外传来细微的喧闹声,卜算云看下去才发现是穿着雨衣的小孩互相踩水闹着玩,有松动的砖块因为积水变成了水地雷,又被彩色的雨鞋重重踩下翘起,最后溅起泥水在其他人身上。
他并不讨厌小孩子,不如说小孩更好骗更好利用,好几次年轻的妖怪求他做事,他还能笑着给人耍了一圈,不过说到也能做到,一切作恶只是调味剂罢了。
这下他看着安静书写认真规划的望海嘴角又勾起了饶有兴趣的弧度,奶茶被放下,他从窗台上跳下来背着手走到望海身边,视线从黏在额头上的几根黑发游离到鼻尖的汗水。
“阿海。”他叫他。
“嗯?”
望海看着卜算云,冰冷的鬼完全不会被这种季节干扰到,甚至他的靠近都能带给望海一丝阴冷舒适。
“我可以亲你吗?”
卜算云手肘撑在桌面上,涂着黑色甲油的手指掐着前倾落在肩上的马尾中的一撮头发,眯着眼睛一脸明媚灿烂用发梢扫着望海的手背。
痒意从手背开始蔓延,仿佛延时摄影的藤蔓一样飞速爬升着,到底是从手背上生长还是心底里扎根,望海完全分辨不出来。
他对于爱意这个情绪十分生疏,而卜算云不着调的各种话语过于直白,过于亲密,过于暧昧,像是潮湿的水汽一样裹挟着他,无孔不入又令人窒息。
紫黄色的眸子没有一点光线,卜算云就这么笑盈盈盯着他,连血红瞳孔的动摇和鸦羽般的眼睫震颤都被倒映在这双眼睛里。
深呼吸了几下后望海觉得自己更热了,他松了松衣领,让自己自由一点,然后说:“阿云,事情还没有办完……”
“嗤,真煞风景。”
雨声夹杂着喉咙间溢出的低笑声让望海突然慌张了起来,卜算云好像恼了,又好像在笑,他连怎么和人交际怎么照顾小孩都是从别人身上学来的,又怎么会懂爱情这词,更别说直白热烈但是捉摸不透的话语。
“我、我是想说,我不是……”
平日里云淡风轻的海老板突然大舌头了起来,怎么也无法给自己解释清楚,只好抓着那只按在桌上的手来延缓这一刻的兵荒马乱。
温热的体温触上冰冷的肌肤,像极了雨水打在干涸的土地上,是饮鸩止渴吗?望海开始贪恋起这份凉意,窗外的雨越落越大,隐约响起雷鸣声,到底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卜算云他完全不想管,脑子里只剩下别让他恼别让他气别让他失落。
“轰隆——”
夏日的雷鸣总是那么突然,窗外的天只剩下阴霾,就连敞亮的室内都暗了下来,视线被手掌盖住,嘴唇覆上了冰凉湿润的柔软,在单方面灼热的吐息中安抚掀起波澜的心。
望海在黑暗里眨着眼,听见了含着傲慢得意的声音。
他说:“谁要听你的啊?”
十王街老街区古玩巷子内有一家三层的古玩店,名字叫做望雾亭在整条古玩巷子里显得格格不入,常年敞开散发寒气的大门,明明无比显眼却毫无客人,偶尔有机车轰鸣一响而过,除了进去过的客人没人知道这家店到底卖些什么。
随着活蹦乱跳的两个人回到店里,似乎驱散了不少阴寒气息。
被叫做海哥的望海并不在店里,望恩把背着的裹尸袋放在中堂之后拿着柚子叶拍打在自己身上,他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小森说过他体质要这么做就乖乖听话。
“怎么办?海哥不在欸,难道这次的交接要我们自己去了吗?”
“传消息的是道术联盟那边,这次问题偏向人类这边,志怪局没有插手的理由……”
望晚森握着拳抵着下巴思考了好一会,蹲下去拉开裹尸袋看了眼逐渐回复理智的老张叔,狰狞的尸体安静了下来,布满血丝漆黑的眼白好像变淡了一些。
“大叔能理解现在的状态吗?”
呆滞的尸体瞪着眼睛摇了摇头。
“你已经死了哦。”
望晚森清澈的声音在夜里昏暗的店铺中更让人感觉到冷冽,望恩搓了搓手臂打了个喷嚏,得到了少女瞪过来凶巴巴的眼神。
「你又惹小森生气了……」
抱着手臂被嫌弃的望恩像小狗一样露出可怜兮兮的眼神,还没说什么就被轻飘飘的东西拍在了肩膀上,与此同时还有不知道哪里响起来幽幽的声音。
“哇啊啊!!!!!!”
即使在这个家住了好几年望恩也没有习惯在晚上看到这家里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会动的纸扎人。
站在他背后的纸扎人是远比望恩和望晚森还先到这个家的家属鬼物,俩小孩不知道纸扎人原名叫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鬼,只知道望海把它当弟弟一样照顾,给了望雾亭三楼的阁楼做了栖身之地。
差点被弹射起来的笨蛋撞凹了的纸扎人捂着身上的竹子,闷声闷气地说着:“小鬼你还这样迟早有一天不是你被吓死就是我被送去维修。”
“呜呜,纸哥你不要在大家干完活的时候突然出现好吗!!!真的很吓人啊!!!”
「笨,又菜又爱逞能,你看小森多镇定。」
被点到的望晚森完全不想理一人一鬼,还在认真和地上的尸鬼解释。
“大叔你还有自己的记忆吗?”
“不……不、记得……了……”
意识恢复了一些但是完全无法记住发生了什么事的老张沙哑地说。
“那我和你解释一下吧,这里是望雾亭,偶尔会接一些生死两边无法界定的伤害事件协助处理,这一次接到了道术联盟的委托来抓你原因是……”
望晚森拿出平板电脑翻着道术联盟发来的档案,看了眼档案上一家三口幸福的照片开始念:“张栋林,男,52岁,死因为裁员后跳楼自杀。按理来说你应该会在12小时内被鬼差带去地府,但是不明原因让你成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尸鬼’,你在自己家和平常感觉一样度过了3天,一开始你的妻儿以为是幻觉,但是由于你还‘活着’这件事足够让她们安心,所以没有意识到危险。”
被朱砂线捆住的张栋林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样,它难以置信地挣扎起来,似乎是想要望晚森住口。
望晚森顿了顿,银红异色的眼睛看了眼挣扎万分但是毫无眼泪的张栋林,继续念着后续的报告:“但是受鬼气影响,你无法控制情绪,缺失记忆,对活人的生气展现出渴望……你,咬伤了自己16岁刚上高中的儿子。”
“不是!不是我!我没有!”
“你有。”望晚森的声音无比冷漠,“你的儿子张涛现在在道术联盟的医院化解身上的尸气,如果不能熬过去的话他就会……”
“不会!我儿子不会死!我明明不会死啊,我只是听那个人说……那个人说能保护我,给我看了跳楼也不会死,说我用这个去威胁公司我就不会被开了!”
张栋林在地上扭动起来,本来平复的状态开始狰狞起来,肌肉诡异地膨胀起来被朱砂线死死勒住流出腐绿色恶臭的液体。
“骗子!都是骗子!!我要杀了你们!”
「你们俩搞得定吗?店里阴气很重说不定会有变故哦。」
纸扎人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已经轻轻飘到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拿出武器的两个小家伙。
“望恩,等下要是张栋林挣脱了你就从背后用力气压制他,绝对不能被牙齿和指甲划到。”
“嗯!”掏出匕首的望恩乖乖绕到背后,绿色的眼睛笑眯眯看着望晚森,“小森你也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