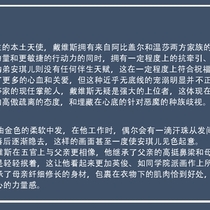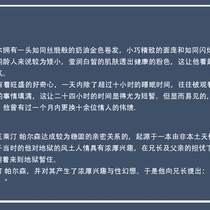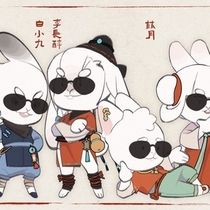

山中闲记·魇
清清在第十六年的冬天生了一场病。师傅说是冬天来了,去山下的镇子给他抓了药。刚开始,他还很有活力,照例每天和山雀说话,和小镜湖的兔子一起玩。
第二年立春时,清清的病好像又重了些,他不会说话了。师傅只是搂着清清,说冬天就快结束了。
到了夏天、秋天,清清总是和师傅偎在一起烤火,这个漫长的冬天好像再也不会过去了,他不爱吃苦、也很怕痛。可他那么想好起来,想要陪着师傅,到病好了再去长乐城看灯会。
可是第三年立春的时候,这座山都死了。
其实没有师傅,也没有山雀、没有白色的熊、也没有小镜湖。
清清是个疯子。
山中闲记·三
师傅问清清,出了山之后想做什么,想当大将军还是做侠客。
那时是仲夏时节的午后,清清在师傅怀里睡得迷迷糊糊的,说不想当将军也不想当侠客,想一辈子都和师傅学功夫,和山里的花鸟树木做伴。
师傅拢了拢搭在两人腰际的薄被,轻轻拍着清清的肩膀,缓缓道:睡吧、睡吧…
但是师傅没说,妖怪的一生太长太长,清清十几岁,师傅三百多岁,他们都有太长的路要走。
从环山的湖引渡、上山再下山,这路太短,难以消磨上千年的时光。
对于清清来说,一辈子就是颠沛流离的七八年,还有在山里的十二载;师傅的剑和他的剑,师傅的琴和他的琴,就是他的一生。
可师傅不一样,山中的十几年不过是匆匆一顾,时间太慢又太快,他记不清走过了几朝几代、杀了多少人、教给清清几招几式。
山中闲记·四
清清打小就爱哭,早在师傅捡他回山里之前就能一嗓子哭跑整条街的小孩,当时他又瘦又黑,胳膊腿细的跟柴火似的,天天还爱和坊间年纪相仿的孩童掐架。
他又没爹没娘,没人教没人管的,动起手来实在没个轻重:谁要是踢他一脚,他要还回去二十脚!虽然大多时候是打的过的,可总也有挨打的时候。
清清怕死痛了,挨打挨的多了就要哭的昏天黑地,他小时候长的秀气,一撒起气来又娇滴滴的好像小姑娘,弄的那些男孩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只都跑回家去不再和他玩。
这且是他没人疼爱的时候,自从在山里安了家,更是有丁大的委屈都要抽噎一阵。只要清清一掉眼泪,师傅再不忍心说他,总是要搂着抱着、温声细语哄好一阵。
恃宠而骄说的正是他了。
拜这臭毛病所赐,师傅教的功夫他总要挑挑拣拣,只选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不用受苦受累的练。
这次又是因为学不来飞燕踏水在哭了,不过是掉进湖里呛了几口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抽抽搭搭的。
山中闲记·五
前些日子师傅给清清在长乐坊订了新衣服,这天早上刚好送到。三月初一,天气也在最近开始转暖了,山上的植被都抽枝发条,拱出了新的嫩芽。
清清比起去年春天又长高了不少,除去披风和坎肩还算合身,其他合季的衣物已经短了一截。
这次送来的几身行头,除却清清常穿的款式,还有两套深色棉麻短打,都做成时下流行的款式,供他替换穿着。
师傅回到听雪小筑时清清刚刚转醒,本还赖在床上滚来滚去,见师傅抱着几只长乐坊的锦盒,耳朵一下子竖起来,摇着尾巴跑过来要看新衣服。师傅先是把盒子安置在橱柜里,又把清清赶回床上训话,训他又光着脚跑来跑去,要他快去洗漱用早食。
二人吃罢后,不等收拾完碗筷,清清便又吵着要看新衣服。师傅催他先把杯盘洗净,自己上楼去把锦盒中的衣物件件取出摆好,检查是否有纰漏。
待清清手脚麻利的收拾完碗筷,赶紧追着师傅去楼上了,一件件摸过看过了,又赖着要师傅帮他换新衣服穿。
师傅常着白衣,清清喜欢师傅,而也喜欢白衣,这批衣物中雪白贡缎、月白薄纱和玉色提花棉制成的套件各有一二,清清就要挑着最雪白、最繁复的那身穿,师傅不允,说他总爱到处打滚,往往前一天还是崭新的白色,次日就要滚成灰的。
清清撅着嘴小声哼哼,却也无可辩驳,白色华服他有过不少,可每次到师傅需他穿着庄重,参加某某大会时,打开衣橱一看,又都是灰扑扑一片。
于是最终,师傅挑了青莲色的棉麻布衣给他换上,清清抓着师傅的手来回转了两圈,飞也似的跑去耍了。
师傅朝他喊了两句须得仔细脚下、莫太贪玩云云,也收拾收拾去了书房,研究他的之乎者也去了。
山中闲记·杂记
事实上清清这两个字也不是他的,是师傅的一位死去的故人
师傅只是随口喃喃,清清以为是叫他,于是他就叫清清了,师傅也不在乎,在山中闲记和万里送行舟的片段里,师傅什么都不在乎
师傅具体叫什么,以前经历过什么,目前为止清清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很多人来山上找师傅或者杀师傅,他们有的叫师傅师大人、师先生、太主傅、王上,或者别的称呼或名字
由这些人的各种称呼中,清清推断师傅应该是姓师,曾有一位女鬼来找过师傅,她叫师傅阿宸,所以清清又猜师傅叫师宸
清清不敢问关于师傅的事,有人来杀师傅,追问师傅从前的事,师傅总是把清清锁在屋子里,封了他的五感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人也没了,来过的痕迹也没了
清清猜他们是死了。
山中闲记·六
师傅是清清第一个男人,约莫是十三四岁那年的夏夜,清清跟着喝了点酒,晕晕乎乎的往师傅身上靠,红着脸趴在他身上乱蹭。
他们的第一夜并不温柔或缠绵,不过是师傅发泄似的索取。
清清或哭或喊,师傅一概不理,只是掐着他的腰、箍着他的手不让他乱动。
那晚上一直从弗入夜做到天光乍破,虽夏夜短暂,可也有实打实的几个时辰。
到第二天早上,清清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他那时还小,身子骨弱,又瘦的皮包骨头似的。经过这么一折腾,浑身上下更是没一处好肉,莫不是青青红红的痕迹。
于是他便大病一场,先是连续不断的低烧,后也吃不进东西、无法好好消化,往往是吃下一口要吐出两口。
可他实在是小,师傅又是独一个爱他的人,接下来几天,虽然清清病着,师傅还是又要了几回,他也不反抗,进而身体又更差。
清清不明白这事是什么意思,只当师傅同他玩,他也愿意一起玩,接下来更是寸步离不开师傅,吃饭、睡觉、更衣沐浴,都要师傅抱着、帮衬着。
他没爹没娘,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之别,也不知什么是断袖之癖。
颠沛流离的那些年,只要有一口吃食果腹、有一方空地休息便足矣。清清不明白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他连什么是小女孩都不清楚,就爬了男人的床。
师傅是清清的救命恩人,是相当于父母的角色,又是他的师长,这时开始还是他的男人。清清的世界里,所有的联系都与他有关,所有的悲欢喜乐都由他支配。
可是在师傅眼里,清清到底是什么呢。
山中闲记·七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定疆、平天下。
这是师傅教给清清的第一课,彼时清清十六岁,学完了师傅教他的身法、读完了四书五经,开始学更深奥些的道理。
师傅问他,清清觉得哪一样更重要些?
清清说正心,正心是根本,世间万物生长消亡,或苦或恨、悲观否、乐逸否,皆为命数,不由人定。独本心不同,唯本心不变,方得大道。
师傅不评判清清所答正确与否,只是叫他记住这话,不止当下、往后数十年上百年,都要牢牢记住,何为正心,何为他所要追寻的大道。
到这天傍晚,清清随师傅用完晚膳,二人依偎在廊上吃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闲话。
清清问师傅,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定疆、平天下,对师傅来说,哪一样更重要?
师傅不答,清清当他在思索,捧着瓷杯看沉在杯底的茶叶形状,等师傅开口。
半晌,他没等到回答,只看到师傅蓦的流下泪来。
清清忙放了瓷杯,胡乱拿袖子去抹他的脸,又问是怎么了,别哭、别哭。
可是这泪一滴落下来,后头的怎么也止不住,师傅拥了清清入怀,依旧不说话,只是默默淌着泪……
这是清清第一次见师傅哭,此时他才真正觉得师傅是真正活在尘世间,是有血有肉的身躯。
那晚师傅搂着他在廊间坐了几乎一夜,到师傅回过神来,小狐狸早冻的手脚冰凉,也不知何时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对于师傅来说,这十三字中最重要的莫过是平天下。可他经历的磨难太多、走过的岁月太长,也想做个普通百姓,和亲人在世间活过几十年,解脱罢了。
寻灯入梦来·一
其实师傅像清清那么大的时候,也有过饱含热情、又参杂血泪的成长历程。
和清清不同,师傅是名门望族的大公子、四圣中的苍龙一脉,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从小到大都是锦衣玉食供着,温香软玉养着。
百十来岁时,正是少年意气风发的年纪,师傅从小天赋异禀,师从当代大能,一招一式都是极其标准的大家风范。
他心高气傲,没吃过苦也没想过苍生,颇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可笑思想。总是仰着头做出睥睨众生的表情,以凸现自己血脉尊贵、与众不同,更不屑于与江湖游侠交往,嫌掉了身价。
清清猜的不错,他从这记录中知道师傅确实是姓师,也曾有过“chen”这个名字。
师傅并非嫡出,虽然血脉正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只是生母无名无份,论传承、不该是他。
因而这个“chen”,不是宸、是臣。
寻灯入梦来·二
江湖上有一号人,是近几年才崭露头角的少侠,被世人称作慈悲剑,这称号的主人名叫师清,实则他用的是一把苗刀,不是剑。
别人口中说的师清就是清清。彼时,师傅已经走了三年余八个月。他先是四处寻了半载无果,只得收拾心情过活。
师傅走后的第二年惊蛰时分,清清在长乐城附近的小镇安了家,收拾出一间双层小楼,样式装潢同山上的旧居一样,还取名叫听雪小筑。当时小镜湖与山顶的妖灵也都被他一同带来,除了没有师傅,清清的生活似乎与往常并无二致。
至于师清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要说起他“慈悲剑”这一名号。从前师傅教他慈悲为怀,要爱天下、爱苍生,清清一直记得。
只是清清从未在尘世间活过,又如何分辨的清孰善孰恶?他以为在哭的悲伤的便是弱小,于是有求必应、使命必达。
无论是杀人越货、或是报仇雪恨,弱小者要他屠满门他便屠满门,要他杀丞相他也杀丞相。
好事清清做了不少,可坏事一样也没少做。有豪侠讽刺他活菩萨假慈悲,也有受惠于他的人赞扬他是大善人,因此得名“慈悲剑”。
那豪侠之中不乏有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可真正愿意为民除害的只出了一人,这人使一双弯刀、头上长着对猫耳,清清认识他:正是当年那只大猫妖。
猫妖与清清交手三次,他打不过清清,清清也不下杀手。于是猫妖大骂他假慈悲、杀人狂!质问他为何不下杀手,又在装些什么。清清只是哭,不住的摇头,说我不知道,我分不清。
一来二去,猫妖竟成了听雪小筑的常客,他教清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人该帮什么人该杀,也教他什么是酸甜苦辣,什么是悲欢喜乐。
猫妖问清清为什么用剑法使刀,清清答因为师傅用剑,猫妖又问清清师从何人,清清不知道。
最后猫妖问清清叫什么名字,清清说叫师清,师傅的师,清清的清。
猫妖是关外人,名叫阿吉夏哈甫,汉名明祁。
寻灯入梦来·三
锦衣夜行,说的是千机阁麾下的一门支部,承接江湖上下各式各样的委托,不论是朝廷重臣或是黄口小儿,只需将请帖送到锦衣行去,由主事的评出甲子级别,缴纳相应报酬即可。
虽然流程简易,可经由天机阁负责的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揭榜率又极高,这行当便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因此应运而生的有许多专职揭榜的野帮。
师清是头一回来到关外,这锦衣夜行所处两国交界的飞砂关,不比他呆惯了的中原地区水土丰饶,边塞常见的风光多是戈壁浅滩、飞石走沙。
此地不隶属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江湖上有名的能人志士多选择这里盘踞。
除却千机阁下属的锦衣夜行,还有通文、烟柳画桥等多方由江湖游侠组成的势力汇集于此。
简单交代完,阿吉伸手将师清头上的兜帽往下拉了拉,这地方不受朝廷束缚,因而见不得光的交易自然更多些,譬如通文旗下的娇子舫:便是买卖少年少女来做皮肉生意的不法组织。
因此在飞砂关居住的百姓往往以兜帽遮掩容貌,以防被心怀不轨的歹人盯上。
师清进了锦衣行的大厅,由明祁牵着他走,这是他第一次到有如此多能人异士的地方,免不了四处打量别人的武器和衣着、或者盯着谁的眼睛看,再被充满敌意的目光瞪回来。
明祁松开拉着师清的手、改为搂着他肩膀,压低声音提醒到:“别乱看。”
于是他就收回目光,乖乖跟着明祁进到内厅去登记些杂七杂八的信息。
寻灯入梦来·四
半旬前的一次切磋,阿吉夏哈甫的弯刀擦过师清的鼻梁,留下一道约有寸把长的豁口。
师清撑着床垫起身时,阿吉正打好了水要伺候他吃药,从半年前师清第一次受伤开始,他的身体素质开始直线下滑,除却身手和灵力不如从前敏捷以外,肉身的强度也明显下降,譬如发热目眩等凡人间流传的病痛,在他身上开始不断出现。
阿吉将瓷碗放在桌案上,扶着师清坐正,说到:“别捂着脸,让我看看鼻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会不会留疤啊?”
“……不会的,好多了。”阿吉抿了抿嘴,没告诉师清实话,事实上那道刀口和之前的情形并无二致,只是刚刚结痂、还有些要化脓的趋势。
师清听完也不做多想,朝阿吉笑笑,问他今天的药喝完了能不能去买麦芽糖吃,又问大夫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正常出行。
“可以,现下日头正好,你简单梳整一下和我出去,买些回关内要带的东西。”
“好。”,师清答应到,又低头扣弄指甲附近的倒刺。
“哥…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
阿吉伸手揉揉师清脑袋,使本就没梳理过的头发变得更加杂乱,竖起一两根倔强的立在头上。
“别瞎想,你才多大。”
这是阿吉今天说的第二个谎话,其实他也不知道师清还有几天可活。从他们碰到小白那天之后,阿吉就明白过来师清其实根本不是个生灵。
师清口中的师傅,师宸,是主管人间的天道,而师清只是师宸的一缕念头。
师宸独活在人世间太久,师清就是师宸对相守的一缕执念,于是顺应了师宸的意思,天道的力量为师宸量身打造了师清,由小白映射出来的师清,专门为与师宸相守而生。
这意味着,师清维持生命的来源不是食物水源或者灵气,是师宸。
此次回关本不在阿吉计划之内,这趟走了不到两年,和他原本的目的地还颇有一段距离。可碍于师清的身体状况,二人不得不改变计划,调头回关内去。
再相逢·一
展信悦,我与阿吉现下在京城落脚,万事顺遂,师傅不用挂念。
前些日子下了雪,我第一次在山外看到雪,京城内经纬横纵、井井有条,前夜下了雪,翌日清晨便有人洒扫利落,只有房檐上或枝丫间有些积雪,与红墙青瓦相映成景。前些年与阿吉在关外游历,立冬过后只有北风吹过,还是京城繁华多些。
此处不比山中清净,但往有商队或戏班往来,街上热闹,也别有一番烟火气。
我们在梁将军门下作客卿,为宗朝做事。梁将军是我揭榜偶然结识,是位文韬武略之志士。
我逐渐理解师傅当年教过,所谓纵横捭阖、君君臣臣。
前些日子我与阿吉听雪夜谈,宗朝当下为边疆战乱所困,是苦关外胡人频频骚扰,朝中主战派请奏出兵,梁将军党正与其争执不下。
而我们正从关外来京城,途中所见种种无不令人忧心,每逢寒冬,关外百姓凡食不果腹者十二三,衣不蔽体者百一二,牛羊牲畜病害者无数……关内水土丰饶、气候和缓,而胡人进犯也是无奈之举。
师傅当年问我何以解忧,如今我也想问师傅何以解忧?如何又能求的天下太平呢?您要我入世历练,是要我体会这时间的悲欢离合,可世间的一切又大多是庸人自扰,凡人的思虑太多,又何以让这苍生得道解脱呢?我现在还不明白。
再过月余就是春节,不知师傅如今身在何方,是否孤身一人。我心头挂念,自千机阁一别已有四载,清清自认为已褪去懵懂无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妖了。
望师傅一切安好,万事胜意。
再相逢·二
展信悦,宗朝与胡人最终没能开战,冬至前后从朔方袭来一股寒流,听坊间百姓说关外冻死了数千头牲畜,大萨满带着部族撤到了祁连山外百十里,临近大海的地方休养生息。
于是庙堂之中也不可避免的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边塞节度使瞒报军情,主战党的丞相联名上书,弹劾梁将军消极避战、有意向蛮夷示弱,实在是荒唐。梁将军年有二八,为宗朝效力十数年,且不论西北方的胡人部族,宗朝能有今日之昌平梁将军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与麾下的将士浴血拼杀将苗疆道截断,中原地区也要被异族频频骚扰,哪来如今的安息。
谈到异族,如今凛冬将至,雁门关外的银狼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宗朝内妖族生存又受到威胁。眼下形势严峻,我与阿吉收留了几只城中流浪的小妖,梁将军备好了,过几日护送我们去城外避避风头。
师傅教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子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可我身在其中,亲历万般苦痛,又如何作壁上观?弟子愚钝,参不透其中道理,又忍不住参杂私心,无法公正。
也许我无法继任天道。
孙巳生在动荡时局的开始,秦二世死后的第三年。
这是一年隆冬、临近年关,哪里却都不太平,陈丙拖着麻布袋在风雪中步履蹒跚,他要带着商队快些回屯上去,最近几日大雪连绵,又从北方传来战事吃紧的消息,他隐约感到有大事要发生。
一行人马将上官道之前被碎石拦了去路,他们回到屯上时已经过了年关,是巳蛇年了。他匆忙赶家里去收拾行囊,准备过了初六就携父老南下避难。
等陈丙回到家中却不见发妻身影,只有妹妹搂着襁褓啜泣,原是孙氏除夕夜小产,诞下婴儿便撒手人寰了。
陈丙为婴儿取名孙巳,随其生母孙氏家姓。
李吭与孙巳互诉衷肠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此时他们随军驻扎在汉中待命,这天入夜后二人偷偷溜出营帐,在茫茫旷野中奔跑,又相互扑在一起在草地上打滚,他们交叠着接吻拥抱,两张面庞上都淌着泪。
忽的远处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先是一处、再慢慢连成一片!先是李吭一个打挺爬起来,抓着孙巳手腕就往回跑,孙巳也从温存中恍过神来,扯起破锣嗓子大喊:“敌袭!有敌袭!!”
这一仗打完二人都负了伤,也因祸得福加官进爵。他们躺在相邻的两张行军床上扭着头对视,过一会又扑哧的笑出声来,两只手拧巴得和凝固的血水和污泥掺和着扣在一起。
孙巳再见到李吭是二人分别的第二年春天,他被抽调来汉阳战场做辎重兵,此时战事稍微明朗,前些天的伤兵都安置在大营内修养,李吭也是其中之一。
孙巳见了李吭便趴在他床头痛哭,嘴里不住的喊着哥,李吭一张脸被布条裹着三分之二,仅仅露出的一只眼也默默流着眼泪,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实在是生不逢时,被时局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向后,每走一步都是生死不由己,唯有劫后余生之时才得以短暂相望。
韩信死后二人便向户部请辞离开了长安,一路向北到范阳附近定居。
当初李吭得以随军打仗是受了韩将军恩惠,这七年来二人几乎一直编在大将营下,随军护送韩信出生入死。如今将军之死犹如阴云笼罩在二人心头,久久不能平息。现天下太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若继续留在皇都,指不定二人也要死于非命。
他们只是洪流中的渺小人物,眼看历史的车辙滚滚向前,眼看亲朋泯灭在车辙下,一声微不足道的叹息,在四面凯歌中细不可闻。
马卡龙三号是在安琪儿 温莎 阿比盖尔将瓦莱汀 帕尔森带回庄园时,经戴维斯 温莎 阿比盖尔亲自挑选的新一列仆人的其中之一。
他经过简单的基本文化教育和佣人规章培养后被安排侍奉安琪儿盥洗双手。他名字的来历来源于那段时间的安琪儿很喜欢吃的一种点心。
马卡龙三号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写成日记记录下来,其中包括对安琪儿和戴维斯的觊觎、对他们的性幻想和对安琪儿的观察,以及宅邸内两位主人的日常生活轨迹。
他没有亲眼见到过瓦莱汀本人,只是偶尔从门缝中匆匆一瞥,或者听到地窖或安琪儿房间内传出的喘息声,马卡龙三号详细记录了安琪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侵犯了瓦莱汀,以及对当时场景和瓦莱汀本人的推测。
时间越久,马卡龙三号越能发现整个宅邸都被怪异扭曲的氛围笼罩,戴维斯对安琪儿的掌控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譬如这位表面绅士克制的先生会在每晚帮助安琪儿换下内衣后,将它们贴在鼻子下疯狂嗅闻!或是将每餐结束后安琪儿剩余的食物当做某种餮宴仔细品尝,这对于拥有相当实力和地位的家族来说无疑是足够失礼的行为。
而安琪儿似乎也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纯洁无辜,马卡龙三号经常听见他的房间内传出凄厉的惨叫声、或是混杂着颤抖的求饶。
在安琪儿发泄结束后,马卡龙三号会被要求闭上眼睛为安琪儿擦洗双手。
有时他会偷偷睁开半只眼睛观察房间里的情况,而戴维斯似乎从始至终都坐在另一张凳子上为安琪儿拿着水杯,平淡的旁观弟弟和别人做爱,这样荒谬的举动令他更加毛骨悚然。
他也更不明白时代歧视恶魔的阿比盖尔家为何会容忍二少爷和一只恶魔坠入爱河,马卡龙三号也有过几次偶然间与瓦莱汀对视,那种藏在灵魂里的贪婪和强欲使他无法控制的发抖。
直觉告诉他这只恶魔并不真的效忠或雌伏于安琪儿,它像一管蓄势待发的炮筒,随时准备将阿比盖尔庄园彻底颠覆!
当然,戴维斯绝不会允许有人偷偷窥伺他的弟弟,这名奴隶正是他故意安排在安琪儿身边的。
马卡龙三号的结局是被秘密的凌迟处死,而这本对瓦莱汀和安琪儿秘密情事的观察日记才是戴维斯真正想要的。
戴维斯需要弟弟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他也很好奇,这样一只低劣的恶魔为何会得到安琪儿的别样青睐?这让他内心产生了别样的波动。
安琪儿日记
7月29日 天气晴
哥哥带回了一位新的情妇,他拥有一头皮粉色长发、五官十分精致,最有特色的是那双微微上扬的杏眼(让我联想到某种行动敏捷的小动物)和小巧的嘴巴,整体看起来像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当然,这要忽略他的喉结和身材特征(他的身高比一般男性更矮,我喜欢这点)。
他的名字是艾利奥诺拉 米切尔,没有中间名,他是一位非本土天使,目前作为普通雇员就职于警署。
据说他的薪水状况并不乐观,甚至买不起一栋像样的别墅,也雇佣不起必须的仆人,真是令人震惊!简直无法想象他生活在何等水深火热之中,实在太可怜了,好在他住在庄园的日子可以不必操劳,我也要给予他更多的关怀才行,原主保佑他。
米切尔先生似乎拥有很强的自尊心,在我询问他是否为哥哥的新晋情妇时似乎有冒犯到他,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可这种身份,天哪,真为我的失礼感到羞愧。
据我推测米切尔先生好像并没有过性经验,但他却装作一副身经百战的样子,真是奇怪。
他很容易害羞也很容易脸红,这让我很想亲吻他的脸颊或者做更进一步的事情,米切尔先生的翅膀根部十分柔软,每次触碰都会让他无法克制的战栗,不知道他的肉穴是否也是如此青涩可人,唉,如果能快点和他做爱就好了。
拥有绅士风度的我还可以忍耐!
附:叔叔似乎对米切尔先生的到来感到开心,这让我非常愤怒…为什么他还是学不会只关注我一个人?我需要加强对他的管教。
(今天的哥哥也一如既往的完美,他的阴茎对我依然充满诱惑力,下一次可以和哥哥尝试深喉、仅仅是想象它充满口腔的感觉就让我忍不住勃起。)
切尔西先生的补充:
“额...物质上确实是超出我想象...阿比盖尔家的人们也对我很亲切友好...兄弟俩,长在我审美点上,平时对我也很好(指床下),,但是其他时候却像野兽一样呢,,,反差很大,,兄长很沉稳,很有家主的风范,弟弟像小孩子一样,很可爱,但也古灵精怪,,(花样也很多),虽然我个人比较保守且偏向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诚挚,但意外的,,在两兄弟这样我也不讨厌……但是!请不要用‘情人’来称呼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绝不是攀附在大树上的藤蔓!如果真的要延续这种关系,我更希望他们能更正式地对待我,像真正的情侣一样。”
时间追溯至二十六年前,年少的戴维斯并不像现在这样疯狂且偏执,恰恰相反,七岁的他是个安静腼腆的孩子,由于成长过程中缺失陪伴,他有着和年纪并不相仿的沉静,像是一坛无风吹拂的死水。
占地颇广的阿比盖尔庄园内并没有第二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孩子,这栋宽阔的宅邸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花园构成了他的整个童年。
可怜的戴维斯不管走到哪里都只有佣人对他简单问好,后又唯恐避之不及似的低头离开,这让心智尚且年幼的戴维斯感到莫大的惶恐和孤独。
而一切的转机是这年的圣诞节,在白雪纷纷扬扬落下的寒冬中,他得到了一张来自母亲亲手制作的贺卡,附带一只羽毛洁白、双眼蔚蓝的鹦鹉,看起来乖巧灵动、时而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
它被取名为安琪儿,无疑成为了戴维斯最好的朋友,恰到好处的填补了少年缺失的部分。
安琪儿获得了最大最漂亮的金色鸟笼,雕刻有繁复花纹的黄金柱子上镶嵌了颜色各异的璀璨钻石,在阳光下折射出漂亮的火彩。
戴维斯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每个风也温柔的午后,他看着笼子里羽毛洁白的安琪儿,听它叽叽喳喳的说些什么,浑身上下都像泡在温水里一样妥帖,每个毛孔都舒适的张大,这正是他一直所缺少的东西。
是啊,他多么想要一只属于自己的小鸟啊。
随着时间推移,戴维斯越来越不想让佣人看到这只华贵的金色笼子和他的小鸟,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宝藏,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对安琪儿的窥伺。
那些平时怯懦的佣人凝视鸟笼的目光是如此贪婪,粘稠的眼神牢牢粘在安琪儿白色的羽翼上,他们一定都是想夺走他的小鸟,夺走他来之不易的幸福。这让戴维斯难以遏制的产生焦虑,他为安琪儿的房间装上深色窗帘,不让哪怕一束光穿透缝隙,觊觎他的小鸟。
但是被藏在厚厚窗帘下的安琪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来,白色的落羽在笼底积累了几乎一层,往日清脆可爱的声音仿佛从未存在过,它也许是哑巴鸟。
戴维斯不明白,猜想他的好朋友或许是生病了,医生说它需要回到他的家。多么荒谬的提议,这里,阿比盖尔庄园就是安琪儿的家。
也许只是太久没晒过太阳,它是在想念温柔的风,戴维斯抱着鸟笼来到花园中,安琪儿张开翅膀难耐的抖动了几下,那对漂亮的蔚蓝双眼再次迸发出光亮,它没事了。
戴维斯放下心来,安静的坐在亭子中,双眼一瞬不瞬的盯着安琪儿看,他的背后、手心都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终于,安琪儿试探性的走出鸟笼。
它好奇的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蹦蹦跳跳,用轻细的叫声表达它的喜悦。
在这个戴维斯终于安心下来的时刻,恰好有一阵春风吹拂,带来空气中花瓣的清香。树影交错间,安琪儿的一双白色羽翼完全张开,那双蔚蓝色的眼睛迎着阳光显得更加璀璨。
安琪儿向前,再向前,飞进无穷远的天空里去……
戴维斯追着小鸟飞行的轨迹向前奔跑,他喊着:你要去哪里!安琪儿!不要走!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我们约定了要永远在一起!!
安琪儿越飞越高,越过了阿比盖尔家厚厚的围墙,消失在庄园内目所不及的天空。而戴维斯还被困在在围墙内,没能跟随安琪儿一起飞向天空,他躲在角落里低声啜泣,他来之不易的幸福又离他而去了。
这都怪他,如果他不让人打开鸟笼,如果不把它带出房间,安琪儿将永远陪在他身边,这才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
在十二岁这一年,戴维斯的灵魂又回到阿比盖尔庄园这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他变得更加沉默,好像弄丢了某种情感,整个人显得麻木且呆滞。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某个时刻,他会用双手紧握住那张代表着希望和幸福的贺卡,祈求神赐予他只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安琪儿。
很快,在戴维斯十三岁那年夏天,他从许久未见的母亲手中接过一团柔软的襁褓,这个刚刚出生不久,皮肤白皙、双眼蔚蓝的婴儿正是他期盼已久的幸福。
戴维斯终于得到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安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