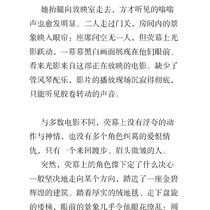
拍卖场不复原有的秩序。
爆炸的冲击震动厅堂已经种下了混乱的种子,但现场气氛的有效平复让人感觉似乎这只是一场还算能够处理的意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一切尚在掌控之中,也很快就会回归安稳。而随之而来的黑暗击碎了刚刚形成的短暂安定。
黑暗带来的令人能听见呼吸心跳的片刻寂静过后,噪音几乎与重新出现的光线同时在场内扩散开来——游客座席间座椅拖拽出刺耳声响,惊叫声、慌乱的啜泣,惊惶谈论的声音,物品碰撞的闷响……全部交织成混乱的杂音。
原本排列有序的座椅现在横七竖八地散落。有人不知所措地木在原地,有人从座位间挤开、试图在人群中撞开一条路向出口奔逃,有人被慌乱人群的推搡裹挟着前进,有人大声呼唤走散的亲朋,甚至有人不知为自保还是攻击抄起手边的器具……
再次初显混乱的场面间,领袖们下达着维系秩序的指令。瓦莱莉亚就近走向了一个略显拥挤,似乎即将发生踩踏的角落:人群涌向一扇紧闭侧门,又像颈部被堵塞的沙漏中无法流下的沙子一样堆集在门口。
“再挤前面就站不稳了,停下!”“天啊,我想出去……”“别过来了,这扇门是锁上的,让我们回去!”“你在做什么?说了这边没路!”“我的提包——”
瓦莱莉亚目光快速扫过环境,从地上抄起一只掉落的金属托盘,以盘底重重敲在同为金属制作的椅子脚上。她以极快的节奏连续敲了三下。
金属相击的脆响短暂穿透这片区域混乱的杂音、打断了慌乱的话语。有人短暂地停下脚步,有人转头,有人本能地后退了半步,原本失控的奔逃生生被卡住半拍。
“站住!停止惊慌,听指令有序撤离,只有这样所有人才能安全离开。”她趁这个瞬间高声道,“这侧的门目前上了锁,现在先退到座席区域,留出开门的空间。慢些动!”
人群开始缓慢地向后疏散,拥挤带来的危险暂时消弭。取来钥匙的侍者在门口区域被清出后终于有空隙上前,而在数名成员的管理与监视下,极少有还未冷静的人在门开时仿佛一刻也不能等般挤向前去,即使出现一两个不理性的人也会即刻被厉声喝止或动手阻拦。
待门彻底敞开后,得到管理的人群几乎是以正常的步速从这一通道离开了拍卖场。放眼对侧与后侧的门,离场的秩序也基本得到了控制。
原定向地表的撤离却远不似这样顺利。
突如其来的爆炸使佩尔洛斯陷入停摆,电力供应切断,回到地表的唯一通道——伊卡洛斯之翼也停止了运转。
瓦莱莉亚眺望着远处的电梯,城内自成一套的秩序、纸醉金迷的气氛令她如鱼得水,她已经有些记不清距离自己上一次乘坐伊卡洛斯之翼到达地面过去了多久。
她的目光经由巨大的金属框架向上掠过,逐渐没入浓郁得化不开的黑暗,思绪也随之短暂飘散……
瓦莱莉亚·卡拉乔洛在佩尔洛斯建立之初即前往此处,参与了加利亚诺家族势力在这座城市的产业转移与扩张。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像蛋糕在烤箱中以肉眼可见的速率膨胀一般美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争夺与冲突。
加利亚诺家族表面的光鲜得体之下,除却唇齿间滴水不漏的言辞、和善微笑间隐秘的利益交换,无法反抗的暴力也是维系地位的必要支柱之一。
瓦莱莉亚——这个名字的词根是valere,拉丁语中的“力量”,承袭自她母亲侧的祖母。[1]正如世代间承袭的名字,她的母辈无论职能是否涉及直接的战斗都世代信奉力量的作用,挑选的伴侣也均是家族中理念相近的成员。
她自小接受这样与光明世界不同却在实际运作中极为有效的、从秩序到理念的全套塑造,在母亲举荐下加入家族后成为优秀的“执行者”完全是顺理成章。地面上秩序最为动荡的几年,家族的意志就是他们掌控区域中最高的秩序,而她会在自己被分配到的位置执行好每一次任务。从看守赌场维护秩序、惩戒违约或背叛之人,到在重要场合中保护上级成员,她擅于且习惯以直观暴力达成驻守、开拓等目的,或协助善言者在谈话中形成威慑。或许名字寄托的寓意的确带来了祝福。她反应敏捷,又对环境中的各种细微变动相对敏锐,因此这一路线无往而不利。即使在经历成长、学会必要的收敛之后,她依然更偏好干脆直接的行事风格。
最初前往佩尔洛斯时,除了家族各项资产向地下的转移需要投入人手外,地表政局的重新稳定也令他们在地上的行动愈发感到处处掣肘。于是她走入“机遇之城”继续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家族发挥作用,血缘关系上的家人也在不久后举家前往佩尔洛斯并在此扎根,亲戚中甚至还有人成为了游客参观特供“家族据点”的导览者,或在酒吧对游客讲述故事的“退役打手”……
几年的蓬勃发展间,瓦莱莉亚对此处生活的认同感愈发深切。佩尔洛斯繁华的同时,她对地面也没有过多牵挂。这里有与地表并无二致的“人造太阳”光源调节,稳定的气温比地表更加舒适宜居;闲暇之余她偏好以热烈气氛刺激感官进行放松,而佩尔洛斯已是全凯维柯最纸醉金迷的都市,夜总会每项演出都足够点燃全场;她嗜甜爱酒,而地下恰好是私糖私酒的源头……那不勒斯裔重视家人,而她的“家人”们——无论是血缘还是家族意义上的——都与她一样为攫取机遇居于地下。她甚至并无地面上的产业需要关照。
但即使她本人极少乘坐,这座电梯的重要地位也不会被她忽视。
伊卡洛斯之翼如同一条巨大的血管,在地表与此处循环输送人员、资金、商品。好奇的游客从此处鱼贯而入为旅游业贡献资金,走私商品从此处悄然流出,非法资金经由操作不断被从合法产业输出……这样的循环供养着佩尔洛斯,日复一日,未曾止息,以至于习惯它存在的人难以想象这条通道的阻断。
而现在它发生了。
片刻追忆后,瓦莱莉亚将目光从这座罢工的巨大框架上移开。在这片突然降临的黑暗与混乱中,还有太多事情需要有人去做。
[注1]母亲侧的祖母:意语父母方的母亲都叫nonna,要区分父母方可以加形容词materno(母亲的)感觉听起来比加个“外”亲近一些遂直译,拗口致歉





她释散感知,遂说黑日下的空气如化鲜活;它将如棘刺般锐利,然而柔和胜过丝绸。你万莫要将光华接纳,使之埋入骨肤。
以斯玫尔各,鬼爪化自乌指的末处;自气流最轻柔的振颤为端,牵扯出密织而浓稠的无形罗网。
夜长旦寡反而令人心知:无处不黑夜,无处不埋惊惧的密藏。然而,黑日的光华只令昼夜模糊、朝夕相类,直到人颠倒晨昏。于是过往的潮水逆流而上,侵吞了每一刻如今。
·
何必追忆在漫野上疾奔的骏马,乌黑的毛皮却在阴郁的乌云下如旧烁光;旧昔的族长手臂稳健有力,兽皮鼓上,三挥重槌,众马归栏。
长青·石是老辈里族长的名姓。她在草原上的帐篷满挂坚实的兽皮,冬时,风霜的侵蚀痕迹便在夜火之中被照显,而兽皮下的图腾也因此染上炽烈的颜色。
塞恩娜曾在长青·石的帐篷里,将图腾的纹样沉默里观摩;她不记得第一次看见这些纹样时,是否曾辨析出那些涂料之下的含义,但她记得自己透过这些厚重的色彩,心慑于万物有神。
于万物共生的野性土地上俯瞰或仰瞻——长青·石娓娓道来,在许久的年岁前,天穹都为明光所布满;在暖夜的篝火旁侧击鼓,齐时,每一颗烁亮的星子都将庇佑我们的族人。
夜里,塞恩娜曾于梦里的山丘看见神祇的影张弓搭箭,有飞空的流矢化作天星。
醒来的白昼,长青·石朝她点头,随后带领着她走到了另一片明亮的夜里。长青·石在前方引导着塞恩娜的行步,二人的足迹并未被岔路分歧;但路径却愈发陌生。尽管,长青·石的背影还尚且明晰,塞恩娜却不再感到踏足草野的自在。天云与土壤都与她根绝了联系。皮履是甚少会发出脆响的,但塞恩娜听得的足音,似钢铁敲击石面。她这才注意到柔软的草地被光滑的大理石所替代,屋厦齐整,无有一处留下过风霜侵蚀的痕迹。而长青·石的背影还在街巷里穿梭,直到高墙畔侧,能够望见天穹的所在。
塞恩娜,长青·石的背影说到,你必将亲睹到天穹诸星。长青·石的手杖指向其上,余光里,塞恩娜感到天穹云拨。
但待塞恩娜抬头,众星的光华骤尔迸裂,掷碎成漫天的宝焰,烧焚到底,只徒有将万籁照得匿销的黑日轮。如同在晨露未消的草原上陡然烧起野火,留下的浓烟、黑尘,挖空般的焦土。
这不曾引起塞恩娜的惋惜;在抬头窥见虚天的齐时,她了然了幻象作祟的真知。这片福佑的天星本当在无边漫野之上升起,长青·石的手杖在泥土里画下即兴的图样作为指示;真实的过往与虚影已然泾渭分明,裹煤的白纸难以充作繁星。
·
何必梦回,梦回到温暖的壁炉旁侧,木碗里盛入肉羹。狼女叼走雪中小兔,却不曾是为捕食。
潘多拉的听觉自然明锐,早便捕捉到了遥远的私语。起初是无数相攒的,不成语句的话音,渐渡到人言的语句,到最后,她甚至隐约感觉像故乡的语言——即便狼人的“故乡”常常只是一处偏僻的屋居。这往往也意味着更多,更熟悉的气味,通常也提供更充足的信息。
但轻微的迷惑与警醒也难以避免;因为帕维纳的城池并非潘多拉的碧眼狼群所居。对于如今的孤狼来言,去分辨假意熟悉下的威胁,她早已熟稔万分。
潘多拉的眼是如碧玺般绿,将隐晦的刺探裹覆得完美;凭虚,她看见不该再来的故人。
未知这样的迷惑会致使多少人的困扰,只知这不会是潘多拉的心头疑虑。血仇的余烬难免不断扬起,如今,这早已不因斯人已去的梦魇;在旧昔的屋居被富裕但恶戾的旧雇主摧毁后,潘多拉欲望追索的报酬,早已不再局限于一方小室。
她誓愿如此,如今才坐拥了真珠宝玉。
帕维纳的异景张开怀抱,所供无非是假意温情;商品既在,潘多拉清算了银财,随后否认了对方的价值。如果当真有哪位路过的行客花费时间在此中沉湎,潘多拉将用相同的时间赚取遂她所愿的真金白银,或焦烧的恨火柴薪。
她随后径直前去,与母亲般的假象错身;她们的身量自潘多拉成年后的许久里,似乎都相差无几。
随后低语的光影也即刻消逝了。
·
何必追忆那辉煌的旧日,因你如今所达及已然远胜曾经。只是水晶悬灯总抛出繁复的纹路,空中的埃尘也被染作琉璃浮屑,难免引目。
厅堂里,旋梯上涌动的血液,自难窥的楼顶不断流淌;汇聚到最后的台阶,涌动成一具人形的模样。这片人形尚在喃喃维多利亚的过去与未来,只字不提如今;贝拉信手捉提起镀金烛台,去照见人形的面目,照见她朦胧的神情、他模糊的语调、它不绝于耳的话音。
她只是好似耐心地倾听。于是血衣人形更加靠近;每是相近一步,人形皮相的枯槁便褪去一分,最后,破碎的血衣化作晚宴的礼裙,这堡中琳琅也齐齐显像。
此刻便将能够看出:维多利亚的辉煌过往,与贝拉所拥有的,内中差异,于微妙处甚多。然而,也无有其它的观者能够证见这意料之外的不同;独惟古旧的血流默然知,维多利亚的族名曾经短暂沉寂——直到贝拉走出那时难免的蛰伏。
旧貌相叠——但贝拉却笑把它召来的景象置无所顾,挥开、折断了血泥人像的手臂,将满室的琳琅斥作废土。
何等、何等,如此险恶的暗喻;但贝拉的面色不见丝毫忿怒,只有手中的猩红蜡烛不断溶烧,烛泪都滴入枯槁人形的心口;最后的余火与蜡,将尸的唇舌也紧密封上。尔后,贝拉将烛台蓦地砸弃,顺势里,尖锐的长甲将腹腔剖。
我亲切的、失落的、啃噬殆尽的,
我的劝诫你须得详听:我创造过太多如你般的残躯,将死但尚且知晓哭鸣;已枯萎的,便毋用再虚耗着缠缚土里。
·
以斯玫尔各的指尖时或现显幽光,彼时,每一个行止都更精妙与郑重。今下则如犹剥离着血织密网:人身肤里的深红脉络。随后幻瘴便如遭遇了剔骨,浮动的黑光化软,劫灰般流散消弭。
从最伊始,围绕以斯的黑光已必被捻提。它无人可化,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