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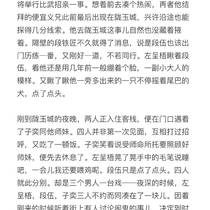
-古来白骨无人收-
江湖门派多聚众,张竹之不喜欢,金钱卦门主是个风流嗜利的人,他也不喜欢。当初来金钱卦时门主抬眼扫过他,只丢出来几枚铜钱,便又回去玩自己的筹码。从模样上看不出门主的年纪,后来才知那人竟小自己几岁。张竹之不由哂笑,合着自己真成了块烫手的货,大当家宁愿丢他去茫茫人海也不愿再带到身边。
当然、如果只论外貌,他看起来年纪要更小,内敛又谨慎,不似吃酒人豪迈、不似红妆女多情、当然也不像裴门主那样浮浪又轻佻,如一桩死木杵在铺子中,整天只有数目在脑袋里过,过来过去成了条蜿蜒的河,奔向万丈深渊去。一时间竟回不了故地、入不了新门,又难寻一处可归或一处愿归。但凡见门主就要对上裴云非那不拘礼节的装束,赶不巧还要往赌坊求见,听着幺三五六的牌。本来张竹之就烦来赌,如此这般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也怕鬼敲门,可躲来躲去还是惹了酒中仙一位,凡事多有此人添堵,一两年下来竟成了惯例。这时距刚入门也有近十年了,江湖早忘了张总账血洗河巷几多无情,只见得市井中一家小小典当铺,几个愚笨伙计,一张长桌案、一台砚、一把算盘、几本账。
大当家叫他忍,忍到他人只当自己是被拔了骨头的兽、胆敢探身进蛇洞,再一口咬住那人喉咙吞吃入腹。只是说这话的人久病在前,自己再起只怕要往后,还要忍吗?这话张竹之不敢问大当家,只怕对方再说些什么惹自己来气,心不在焉听大当家讲商行的琐事,这家生娃那家结亲、张三打架李四骂街,讲到后面张竹之又想起来黄七,很是可惜没留着那人活口,还能多敲出来点东西。大当家见他心思不在谈话里,话锋一转提起云舫拍卖,问张竹之如何能笃定有人来买、毕竟买卖矿场兹事体大,不少人都要细细考量再来一举拿下,张竹之此行只在楠栝州留三天,又如何见得交易后的蛛丝马迹。这般前因在右诡那儿,张竹之得了青楼主人的消息,他在东临州的几天确实有两派人盯上了铺子,一行人使窃贼盗走账本、另一行人只是四处打听典当铺,不知用意为何。他没对大当家提起这些,心中已有打算,明知大当家不同意便擅自瞒下来。
“…虽说谁来买卖都有回还余地,但两者行事云泥之别,你就放心那豪族能给你办妥?”大当家非他能左右的人,多少有所察觉,“有这笔钱的人,在楠栝州也能数出来了,对上哪一位都不省事啊。”
“我猜是新瓶装旧酒,”张竹之道,“既有我这番计策,也该有他们的对策,拟一个外来的富贵人有何不可?”
“这不更是难上加难。”大当家无奈笑出声了,“好,你不想说便罢,我和子期在谋算上……是从来不如你这个徒弟。”
二十来年前,张竹之还在生养他的村落里。村子以务农为生计,从南到北都是大片的田地,多数种的是麦粟米粱而仅有少数几户能饱腹,只因当地多数田都要从商户手中租来,每年交付租金或以粮食抵押。原本家家户户都是种田吃饭,交一部分给朝廷赋税,留一部分熬过来年,剩下的也实在卖不出多少钱了。可自昭月年末昭明年初来,朝廷征用壮丁充军,服徭役者十死无生,老幼无力劳作只堪堪种出些不足饱腹的米粟,又有商户一口咬定村民无力交租,强夺走一年的收成后自建粮仓,囤货居奇。才过初冬村子中饿死冻死者无数,曝尸荒野。
张竹之生在的那家同样穷苦无力,上有老人天年下有儿孙五人,他是家中老三,不及年长的有力也不如年幼的看着可怜,赶集时被母亲扯到集市上卖,卖去一家典当铺子做苦力。原本那铺子不缺人,但看他长得白净相貌精明,价格又便宜,寻思做伙计也是能装点门面的,花几两银子领走了。几两银刚够交付当年的田租,张竹之心里清楚,生父母只是为家里少一口饭、也多一年的粮。
实则往后的日子他也吃不饱饭,典当铺那主人家吝啬又小性,整日无事生非克扣他的饭食。这么挨过四年,集市门口来了位老者摆谱,占着正路中央下棋,约定别人赢一局就给一锭金子,输了什么他也不要,便有好些人跑去看热闹。张竹之不想回铺子里挨打,蹲在旁边看了半晌,自觉学会了就说我想试试,被人起哄着推坐到老人对面。起先三局输得很快,老者也不着急,还为他讲解棋理,而后三局对杀焦灼,竟磨到傍晚仍未见分晓,老人叫他先回去、翌日再来对弈。那一晚到店铺中,主人家非但没动手反而找出几件好衣裳让他穿,又摆一桌丰盛菜肴,张竹之便心中了然,多半是老者的身份不同凡响,这家人想靠他巴结上对方。二回坐到棋盘面前时天刚蒙蒙亮,老人来得更早,叫他先手执黑,两人又对杀至夕阳照晚,以老者连输三局收场。
自那以后张竹之就不回典当铺了,老人领他往城中繁华酒楼去,见两名青年一人举止轻狂一人温和有礼。老者推张竹之去那如玉般的人跟前,说这是你将来的师长莫子期,他与师父相识便是这番缘由。之后陆续了解到商行最早乃周姓一家建立,少当家周辞的父辈因故逝世便由名为倪古的拜把兄弟打理。领张竹之到商行的老人是倪古,而倪老寿终之后周辞也顺理成章坐上大当家的交椅。
起先拜师的内容张竹之忘得不剩多少,依稀记得倪老对师父说过,让师父正他棋风、立他心骨。因而尽管练剑的事不了了之,但念书习礼还得继续。出了大当家的院门,张竹之就把寒暄内容忘了大半,大约因周大当家聊了两个时辰里有多半内容都是家长里短,听完直往耳朵外面飘。他见门外伙计迎面撞上后神色惶恐,隐约想起辞别前自己说了什么,让大当家一时愣怔,又苦笑不言。
当时大当家叫了师父的名,他怎么答的?张竹之想来一阵,想起自己说师父不是不如他,只是不用那些伎俩。
许是那几年师父眼看练剑不成,忧心他郁结在此便每天留些时间同他下棋,从结果来说是他输多胜少、顾头失尾。下棋的事随日后波诡云谲不了了之,再见到那副棋具已是师父离世一年,张竹之背着满身血债,竟不敢碰这些晶莹如玉的棋子。河巷的账从倪老还在时算到了二当家离去,共计死伤百余人,有藏私卖信的商户、收钱放人的打手,上到祠堂里坐交椅的元老下到弄堂里跑腿的小厮,仿若有人在商行里织了张天罗地网,凡有干系者非死难逃。起先人们说他杀孽繁重神佛不收,后来便暗自庆幸没贪图别家给的好处,到现在、记得张竹之的人很少了,少得连他找大当家都要被看门的拦,叫人哭笑不得。
现在看门的瞪着眼睛目送他出去,见人上了马车不往来处走,反而驱赶向城郊的位置,再转头看屋里的大当家早已躺下打盹,哪还有留心这人的去向。楠栝州山野里曾建几处庙宇,其中一处临水而立,庙中立一高大的银杏树,每逢秋季漫天碎金。本就是临别楠栝前与故人告辞,马车出了城郊直往驿站与走货汇合便是,张竹之心下想了想,还是叫车夫去寺庙一趟,又怕身边的阿伽利叶带着血煞之物惊扰僧人,便把这贴身的护卫留在车上。山中走几十台阶就能见庙门,有僧人在门前扫洒,张竹之上前见礼跟着进门参拜,上过几次香,到庙后庐舍喝碗茶。僧人说他不像特意来为人祈福,张竹之应下说是,问山中不见福祸、怎知他来求何?
僧人道:“来人所求大都如此,生老病死。”
张竹之哑然,才想起就算是常人家里,求神佛也不过为荣华富贵、为生平顺遂、为久病得医、为死者安息。
下山路上天色渐暗,僧人送他盏灯笼以免夜黑踩空,果真行至半路天边只剩一线金红,黑云惨淡飘摇数立,透过重重山林只看得影影绰绰些许,金光如豆粒粒下落,再过几个弯就全然沉落山中。还不到山脚,张竹之闻到血气飘来,手中暗暗夹了铜钱在指缝,又握住腰边的刀。敌暗我明总不算好局面,他想要不先吹灭灯笼,可没了亮光自己才更无力,便一路警惕着走下去。路旁山坡里传出窸窸窣窣几声钻出来个浑身褴褛的人,身上多处枝条剐蹭的小伤口,看样子是阿伽利叶也顺着光来找人。野崽见他后反复绕了两圈,确认无事又莫名凑到脸边舔,叫张竹之骂也不是,只能强推着人抗拒。
到山脚清点过尸体,发现来人不过两三位,车夫还好端端躲在轿子里,大约是丢石子探路,对放也拿不准他的行踪。念在事出在佛山脚下,张竹之双手合十道声阿弥陀佛,叫阿伽利叶把刀上的血迹擦了继续赶路。
“去东临驿站,飨水滩那边就算了。”张竹之对车夫道。
车夫是自家人,立马转了路,又忍不住问:“水路的几位可要通信……?”
“不用,他们自会安排,”张竹之发出声嘲弄似的笑,“瓷器玉器都运过几回了,难不成离了我就不能动弹?那养他们作甚。”
车夫没说话,自己擦了把汗闻闻草药包提神,琢磨着路上应不得安生,再赶路时得把脑袋栓牢了盯稍。楠栝州到别春州的路有好几条,两州紧邻交界处是国都,不能直行,而西王州地险人疯,非必要不走,剩下只有走东临州的陆路和从飨水滩出去到界石岸的水路。水路拿来运货极好,除却风浪一路上无山匪劫货也无重重关卡,上岸便是盐贩聚居处鱼龙混杂。而陆路看似临近却危机四伏,车夫不敢托大。早年只做放贷门路时,张竹之偶有一天想起东临州农庄上的生父母家,收了几家的抵押货物后孤身去村落里找,四处打听却没见踪影。
当地人问他家中种植何物,说不准是田野大多相同,他记错地方了。张竹之仔细回想发觉自己早忘了田里是什么作物,连生父母的姓名模样都不怎么记得,只记得离家前有次年节风雪载途、一路冻骨,家家白幡吊丧,可谓哀鸿遍野。这事不好去烦扰当地人了,张竹之反复思索,愈发觉得乏味,正要离去时见到跑了几个月的老赖正在路中等他,身边跟着个白净又寡言的小孩。那人说用着孩子抵债,将卖身契一起送来,张竹之本不愿收下,但那孩子直勾勾盯着他,一时间没推辞老赖那死乞白赖的行径手中就多出薄薄一张纸。
小孩不会跑,老赖人都没影了还在原地站着。张竹之茫然之余想到,如果小孩跟他去商行没人照顾、去没开起来的店里还不够做苦力的年纪,带在身边的话自己只顾奔波、更是无能为力。两人在路边一大一小傻站着,张竹之拉着孩子在村中转两圈,仍没找到生父母家在何处,小孩自始至终也不说话,跟在他身后当尾巴。说起来自己那家店开起来,应当也是一家典当铺,典当铺里不可能再需要个白净且沉默的小孩。
“…你想去哪?”张竹之蹲下来问那孩子。
小孩仍不开口,显得有些木讷。
“跟着我也不好活命,”他猜不出自己是什么表情,没有面对孩童的经验,自顾自说下去,“山有马匪,市有奸人,我这条命现在可很值钱,捎带你一个也不多。”
卖身契末尾写着小孩的名字,上面有生辰八字和画押,张竹之看小孩姓安,不似普通人家的名讳,但此时腾不出心力往下追究了。一张纸折四折,里面的出卖的钱两被他抹掉,放到那小孩怀里,又掏出自己的盘缠数了数,拿出一串钱给这娃娃。
“那混货卖得真是便宜。”张竹之嘀咕了句,指了指契书,又指了指钱串,“小孩,要是有人盯着你的钱、你就跑,要是有人先拿卖身契,你自求多福。”
“……要是运气好,碰见个善人,就好生去过亮堂日子吧。”
当时的情形日后回忆也如梦似幻,记不真切,张竹之记得卖身契上写了什么,那小孩的模样和村子又如父母的踪迹一样没下落了。行车到东临路上,半夜抵着车轿打盹,似乎又回到那个绿汪汪的山间,山重水复都似故景,怎么都找不到相识之人,他记得接下来去田边问农民,问了又走出几里,折返回村口,村口有个嗜赌如命的脏手货,整日卖拐走失的小孩。他历来不收那人拐的孩子,当天不知怎么,被强塞着拿了一纸卖身契,又丢下小孩平白销一笔账。正当他往后寻索,车前有人高呼救命,张竹之猛然惊醒看到阿伽利叶反身抵着轿厢掏刀出去,轿子外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人厉声惨叫。车夫大约也抽了刀,满口家乡话骂骂咧咧的,喊着什么丢你老母的这下得罪主家,马车如离弦之箭飞奔出去。
掀开轿帘看见身后几人黑衣,夜深清点不出人数,张竹之飞去铜钱竟打到了人,便清楚非实力强劲的。马车疾驰时铜钱打灭了灯笼,车夫没看见似的仍在赶路,听见身后一阵叮当作响,夜色里一卷云帘珠挂翻到车轿顶上,心下清楚主家已经醒了。两边夹道树林,的确是埋伏的好地方,若非经验富足的人叫这群蛮匪拦住一次便再也走不动路,哪怕脱身后看这些林子也似鬼影重重,车夫捏了把汗接着策马,还是不敢问主家到底惹上什么祸事。
“刚才什么情况?”主家先开口问。
车夫想了想道:“路过一山口,山上有人拿绳标钉轿子,还好跑得快没钉上,后面就有人来拦车了。”
“没用铁蒺藜?”
“主家您这话说的!”车夫又气又笑,“要是用那玩意今儿我们就别活了!”
张竹之沉吟一阵,觉得不对:“这条道今天先有别人走了。”
“啊?”车夫认为不可能,“这个时辰走夜路?”
话就没往后说了,张竹之记得右诡给那两派人的评价,一派做事毛糙急于求成、一派暗中试探鬼鬼祟祟;以他猜测前者属商行内人士,意在等大当家过世后迅速取而代之,而后者最可能是西南商会的人手,果真一直暗中掣肘,才会在他要卖了矿场时动手。然而不论哪一方先派人跟来,都没道理替他撤了铁蒺藜,难不成还有人跟踪?张竹之想不出结果,叫车夫先去驿站住店,第二天天亮就启程。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