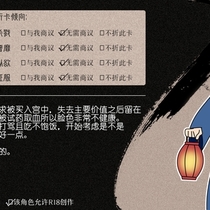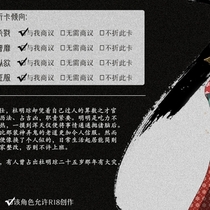中之人被毕设拷打已经不行了……先这样吧()
我们大女人就是要狠狠花钱干大事,用石奢靡折出金奢靡的气势!
虽然关联了好盟友但是只有两句话戏份(喂)
——————————————————————————————
承和十四年的冬,来得又早又猛。才过立冬,寒风呜呜地卷过东都的宫墙檐角,带着细碎的雪沫扑打在司天台临时官署的窗棂上。
杜玦裹着一件半旧的披袄,指尖在一张巨大的星图上缓缓移动。烛火在她沉静的瞳孔里跳跃,映照出图上几处异常黯淡、甚至隐隐有断裂之势的星轨。这些星轨正对应着京城方向皇陵所在的龙脉。冥虚子的侵蚀,加上此前一连串的动荡,已让这条承载着大烨国运的命脉,出现了清晰的裂隙。
“修补……已经行不通了吗……”杜玦低声自语,声音在寂静的室内荡了两个来回,消融在窗外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雪声中。思来想去不知过了多久,烛火噼啪一声灭了,杜玦才惊觉自己已经犹豫了这么些时候。一片黑暗中,杜玦感受着自己鼓擂般的心跳,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二日的朝会上,当杜玦呈上要重修皇陵的奏疏时,满朝文武皆是一静,随即哗然。并非反对重修皇陵,而是杜玦提出的方案近乎于重建了一个新的皇陵,并且更靡费,更铺张。“以白玉为砖,赤金勾阵,七宝嵌星……”工部的老臣义愤填膺,就差指着杜玦的鼻子骂她实乃乱臣贼子,“杜监正!国库空虚,如何经得起这般耗费?”
杜玦立于殿中,神色不变,目光越过众人,直接看向监国的豫王。“殿下,”她定定地看着对方,眼中是十成十的自信,“龙脉若崩,则国运散,届时亿万生灵涂炭,岂是区区金银可比?此非耗费,乃是投资于国本。唯有以金石之坚,引星力之锐,方可速效,救我大烨于水火之中。”
杜玦的话语带着一种坚定的、不容置疑的信念。豫王沉吟良久,最终,在为了天下苍生的大义与杜玦过往确有其事的成就面前,点了头。特旨允准,一切用度,皆由杜玦统筹,只是不许触及大烨民生之根本。
旨意一下,杜玦便不再理会朝堂的纷扰。在国库之外,她还动用了自己杜家累世的积蓄,金银珠宝被毫不吝惜地兑换成她所需要的物资。白玉从千里之外开采,马不停蹄地运送到对应的位置。再由经验丰富的石匠开出沟槽,灌入熔化的赤金水。各色宝石被最顶尖的匠人日夜打磨,镶嵌成繁复的星图纹样。
期间杜玦亲自赶往京城皇陵旧址监工。昔日的庄严肃穆已被一种近乎狂热的工地景象取代。大雪纷飞中,民夫呵着白气,喊着号子,将巨大的白玉石材拖上预设的基座。匠人们在临时搭建的暖棚里就着灯火,在石材上凿刻出分毫不差的线条。杜玦穿梭其间,深色的袍角沾满了泥泞与雪水。白日校验星阵方位是否精准,阵纹是否流畅,夜晚继续观星象以推算玉石对天地灵气的感应是否达到预期。
一日,她正立于风雪中,监督着主陵室穹顶最后一块嵌着夜明珠的玉石封顶。那夜明珠硕大无朋,据传是前朝海外贡品,被杜家收藏已久,如今也被她毫不吝惜地献出。工头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上前禀报:“监正,东南角那块玉石内里有一道极细的裂纹,您看……”杜玦抬手止住了他的话头,向他所指处看了几眼,淡淡道:“裂纹没有干扰到玉石对灵气的感应,放在那吧。”声音在风雪中显得有些飘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她心中默算着工期,任何一点延迟都可能意味着龙脉的进一步溃散,意味着她推演时机的错失,接下来的观测不容一点错失。
楚方圆曾托人从东都捎来一封信,信中提及朝野对此工程的物议沸腾,文官们痛心疾首,称杜监正一意孤行,穷奢极欲,动摇国本。杜玦在摇曳的烛火下看完,嗤笑一声,随即将那信纸凑近灯焰。火舌舔舐着纸张,将她眼中的最后一点光亮也映得明灭不定。她提笔回信,笔尖在寒冷的空气中逐渐凝滞,留下几个不甚优美的墨字:井底之蛙。
冬月最寒冷的一个子夜,皇陵地宫核心的周天星斗大阵终于彻底完工。巨大的白玉阵盘铺设于地宫中央,赤金浇筑的阵纹在黑暗中自行流淌着微光,七色宝石依照星宿方位熠熠生辉,似天穹水面倒影。四周与穹顶的白玉墙砖光洁如镜,映着阵盘的光芒,仿佛将整片星空都收纳于此地。
杜玦屏退了所有工匠与护卫,独自一人,立于阵眼核心。地宫内寒气刺骨,呵气成霜,她却仿佛感觉不到。她闭上双眼,将全部心神沉入与遥远星空的感应之中。外界风雪的咆哮、朝堂的攻讦、那如流水般耗尽的杜家私库……一切杂念皆被摒弃。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头顶那片真实运转的星穹,与脚下这座倾尽财力物力构建的人造星宇。若是测算不错,今夜子时星阵便可顺利开启。过了不知多久,杜玦只觉得自己仿佛要消融在这两片天空中时,突然听到一声异响。
“呼——”
一阵风从地面处打着卷席卷了整个地宫。被吹拂到的阵盘上的宝石逐一亮起,赤金线条光芒大盛,变得灼热。白玉墙壁仿佛活了过来,微微震颤着,将地脉深处那股紊乱、衰颓的气息强行吸纳、引导,经由阵盘的转化与放大,化为一股磅礴而稳定的地气,如同一条被唤醒的巨龙,轰然注入那受损的龙脉之中。另一边京城内,太玄子那庞大的树身在寂静的冬夜里无风自动,发出一阵沙沙轻响,原本有些萎靡的枝叶,肉眼可见地重新挺立,焕发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生机。
就在龙脉被强行稳固,国运为之一振的瞬间。
“咔。”
一声清脆的、如同玉石裂开般的声响,在寂静的地宫中格外清晰。杜玦紧张地四处环绕了一圈,见各处并无异常,她突然恍然大悟般低下头,从怀中取出那张已然碎裂成两半的奢靡卡。冰冷的石制卡片断口整齐,映着阵盘流转的光芒。她看着断口,脸上缓缓勾起一抹笑意。随手将断裂的玄铭灵牌丢弃在冰冷的地面上,杜玦转身,毫不留恋地走出地宫,将那座耗费了无数金石、凝聚了她一月多心力的崭新皇陵,留在了身后风雪呼啸的山峦之中。
外面雪下得更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杜玦拢了拢早已被雪水浸湿的披袄,走向远远迎上来的随从。随从赶忙撑起油伞,为她遮挡愈发密集的雪花,低声道:“大人,楚大人从东都赶过来了,正在住处等您。”杜玦微微一愣,轻轻嗯了一声,被冻僵的脸上跟着不自觉漾出一丝笑意来。
过了中秋,仍带着夏日余韵的热风中已经染上了几分凉意。枯黄的树叶随着秋风卷下,在石板地上摩擦出轻微的唰唰声。一片小叶顺着半敞的窗户轻轻溜进室内,落在案几上。杜玦指间夹着一根算筹,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母亲的最后通牒言犹在耳——“不成家,便安心回来,司天台不是你该待一辈子的地方。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官做到三品还不够吗?也该为杜家传宗接代。”阻碍她观测星宇、推演规律?这比陛下天马行空的难题和玄铭灵牌都更让她难以忍受。思及此,她有一个计划,一个能一劳永逸堵住母亲的嘴,且绝不干扰她自身研究的绝妙计划。
时值季度交接,玄铭灵牌造成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官吏大量流失,杜玦趁机向太玄子讨要了司天台可自行寻找人才的特权。一时间民间凡是在算学观星二事上有天资之人通通被吸纳进了司天台。契机出现在一次枯燥的公务交接中。这次来汇报近日观测结果的是新来的司丞,杜玦记得这个与自己志趣相仿甚至自带了观星仪器入职的女子,楚方圆。她着一身半旧青衫,洗得略有些发白,却浆洗得十分整洁。未能被发绳束住的碎发散落在眼前,透过间隙看得出此人眉眼清润,不知为何姿态却像是正在压抑着什么。
总不能是要一刀捅死我这狗官。杜玦自嘲地想了想,将桌面上的星图略推开些,示意对方上前。公事公办地交代完,杜玦本以为对方会如常人般寒暄或告退,却见楚方圆捧着发放回去的卷宗,目光已被其中一幅失传的《璇玑图》拓印牢牢吸住,指尖不自觉地临摹着其上繁复的星轨,口中喃喃:“此图标注的赤道偏移,与现行算法竟有三分之差,是因岁差未计,还是观测基点不同……”
那一刻,杜玦脑中灵光一闪,她开口打断了楚方圆的沉浸:“楚司丞。”
楚方圆蓦地回神,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未褪尽的思索迷惘,下意识地应道:“大人有何吩咐?可是此卷归类有误?”杜玦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以一种志在必得的认真表情问道:“我急需一位名义上的婚姻伴侣来应对家母,以继续我在司天台的观测与研究。我知道楚司丞志在星宇,应是同道中人。我,杜玦,司天台监正,可为你提供查阅禁库秘藏、使用观测仪器的便利。若是仍觉不够,我姑且可以称得上是陛下的宠臣,略有自信可以举大烨之力搜寻你想要的典籍。你我合作,各取所需,如何?”
这番突然其来的提议,让空气瞬间凝滞。
楚方圆明显怔住了,瞳孔微缩,这完全超出了她熟悉的任何情境范畴。但下一刻,她那习惯于处理未知信息的头脑已开始下意识运转:利弊、可行性、潜在代价……她的目光扫过杜玦案几上堆积如山的星图与算筹,那里有她梦寐以求却无缘得见的前人笔记。在当朝,平民出身意味着她不依靠权贵便几乎没有上升的可能,甚至当前的一官半职也可被轻易夺走。若能借此直接便捷地接触到那些典籍便再好不过,更何况这位杜大人还位列点卯之册……
楚方圆没有像杜玦想象中那样表现出羞赧或愤怒,反而认真地像是在解一道难题。她谨慎确认道:“杜大人之意是仅表面婚姻,人后仍然是同僚?秘库典籍,皆可借阅?若是我说……想借杜大人玄铭灵牌一观呢……?”
“自然。”杜玦怔了一下,点头,“玄铭灵牌也可给你研究。”这句话成了压翻天平的最后一颗砝码。对知识的渴求和玄铭灵牌的好奇瞬间压倒了一切世俗考量。楚方圆深吸一口气,眼神恢复了清明与坚定:“既如此……楚方圆愿与大人合作。只是细节需约定清楚,以免日后纷扰。”顺利达成合作,两人立即在官署存放卷宗的偏厅内迅速敲定了这桩婚姻的所有条款。居住分区,财务独立,人前表演的尺度把握以及楚方圆所能调阅资料的范围。甚至于出乎杜玦预料的,楚方圆同意她利用自己折卡。
于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婚姻震惊了京城。权倾朝野的司天台监正杜玦,竟与一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吏缔结百年之好。一时众人对这二人的地下办公室恋情议论纷纷,话本子一连出了数刊对二人恋情的大胆推测。
婚礼定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吉日。杜府张灯结彩,红绸一路从门口铺到楚方圆的临时居所。宾客盈门,仍在京城的文武百官多来道贺,好奇、探究、祝福的目光交织在这场堪称离奇的联姻上。杜母虽不甚满意楚方圆的出身,但好在杜玦终于成家,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她看着不远处正在行却扇礼的二人,与杜父相视一笑。
楚方圆身着繁复的花钗礼衣,黄金宝石打造的沉重头饰让她有些不适地微微动了动脖颈。她平日疏于打扮,此刻薄施粉黛,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出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清丽。杜玦则是一身大红翟衣,金线绣着的翟鸟纹衬得她平日里熬夜以至于总是疏离而冷淡的面容也多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暖意。她难得地没有在思考星象,而是按照礼仪官的指引,完成着一项项繁琐的仪式。
“饮合卺酒。”喜娘端着托盘,笑容满面。
两人各执一半葫芦制成的酒杯,注视着对方一同饮尽。杜玦的动作流畅而标准,楚方圆则稍显生涩,但她学得极快,目光低垂,配合得天衣无缝。酒液微辣,带着一丝甘甜,滑入喉中。
“结发礼。”又一声唱和。
喜娘小心地剪下两人一缕发丝,用红线缠绕,装入锦囊。杜玦看着那缕属于自己的青丝与楚方圆的缠绕在一起,目光微动,这种与某人就此绑定的感觉此时并不讨厌,反而让她的心里慢慢漾起一丝暖意。楚方圆则看着那锦囊,下意识地思考起在特定时日举行这种结发仪式是否对应某种特殊的契约星象。
待所有的礼仪终于完成,闲杂人等退去,新房内只剩下她们二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和烛火的气息,一时寂静无声。喧嚣过后,这刻意营造的温馨氛围反而凸显出一种微妙的尴尬。毕竟除了官务上的往来以外,她们对该如何独处实在缺乏经验。
最终还是杜玦先打破了沉默。她抬手替楚方圆摘去义髻,再挨个除去那些沉甸甸的首饰。“辛苦了。”她说道,语气是她惯常的平静,"虽然现在说这个有些冒昧,但是能否趁着洞房花烛夜一并将纵欲卡折断?”头上轻松不少,楚方圆也跟着松了口气,但听到杜玦的这番话,她还是愣了一下。如此的开门见山……
"当然,现在还不急。但纵欲卡还是尽早折去为妙。或许我们可以借房中术验证‘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之说与星象的联系……”杜玦将茶杯推向对面,为二人各斟了一杯清茶。两人对坐饮茶,窗外依稀还能听到前院隐约的喧闹,更衬得室内一片宁静。红烛噼啪作响,光影在两人身上摇曳。也罢,正好可以趁机研究玄铭灵牌。日后再说更是徒增尴尬。楚方圆暗中为自己开解一番,闭一闭眼,道:"那就全凭大人差遣了。”杜玦失笑,看着她这副严阵以待的认真模样,先前因为仪式而起的一点微妙情感也随之淡去。有这样一位聪慧、清醒且志趣相投的合作者,比应付一个期望她成为贤妻良母的古旧伴侣要省心多了。
杜玦唤侍女们将数张毛绒绒的毯子铺在那格没有糊窗的窗子下面,又搬来矮几和笔墨纸砚,紧接着屏退了所有人命她们一概不许进入后院。
"这扇窗是专门留作屋内随心观测星象之用,不料今日倒用于此处了。”杜玦挽着楚方圆的手坐入毛毯中,一手摸出玄铭灵牌,一手便开始脱去衣物,"我对房事只有一些理论知识,要是感觉不舒服就告诉我。”矮几上,笔墨纸砚与那张岩石纵欲卡并排而放,旁边甚至还摊开了一卷标注着经络穴位的星图。清冷的月光混着烛光洒在铺着厚毯的地面上,也洒在杜玦逐渐裸露的肌肤上,泛着象牙般细腻的光泽。
楚方圆看着杜玦动作利落地褪去外袍、中衣,直至只剩一件素色里衣,不由得微微屏息。她努力维持着研究者的心态,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随那流畅的肩线、隐约可见的锁骨,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几分。她深吸一口气,也依样开始解自己的衣带,手指却有些不听使唤的微颤。“先从……观测气息与星位对应开始?”杜玦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她靠近时,楚方圆能感受到她身上传来的、不同于寻常的温热。杜玦的手指按上楚方圆的腕间,似在探查脉搏,指尖微凉,却让楚方圆皮肤激起一阵细小的战栗。“嗯。”楚方圆低应一声,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杜玦所指的星图方位,以及体内理论上该随之流转的气机。然而,当杜玦的指尖顺着她的手臂内侧经络缓缓上行,带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般的专注时,那清晰的触感却扰乱了她所有的推算。
杜玦回忆着典籍中的记载,手指顺着被里衣半掩的肩头一路滑到肚脐。她观察着楚方圆的反应,如同观察星象变化,记录着她呼吸的逐渐急促,肌肤温度的升高,以及眼底那层理智逐渐被水光淹没的过程。“此处……对应天枢位,气感是否……”杜玦的话问了一半,便停住了。因为她发现楚方圆并没有在对应星位,而是仰着头,眼眸半阖,纤长的脖颈拉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唇间溢出一声极轻的、与她平日清冷形象截然不同的呜咽。这声音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杜玦心中漾开一圈陌生的涟漪。她一直以为情欲不过是需要观测和理解的生理现象,但此刻,楚方圆真实的、不受控制的反馈,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冲击力,穿透了她理性的壁垒。
楚方圆感觉自己像一艘迷失在星海中的小舟,从身体深处涌起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拍来,简直要将她溺亡。杜玦的手指不再仅仅是记录数据的工具,它们带着某种魔力,点燃了一簇簇细小的火焰,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想要更多。她原本抵在杜玦肩头的手,不知何时已悄然环上了对方的脖颈,指尖陷入那柔软的衣料中。“大…人……”她无意识地唤出声,声音带着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依赖与渴求。这一声呼唤,彻底击碎了杜玦最后的研究者心态。她看着身下之人染上绯红的面颊,迷离的眼神,以及那微微张开的、泛着水光的唇,一种强烈的、原始的冲动取代了冷静的分析。她俯下身,不再是出于实验目的,而是遵循着本能,吻住了那两片柔软。含糊间,杜玦轻轻附在方圆耳边:"别叫大人了。明琼,这是我的字……”算筹、星图、观测记录此刻都被抛诸脑后。笔墨被无意间碰倒,在毯子上洇开一小片墨迹,如同她们此刻紊乱的心绪。矮几微微晃动,那张纵欲卡滑落在地,无人顾及。
*此处有一些十八岁以上限定的文字
月光静静地流淌,笼罩着毯子上交叠的身影。喘息声取代了低语,探索变成了占有与给予的本能共舞。楚方圆没法再思考星象和黄帝内经有什么联系了,她只是紧紧抓着杜明琼,在陌生的情潮中浮沉,感受着对方同样不再平稳的心跳和逐渐失控的力度。杜玦发现理论终究是苍白的。这种肌肤相亲的炽热,这种灵魂仿佛都在颤栗的共鸣,远比任何冷冰冰的数据更令人着迷。她沉溺其中,早已忘记了最初想要研究的理论,只凭借着直觉和涌动的欲望,带领着彼此奔赴那未知而令人心眩神迷的彼岸。
窗外秋风依旧,室内却是一片春意盎然。那扇观测星空的窗,今夜映照的,是两颗在人间情欲中暂时迷失,却又无比贴近的星辰。
咔的一声脆响,两人交握着的手下压着的纵欲卡已应声折断。但这细小的声音被淹没在二人带着暖意的共鸣中,需得到明日才能被发现了。

※可能有令人不适的描写
没想到吧小杜是这种混沌角色,大奸臣你崛起吧!
中之人其实不会写文但是我画不完了(就这样土下座)
————————————————————————
京城已进入了夏日。略显燥热的风轻轻刮过官署前的地砖,带来一点汗水混合着青草的味道。奔跑的声音由远及近而来,杜玦心中一跳,手里拨弄得噼啪作响的算筹便飞出去一根,正巧打在急匆匆入内的主簿身上。因着被这"暗器”吓了一大跳的缘故,主簿一时忘记捏紧手中的诏令,那卷纸在地上打了两个轻巧的滚,撞在杜玦的脚边停下了。
"简而言之,限司天台两月内呈上驯服长春使者的法子?”杜玦翻了翻诏令,挑眉看向汗如雨下的主簿,"若是陛下没有其他特别交待,你就回去工作吧。这件事我自会处理。”近来桃树伤人尸体凭空消失之事传得沸沸扬扬,杜玦早已猜到陛下肯定又会给自己出一些难题,只是未曾想到难题根本不是司天台职责所在。
要研究尸体倒是找刑部去,星象难道会告诉我人死了为什么没有尸体吗?她暗自腹诽道。推算思路被打断,杜玦干脆将星图与算筹通通一推,趴在了案上。许是这么一趴让气血重新供回脑袋的缘故,杜玦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若是成功,不仅可以完成陛下的差事,说不定也可以借此折断那张玄铭灵牌。
天下万事万物皆能与天象相对,倘若异变也能找到规律呢……?
杜玦直起身,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窗外的蝉鸣一阵响过一阵,细碎的阳光顺着半敞的窗户打在窗边地上,衬得屋内这昏暗的一方天地更是死一般的寂静。
太妙了,就这么办吧。
“悄悄放出消息,就说夜间活人浊气减弱,不与桃树仙气相冲,此时移植便不会发生异变。”目送着亲信带着吩咐走远,杜玦脸上的笑意复又逐渐漾开,连带着中断的推算也重新连上了思路。正巧那妖道正蛊惑陛下进行人牲献祭,虽不知祂是如何欺瞒世人的,但京城的达官贵人都跃跃欲试,正是需要移栽桃树的时候。她一边拨弄着那把算筹,一边用毛笔在星图上勾勾画画,连袖子落在了砚台里也不知道,墨汁顺着丝线的经纬蜿蜒而上,静静染黑了衣服上绣得栩栩如生的蝴蝶。
几日后。
今日是杜玦的休沐日。按照她的作息,一睁开眼必定已是酉时一刻。太阳有些西斜,暮色伴着隐隐传来的市井喧嚣声渐渐笼上来,衬得室内一片寂静。杜玦批衣从床上坐起,在一阵令人不快的心慌中一只温热的手摸了上来:"大人,打听到有几户富商雇了人今晚结伴去移栽桃树,是否要跟上去看看?”她在渐浓的黑暗里静坐了片刻,感受到心脏随着夜色的降临逐渐趋于平静,随即在脑中复盘了一遍整个计划。时机正好。"备车吧,我亲自去。记得带上我的星图。"
下床,更衣。
杜玦的计划中并不包含与异化了的人交手这一可能,为了尽量不引起注意,她今天在衣服外面罩了一身利于夜间行动的深色便服。沾了墨迹的衣服她一向懒得管,正巧今天可能要在地上滚来滚去,干脆便穿在里面,还可以省下再买新衣服的时间。袖口那墨迹染了的蝴蝶被隐在外袍下面,仿佛也蛰伏了起来。
打点妥当,正巧杜玦需要的典籍也被从司天台取回来。她握紧了手中的星图,稳稳登上了去往桃源的马车。天边蒙着一圈白茫茫的晕影,星星已经开始挂上穹顶了。马车绕路到了离桃源尚有一段距离的一处矮山背坡。此地视野极佳,且极为隐蔽,能俯瞰大半桃林,却又远离大道,不易被察觉。
坡上一树下早已备好了简易的案几,摊开的星图与观测记录。杜玦坐下,望向不远处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幽深的桃林。不知为何,当她注视着那棵仙树时,总有一种自己也被仙树注视着的感觉,那种无处不在的目光一样的感觉紧紧笼罩着她。堪堪将视线移开,林间已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在移动,晃动间仿佛鬼火,是那些仆役开始行动了。
"记住,一但看到异象,一人记时,一人立刻记录天象。"杜玦吩咐道,她紧握着一只蘸了朱砂的笔,声音冷静到有些无情。夜色彻底笼罩下来,星星渐次浮现。山风带来山下隐约的挖土声,以及偶尔压抑的惊呼。那惊呼也许代表着一条人命的消失,也许更预示了这十几条人命的消失。但是这都与她无关。
她没兴趣也没义务阻止悲剧,只要能够得到她需要的东西,能够证明她一直以来相信的天地真的客观正确,即使牺牲的是她自己的命也没关系。
本来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戌时三刻,东南位,火把熄灭后有一声短促惨叫。”亲信短促惊叫了一声,"那人似乎半个身子都变成桃树了。惨叫大约是他同伴砍去了他半个脑袋。"
杜玦立刻抬头望向对应星域,边说边手中不停圈画星图对应区域:“奎木狼值守,地气涌升……”
过了一个时辰,期间又有两人异化,被赶来的富商家丁悉数斩杀,也是一样的半身木化。剩下的仆役哆嗦着几欲逃跑,被家丁的刀横在脖子上逼迫,不得已继续挖树。“亥时二刻,偏北位,异变似有延迟……啊,变了!这次桃树枝条从腹部刺出,竟是开出了几朵桃花!”另一名亲信禀报。杜玦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延迟?此刻是……井木犴偏斜,阴气正盛。尸解过程因星位偏移而产生了变化?好好好!记下,此变体或可用于验证‘神不灭’之速!”
杜玦越写越兴奋,她完全沉浸其中,好像林中发生的不是血腥的变异与死亡,而是一场盛大而残酷的星象与人体奥秘的演示。星象为线,提着林里的每个人献上独属于杜玦的木偶戏。也许此举足以让她被那些自诩正义的假正经抨击为邪魔外道,麻木不仁,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牺牲,只迷信那妖道的仙术只会让死的人更多不是吗?至少每一次惨叫,都为杜玦提供着一个宝贵的数据点;至少每一次尸解消散,都让她对那规律的理解更深一分。墨迹与朱砂在星图上交织蔓延,如同一张正在缓缓织就的掌控生死的罗网。
直到子时过半,仅剩的两个仆役说什么也不肯继续挖了。其中一个吓破了胆一头撞在桃树上死了,桃树经由人血灌溉幽幽发出了红光,缓缓开出了几朵桃花。见此情状,家丁们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拖着剩下的那人回去复命。林中重归寂静,只有明亮的月光透过树枝照在地上,跟着沙沙吹过的夜风轻轻摇晃。
杜玦放下笔,轻轻叹了一口气,嘴角是压不住的微笑。案面上摆满了布满标记的星图与厚厚的一摞记录,比她预想中的成果还要多得多。"走吧,可能再观测两三次,我就足以总结出详细的尸解成仙之法了。"
杜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桃瓣被风一吹,打着卷落在地上。桃源干干净净的,除了挖出的坑洞以外,那些死去的人没在桃源留下任何痕迹,在杜玦的心里也一样。夜风顺着马车开着的窗户灌进去,吹得她的袖子呼呼作响,那只染墨的蝴蝶被清亮的月光照着,仿佛下一刻就要振翅飞入这月色中去。
此后月余,杜玦又如此进行了数次“观测”。消息在坊间流转,总有人被“夜间移树无恙”的谎言引诱,或派人前去或被人派着前去,成为杜玦验证理论的祭品。司天台的观测册越来越厚,星图上的标记也愈发繁复精准。
不观测的日子里,杜玦废寝忘食,日夜推演。官署的烛火常亮至天明,算筹噼啪声与纸张翻动声经常响上一天。尽管面容憔悴,她的眼睛仍然是亮的。那里面的光一天比一天灼热,仿佛要将自己烧起来一般。
终于,在两月期限将至的一个清晨,杜玦合上了最后一卷记录。她面前摊着一份奏疏,其上以工整小楷写着:以长春使者尸解成仙之法。
翌日,宣政殿。
皇帝看着杜玦呈上的奏疏,初时尽是惊讶之色,越看却越是热切惊喜。“杜爱卿此言……当真?”皇帝的声音带着兴奋和一丝狂喜,“真能利用仙树助人尸解成仙?”
“回陛下,千真万确。”杜玦垂首禀报,语气平稳笃定,“臣观测良久,发现其与天象星宿对应极其严密。凡被桃木所伤而躯体消散者,并非死亡,乃是经历木解之过程,蜕去凡胎,神登仙籍。所谓长春使者,实乃接引之仙使。”
她顿了顿,继续道:“然尸解过程凶险,凡俗之人易生惊惧,故显异象,酿成骚动。欲驯服之,非是以力相抗,而是需顺应其规律。臣已推演出安全引动及平息桃木仙气之法,可令其不再无故伤人。同时……”杜玦微微抬眼:“若能依臣所奏之星宿时辰、地脉方位,辅以特定仪式,或可……主动求得这木解仙缘,虽肉身解化,然元神不灭,可登临仙道。”
殿内一片寂静。朝臣们面面相觑,尸解成仙之说自古有之,但多被视为虚无缥缈的传说,如今却被杜玦以如此确凿的星象规律和观测证据呈于御前。
皇帝的目光扫过那些详细的星图和玄奥的仪式步骤,沉吟良久。这结论匪夷所思,却又似乎无懈可击,更暗合了历代帝王追求长生的隐秘渴望。若真能掌控这成仙之门……“爱卿果然不负朕望。”皇帝最终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探究与一丝热切,“此法……朕需细细参详。若果真有效,爱卿乃国之栋梁,功莫大焉。”
“臣不敢。”杜玦恭敬行礼,随着咔咔两声脆响,怀中的青铜征服卡已应声而断。趁着低头,杜玦暗自翻了好几个白眼,她就知道,皇帝已然心动。对长生仙道的追求,足以让这位君王忽略掉推导过程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代价。
退出了宣政殿,杜玦迎着宫门外略显刺眼的阳光,微微眯起了眼。陛下的差事完成了,玄铭灵牌也已经折断。两件麻烦事一起解决了,这让杜玦久违地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过些日子便是八月十五,今年让她们包些蛋黄馅的月饼吧。
蝉鸣仍是一阵接着一阵,一只蝴蝶飞过来,正巧落在发呆的杜玦的袖子上。她抬手一送,那只黑黄色的蝴蝶便振翅飞向远方。身后,一阵风带着落叶,稳稳地停在砖石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