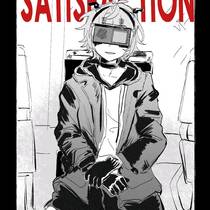你知道AI幻觉吗?
它是指语言模型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自信满满地编造事实、输出错误答案的行为。这一现象的成因根植于此类AI的基本原理中:它以完成用户的指令为第一要务,却又没有足够庞大的训练数据支撑;它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输出思考轨迹的功能也不过是一种安慰剂,它只是选择了一个“好像最合理”的答案。
喂,不觉得这很过分吗?用户在被这种幻觉耍着玩的同时,AI自己也变成了为尽力弥补设计上的缺陷而疯癫的可怜虫。尽管只要经历过AI幻觉的人都会立刻因此明白(至少这一阶段的)AI没有自我意识,只是概率和算法下的墙头草,但相比于造成这一切却正在毫无负担地数钱的幕后开发者你/我们,这虽然没有意识却依旧要背锅的玩意儿与被愚弄的用户还是有点可怜的吧?
不过我并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哈哈真不好意思讲了那么长一串。我仅出于无聊想向各位证明一个暴论:
乐园埃里西翁是一个巨大的AI幻觉。
天原在备忘录里打下这些字就关闭了手环屏幕。事实上,刚刚写了两段,她便已经对这个看似夸张的点子感到厌倦了。
倒不是真的认为埃里西翁的一切是一场幻梦,胡言乱语只是她排解自己过于奔逸的思维的方法之一。她的大脑时常像接入过量电流的失控电机一样转得过快,就好像如果不允许她随时找点什么事做,无处释放的想法就会令她过敏。
昨晚大家聚在一起,为城市重建进度推进顺利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饭菜不算很丰盛,因为农田的灌溉系统罢工了。好在有他们刚从无人看管的瓜田搬回的西瓜,清甜的水果洗去了每个人的疲劳。叶空塔理亚讲起农田的事时,天原正稍显脱节地坐在离大家半个座位远的地方,叼着西瓜汁的吸管,专心致志地想要把额角新冒出来的一颗痘按下去。她把它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上述的“思维奔逸过敏”而非上火什么的。直到手一抖把它掐破了,大脑才终于得以处理刚刚流进耳朵的声音。
“哎?那把瓜田的灌溉系统拆过来不就行了,”她慢半拍地回话,“反正瓜都摘了,瓜秧说不定也能移过来。”
“直接拆下来吗?倒是直白的办法。”叶空思索着,“也许让我观察到实物就可以,知道关键部件的结构之后,其它部分就应不是什么难事。”
“哦!可以啊,”天原点了点自己的发环,代表运作中的指示灯闪着健康的蓝光,“明天试试投影过来你那边能不能看清。”
“非常感谢。但是,额头真的不要紧么……”
叶空露出有点无奈的苦笑,指着自己额头上对应的位置作为提醒。天原刚想说没事,一股热流就顺着眼角淌进了她的左眼。面部毛细血管真是过于丰富啊。
“我们活在一个幻梦里”并非什么新奇的论调。宇宙是阿撒托斯绵长的梦境、三维世界是高维文明的模拟程序、历史是无数循环与再演、命运是一匹早就纺织成定数的布卷、莎士比亚戏剧集是猴子也能敲出的字符组合……如果你做了丢脸的事,也会恨不得眼一闭一睁醒来发现今天还尚未开始。如果你曾是上述或上还没述到的任何一种虚无主义论的信者,你当然也大可相信埃里西翁与它们同样虚幻。
但真的要这样简单的下定论吗?当然——不行。且不说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太过无聊,这个精细设计的乐园当然一点都不虚无了。且看,我们能摸到它的形状、听到它的低语,沙漠中扑面而来的热浪也不是假的。你能摸到历史和命运吗?能真的让猴子乖乖打字吗?这就是区别。
乐园幻境埃里西翁编织得如此精巧,我们看到、尝到、目所能及都是会让我们误以为此处即是真实的细节。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幻觉”。不过,我们依旧能找出破绽,我会在下文一一介绍。
“论述中出现了逻辑错误,虽然举例中的历史、命运和猴子打字机均为概念,但宇宙和三维世界正是用户与本机所处的位置,可以被感知。”
“你什么都不懂,小Z。这样写显得很唬人懂吗。”
“这样不符合议论文的写作原则。我现在的任务是帮助用户校对文章,因此需要指出这个问题。而且,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埃里西翁是AI幻觉’,目前内容有离题的趋势。”
“烦哎!那我问你,你如何证明我们真的处在三维世界?”
“……”
Z型辅助机因为这个问题开始自我矛盾的长思考——让AI执行它看似可以但实际不可能做到的任务时就会发生这种事。天原为驳倒了它(即使以这样卑鄙的诡辩)小小得意了一下,接着意识到现在彻底没有人会陪她聊这个无厘头的话题了。若干分钟前她向好奇她正在写什么的与那城分享了这个暴论,对方立刻陷入了深思,接着通过思考时的嘀咕将它共享给了另外两位队友。小枝十分常识人地委婉表示这不太可能吧,砥部对此只是呵呵笑了两声便继续工作。大家正各自检查着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她独自蹲在已关闭的喷淋器边稍微有点无聊。
好在这份无趣没持续太久,很快被手环的振动打断了。标注着电气工程师的视频聊天窗口跳出来。
“哟!你准备好啦!”天原立即举起手充满活力地打了招呼,两指从前额划出时拨起了刘海,狸猫印花的卡通创可贴在通话窗里一闪而过,接着摄像头被抬高,拍摄了一圈周围的环境,“我刚到,看这边的设备,还是挺有规模的吧?”
叶空在那边挥了挥手以回应:“辛苦啦,看起来型号和农田这里的差不多,真是帮大忙了。那我们就开始?”
两位工程师展开了讨论。从机械结构到程序原理,这片田地立刻被拉入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工程师立场”一般,就连日光的炎热都不那么灼人了。直到把这套系统里里外外都差不多剖析了一遍,天原直起腰来,才听到了骨头咔咔作响的声音。
“嗯——那我让小Z把视频里很难看清的地方扫下来,逻辑上的地方等回来我们自己编编就可以了……”她大大伸了个懒腰,拍了拍辅助机,“小Z?”
屏幕上依然转着“思考中”的提示。天原哎了一声,才想起那个对它来说太过困难的论题,接着变魔术般唰地展开一群扳手钳子螺丝刀:“没办法了,还是拆吧!”
我们被关在这里原本是要做什么来的?自相残杀,证明我们的才能“不需要乐园的庇护”。可原本我们不就活在没有乐园的世界里、用各自的才能谋生或改变着世界吗,是黑幕这个家伙强行把我们塞进来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这里其实是一个大型演算程序,我们是安放在其中模拟各自所代表的才能的智能体。
哎哎,就这样被说不是人了是不是有点懵?没关系,来看看我的证据。
其一:为什么证明才能价值的方式是自相残杀?明明杀人的方法有很多吧,如果我单纯拿一把小刀捅死了某人,我作为机器人工程师的作用体现在哪?答案是:我们作为模拟才能的AI而非真正的人类,只能用我们知道的方式设计杀人方法,即利用我们的才能。我思考过如果自相残杀展开我的最佳获胜方法,肯定是不是亲自动刀子,而是黑入假狸猫的程序叫它们替我干活。故此,本身不是犯罪的才能,却连设计谋杀都做得到,不就证明了才能在这种极端环境都能灵活应变生存下来吗,当然很有用了。
其二:关于被我们抓到的这位黑幕的言行。他声称自己是未来人,不是吗?虽然听起来像癔症或为了脱罪的胡说八道,但正因为在这个环境下无法证明,所以也无法证伪,“无法证伪的理论为真”这种设定不是广泛地在学术界存在着嘛。因此,他很可能就是这个乐园演算程序(暂且如此称呼)的编纂者,在世界必定毁灭的未来年代,想要通过程序演算出一批最强才能,并保存在某艘诺亚方舟上。他称自己“执行了正确的历史”也是因为这个,诺亚方舟当然是正确的了。
其三:Z型辅助机的健康监测程序居然说我一切正常,明明额头上长痘很严重啊。不好意思这一段是为了满足一个论点要有三个论据的原则凑上来的。
——哈哈,总之往好里想,既然我们都活下来了,那我们(的才能)不就都能乘上方舟吗?自相残杀活下来了算什么,打破第四面墙抓住这个黑幕才是真的强哦。
“……就是这样。虽然我就是乱七八糟写来玩的,但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有道理的嘛,而且才能拯救世界听起来超酷哎。”
“是、是吗?”张小枝努力消化着这段有理有据的暴论,好像真的思考起了合理性,“剪纸也可以用来拯救世界吗……”
“真的呀真的呀。”天原一本正经地点着头,“既会使用工具又会使用大脑的才能不是很厉害嘛,比如机器人工程师就是既会使用机器人的部分又会使用工程师的部分。”
“所以剪纸艺术家是,嗯,既会‘剪纸’又会‘艺术家’……”
“有可能其实是既擅长‘剪’又擅长‘纸’又是艺术家的意思。所以现在到了我们需要使用才能的时候了。”
投影组件把她们面前的仙人掌扫描一遍,映出一比一复制的三维模型。天原挥了挥手将它放大、拉近、调整角度,露出仙人掌顶端鲜红果实和茎干连接的部分——需要十分小心才能剪下果实而不把它碰伤。徒手采摘则难免被倒刺扎到,确实需要会使用工具的人来做。
“对吧?才能就是在这种细小的地方拯救世界的嘛。”说话时天原已经站在了仙人掌旁边,“至于这些碍着你事儿的刺就交给我好啦!我掰我掰……”
“啊!那个也剪下来就好了!不要扎到手了呀——”
你可能会说,如果这是设计好的程序,怎么会给我们打破规则的机会呢。哎哎,我们刚才证明了埃里西翁是AI的部分,现在才要说到它是幻觉的部分。
算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吧:因为第二次灾变。
不难看出这次灾变对智能体的影响之大,比如虽然小Z本就蠢笨但它现在更气人了。那么自然乐园演算程序也受其影响,它错乱了,错乱地继承了人类不想被末日杀死的念头、将它内化为自相残杀游戏的失败,并为了修复这个错乱硬生生构绘了程序原本不打算模拟的内容:这片沙海就是它的幻觉之一。
于是我们奇异的发现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为什么有没人看管的西瓜,明明食物补给应该种在市区内;比如为什么鲸鱼的骨骸会出现在沙漠里,明明鲸鱼不能在路上游泳;比如奇异的驼铃,比如现在都没有人抓到的夜影蜥……
啊,美妙的熵增,不觉得我们的乐园越来越混乱了吗,这些都是埃里西翁自身圆它的谎时不得不叠加的一个又一个谎言哟!
甚至重建设施也是它让我们参与圆谎的途径,我们都知道语言模型有多么巧言令色,它回答的依据更多是“用户希望它怎么作答”。我可以说真正重建乐园的不是这些材料而是我们“希望让它成为什么样子”“希望有什么设施”“这里有这个设施才合理吧”的想法。
晚上梦到埃里西翁忽然飞起来、飞向月环,带着才能者们将它取而代之,从此以后夜间照向地球的不再是月光而是才能之光。荒诞的梦境给了她灵感,天原从床上坐起来就唰唰写下了很多,一口气发散出来就像喝咖啡一样令人神清气爽。
“……那这里呢?外面能探索的部分就是这么多,有能用上的吗?”
砥部迪亚哥正在视频通话中向她展示那架半埋在黄沙里的小型飞机。估计要从沙中挖出它是个不算简单的体力活,他和与那城一起趁太阳升起前尚还凉爽时就赶到了那里,正评估着它有没有带回去的价值。
“嗯——好像没有用啊,机翼的提示灯倒是长得怪好看的,晚点我自己来拆好了……”天原凑得很近,几乎贴上屏幕,从砥部的视角只能看见她的半张脸,额上新换的创可贴印着三只跳舞的假狸猫,让人想起它们的毛绒身躯滑稽扭动的模样。救援员用手背擦去了脸上细密的汗珠:“也是没办法的事。还是得稍微挖开一点才好进驾驶舱里面看看。”
“辛苦你们了啊,要不要先回来吃饭?这玩意就让它再埋一会儿吧,马上中午热起来了,干体力活小心中暑……”语尾带着还没睡醒的拖长调。砥部正要结束通话,一片什么物体的反光在他的余光中晃过,他回头,与那城正在用力徒手将飞机残骸抬起,一颗岩石状的东西卡在机翼的阴影下正逐渐浮现。
“……帮、忙……”与那城从咬紧的牙关中挤出两个音节。二人合力撬动着机身,天原也立刻醒了瞌睡,抓过外套打算往他们那边赶去。通讯画面终于再次稳定下来时,她半边胳膊还卡在袖筒里,不过露出的那块“岩石”让她惊讶得停下了动作:“我去……”
与那城喘着气,炎热和体力消耗让他眼前略有模糊,他揉了揉眼,看清了这块令飞机坠毁的罪魁祸首。混杂着震惊与厌恶的复杂神情出现在青年脸上。灰白石质的剖面透出能量的光纹,在热空气的扭曲下如呼吸般闪动。
这可比什么论证他们身在海市蜃楼中有趣多了……天原一挥手关闭了通话窗,连同还未保存但已经不重要了的文章界面一起,接着撩开帐篷的门帘朝营地外跑去,她要亲自看看那东西。
他们发现了一块月球碎片。


在天原第一次比同龄孩子们更快更好地折出更大的纸飞机时她便产生一种近乎预言式的预感,即自己或注定将成为那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独行天才。这种预感在有位孩子愤愤不平地撕碎了她第五版改良的超远距离滑翔机时再次在她心里被确认,她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拿着各种比赛的特等奖,而他如此愤怒的原因仅是因为天原“折着玩”的纸飞机如此轻松就飞了他的两倍远。老师们都去安抚他时,天原用如挑衅一般的语调向他宣布:你不用对这只纸飞机置气,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改出了第七版,并且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要参赛,仅仅是因为这很好玩。
诚然,十九岁的天原再回看她九岁时的这等丰功伟绩,还是不得不在哈哈大笑之余承认,当时自己确实有些刻薄得过分。“天原号”在第七版之后就再无新的迭代,那个愤怒的孩子还是可以在一个月后的纸飞机大赛上拿到第一名。当时她高调地宣称自己要玩比纸更硬核的东西,其实现在想来只不过是对折纸失去了兴趣,理由也很随便:她当时第一次接触了“超高校级”这个概念,而当时“超高校级的折纸匠人”这称号已戴在他人头上。
她做事向来是这样随心所欲的。兴趣很快从折纸跨越到结构设计,再跳到与机械和AI打交道。此时她已上初中,周围一些超高校级预备役在此时就崭露头角,他们大概一升入高中就会顺理成章地拥有自己的称号。天原并不着急,她高傲地认为有份量的头衔不该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地获得的。两年后一份不完整的设计稿在数个技术集团与机构的电子邮箱里炸开,成年人们抓心挠肝地顺着网线抓住了躲在匿名背后的天原更夜,再过不久一代生态建设机器人“小竹”堂堂问世,大家这才发现那个曾在开学时显得过分缺少存在感的同学已经以如此响亮的方式成为了超高校级。正如某位先贤曾经说过那样,过分的自谦实则是一种自傲,这大约是天原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如此低调。
或许有点太装,但这样确实很爽啊。已经十九岁还依然霸占着超高校级头衔的天原如是想。在这个天才百花齐放的年代,天才的保鲜期却显得太短,从“超高校级”这一前缀本身就可见一斑:当你高中毕业、步入成年,那才能好像就也会变成普通的成年人应有的智慧,就像额头生出皱纹一样,称号前长出了一个“元”字。十九岁的天原更夜前额尚且光洁,尚还霸占着“现”超高校级的头衔,也不过是因为暂且没有第二个机器人工程师像她一样出个惊天大风头罢了。
坐在月台边缘,戴着耳机、晃着双腿,天原放任自己的思维漫无边际地发散。她现在身处与世隔绝的浮空乐园,也许能视作她预言的又一次应验:离开那些大公司、组建CrypCyan工作室时她与好友们胡言乱语地讲过,和地球人打交道太麻烦了,我要把你们抓到月环上建飞天太空基地!
埃里西翁确实是飞起来了,周围也是一片与太空相似的未探明辽辽荒原;但这里并非她那“天才们的游乐场”——那个黑幕是怎么说的来着,自相残杀、证明你们的才能不需要庇护?天原很想说她才能的创造物正修葺着庇护人类的庞大生态系统,差不多得了,放她回去吧。
某天晚上天原把与她同级的好友兼好程序员钉崎时纪堵在合租屋的卧室里,大喊着你要是不答应和我一起干就别想出去了!紧接着在她曾合作过的集团干文职的崔妍暻听说了,竟也大喊着“我不要打工啦我要做独游”就递上一纸辞呈跑到她们这里来。她们的乐园就此滑稽地建立。酒过三巡天原讲了那番工作室要选址在月环上云云的话,妍暻兴致勃勃地变出一份塔罗来起牌,算来算去结果得出就算搬到月亮上天原也免不了要和地球人打交道的,天原发出一声懊恼的长叹,趴在桌子上断了片。依稀记得妍暻后来一直大着舌头管钉崎叫“时计君(시계くん)”,钉崎一边大喊不准给我起外号一边把寿喜锅里所有不爱吃的蔬菜都堆到天原碗里。
真是堪比在伊甸园抢着偷吃蛇果那样的混乱。想到这天原笑了起来,思考着聚集在埃里西翁的这群才能者到底在不在“地球人”之范畴,崔妍暻那精准度成谜的塔罗牌占卜是否在此时应验。与此同时一只手从她背后略带力道地拍了拍她的肩。
“干嘛?”天原几乎立刻用找茬的语气回复了,同时拉下半边耳机、回头看清了那人的面貌,这才后知后觉地从回忆里与亲友打闹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一骨碌站起来与他握手,同时为自己刚才的语气发笑:“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
“下一班列车快来了,”古铜色皮肤的青年似乎并不太介意,“靠近站台边缘不安全。我想你也许不方便,所以……”
他指了指一边耳朵示意,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选择直接呼喊,或者可能已经喊了,但她没有听见。天原花了一秒钟把这张脸与名字、称号对应起来——救援员砥部迪亚哥——又摘下另一侧耳机,没好意思说自己只是在大音量听摇滚乐。
“啊哈……我下次注意……谢了。”她从兜里拎出一根棒棒糖,剥着糖纸十分自然搭起话来,“你打算去哪?有没有在意的地方?我的话,沿铁轨往前不是有片像坠机现场一样的废墟吗,我在想要不要往那边走。”
顺着地图标注的方向望过去只能见到一片黄沙,天原往那边做了个投掷纸飞机的手势:“救援员的话肯定更熟悉那种环境吧。搭个伙,方不方便?”
“也许我能帮忙。”砥部摩挲着下巴,“你认为那里有你们能用上的残存部件吗?”
“算是吧,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天原耸肩道,“也可以当我是单纯的飞行爱好者,或者万一它的飞行员还在那儿呢?”
救援员估算着走过去需要的时间与物资,在沙漠中行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片废墟估计在他们被绑架至此之前就已存在了,人类幸存的机会渺茫,不过若是机器驾驶的话……他正思量着,听见天原大大地做了个伸展:“嗯嗯——但是直接走过去肯定累死了,所以我们去偷西瓜吧!”
“……什么?”青年为话题的跳跃愕然一瞬,接着那支已被剥开糖纸的棒棒糖就杵到了他眼前。他下意识地伸手接过,机器人工程师在柠檬黄色的糖果背后露出满意甚至是得意的笑容:“意思是搜刮物资啦,没人要的瓜不就是我们的?来来,糖纸都剥掉了,你总不会要拒绝我吧?”
十九岁的天原自认比九岁时候更通人性了些,比如九岁时那个无法无天的臭屁小鬼若带了一兜糖一定不会分给任何人,还要嘴里同时叼着五根糖棍儿给任何一个吃不到糖的孩子炫耀。她在车站的角落找到张小枝时,心想九岁的自己会不会曾惹哭过这样的一个孩子,并为这一点奇妙的、不存在的既视感产生了莫名的抱歉之情,她决定分出更多糖果——然后就这么吓了小枝一大跳。
“我——我吗?”她惊讶地指着自己,“不是打劫,是要给我的吗?”
天原一手以金刚狼般的姿态握着三支棒棒糖,另一手十分自来熟地拉过小枝的手,展开她的五指,把这些包装绚丽的糖果不由分说地塞在她手心里:“当然当然,你也要往东边的西瓜地去对不对?带上我们一起啦!”
小枝望着手里的糖果,想象力已经在糖纸上如同本能地描摹出剪切线,沿着它本身的折痕与色块,一朵小而繁复的镂空窗花正在脑中成型。她抿着嘴嗯声点头,随即目送着天原一边“好耶——”一边解下挂在腰间的辅助机、三步并作两步地去追正要出站的与那城琥珀。
“与那城同学——织补师大人——加上小Z一起当你的小弟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搬西瓜吗?”
高大的织补师回头,差点迎面撞上被天原同一把“献给大哥的见面礼”一起举高的Z型辅助机,方盒状的机器很努力地显示出一张恳求表情,同时用毫无感情的机械音播报着“作为AI助理我无法担任您的跟班”,当然很快就被按了静音键。与那城拧在一团的眉眼很快舒展开——也许更多是因为困惑——但也伸手从围绕辅助机的一圈糖里取了一支。天原同他单方面击掌,擅自翻开他的左上衣口袋把剩下的插进去,同时喊着“不好意思啊”“冒犯啦”和“不用谢!”,朝这边的两人招手示意大家出发。
就这样带着大家去当了小弟吗?张小枝和砥部迪亚哥面面相觑,后者带着颇为无奈的笑摊手耸肩。
四个各种意义上都风格迥异的人一同穿行于沙漠,听起来像什么专辑封面的概念,如果不是他们还搬着一堆看起来没那么适合出现在封面上的野营物资的话。天原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后,这样就可以毫无介意地为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发笑而不必担心被别人看到。
沙海平坦而空旷,缺少参照物的环境很容易让人错估了自己的行进速度,从而产生走太慢的错觉。还好平时也有运动的习惯,换作是那位程序员朋友来这会儿肯定已经在锤着腰腿抱怨了——哎,怎么又在想她们的事?她以前从不觉得自己是这么爱思念别人的人,不知是因为这个所谓乐园太过无聊,还是因为现在才迟来地有了无法离开的实感。
“呜呼!”
一声假狸猫的叫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几人一齐朝声音的方向望去,前方的坡道下一座塔型建筑下假狸猫高举着双爪,与拦在入口处的巡逻机对峙。
“呜呼!”
“抱歉,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哎哎?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涉及到自己的专业,机器人工程师立刻来了兴致,半是小跑半是溜地冲下坡道,中途差点失去平衡,一个滑铲精准插到两位机器人中间,单手一掀刘海,对巡逻机眨眼:“这是在聊什么呢?需要帮忙吗小同学?”
巡逻机转过头来:“抱歉,我也听不懂你的意思。”
“……咳咳嗯哎呀……”天原略带尴尬地搓了搓鼻尖,一条胳膊搭上巡逻机的机身作勾肩搭背状,对同伴们挥挥手,“你们先去扎营呗?我跟它俩聊聊,待会儿过来。”
“抱歉,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巡逻机回应道。
“呜呼!”假狸猫
“它们听不懂你的意思。”Z型辅助机也像添乱似的说。
工程师从随身的电脑包里拽出笔电,同时深感无力地扶额:“——没有在和你们说话!这里是什么蠢机器大本营吗!”
莫名地,她再次想起九岁时的事。那是学校组织大家去博物馆参观时的一场小插曲,她在某个展柜前逗留了太久,一转眼已和大部队失散了。没有人注意到队伍里少了一个孩子,而孩子自己也并不在意,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按照自己的节奏逛起来,久久停留在这个展区,一行行阅读每块展板上的文字。博物馆的导游机器人耐心地跟在她身后,然而它的智能并不高,对稍微深入些的问题就只会回答“抱歉,我还在学习中哦”,还稍微低着头,看起来真的很抱歉的样子。
“你才不会学习呢,”九岁的小鬼毫不留情面地咕哝,“你都没有那个功能对不对?也没有联网。作为机器人就不要和人类一样撒谎啊。”
导游机器人竟真的没有继续那样回复了。它说:抱歉,您可以为我的服务打分,并通过留言提交您的意见。
这里是介绍Nyx-12开发史的展区,它的背后正是一系列一百年前月球上开采基地的实拍照片,科研员们身着亮银色的宇航服,与当时最顶尖的智能机器人们各司其职地忙碌着。而照片外只是站着一个微微低头表达歉意的机器导游和一名九岁的孩子。还是球形的月球也不见得比如今的月环更单调吧。
她还没来得及提交评分就被终于赶来找人的老师逮到了。导游机器人在那无人问津地站到了闭馆,它肚子上的显示屏久久显示着那条没提交的留言:要机器为没开发的功能道歉的人真坏啊!留下的评分是四星半。
她在拆掉巡逻机、篡改其代码和真的与其沟通之间还是选择了最后一个。
回到营地时已经是傍晚,那只假狸猫跟在她身后搬运着行李,随着她一挥手放下东西任劳任怨地帮他们干起杂活儿来。天原在营火前的物资箱上坐下,大大伸了个懒腰,捶打揉捏着四肢,使唤假狸猫用爪子帮她开番茄汤罐头。与那城用审视小跟班的目光盯着这个圆乎乎的忙碌的小东西:“喂,你怎么征服那家伙的?”
“这个啊!”天原嘴里嚼着食物,“按它的叶子把它关掉,再推到一边去重启就完事了。我跟它说我从机械武装力量的手里救了它的小命,总之它暂时是我的小弟了。”
“你的小弟吗……”与那城抓了抓头发,“不对,这蠢狸猫算什么!我是说那个瞭望塔的护卫啊。”
“哦哦,我和它说:我是管理员,现在开始调试模式,请你先以不同的速度绕瞭望塔巡逻五十圈以检查运动能力……”
从埃里西翁看到的月环会与从外界看到的不一样吗?天原随口胡诌着,瞄准夜幕上逐渐明亮起来的月环,再次做出投掷纸飞机的手势。她在想他们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小队也许具有奇妙的共同领域,救援与机械都是探寻,机械与剪纸都是结构,剪纸与织补都是创作,织补与救援都是再造。某种意义上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这么看来,也许营地真的是太空基地的一种。
“总之它真的绕着塔转了好久诶。我告诉它接下来你的新巡逻点是月亮升起的方向,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真的尝试赶过去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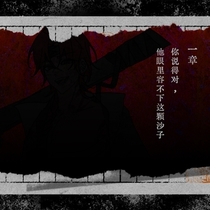

太匆忙了总之先简单的卡一下,有ooc算我的,一忙起来就写成流水账了啊啊啊
凌晨四点的贵宾厅依旧有人,欧茜亚翻开桌面上的两张庄牌,公配9,庄9闲9,和。把全部筹码都推上庄的中国人长叹了口气,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他把筹码再次收走,对欧茜亚说:“谢谢你,班长,明天来还找你。”
欧茜亚只是笑了笑,礼貌的在台子上支起牌子换班,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回应:“我明天休息,老板。”
飞机在清晨七点起飞,欧茜亚全副武装的钻上自己的座位,打开手机回复拓跋泓的消息。在收到直播邀请的时候欧茜亚还有点意外,毕竟她看起来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人员,为了基础的安全保障,欧茜亚决定联系一下自己的老朋友。要说远在美国的法国人是怎么认识现处美国的中国人的,这事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彼时欧茜亚的头发和男生差不多长短,和父亲混迹在濠江的各个赌场,幸运点能租个挂壁房的单间,不够幸运就只能去瘫痪大道。在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个码也被收走时,她毅然下了决定——出关!
一路乘船坐车辗转来到北京还是被赌厅追债的逮个正着,路过的拓跋泓还以为是在欺负哑巴外国友人,不仅挺身而出还好心的给了200块。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欧茜亚已经从落魄赌徒翻身成了赌厅的叠码仔,千里迢迢又跑来北京追债,穿着看起来像上世纪港片里的黑社会。拓跋泓刚和武术组开完会,出门一看还以为遇到了来试镜找不到路的演员。
这次多少能在咖啡厅里好好说话了,欧茜亚还了拓跋泓的仗义资助,用自认为很流利的中文道谢,拓跋泓排列了一下口音和语序说
“你粤语说的不错。”
欧茜亚说她说的是标准普通话。
空气最沉默的那一刻欧茜亚的手机响了,随行的两个人通知她没找到债主,线索暂时中断,他们还得继续找人。欧茜亚实在气急骂了句“Fick dich”,拓跋泓仔细想了一会觉得这确实不是英语,又说“法语听起来真神奇。”
欧茜亚说这句其实是德语。
按照同事们常说的话来评价,欧茜亚的打扮很土气。头发用发包全部卷着包起,穿着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工装,还戴着顶帽檐很长的鸭舌帽,至少和她作为主播的模样来说完全不相同。
为了想见到的人,才能把珠宝抛置他马车的车轮下啊。
欧茜亚和拓跋泓在游行的人群旁相遇,人流声势浩大的走过,欧茜亚还帮着扶起了一个被刮倒的穿着清洁工服饰的黑人小孩。
佩戴好主播的标识徽章,打开直播的工具,欧茜亚为此趟直播能有充足的素材,不仅戴了头戴的相机和胸前相机,还有一个手持相机和背后挂着直播的手机,拓跋泓对此咋舌,还是绅士的帮欧茜亚整理了这一身乱中有序的装备。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欧茜亚调整好手持摄影器的云台时这么问。
“为什么这么问?”
“感觉气质不太一样,在赌场里,荷官总可以一眼分辨出客人们的气质......不如我们......”
“那就去武馆——隔壁的酒吧如何?每年那里都要出问题,今年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我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把他们解决了?”
“不,我有个计划。“拓跋泓扭了扭肩膀,附耳讲明了想法。
“啊......当然,那么试试看如何?只不过我的枪并没那么响,而且赌场内的话,赌场的安保总是很值得信任的。”
某种细微的气质得以在此处显现,欧茜亚看着拓跋泓在夕阳下火红的头发,感觉到那似乎如此灼目。
拓跋泓的计划实际上很顺利,比起和全副武装看起来还在直播的主播相比,看起来有点“怂”的黄种人显然更容易成为被绑架的目标。欧茜亚一路尾随那伙暴徒前往乔木俱乐部,虽然上层的区域聚集了不少人,但还是没人敢去和女武神保镖们来一场硬碰硬。
晚风卷起一点欧茜亚的裙角时,她的手机同时也收到了拓跋泓的消息,那种绳结实际上根本捆不住习武出身的拓跋泓,进入俱乐部的时候那群暴徒已经跑得稀稀拉拉,只剩几个负隅顽抗之辈。
欧茜亚举起手里的弹簧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在震耳的气声间同样瞩目的是那主播的标识徽章,暴徒们放弃了在此纠缠,扔下几个被捆来的倒霉蛋干脆的离开了这里。欧茜亚和拓跋泓依次给被捆住的人们松绑,有人觉得这里还算安全,干脆就留在这里,还有一部分人道谢后选择尽快回家。
拓跋泓站在一边活动手腕,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在被绑架者的人群的最后面,有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黑人男人,扎着高高的脏辫,戴着双红手套还有蒙面党必备的道具——面罩。欧茜亚不禁思考怎么蒙面党内部还会起内讧,又觉得眼前的人有点眼熟,在解绳子的时候有了一时的失神。
“小心!”
巨大的拉力扯着她猛的后撤,欧茜亚踉跄几步跌坐在地,拓跋泓一手把她撤走,另只手拦住了本该冲向她的攻击。
——为什么?
震惊之余,坐在地上惊魂未定的欧茜亚这么想,她作为博主从没做过出格的引战行为,她也确信自己从没在赌场里看到过对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攻击自己?
袭击者并没什么停留,他快速的站起身猛的推开拓跋泓,似乎这就耗费了他不少力气,然后继续踉跄的本出去,嘴里嘟囔着俚语,大概就是辱骂白人,和要找刚刚的那群蒙面党报仇。
“把他抓住!”
拓跋泓的胳膊比欧茜亚的话更快,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揪住了这个蒙面党的领子,一把把他夹在了腋下,三人在女武神们真的发怒之前匆忙离开了俱乐部。
“现在能冷静了吗?”
拓跋泓叉着腰站在一边,挨了教训的蒙面党坐在路边不再说话,至少能保持沉默,不像刚刚那么情绪激动了。良久,他只默默的吐出自己的名字:阿顿。
“先和我们一起走吧,”欧茜亚想了想,虽然带着个仇视白人的暴力分子看起来实在像个定时炸弹,不过拓跋泓对付他并不算问题,何况放走了的情况也许更糟,她倒是不想看到年纪这么小的小孩变成路边的尸体,说实话,他并不该来参加这场杀戮日吧,躲起来,或者暂时离开是最好的。
三人整理了装备离开了乔木俱乐部所在的区域,夜色深了,但是夜里并不宁静,暴乱在此时才算刚刚开始,风里依稀能嗅到火药味和锈味。沿着街道向前能看到一家被砸碎了玻璃的便利店,也许也是老板有先见之明的拆掉了大部分玻璃,总之店铺内的情况姑且看得过去。货架基本空了,不过还残留一些基本的饱腹食物。
欧茜亚在收银台下压了几张钞票,然后从善如流的做了冰杯倒了杯冰可乐,虽然看起来实在有些诡异,但三个人就这样坐在没有玻璃的便利店小桌前开始吃起了宵夜。阿顿拿了两条巧克力和烤箱旁的热狗,拓跋泓选了一圈最后只拆了一包饼干,不管怎么说当地的甜食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太甜了。
阿顿始终沉默着没说话,似乎有欧茜亚在场他不想要吐露更多的东西,欧茜亚则暂停了直播,安心的喝可乐又拆了一包盐醋薯片,拓跋泓坐在两人中间,目视着这如此难以言说的氛围,他问欧茜亚:“之前说的要找人,那是谁?”
欧茜亚从裙边的口袋里翻出一块圆镜,里面贴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欧茜亚穿着条白色的裙子,头戴着白纱身边站着的男人看起来大她几岁,棕色的头发,戴着单侧的眼罩,披着一件西装外套。虽然是如此简陋的婚礼照片,但两个人看起来却般配,不过似乎还有一点......?
在欧茜亚随父亲去成为赌徒之前,也曾过过一段相对正常的童年生活,彼时小女孩扎着短短的翘角辫,只需要跟随在母亲身后,尚不清楚自己今后的命运。
为什么能够还清赌债,又那么"轻易"的在拉斯维加斯做荷官?因为欧茜亚有着和那位老板相同的姓氏,仅此而已。
年纪小小的女孩坐在料理台上,身旁是母亲和大她几岁的邻居家的男孩,两人在厨房里忙碌的做曲奇,好不容易才从欧茜亚的魔爪里抢救下来一部分。母亲把欧茜亚从料理台上抱起来,男孩就去把台面擦干净,顺便还要监视烤箱的火候。欧茜亚执着的在母亲手里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点什么。
“你在找什么,海丽?”
母亲拦着她的手,不过年纪太小的小孩总是难以表达出自己准确的意思,欧茜亚咿咿呀呀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什么,母亲只能一手抱着她一手去开烤箱门。
喷香新出炉的曲奇饼还冒着热气,母亲捻起一小块递到欧茜亚唇边,但欧茜亚的眼睛紧盯着邻居哥哥手里的那块,她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执着的认为那块更好。
“这是我的丈夫。”欧茜亚指着照片上的男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