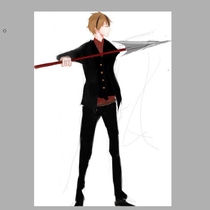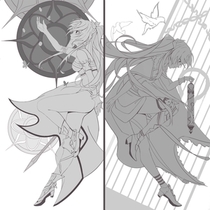

*一个没什么意义的随笔,感谢大师在群里贴出的那张照片,脑洞爆发(。
*并不是想探讨些什么……如果看着像,可能是这两天《不朽》读多了(
————————————
细雨织出了帘幕。天际灰蒙,凉意更甚。
黑衣少女撑着油纸伞,同女性缓缓步于雨中。
她们的速度很慢。不时有行人与两人匆匆擦肩而过。
由于身高相近,少女不得不微微抬高了拿伞的手臂,又斜了斜,使女性远离那渗着冷凉的雨丝。
“不必在意我。”
女性静静说道,“我是‘九十九’,淋不着雨的。”
持伞的手动了动,随即更用力地握住了伞柄。少女抿了抿唇:“……嗯。”并没有将伞归正。
女性便也不再多提了。
细雨绵绵,穿过两人之间的沉默,不断跌落在地,不多时,在街沿汇聚成了极细的水流,自脚边淌过。木屐溅出了水花,水花又沾湿了白袜。少女没有在意,微垂着头。刘海掩去了她的眉眼。女性仍是如常,那些滴落伞面的雨声,直直穿透了她的身躯。
如此一看,二人便仿佛逆流而上,似要追本溯源般,缓缓走去。
——目的地是明确的。
细密的雨幕笼罩山林,那满眼苍翠亦被淋湿了,色泽沉淀了下去。
两人行了一礼,跨过山门。写着“增上寺”的白灯笼被护在檐下,目送着二人朝上走去。
“你其实不用陪我来的,真黑。”
少女看着脚下的石阶,忽然说道。
“嗯,”真黑应着,笑意温婉,“我担心凉子迷路。”
顿了顿,凉子低低问道:
“不会累么?”
“‘九十九’是不会累的。”
“也是。”
这对话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因而掉进水流里,便再也寻不见了。
寻不见,是好,还是不好呢?凉子怔怔地想。
这身黑衣还是崭新的,因为她极少参加葬礼。可她到了这样的年纪,周围的人免不了会比她先行。
彼时,少女静静地望着睡在棺椁里的人。棺椁也是崭新的,可棺椁里的人却不是了。那张青白的面孔刺得眼睛作疼。
她没有哭。将花束献上去时,她只是在想:亲朋好友都围着他,都寻着了他沉睡的身躯,这是寻见了吧?但内里的、大家所熟悉的他的灵魂却是早已消失了,这便是寻不见了吧?
好坏与否,寻得与否,仔细想来还真有些麻烦啊。
“你说,浅原师傅这时候在不在呢?”
她的眼里藏了三分叹息:“我唐突来找他,会不会扰到他了呢?”
“必须找到他才行么?”真黑的声音素来是静的、缓的。
凉子被问住了。双唇抿作一条线。她想了想,踌躇地答:“……也不是。”
真黑笑了笑,便没再继续了。
凉子也没有再提出新的问题。石阶绵延而上。少女瞧着湿了袜子、流经脚边的雨水。雨水浸润之下,灰白的石阶便柔软得似一匹绸缎。
奇怪的比喻。她心想。
半晌,两人站在了平整的地面。建筑物皆不如上次来时那般通透可见了,罩着薄雾,看不真切。那几棵古树倒仍在雨中伸展着光秃的枝杈,不言不语。
少女四处望了望,迎上了撑伞而来的小沙弥,便慌忙叫住,询问浅原一真的去向。小沙弥大抵是没料到这雨天也会有来客,惊了一惊。
“浅原法师好像刚离开。”
小沙弥忙收了惊诧,如此答道。
凉子笑了笑,谢过男孩儿,待到送走了他,才叹出声来。
“是挺不巧。”
“必须找到他才行么?”
“……也不是。”
真黑笑了,又道:“那就散散步吧。你看那儿的门,通出去,也许别有洞天。”
本来也没什么事,凉子便依了她。真黑所指的门在斜对面,是个低矮白墙砌出的拱门。
两人缓缓前行,穿过拱门,入眼即是拔地而起、直入天际的古木,肃然静立于小径两旁。
雨雾濛濛。曲径蜿蜒而下。两旁的林木愈是向前,就愈是影影绰绰,连那绿意也不甚真实了。
那把纸伞正缓缓行于雨里。
一派空濛之中,青年的袈裟也不似以往那般惹眼了。
金黄被雨洗得深了些,黑衣则稍浅了些。
身形是熟悉的,走路是熟悉的,凉子甚至一瞬想象过,若是她喊他的话,他回过头来,定会先向她行一礼,一如往常。
然而,那身影已是远了,远得少女听不见禅杖落地时铿锵的响声,远得她的呼唤穿不透这雨、这雾。
凉子张了张口,旋即作了罢。
她仅是静静地望着,望着浅原一真的背影渐行渐远,终究只剩豆粒大小,消失在了古林深处、小径尽头,彻底消失在了她的视野里。
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
良久,她开口道:“可惜了。”
“可惜什么?”
“……没什么。”
她转头望向真黑:“走吧,回家了。”
伞面上落了些薄薄的光。少女眉眼里氲着的雾也散了。
真黑笑道:“好。”
更多的雨滴落下来了,自脚下湍湍而过,它们带走了“寻得见”的与“寻不见”的一切,将天地化为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