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很多地方,準確來說,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故事。有些短,有些長,每個人都盡量想寫多幾頁,但是有時候,老天爺留給你的書到底有多厚,實在是很難預料的事情。
------
日向寺睜開了眼睛。
房間的窗戶沒有打開,睡前拉緊的窗簾掩去打扮的室外陽光,只留下一線光輝落在滿佈雜物的地面上。他雙手交疊放在腹部上方,側頭看了斜照進房內的陽光。
在戰場上沒有方便的報時方法,西洋鐘依然笨重,不適合帶進戰區。因此他早就學會怎麼樣用陽光的角度判斷時間——日向寺從鼻子哼了一聲。他現在只需要看一眼鐘面就可以了,這種便利反而讓他的心情更惡劣了幾分。
安逸,無比的安逸甚至可以被稱為沉悶,無聊,讓人絕望的寂靜伸著冰冷的雙手壓在他的喉嚨,不間斷地,一點點收緊掌握。
他知道現在早就已經過去了他應該要到地圖室報道的時間。但是他不著急,地圖室的人也沒有來找他的打算——他本來就是外人,急躁的他的加入反而對他們穩定的狀態造成干擾,帶來不穩定的漣漪。他們不喜歡,只是礙於他的面子沒有說出來。
但是其實日向寺真的不是很在意。反正他的現在只是在那裡掛個編制,就算所有人都抱著地圖不讓他進門他都不在意。他總歸是要走的。問題只是時間。
想到這裡,日向寺舉高了右手,盯著自己張合的手指,肌肉的收縮牽引到他臂上被子彈穿透后愈合的傷口。然後又把手放了下來,溫熱的掌心壓上另一隻手的手背。
無聊,太無聊了。他翻了個身,視線對上墻上畫像中的少女,她哀愁美麗的眼睛半垂眼簾,也在注視著他。
XXX
“赤城。”被叫到名字的男人身體一僵,緩緩轉過了身來。在眼睛對上前的一刻,赤城幸秀露出了有點滑頭的笑容,就像他平常在鬼父之間周旋那種。
“又見面了,日向寺。”仿佛是對對方用姓氏稱呼自己一般,赤城也換上了嚴肅的口吻,對舊友點點頭。日向寺依然沒有拆除頭上的繃帶,赤城知道他回來已經最少三個月,傷也應該早已復原——他的傷可能比想象中嚴重,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在戰場上得到的傷疤過於嚇人,日向寺決定暫時留著繃帶。
赤城並沒有得到回應。年輕的軍人只是把煙卷叼在嘴邊,然後低頭點著了煙頭,深深吸了一口氣,再把白煙從口中輕吐出來。裊裊煙霧圍著他們轉了一圈,慢慢散去。
“珊瑚,”日向寺把煙卷夾在指尖,取了下來,“找到了嗎,兇手。”
赤城一頓,回答:“這個你不是應該去問巡警嗎?”
日向寺瞥了他一眼:“別裝傻了,我知道佐佐木接了委託,我不想見他,天天去蹭飯的你完全可以代替他回答我。”
“我沒有蹭飯,我只是去幫他們合理分配資源。”
”那樣就是蹭飯。“
兩個男人對視了一眼,那樣實在有點奇怪,畢竟其中一個人現在只剩下了一隻眼睛。無論如何,他們在對方的眼睛里模模糊糊地,找到了一點幾乎不可能被看見的熟悉。那種詭異的感覺就像一隻手在輕輕撓了撓他們——於是他們低聲笑了起來。
日向寺的笑聲似乎有點苦澀。琉璃對他們描述過的瘋狂似乎就只是少女奇怪的幻想。現在的司異常地和當初得知珊瑚死訊的他相似。低沉,像沒有風的夜晚,月光照射在雪地上,反映出的光線讓周圍異常明亮,只有白雪,還有白雪,他們呼出的白霧轉眼就在空氣里消散,於是那兒只有雪,和寒冷。
職業騙子本能地感到違和,他皺起了眉頭。
“要是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你的。”最終赤城只是留下了一句,和日向寺握了握手。
XXXX
他還是選了祭典。
日向寺牽著滿心歡喜的年輕女郎。她好像是叫阿藤,還是叫蘇菲?在閉關鎖國結束后越來越多的女性踏上了學習之路,她們就像乾渴了千年的海綿,終於回到了大洋之中,拼命地,拼命地吸收一切他們能搞到手的知識,或是隨便的什麼。改變,她們說,她們是摩登女郎,不再是唯唯諾諾以父為天,纏繞著丈夫寄生的絲蘿。
他喜歡這樣的人,充滿活力。他低頭對她微笑,伸手把她因為人多擠迫散落的碎髪別到耳後。她沒有紅著臉退開,摩登女郎抬起了臉,對他露出了一個知曉一切的微笑。
哦,他實在喜歡她。莫妮卡不像她以為自己表現出來的淡定,她右眼的虹膜有金光一閃,貓科的尖錐形瞳孔出現了不到一秒,然後就變回了屬於人類的眼睛。日向寺的手已經康復痊愈了,於是在她的手搭上了他的臂彎,輕輕搔了搔的時候,手指剛好就在他那塊傷疤上。
他實在喜歡她,也許和栞差不多。
日向寺也這麼告訴她了,就在他用她的圍巾扼住她的咽喉的時候。
莫妮卡睜大了眼睛,纖巧的手指扣在自己頸間的束縛上,粗喘著氣,只是為了獲得最後的一絲空氣,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放心吧,”他輕聲說,注視著她的眼睛里有著一絲狂喜。日向寺近乎迷戀地看著她的虹膜因為失去控制而漸漸變成金色——她的最後一絲力氣大概都在手指上吧,畢竟活命還是比用人類的外表融入社會更重要。
“圍巾太柔軟,它頂多只能讓你休克。”
日向寺看著她慢慢閉上了眼睛。
啪嗒。
日向寺抬起頭,看著一個纖細的身影從暗影中奔跑離開。
XXX
“綾瀨川小姐,”日向寺站在了神社前對巫女露出微笑。有著凌然眼神的巫女對他點了點頭,正打算開口——但是日向寺又繼續說:“我希望捐贈一座鳥居。可以和你詳談嗎?”
“不久前的祭典,不知道你還記得不記得。”他說,“我對神社的鳥居印象深刻,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能參與這些壯觀建築的組成。祭典那天在燈火照耀下太美麗了——”
他停下笑了起來:“不對,你是策劃者,那天也一直在祭典上監察,不可能不知道吧。希望你那天有到處逛逛,我玩得很愉快呢。”
“愉快,不是我會用來形容那一天的方式,”綾瀨川結花把手中的掃帚放到墻邊,然後笑著對上以探究眼神看著自己的男人說,“請到這邊來。”
TBC



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46573/
短的要死,不要介意,小结之后会补上新的线索。
————————————————————————————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野津虎助压抑着怒气,如果说这愤怒有个温度的话,此刻他湿透的外套应该早就泛起蒸汽了。这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对自己的同胞兄弟产生如此的怒气。要不是一侧的座位之上,他的“临时盟友”坂野慎之介正坐在此处,他几乎无法克制冲上去狠揍这位趾高气昂的胞弟一拳。
野津雪助也抱着手臂仰起头,野津家的两兄弟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互相审视着对方的表情,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
“够了。”坂野慎之介站了起来,“野津中佐,麻烦您先出去吧。”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坂野先生。”虎助的脸色阴沉,他完全没有料到那个精明的年轻企业家竟然会说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话。
“关于今日发生的事,我想单独和这位宪兵先生谈一谈。”
“当然,稳健的坂野先生的提议一向令人放心。”野津虎助打断了对方的话,嘴角弯起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海军的利益理所当然不会受到损害,没错吧?”
坂野慎之介叹了口气,但语气依然是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看着海军中佐的双眼:“请您,放心。”
“如你所愿。”
虎助冲出了房间,他需要冷静一下。说实话他并不埋怨慎之介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如此情况之下把自己清出房间对谈判而言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此刻自己已经全无判断能力。
但在此刻,等待无疑是煎熬。
烦躁不安在走廊中的踱步,他知道自己看起来很糟——为了等待消息而早早候在一边的佐藤工头似乎也被传染了这份情绪,这位老船工咽了口唾沫开口问道。
“坂野老爷,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虎助将手用力按在面颊之上,克制着自己,他不能用这张面孔去见那些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的船工,“但是他会有办法的。”
佐藤看起来松了一口气。如果可以的话,虎助也想如此就能骗过自己,但光是努力做出一副冷静的表情已经费劲了全力。雪助的出现让他摸不着头脑,他的表现更是,除了是来找麻烦的,虎助无法给自己胞弟的出现找到更好的理由。无法做到单单在此安静的等待,野津虎助停下了如困兽一般的踱步,锁定了自己的目标。
“叫上所有人,去仓库。”
“诶?可是大家都刚冷……”
“我要知道是谁通知了宪兵。”
送走那位麻烦的野津少佐已经是几小时之后,坂野慎之介只感到身心俱疲。不出他所料,这位宪兵少佐似乎并不是有意上门找麻烦,但无论如何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即便不想惹上宪兵队的麻烦,自己也要花些时间做好再和那些军部中大人物周旋的准备才是。
至少停工是可以暂时避免,一如他和那位宪兵少佐所说,因为船坞的下水本就是以岩洞改装而成,涨潮之时也偶会发生废弃物随着洋流倒灌,如此推测铁栏之外的尸体若是顺着海水飘来的可能性也极大,从尸体看也无法即可定义谋杀。既然已经全权委托野津雪助少佐调查,所需要做的只是努力配合而已。
工人们早已离去,慎之介走过空荡荡的船坞,却看到一位熟悉的身影。
“他走了?”
野津虎助也注意到了慎之介的存在,他将面上的口罩褪下抢先开口问道。
“走了。” 知道他在问的是谁,身心俱疲的企业家点了点头,又皱起了眉头。慎之介瞥到了这位身材高大的海军中佐手背,在不久之前还完好无伤的手渗着鲜血,血痕顺着绷带蔓延而下,可不只是擦伤那么简单。
注意到了慎之介的视线,虎助将那只手收到了背后,他不耐烦的回答:“人没死,我只用了左手。”
据说,不久前工人们又被重新聚集在仓库,就算是用脚趾思考也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坂野先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处理内奸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相对于激烈的处置方式也能给剩下的船工敲个警钟。
“宪兵那边暂时不用担心,再不济,也会有办法的,操之过急只会浪费精力。”虽然知道对方早已冷静下来,慎之介依然说了下去。
“早些休息吧,坂野先生。”
野津虎助点了点头,他从容的换上了防水的长靴,再次测试了手电的亮度。
“野津中佐呢?”
“下去看看。”
见识过了野津家两位兄弟的脾气,此刻他也无意劝阻对方。
夏日的气息已经逐渐到来,可是此刻慎之介周身却无暖意,点头致意之后他头也不回的走向了厂门之外,此刻的他只想早些离开,哪怕在家中等待的是那只性格叵测的妖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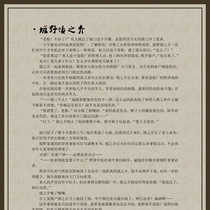
门被猛烈的拍击着,野津虎助不耐烦的翻了个身,坐了起来。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外套,他看向了挂钟。
6点。
太早了,就算是赤城也回来的太早了。
提前告别甜美梦境的沉重感让他身心俱疲,拖着步子他走向了玄关。
那敲击声并未停下,那噪音穿透耳膜,似乎是谁用手掌和身体一起撞击在门板上一样,只是为了让这声音停下,野津虎助打开了门。而在门外的人,却是他预料之外。
坂野家总是诡事缠身。
无论是走失的孩童,还是奇怪的妖异,凡是在此处工作过的人都已见怪不怪。毕竟作为军工造船厂,此处也不是一个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地方。倒不如说,得是有些胆量的船工才会与这家船厂签下合约,留下工作。
因此看到佐藤工头的面容时,野津虎助是有些惊讶的。这名将近五十岁的老船工表情惊慌,工服已经整个沁湿,裤腿和长靴上沾满的泥水,再加上因为一路从厂房顶着大雨跑到这里,他张开嘴一时间居然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活脱脱一副溺水模样。
“船……下水……鬼……女人……”
“慢慢来。”虎助从他的只言片语里收集着讯息,这位老船工的失态让他有些焦躁,伸出手拍了拍对方的脊背,他安慰道。
“石田他在清理管道的时候被头发拖进海里了!”
佐藤工头被这几下拍的喘过了气,他深吸了一口并一口气喊了出来。
“在船坞……?”这粗狂的嗓门像是一记重锤敲在海军中佐的脑袋上,让他的意识逐渐清醒了过来,他揉着太阳穴拿起来长靴向工头最后确认了一次事发地点,便冲了出去。
从夜间开始就一直飘着小雨,直到冲出房门时,野津虎助才意识到似乎应该拿一把雨伞。
船工之间一直有着奇妙的传闻,夜间船坞里的女性呜咽之声,从水槽里捞出的和服腰带,下水内漂出的女性头发。但传闻毕竟是传闻,这里是坂野家,虎助更愿意相信一切不过是船工的臆想,或是某只妖异的恶作剧。
……被头发拖进海里?只是被废弃物缠住了脚吧……但是出人命就麻烦了。无法散去的不安感让虎助的脚步变为了一阵小跑。
“中佐先生!”
“野津中佐先生……!”
工人们本围作了一团,在看到虎助来到现场之时,纷纷对他行礼并让开了一条小道。虎助挤过嘈杂的人群来到中央,那名落水的工人石田已经被人救了上来,有些虚弱的躺靠在一侧。虽然经过了紧急救援,脚上包着绷带似乎是受了些轻伤,只是看起来吓得不轻,有些虚弱而已。
至少没丢命,但指望从当事人嘴里能听到点什么大概不可能了。虎助松了口气,看向了周围的人群。
“头发……下水…………女鬼……”
工人们七嘴八舌的对他搭着话,虎助从一人手中抢过了扳手,不耐烦的用力敲响了一侧的钢筋骨架。敲击声回响在船坞中,被这声音所震慑,人群终于恢复了安静和秩序。
“出来一个人说话,我要知道全程。”
一位身材近乎和他一般高大的男性走了出来,这名工人并没有穿着外衣,鞋也拎在手中,似乎是刚刚下水救援的其中一人。
看着那张脸虎助才努力的回忆出了对方的名字:“小野?”
“是的,中佐。”那名高大的船工点了点头,却只说出这四个字。他的面容上透出了一如佐藤工头那般深深的不安。但一连串的无厘头事件只让虎助觉得恼怒,他感到自己的怒气从胸中升起——但那名船工战战兢兢的举起了右手,在看清那手掌中物后,仿佛被一桶冰水浇盖而过,蓄积的怒气消散了。
虎助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那刺骨的寒冷由脚下穿过全身。他伸出了手,克制着自己,用手指捻起了那几缕乌黑色丝绸。湿润而黏稠的触感昭示着这濡湿的长发并非人造之物,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某位……人类之身。
感到所有人的视线如芒刺一般在他周身,野津虎助僵硬的点了点头,示意那位早已无法冷静的工人放开手中之物,退向一边。
将外套脱下,在此刻野津中佐必须保持镇定:“叫几个胆大的,我们下去看看。”
普通人类也无法忍受这里散发出的恶臭,虎助屏住呼吸,从小野手中接过了一只口罩。直到那白色织物完全掩盖住口鼻,他才张嘴深深的吸进了第一口气。
即便隔着厚实的工业口罩,腐烂而又刺鼻的气味依然灌入了虎助的口鼻之中。对于山犬半妖来说,没事来下水道闲晃可不是什么好选择。更何况是雨天,原本潮湿发霉的地下管道中流淌着污泥,有些气馁想起自己还穿身那身白衣,虎助带着三名船工试探着在水道中前进。
十米,二十米……五十米……
暂时并没有任何发现,很快管道就要到了尽头。也许最后他们会无功而返——这也是虎助所期望的,毕竟那只是几缕头发,可能只是不小心顺着洋流飘散于此,又不小心缠在了石田脚踝上的杂物中。只要走完这一节,确定并无异样,他就可以安心回到船坞之中,想办法编些激励人心的句子控制局面就好。
即便这样安慰着自己,虎助依然感到自己的神经紧绷,不得不承认似乎有一丝丝恐惧徘徊在他的心中。阴雨天的阳光显得有些阴冷,四周腐朽的木板和杂乱的钢铁废料之间,黑暗无声的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偶尔传来细微的声响,令人汗毛倒立。
下水的出口就在眼前,虎助低着头有些麻木的看着脚下的泥流逐渐被阳光所照亮,背后却传来惊呼。
小野总是一惊一乍的,这是第三次了,大概又是被水里的螺钉绊住了脚吧,虎助有些无奈的想。他想要回头,但那狭长的影子锁住了他的一切动作。虎助无法控制的抬起头,看向了小野所指的方向。
日出的逆光之下,在排水口的围栏之外,那是一只纤弱又白皙的手。
有一位胆大的船工似乎想上前去,却被虎助伸手拦住,他对这位年轻人摇了摇头。
虎助深吸了一口气,大脑已经开始逐渐适应四周腐臭的气息,所以在他跨过那堆积的杂物,看到那名少女的尸首之时,他感到自己的呼吸依然是平稳的。
那只完全失去血色的手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姿势凝固在水面之外,一如那失去光泽的瞳仁中印出的绝望一般。他伸出手替她解开了束缚在脖颈之上的纠缠之物……头发,水草与不知名的织物,在少女的耳际似乎闪着一缕青色的光芒,近乎通明淡蓝色鳞片附着在青色的皮肤之上。
尸首已经开始肿胀,并轻微的腐烂,但按照目前的气温来判断,这位姑娘死去的时间并不久。
“小野。”
“在在……”在背后不远处,船工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回应着。
“去告诉坂野先生,今日封港。”
——————————————————————————————————————
本事件由妖都侦探剧组特别发布,如有疑问不欢迎质疑。
那啥,我交棒了。你们看着办吧。
如果有人看到了bug,一定是你的爱不够。
老改错字对不起响应的人,所以干脆连剧情也改了。
留言的也对不起了!
————————————————————————
野津中佐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喜爱观察别人的人,所以当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注视着对方幽暗的黑色瞳孔好一阵子时间时,是有些吃惊的。
“怎么,我这位可怜人有那么值得你注意吗?”那位身着制服,看起来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举起酒杯。他的头部和一只眼睛包裹在绷带之中,手臂似乎也受了伤。野津虎助顺势看向了对方的肩章——少佐,恩,陆军。
他继续发问。
“是在战场上受的伤吗?”
而被提问之人立刻转过头来,似乎抬眼看向了虎助的肩章,“是的中佐阁下,是战场的伤。中佐有那么灵敏的鼻子,不如帮我们去战场上找找地雷如何?”
“……”
知道是自己理亏,提问者收回了视线看向了吧台,中断了这场无聊的对视。老实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今日的反常……也许,是因为那股淡淡的血腥味。
若是伤口的气味,也不是说不通。
如此说服着自己,但他依然为对方所说的话而不快,或者说,对这个人,无理由的感到不愉快。
抬头看向了一旁的挂钟,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原本来到此处便是为了约见一位老友,本是喝酒绝不会迟到的那位,这次居然迟到了。
食物的香气开始散发在空气中,他听见自己的胃发出了不满的声响。
太慢了。
虎助有些抱怨的敲了敲桌面,他忍不住再次转过身,偷偷看着那位陆军少佐用他仅剩的那只手臂,一点一点的切开他桌上的食物送入嘴中。
但如果以军人的标准来看,对方的手似乎太过干净了,并没有明显的伤口,似乎连老茧都有仔细修过。
而在那肉块被划开之时,甚至可以从那手势中读出一丝优雅……
真是奇怪啊……
这么想着,虎助撑起了脸,但依然无法移开视线。
此时自己的脸色应该相当难看吧。
直到对方满足将酒杯中剩余不多的液体灌入口中,认真擦干净了脸,手和沾上了汤汁的绷带,然后站了起来,似乎是打算离开了。
野津虎助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看向正在吧台后忙碌的店员,仿佛艺术品一般的食物堆积被慢慢的堆积在餐盘之内。
店门伴随着清脆的铃声被一把推开,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似乎要将那食物的香气灌入自己的鼻孔之中——但虎助所能闻到的却是一股刺鼻的血腥之味。
原本身为半妖,虎助的嗅觉就比一般人灵敏许多。此时完全没有防备,那呛鼻的气味让他狠狠的打了个激灵。
这绝不是什么伤口的气味。
本能的扶住了自己的佩刀,虎助猛然站了起来,木质的板凳在地面上摩擦,发出了巨大的噪音,人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着这位有些失态的年轻男性,脸上写满了疑惑。
管不了那么多了。
把酒钱丢在了桌面之上,他冲出了店门之外。夜间的空气清凉而有些湿润,虎助深吸了一口气,那残留的血腥味还停留在空气之中——这个动作多少让他觉得有些丢脸。
已是深夜,街上并没有车辆,本就是灯光甚少的小巷之内,也并没有太多混杂的气味,顺着那逐渐消散的气息,他快步追了上去。
气味越发模糊起来,这一代的市区状况并不大好,建筑物老旧不堪,不知是何物发霉的恶臭从街角传来,街灯时明时暗。
追踪可不是自己的老本行,虎助这么自暴自弃的想着,或者说,今天原本就不该来招惹这种破事。
他的脚步尽量放轻,感受着周围的动静。
此时的街道却是寂静无声,无法判断气味的来源,似乎连对方的脚步声也远去了。
追丢了吗?虎助懊恼咂了咂嘴,強行压下了胸中的躁动感,快步朝着巷子的另一端摸了过去。
通路由窄变宽,很快将他引向了一条稍显宽敞的街道,血腥味几乎已经消失了,但此刻却有人声从拐角处传来。
灯光有些灰暗,但依然不妨碍探查,虎助侧靠在墙壁之上向外张望。单凭地上晃动的人影和断断续续的交谈之声,对方似乎是有三人。
“这小姑娘抓了也好,要不到赔偿金,就让我们兄弟乐一乐。”
本就是以混乱著称的老街之上,发生这种事也算是意料之内。原本虎助便是不喜欢这些下滥低劣之人,再加上此时已经确认自己追踪失败以失败告终,那股挫败之气只让自己更加血气上涌。
但还不至于失去理智。
即便是自己,想要同时面对三人,想从正面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此时无法判断对方的武装程度,或是否有佩枪。此时应当以直接救出那位被绑来的姑娘,并尽量不惊动其他人为优先才是。
紧握自己的佩刀,虎助压低自己的身体借着街角的黑暗之处缓慢的接近,那股混着着浓烈霉臭的气味越发强烈,多少让他有些分心。
不远处,那位正在收拾赃物的人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随着逐渐靠近,对方的身形都可以逐渐看清,三人皆是普通身高的男性,还有一人在马车之上,而最后一人在另一侧似乎在收拾着什么。
只要靠近他打晕过去,拖进一旁的巷内的话……
等等……
……马……车?!
虎助看着那黑暗中马车的轮廓,刚想要向后退去,那匹高大的花色驮马立刻高声嘶鸣起来。
马匹鸣叫着,不安的用前蹄踏击地面,站在马车上那位看起来是就是带头的,他立刻站起身,高呼着让自己的同伴警戒。
而此时不出意外的,距离最近的这名年轻男性也立刻发现了虎助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去陆军……
“……!”
这名年轻人在看到虎助的肩章和佩刀之时,立刻大声的高呼起来,看起来颇为惊慌失措:“军,军部的狗腿!”
“闭嘴。”
虽然不论从“狗”还是从“腿”这方面都无法反驳,虎助有些不耐烦的想着,直接抽刀上前,手腕一转剑尖向前,就这么直直刺在了对方的鼻梁之上。
想象中的献血迸裂之景并未降临。
那是当然的,毕竟是为民服务的军队,哪有滥杀平民的道理,当然是带着鞘的。
这一下似乎比自己想象中的更重,但却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名为野津虎助的海军中佐被一些事分了心,他享受着着手中那血肉和牙齿迸裂的触感——通常这时候他并不愿意分心,然而这时他却忍不住将注意力放向了路面的另一侧。
另一位正在收拾东西的盗贼似乎也发现了什么一般,高声叫喊起来,但那声音顷刻之间立刻变成沉闷的呜咽和呻吟。
虎助吸了吸鼻子,就算不用回头,他也知道在另一侧出现的人是谁。
……另一名“野津”。
这多少让他有些意外,虽然其实自己再清楚不过,实为胞胎的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一样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好手。
看着与自己身型相似,却有着一头亮银色短发的胞弟,虎助皱起了眉。此时虽然有个帮手却是不错,但发生过那么多后,他并未想过再与雪助见面时会是这样的情形。
而更令他烦恼的是,他并不想承认这位有和自己极其相似面容的兄弟,有时候看起来真是帅气极了。
两位野津的动作一气呵成,在一瞬间失去两名同伴的盗贼首领似乎吃了一惊,而此时能保命的办法不多,为数不多的理智让他爬进车内,抓起了那名似乎是已经昏迷过去的女性。
“混蛋狗腿,不想让这小姑娘没命就让开。”
虎助眯起了眼,他知道对方并没有开玩笑。
那位看起来是16.7岁的少女,眼口被掩住,手臂则被绑在背后,看样子和打扮似乎一位华族小姐。一把闪着冰冷光芒的小刀正比在这位少女的脖颈之上。
“放人,我们就让你走。”
对方意思再明显不过,但虎助依然拦在车前不想退让。鲜血顺着刀柄低落,血珠蜿蜒顺着脖颈流下慢慢的染红了少女的衣襟。虎助并无意激起对方的对抗心,但此时他需要再拖延一会。
他对那份默契颇有信心,这是他们小时候常玩的游戏……
但不知为何这份信心伴随着少女脖颈上逐渐拉长的伤口,却有些动摇了起来。
而对方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干脆将少女一把甩开,为首的那名盗贼把手中的匕首直接刺向了驮马,马匹吃痛,惨叫一声扬起前蹄向前撞去,虎助本想要闪开,却发现失去了支点的少女就这么滚下了马车。并没有太多思考时间,他此刻所能做的只是将对方护在怀中。
“啧。”
目送绝尘而去的马车,野津雪助甩了甩刀背,他的外衣上面似乎沾了一些血,这让他有些不高兴。
他看着自己的兄弟狼狈的坐在地上,怀中正护着那名被绑架的少女,来不及回避马车的冲撞,虎助手臂上的外衣撕破了,红色的痕迹应该是血吧。
“不去追吗?”
虎助抬头看向已经收起武器开始整理自己外衣的雪助,看样子他并未打算去追捕那驾车逃走的盗贼。
“宪兵来管这种闲事,让那些警察吃白饭吗?”
雪助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即便是半妖他也不想和马比什么脚力。两人沉默了一会,雪助伸出了手,而虎助则拉着他站了起来——他的小腿也受了伤。在确定自己的兄弟行动自如后,雪助依然看着自己的胞兄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离开,他在等。
虎助看向怀中已经完全晕过去的少女叹了一口气,只是这点皮外伤去一下医院倒是没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他并不想如此拜托自己这位兄弟。轻咳了一声,他才开口:“我在酒馆约了人……”
“我知道了。”
野津雪助正了正衣襟,头也不回的向街道的另一侧走去,“然后我会去报警。”
————————————————————————————————
之后虎助送铃铃去了医院,就接上她的两篇算是解释和后续。
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143/ http://elfartworld.com/works/41786/
惊慌之下不知道填谁的名字好,就写了自己的,意识模糊的铃铃则抓住了对方的手。
恩,就是这么开始的。
雪助则受了拜托去见了那个被爽约的可怜人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