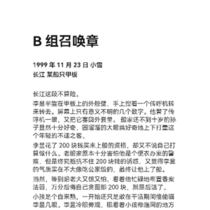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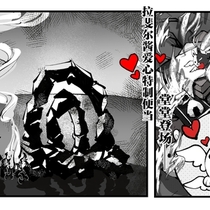




本来想赶儿童节(??)更新的但出了点事没赶上……总之终于迈入了四月!并在四月初来了一次花家书院的副本遗址夜游惊魂,虽然最后啥也没发现……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19400/(的后半部分)】
谭枢下了衙出来的时候,门口有人在等他。
纪舒平的公服还没有换下来,一身银绯的站在阶下,瞧过去稍有些打眼。他去年才刚离开皇城司,人缘又好,许多同僚都还记得他,便陆陆续续过来打招呼。他心里仿佛藏了事,眉头不自觉微微收紧着,一面简短应答着同僚们的问候,一面目光却直往门口瞟,等终于见着谭枢高挑的身影出现的时候表情才稍缓了缓,向跟自己寒暄着的旧同僚道了抱歉,快步走过去截住他。
“劭周,我有事与你商量。”
他的语气郑重,谭枢听出来并不像是寻常闲谈的意思,便也没多费时间在寒暄上,只简洁地点了一下头。
“拣个安静些的地方说。”
怡乐楼临近荐桥,在繁华靡丽的行都算不上什么数得出名头的大店,然而因着交通便利的缘故,每日里人流却也颇为熙攘。好在楼内的酒阁子素来以闹中取静著名,沿着二楼的走廊左拐右折,转进雅间之后就隔开了前厅嘈杂的人声,连隔壁客人的谈笑也不会听见。
纪舒平略有些不大耐烦地扬扬手,让伙计撤走桌上小山也似的看盘。明前新焙的团茶带着袅袅热气薰出含蓄清雅的淡香,然而饮茶的人却并没有细细品啜的兴致,只草草抿了一口,待端茶的人轻掩门扉走开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了谭枢。
“花家书院的事,你听说了吗?”
三月末的时候城西厢的花家书院招亲,这在见天都有新鲜事的临安城里原是件投个石子都听不见响的小事,然而当招亲结束,花家闭门谢客后的第二天清晨,却有浑身浴血,神态惊惶的人冲进钱塘县衙报官,称这花家书院实是彻头彻尾的吃人书院。他们将一众参与招亲者骗入书院,困在地底密室内如猪羊一般任意屠戮,甚至还将人肉做成饭菜待客。
县衙的人一开始还觉得只是他受了惊吓的胡言乱语,拖拖拉拉遣人前去查看的时候,才发现实情竟比报案人颠三倒四的描述还要惊人。花家书院的侧院地下埋了层层叠叠新旧交替的白骨,官府赶到的时候不知被何人全部起了出来,草草和几具新鲜尸体一起掩埋在书院后院山坡上,规模却依旧骇人。欲盖弥彰的样子,更教人琢磨不透用意。
因着此事实在太过耸人听闻,恐怕百姓以讹传讹多生事端,钱塘县衙当即便封锁了消息。然而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吃人书院的传闻在市井里传得飞快,加上真真假假的亲历者证言,愈发像一个离奇古怪的吓唬人的故事。
然而倘若只是个吓唬人的故事,显然并不至于让纪舒平摆出这样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皇城司掌宫门锁钥,司都内安危,临安城里一片叶子落下来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自然少不了这一件。谭枢垂着睫毛啜了一口茶,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把他所听说过的这桩案子从头到尾飞快地梳理了一遍,一时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别值得在意的地方,便只谨慎的抬眼望了望他,眼神里带一些探询的意思。
“……知道一些。怎么?”
纪舒平没有马上答他,心不在焉地摩挲着手心里油滴鹧鸪斑的黑釉建盏,像是在犹豫措辞。片刻之后才将盏内残茶一口饮尽,注视着盏内残存的一圈雪沫开了口。
“有个认识的人,恰好在那日参与搜查花家书院的行列中。——此事本不应为外人道,然而昨日他邀我喝酒,多饮了些,无意间便多说了点细节。”
纪舒平顿了顿,抬起眼去看谭枢。对方只是一如既往神色沉稳地等待着下文,目光礼貌而专注地停留在他鼻尖到下巴之间的位置上,并不令人觉得轻浮随意,也不显得咄咄逼人。纪舒平抿了抿嘴唇,沉声继续往下说。
“……他说,花家书院的地底有一座奇怪的大厅,初看瞧不出端倪来,仔细丈量才发现是由几个小厅拼作六角形状,地面还刻着花纹繁复的沟槽,然而每条沟槽都汇往中央的一个窨井……”
谭枢的眼神随着他的描述轻微地动了动,然而并没有马上吱声。
“六角厅附近发现了大滩血迹和分尸的工具,虽然并未见到尸体——也有可能是被人掩埋了,后来挖出的尸首据说有的亦残缺不全。但更重要的是,满地沟槽和中央的窨井都透着浓重的血腥气,已经被染成了赤褐色,显然是经年累月有血水浸润的缘故。……劭周,你不觉得耳熟吗?”
谭枢抬了抬眼神迎上他投过来的目光,以不易觉察的微小幅度轻轻地蹙起了眉心。
“夔州?”
纪舒平没有答,然而坦率直视他的目光里已经分明地写明了他的意思。谭枢的眉心以肉眼可见的幅度收紧起来,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口。
“……先前未过多关注此案细节,确实是我失察了。然而这事现在不在我手里,若这时要追下去,恐怕有些麻烦。”
纪舒平点了点头,没什么意外的表情,显然这事他早已经知道。
“小韩那里?还是阮指挥?”
谭枢摇了摇头。
“此案虽然离奇,恐怕责审的人暂时还未联想到淫祀巫蛊之类的事上,案子多半还留在钱塘县衙那里,皇司没有插手。——不过,豫持兄,请恕我直言问一句,你查问此事,是于私,还是于公?”
纪舒平避开了他直视过来的视线。
“……是我自己想查。”
谭枢柔和的声音几乎不像是警告,而像是恳求。
“你当还记得那时候官家说了什么。”
纪舒平垂了垂眼睛,有些沉郁地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是在表达懊恼还是不满。
“我知道官家不欲细究此事。只是……”
谭枢摇摇头说了句“天意难测”,像是即便在静室里也不愿听他口出无状引来言官弹劾似的,倒叫纪舒平忍不住看着他,短促地笑了笑。
“劭周,你不必拿这话来堵我。我也并非对前夔路转运使和天家阴私有什么非要刨根问底的执念。如果说想要弄明白什么……比起许确背后的人,我更在意的是那位稜驣神的大巫。——还记得那个你来时刨地三尺也没找出来的大巫吗?”
谭枢略点了点头。这件事收尾的方式的确是显得出人意料了点,然而追究到纪舒平一开始被遣出去的缘故,确确实实是“夔路淫祀,与贵人勾连,杀人祭鬼目无法纪”。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官家,在接到表文后都一针见血指出了“此必有大巫倡之”,然而问题偏偏在于这个事件的核心,那位在夔州一路势力一度呼风唤雨的稜驣神大巫,在这事件暴露之后竟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仿佛凭空蒸发了似的,以谭枢之能,竟然也没能查出一点蛛丝马迹。而后更是只能在官家的指示下草草收尾,别无后话。
“你未亲见过,恐怕没有什么实感。我见过一次,那人身上明显是有功夫的,而且多半不是什么正经功夫,邪门得很。回来之后我便留意了一下……你莫皱眉,不过是找可靠的朋友探听些消息……说是可能出自于江湖上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做星罗宫。——更巧的是,这次花家书院的事,我听说,也与这个星罗宫脱不开干系。
“劭周,我想到那个地牢里去看一看。”
纪舒平直率地说。
“道听途说来的消息毕竟不能尽信。然而书院现下叫钱塘县封了,不许人进去,我也不方便借机速房的名头。不过他们只派两个人把了正门,想用别的方式进去,也并不很难。”
谭枢沉默了一会儿。纪舒平也没说话,静谧的雅室内听不见什么多余的声音,连角落里梅花银熏炉的香烟也只细细一线,袅袅地往上攀升。
“……这会儿还是月初,月光偏淡,落得又早,虽说方便遮掩一下行迹,不过若为了查探起见,还是需有些光线的,放在前半夜要好些。”
谭枢轻声提着建议,纪舒平点了点头。谭枢顿了一顿,又问他。
“你打算几时去?今晚吗?”
“不……今晚还是略仓促了点,我想稍做些准备,明晚再去。”
“好。明晚戌末时我去寻你,可好?”
这一句却让纪舒平露出点意外的表情来。
“你同我一道去?”
谭枢亦回望他,表情里倒像是也有一些诧异。
“怎么?……我想夔州之事我亦曾参与,或许也能有些许助力……不过若你觉得我去不好……”
“不是。”
纪舒平截断了谭枢的话,笑意攀上他唇角,仿佛扫去了从方才起一直盘旋在他眉间的隐忧似的。
“只是觉得你不必非要来跟我蹚这一趟浑水。”
谭枢也笑了笑。
“豫持兄,且不论我在此事中的干系,这浑水我蹚与不蹚,早就身在其间了。倒是你这般见外,却是置你我十年情谊于何地?”
纪舒平大笑,轻拍了拍谭枢手臂,语气诚挚,眼里仿佛闪着光。
“我知道。是我生分了。”
戌末亥初对于临安城来说还算不上晚,御街上夜市灯火通明,远还没到入睡的时候。即便拐进城西厢,亦不时能见到从各处瓦子勾栏里兴尽晚归的人,醉醺醺的或是扶着从人,或是三两为伴,口中喧笑哼唱着方才听来的新曲,提了灯烛照路。倒是衬得换下了官服的两人走在路上丝毫引不起什么人注目。
花家书院在临近钱塘门的偏僻地方,附近没几户人家,灯火稀疏得很。一勾上弦月这时候已经落得很低,稀薄朦胧地照着黑魆魆的园子,显得比传闻中的吃人书院还要多几分吓人。门口确实有两个钱塘县的兵卒守着贴了封条的正门,瞧去年轻得很,多半是同僚欺生,才被排挤来担这么个苦差事,这会儿心不在焉地凑在一处坐着聊天,浑然不察几步之外两个人影悄无声息地攀上院墙,翻进了被封锁的院子。
纪舒平伤了右手之后,攀爬上便有些不太方便,落地的时候谭枢不着痕迹地借他一把力,换了他一个感激的点头。
黯淡的月光被院墙遮去了一大半,只能见墙边密密栽着树木,生得茂盛,却似乎未怎么修剪过,枝桠横斜,虬结在一起,费了一些功夫才钻过去。院子方方正正,不大,地面却像是被整个翻过来似的,被彻底挖开过,七零八落地露着新鲜的泥土。谭枢弯腰捻了一捻,指尖还有些潮湿的雨气,他直起身压低声音对身旁的纪舒平说话。
“恐怕此处便是那埋尸的院子。”
纪舒平从一开始起注意力便落在院子正中那口井上,此刻也直盯着那在一地杂乱衬托下显得有些突兀的井口,没有移开视线。听见谭枢说话,只轻轻嗯了一声,径直便朝井边走过去。
昏暗的光线只够勉强看清井边垂下的软梯,再往下便是一片漆黑。纪舒平往井里探了探身子,伸手试了试梯子的分量。
“我下去看看。”
谭枢应了声好,替他守了井口,看着纪舒平沿着软梯爬下去。过了一会儿听见井底传来一声轻而沉闷的声响,知道他已经着了地,四下环顾并未见到什么异状,便也跟着爬了下去。
踩到井底的时候周围并不是一片漆黑,纪舒平点了一只随身带来的琉璃灯球,暖橘色的光被封在透明的琉璃罩里,不摇不颤地被他举在手里照亮面前一扇闭紧的门。
谭枢落地的时候便借着微光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笔直的井壁由普通的砖石砌成,除了没有水,和一般的水井内壁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出什么花样。光秃秃的砖壁上只有这扇小门看起来是唯一的出入口。
“这里通往地牢?”
“多半是。”
纪舒平简洁地答他,一面举着灯仔细去照门把,看清的时候忍不住皱起了眉。
“……他们居然把门封死了。”
门把被铁条密密实实缠了好几圈,边缘灌了铅水,封得严严实实。纪舒平与谭枢两人尝试了好半天都没能撬开一道缝,只得作罢。除了那道被封死的门,井底并无任何机关花巧,将狭窄的空间细细摸过一圈之后,一无所获的两人只能先后沿着软梯爬回地面。
四月初的临安,地气已经很暖了,中午时分甚至可以说得上炎热,然而还未完全入夏,太阳落下之后还是有些沁人的凉意。花家书院里林木繁茂,地方又荒僻,更透着一股仿佛挥之不去似的森冷寒气。沿着明显疏于打理而显得破败的走廊往前厅走的时候,忽然有不知是猫还是别的什么活物,在草丛里窸窸窣窣动了几下,惹得两人警惕地把手搭上刀柄,凝神看去却只见小小一团黑影飞快蹿过走廊消失不见,只是虚惊一场。
前厅一无异状,门背后整齐码放着几张长桌,拭抹得一干二净,和积着灰尘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几张桌椅,这个厅堂的其他部分像是很久未使用过一般,亦不见有人踏入的足迹。与前厅隔着一条走道相连的书堂里摆了些零散的书籍,一些陈旧的儒家经注、若干文人的笔记志略,杂着些坊间流传的话本,上面倒是有些新近翻阅过的痕迹。书堂再往里,隔成小间的厢房看起来便是花家安置招亲客人的客房了。据说花家便是在这里安了机关,半夜将床板翻转,让熟睡的客人跌入地牢的。
客房内每间陈设看来都十分相似,薄薄的床板底下铺着的竟然是厚厚的铁板,从敲击的回声上听来少说也有半寸来厚。谭枢抵着床板的边缘试了试力,朝纪舒平摇了摇头。
“……是玄铁。”
纪舒平皱起了眉头。这样厚度的玄铁,若是寻不到机括,怕是用火烧上三天三夜也不见得能让它损伤一丁点。一排二十余间房舍全部做这样布置,别的不说,这些托名为花家的人,至少在财力上恐怕颇为可观。
淡薄的月色早已经隐没到了高耸的围墙后面,院内肆意生长的树木更笼蔽了仅有的稀薄天光。浓重的黑暗里,两人小心地借着琉璃灯的微光试图从床板底下找出一条能够进入地牢的通路,然而开启的机括估计被藏在了地窖之内,以纪舒平与谭枢应对机关密室的经验,在沿着房舍屋角细细搜寻了一大圈之后,竟仍然不能得门而入。
寻觅了很长一段时间仍徒劳无功,却隐约听见隔了几条巷外梆子闷闷的响,打了三更。能翻的地方已经都摸过一遍,再多耽搁下去也无益处,便只能沿了墙角悄悄翻出去。此处的坊巷本就荒僻,这个时间更是静悄悄的全然不闻人声,一直到拐出市西坊才见几点寥落的灯光,老妪守着晚收的馄饨摊打着盹,一只黄猫儿在她系着围裙的膝上睡作一团。
“钱塘县这边我也会盯着些,有什么线索及时知会你。”
谭枢边走边偏头低声交代,纪舒平点点头应了一声好,又补了一句。
“倒也不必追得太紧,你那个位置,别惹了有心的人胡乱揣度。”
“却是不妨的。”
谭枢抬眼朝他感激地笑笑,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顺手摸出个扁小的酒壶,拧开壶盖,对着壶嘴便灌了几口。不知是灌得急了还是不小心,洒了几滴在衣襟领口,浓酽的酒香在夜风里泼散开来,熏人欲醉。纪舒平惊奇地挑了挑眉毛。
“……这又是怎么个说法?”
谭枢痛快地几口饮完,用手背拭了拭唇角,就手甩了几下空酒壶,残酒散乱地溅了几点在他袖口和袍角,酒气便愈发浓重,简直和刚散了什么酩酊的宴席下来的醉客没什么区别。他喝得急,酒意涌上来的就快,眼神虽然依旧清明,却显得比方才要稍微亮上几许。他拧上壶盖一边将酒壶收起一边带着歉意向纪舒平解释。
“朱翊今晚住我那儿。我不想惹他对当年之事再生什么疑惑,便对他说今晚我有酒席应酬……”
纪舒平不禁失笑。
“多大了,还老爱蹭着你住?你屋里的褥子是分外软和还是怎么回事?”
揶揄之后又忍不住摇了摇头。
“……倒是星罗宫这事,本来牵涉江湖,朝他打听恐怕更容易一些,只是……唉,还是罢了。”
谭枢知他依然不愿朱翊涉入天家是非,便也没再多说什么,只垂了垂眼睛,承应由别的渠道也替他查一查这个组织。
谭枢到家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掩了门往平日起居的院里走,在月洞门口停了停,吹熄了朱翊替他留的一盏照路的灯。往房里走的时候却意外地见朱翊举着个烛台正从书房里出来,着了寝衣,头发也披着,眯着眼睛掩口咽下半个呵欠,抬了烛火照照他,抽了抽鼻子。
“思堂春?能有七八年陈吧。谁请的客,手笔不小啊。”
也不像是真想听他答的样子,一面漫不经心问着,一面脚步也没停,擦过他肩膀便往厢房那头走,施施然从容自在,仿佛谭枢才是来借住的客人似的。
“小厨房灶上给你留了热水,自洗漱了去睡罢。我困了。”
谭枢略偏了偏身子,追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静静应了一声。
“好。”
【注】
•去钱塘县衙报案的是个npc(当然是pc也可以,剧情合适的话欢迎取用),县衙直到上班接警之后还拖拖拉拉了好一会儿才派人去看,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根据飞白里之人的意见,这会儿飞白已经把人全部埋好了……所以截止本文发生的时间点,从官府(钱塘县衙)的视角来看,暂时还并不知道是谁埋的人,对于为什么要把人挖出来重新埋也是十分懵逼的……【之后官府查案的进展如何,要看还有没有别的活的官家角色跟我撞剧情,总之如有需要欢迎沟通_(:3」∠)_】
•花家书院的床板是玄铁的梗照抄自羡老板投稿:http://elfartworld.com/works/140082/
•怡乐楼当然是我虚构的。【你



蚂蚁或者工蜂构建的巢穴与人们所生活的地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办公室与你所见的任何的办公室在装潢格局上没有任何的不同。从本质上来说,设计者的大脑似乎也是用冰冷的机械批量生产出来的,他们用电脑计算出来的完美比例以及被认为是最适宜的颜色搭配来掩盖着他们毫无想象力的事实。
空调发出着疲惫的声音,室内的温度明显低于人体感到舒适的界限。清洁液与空气清新剂显然都无法掩饰住这间办公室浓重到令人皱眉的烟味。一旁上了锁的书架仅仅是个拥有着摆设意义的存在,里面摆放着的书籍资料一丝不苟地用不同颜色的书签标上了号,但是实际上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经过翻阅了。
“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嚼子、马刺会永远锈蚀,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
第三行正数的一本厚皮笔记本里面夹着这样的纸条,它的质地让人想到莎草纸。上面的字字体有一种故作潦草的孩子气。
“所谓核残缺不过是中央政府的说辞。”斐迪南听到一个声音说道,“他们用核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我们认为残缺者是他们的失误,实际上这是他们用来除去异己的方式。我们所用的所有能源都是来自于那些被认为死去的人们身上的核。”
“愚蠢的阴谋论者。”斐迪南说话的时候就像是自言自语,他望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瞳孔带着一种刻意的涣散。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或者说,感受到了某种感召般地伸出手,在空中似乎是漫无目的地抓了两下——一根橡胶管映在了他的视网膜上,斐迪南像个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来吧,宝贝儿。”他冲着消过毒的针头说道,声音就像是耳语。蝎子卷曲的尾巴蛰了一下他青筋蛰伏的右手。
“这个充满智慧的文字的作者是伟大的马克•奥威尔,写于三年级政治课第十节‘思想本身是犯罪’。”
这个声音显然故作炫耀与洋洋自得,就如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不值得思考的荒谬与说话人让人感到的愚不可及一般。
“我不认为伟大可以用在任何自传中。”斐迪南漫不经心地靠在了椅背上,重心的后移让它发出了似乎有些不堪重负的呻吟,但是他的大脑却丝毫没有因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脊椎断裂的结局而发出警告,官能的快感如同在空旷教堂中唱诗班的声音不断回响,其余一切无暇兼顾。他的言语似乎也没有经过思考,“或许你认为执行官是一只巨大的蜥蜴?”
声音的主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或者说他一直就在那里。
“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斐迪南,谁没有一个难以启齿的过去呢?没有人会关心你八岁的时候把你母亲的金鱼缸打碎的事情呢?”马克把自己扔进了皮质沙发的怀抱里,用一种轻浮的口吻说道,“我敢打赌,把你如今的字迹与过去的用‘科学’的方式相对比,或许会得出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结论。”
叩击门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斐迪南的大脑当中跌跌撞撞,他花了一秒钟企图找回自己游离的神智,然后又用了半秒时间放弃了这个打算。
“进来。”他懒洋洋的说道。
门口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脸上有粉刺,下巴上有着没有刮干净的胡渣,就像是故意这样做的。他穿着警服,就像是所有那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自认为严酷的训练,而正义感、冲动与欠缺考虑的愚蠢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就像刚刚学会捕猎的豹子,牙尖嘴利,身手矫捷,可惜他们面对的是钢筋水泥的玉林。
“科长。”他的手中拿着一份报告书,“我很抱歉打扰您……会客。”他似乎在措辞上让人感到谦卑与客气的,但是实际上他在推门而入的瞬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话语,这个失误让人能够明显感受到一种急切的不满,以至于他那刻意的言语让人很明显地感受到这是在肚子里演练了许多遍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他在扫视了整个办公室后再小心地开始他的话语,那么显然不会那么尴尬——这个办公室中明显只有斐迪南的存在。
“我想上个月玛丽•奥利维亚女士的死仅仅以车祸事故妄下定论实在是缺乏考虑。”在一个令人尴尬——或许是仅仅令这个年轻的警察尴尬的停顿之后,他继续了他的话语。
“听听。”马克说着风凉话,“妄下定论。说得好,妄下定论。”
“哦?那你觉得她是怎么死的?”
“很明显,她是被人蓄意谋杀。”年轻的警察以一种笃定的语气说道,他似乎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那辆没有车牌的黑色卡车明显根本没有理由会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点……”
“所以,这很明显是卡车主受人教唆去刻意撞死奥利维亚女士。而实际上指使这场车祸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官员,因为奥利维亚女士企图以怀孕为理由勒索大笔抚养费。”斐迪南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言语,他以一种可笑的夸张模仿着警官那种语调。年轻的警官脸上露出了一种意料之外的惊讶。
“听着,士兵,做好你的分内之事。”警官注意到斐迪南的眼神这才从天花板上挪了下来,他在注视着自己的时候的表情有着一种明晰的空白,这种空白本应该只在醉酒者与先知脸上存在,“玛丽•奥利维亚死于车祸,肇事者逃逸。这是事实。除此之外,士兵,这不关你的事。”
钟表的声音响了三下。警官这才突然觉得这里的空调开得似乎过大了,以至于他甚至有些战栗。它的声音轰鸣得简直就像是低空飞行的直升机,而他是无辜碎裂的玻璃。
“你可以走了。”转椅的声音撕破了大脑中的蜂鸣,随即是一个冷漠而不容的质疑的声音。
“是的,先生。”
“你吓到他了。”马克的笑声隐隐传来,他用一种近乎神经质地手舞足蹈叫喊道,“天哪——不敢置信!他竟然在办公室里嗑药!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士兵,这不关你的事!’简直是独裁者!’
斐迪南不耐烦地摁住了太阳穴,马克的聒噪源源不断地撕咬着他的神经。
“闭嘴。”他忍无可忍地说道,然而实际上伴随着这句咆哮崩溃的是他脆弱的如同绷紧弓弦般的神经。他的身体中平白无故地涌现出一种愤怒。
他的大脑中无数的影像源源不断地涌现,有些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而更多的不是。一只从湍急河流中救起的野猫,在第三天死于破伤风;抽屉里的自杀专用左轮手枪;一个破损了的石碑;玛丽在死前脸上化的妆如同中世纪贵妇般的浮夸。
愤怒的热量渐渐流尽,他卷曲的手指松懈了下来,手掌心的疼痛感让他缓慢地意识到他当时准是把指甲都攥进了手心肉里,指间只能够感受到骨头,因为肉是黏在骨头上。骨头上面满是被风蚀的洞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