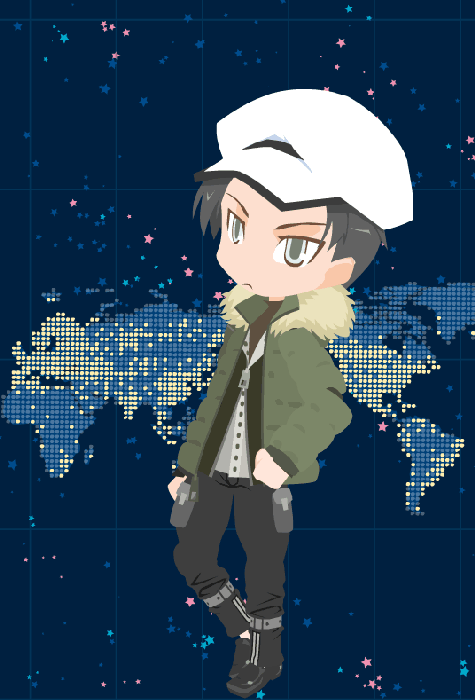
-

安嘉
-
零、第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平平无奇的生活里总有一件普通的事让你意识到不对劲,接着一个又一个荒唐的令人浑身发冷的想法从你脑子里窜出来,你知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于是你从那里逃走了。
只有你活了下来。
……
但它是一只残忍的活猎狗,它会永远追逐跑掉的猎物,从此以后你在洗脸、吃饭、赶路时都能听到它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能闻到它带有腥味的体臭,偶尔还会在寂静的夜里听见响亮的犬吠,让你从睡梦里突然惊起。
尽管传说号上人人都会讲几个拿手的恐怖传闻,但我只从我的养父那里听他说起过一次这种事,当时他喝得烂醉如泥,跟其他水手大肆吹嘘他是如何摆脱那个丑陋怪物的追杀的,甚至还提到了我——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把我从那个苦寒之地带出来是有原因的。
他完全忘记了我也在场。
第二天早晨,当他酒醒了,他就不再说了。到他死之前他再也没喝过酒,我也再没有听他说起过。
我出生在因纽特人的聚集地图克托亚图克,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海港小镇,直到2014年之前甚至没有开通公路。冬天最冷的时候通往内陆的河流会上冻,大家就从冰面上驱车到最近的人类城镇里出售猎物,通常都是海豹制品,驯鹿皮衣、皮帽或皮靴子等等,再购入一些必需品,比如盐、汽油和一些机械零件。但一旦冰河化冻,不在任何航线上的图克小镇就几乎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只能靠直升机才能达到。
倘若有人生病的话,就只能期盼冬季的来临,因为呼叫直升机的费用十分昂贵,而脆弱的婴幼儿的死亡率比大人更高,在这里养大一个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除了有钱以外还得有充足的运气。
从我出生以来几乎就没见过什么生人,整个聚集地大约只有200居民,人和人之间都十分熟悉,聚会时没有一件新鲜事儿可以讲。因此当他突然出现在图克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开心坏了。大人们也全盘接受了这个遭遇海难的外乡人,他们给了他毯子、烈酒和深刻的同情,承诺他,直到他的船修好之前,他都可以住在这里。他的到来使得沉寂的小镇眨眼间变得生机勃勃。
我父亲招待他在我家住了一晚上,按照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说我母亲在晚上去了他的房间。
那天晚上,我和我父亲并排睡在一起,因为我的房间让给了客人。但我一直没有睡着,我听到我父亲发出的鼾声,窗户外刮起惊人的风声,还有永不停息的海浪声,和隔壁的声响。
我躺在我父亲身边想着那个外乡人的来历,要知道对一个12岁的因纽特孩子来说,聚集地就是整个世界。他从白令海来,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说他从月亮上来一样奇妙,我试图想象我根本没有去过和没有见过的地方,这给我带来独特的感受,因为即使我一无所知,但我也可以从一片虚无里体会到激动、快乐,这感官很难描述,不过对一个敏锐的孩子来说是切实的感受。
到了再晚一些,我听到有人从隔壁起身打开门,进入了浴室,水哗啦啦地从管子里流出来,接着是织物的摩挲声,关灯时弹簧板咯噔一声,然后我们这边卧室门开了,一个柔软的身体带着水汽躺到我身边,床垫向侧面陷了下去。我闭眼装睡,有一会儿来人屏住了呼吸,我感到她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她在仔细地观察我是否有睡着,但后来她终于放心地把头落在了枕头上,然后过了没一会儿,她带着香味的均匀呼吸就扑在我耳边。
她睡熟了。
那时——我突然发现,隔壁房间静了下来,静得可怕,我意识到从母亲离开那张床到现在,那个外乡人似乎是死了一样沉寂。我想象他躺在我的床上,但我想象不出来,因为真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没有走动,没有咳嗽,甚至没有呼吸声。我的想象力开始跟我作对,把我熟悉的地方扭曲得陌生又怪异。即使我的父母都在我身边,但——
他还在隔壁吗?他还活着吗?他是什么?
陷入恐慌之中,我甚至想不起来那间房间的样子,我听到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各种吓人的怪异事物在我脑子里盘旋,那时候我的所知还相当贫瘠,最可怕的经历也仅仅是有一次在玩躲藏游戏时我藏进了一条一角鲸尸体的胃里,切割人工作时差点把我一刀捅死。
而在我想象里最可怕的无非就是死亡和尸体,我听闻过莽撞的猎人冻死在1.5公里外的冰湖,每到冬季,他就在那条冰路下四处敲打路面,贴着厚厚的冰层就能看到他冻得青白色的脸,如果你看见他,他会张大嘴向你呼救,但没有活人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也听闻过被扒皮的北极熊活着追杀猎人的故事,它整个躯体都是红色的,冒着热气,它把带着熊皮逃走的猎人吞进肚子里。后来的救援者在那只熊的胃里找到了被融化了皮肤的猎人,他全身也是红彤彤的。我听说过最妖异的就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无法决定出一个我最害怕的景象来说服我自己。
或许比起那些东西我更怕的是那个外乡人本身,我害怕的是我和我的家乡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太过害怕了,我全身僵直,时间过得异常的缓慢,我以为我必须要这样躺到天亮。
但忽然我听到碎玻璃的声响,或许是风卷着什么东西打碎了窗户。于是港口的狗群大声地叫了起来,一声又一声,一家又一家的狗接连叫起来。
犬吠开始的时候,隔壁就传来了一声惊惧的喊叫,那个外乡人像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他从床上弹起来,害怕地呻吟了起来,然后疯了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接着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祈求什么。说来奇怪,当我终于听见他的哭声时,我就松了一口气,起先的那种恐慌无影无踪,我在我父母身边睡着了。
在住宿了小半个街区后,外乡人修好了船终于决定离开,临行时他向我父亲请求带走我,我当然也很想到别处去,这种渴望几乎让我把那天晚上对他的恐怖幻想都忘光了。
我父亲征得我的同意后,按照传统,满足了他的领养请求,并且以生父的名义祝福我,请求海女神席德娜降福于我,保护我和我乘坐的船,请求弓头鲸庇佑我,使我在危难中可以免于受苦和饥饿。
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年轻人决定坐他的船离开去外面看一看,等到冬天再回来。那可是一艘捕蟹的大船,装得下十来个人,更何况对这些早就想外出的年轻人来说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
他教我们如何检查船体、如何开船、如何看各种仪器和地图。可是我在船上越久,学得越多,就越感到蹊跷,在海上远行是一件多么疯狂而又辛苦的事?
在风平浪静的白日里还好,但到了夜里或是有暴风的日子,我们必须轮岗值班,时刻提心吊胆是否会有意外,或是船体的修补部分出现损坏,或是在无意中偏离航线,或是触到了海底暗礁,哪一个差错都会导致我们葬身鱼腹,到了最后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而从那时起,有一个想法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假如我们六个人要竭尽全力才勉强能应付这位钢铁美人,那么当初他一个人是如何做那么多事的呢?
或者,换句话说,他是拿了什么做交换才能一个人把船一直开到图克托亚图克呢?
星期一我要环游世界
-
星期二我不杀人
壹、第二个故事。
几个世纪以来,水手都极为迷信,这样的迷信与宗教截然不同。它是经验、忌讳、仪式、灵感和征兆的组合,它是流动的、有生命的,从海上讨生活的人的口里成型,随着洋流和季风漂洋过海,每一年与过去都有不同的地方,而多年之后流言可能就成为了传统。
在我的养父杰罗姆闯入图克托亚图克之前,他的征兆就早已经出现了。
“那东西从海里爬出来……跟着我。”
2009年的冬天,杰罗姆在荷兰港罗斯玛丽号捕蟹船上当水手,一旦出海他们就得不分昼夜地干活,而螃蟹总是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这个移动的金库会出现在哪里,于是水手们要不停地把重达363公斤的捕蟹笼推进海里又捞起来,若是再加上北极的海上风暴,那可就真是要人命。但无论如何,只要抓到螃蟹就能赚钱。
他们撞大运遇上了螃蟹潮,每次捞起来的笼子都有70只以上的帝王蟹,一大堆螃蟹从笼子里被倾倒到分蟹台上,硬壳落到铁皮上“哔剥哔剥哔剥——”,对水手来说就像听见了钱落进了钱袋的声音。他和他的同伴量出螃蟹的大小,小的扔进海里,大的才能带回去。
他动作飞快地捡起在台子上乱爬的美金,这时,他注意到其中的一只,它的蟹盖是正常的朱红色,也足够大,那是非常标准的帝王蟹尺寸,但——
它在空中四处摆动的蟹脚灌满了鲜艳夺目的彩色荧光液体,里面的水光在蠕动,而越是到蟹脚末端,那种混合的色彩就更鲜亮更诡异,没有一种自然里的光和色彩是这样的形态。
邪门,他只看了一眼就感到背脊上窜过一阵凉气——尽管他现在已经在冬天的白令海上了,头顶飘雪,又湿又冷,但那阵凉气比什么鬼天气都厉害,让他从骨头缝里结出冰来。
那是从蟹脚倒灌进螃蟹的什么液体吗?海洋污染导致的见鬼的感染?但它看起来活力十足。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反胃。
或者说那色彩是活的?它悄悄从螃蟹脚爬进螃蟹壳,把血肉掏空,可能在那朱红盖子底下的身体已经融化了。螃蟹没在里头——
它完啦——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可不妙,这——
水手马森抬手就把那只晃动着魔鬼脚的怪物扔进了水槽。
你瞎了吗——杰罗姆差点放声大叫,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他想要怎么办,一只螃蟹而已为什么不把它扔进水槽?海里什么东西没有?或许只是一种新的寄生物罢了,只是会给螃蟹脚上染个色。
船舷旁的克劳得一边大吼小心,一边把另一笼满满的螃蟹倒了出来,哗啦一声,把之前的螃蟹推挤到了边上,它们个挨个,个挤个,个个都晃动着肢节想要逃跑,敦促催促他们加快收货的进度。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杰罗姆机械地把小螃蟹抛进海里,他身上因为干活而冒出的热气儿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
——来不及了,它已经上来了。
它上船来了。
它现在就待在水槽里,水槽下面有数百只活的螃蟹,等盖上盖子,它就可以在里面大杀特杀。
他们自以为满载而归,但等他们打开水槽盖子,海水里说不定飘满了蟹脚——
全是蟹脚——
水槽里除了蟹脚,只有那荡漾着的鲜艳夺目的彩色液体。
“一只螃蟹,哈哈哈,杰罗姆你真是尿裤子先锋。”水手们哄然大笑,“你是怎么一眼从上百只螃蟹里把它选出来的。”
不,根本不用选,是它选中你。
只要见到,就知道什么是它,只要见到,就知道它是冲你来的。他们疯狂地嘲笑自己胆小的伙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杰罗姆说的没错,每个人在第一次碰到它的时候就能认出来。就好像你总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影子。
从那之后那征兆无处不在,它化身六尺高的疯狗浪弄死了罗斯玛丽号的船长和三个水手,化身乳腺癌让他老婆躺进棺材并使他背上巨债,它一步都不肯停地跟着杰罗姆上了冷锋号,上了夏季湾号,上了皇家号……
直到他找到我。“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讨海人来说父亲的祝福总是管用的。” 以及那个更隐秘的期望,用新鲜的血肉填满它、喂饱它,让它找到新的饵料、钻进新的蟹笼——
“那么或许……有一天它会跟我说再见。”
他盯着啤酒杯,那双喝得通红的眼珠透过橙黄冒泡的液体看向我。
船舱又闷又热,散发着一股潮湿、难闻的发酵气息,汗湿的背心和鞋袜的臭气、喝了一半的超级波克精酿的酒酸味、过了一个捕蟹季的被褥的怪味。
杰罗姆倒头呼呼大睡,我多少已经有些警醒了:
第一,从2009年征兆出现到2012年杰罗姆一头扎进图克,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显然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都像女人似的喜欢慢慢来,毕竟婚后的生活都是逐渐变得糟糕、变得难以忍受的,不会一个照面就拿碎冰锤往你脸上招呼。
第二,我怀疑——
老早就怀疑,那只怪物为什么没有一口吃掉他?除了笼子,当然要给它吃饱。吃饱了以后,野兽也能变得斯文起来。
因此他必须要带人一起出图克,这是关键,但我父亲给了他惊喜。
第三,现在,按照那个传说——我说过所有水手都很迷信,那么从他们迷信里脱胎出来的怪物也应当遵守《大洋公约》不是吗?这就是说只要我和他呆在一条船上,它就拿他奈何不得。
回过头想想,是的,除了我第一次航行以灭顶告终以外,我们确实再没出过大岔子。2012年我们最终没有把那艘多灾多难船开进荷兰港。
那时我们刚刚行驶到红眼雪蟹渔场1141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我差不多已经习惯像只小海豹般仰躺在狭小床位上被海浪摇来摇去,而不会吐得一塌糊涂了。我还靠强记学会了一些常用的单词拼写,用来辨认仪器。认错当然是难免的,毕竟英语不是因纽特通用语,因纽特人要到16岁以后才可能通过和成年人交谈学到英语,我几个年长些的兄弟就要比我好得多。
但我也能听懂杰罗姆简单的命令和脏话——我每次犯错,他都会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而我和所有菜鸟水手一样容易犯错,所以婊子养的是我最快学会的语句之一。
然而越接近目的地,他越显得心神不宁,四处找茬、疑神疑鬼,总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做检查,我们在船上爬上爬下,被他操得疲累不堪。哈布恩——我那四个兄弟之一——私下里提起这事儿就皱鼻子,说只有新生儿才像他那样善变又需索无度。
不过杰罗姆该死的又对了,他的疑心病是有道理的。我不得不摆明这一点:渔船灭顶是由于防撞舱不知为何进了水,重心前移。
但——难以置信的部分是——在灭顶前负责检查甲板和开船的人都没发觉任何异常,考虑到我们频繁检修的次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事实如此,晚上风浪一起,船就被浪推着一头扎进海里。我们无计可施,只好放了救生艇,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了很久,差点被冻到失温,最后一艘路过的渔船发现我们,把我们捞了起来。
恐怕我的处女航就是它的反抗,它透过那艘船蒙蔽我们、影响我们,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毕竟那时候它徘徊已久,即使杰罗姆找到了学徒护身符,它也要放手一搏,享受这最后的大餐,但即使它没有得逞,它也不会消失。
它只是围着将死之人团团转,等待时机。
可打那以后杰罗姆和我从未分开过。他在哪儿我就必须在哪儿,他甚至逼得船长同意一个未成年在船上打杂。雇佣未成年在美国是个挺严重的罪名,所以我只能又多了一个船长叔叔,亲戚的小孩来船上过假期听起来就好多了是不是。
第四,让我喘口气,第四,现在——
它是螃蟹,我是水槽,我替水手杰罗姆盖着那个盖子呢。
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个征兆会不会找上我?我这会就在琢磨,它打碎盖子从水槽里爬出来是早晚的事儿,而这种结局杰罗姆理当早就知道,因为近两年,是的,自打2016年年底,他脾气变得暴躁、时常酗酒,尤其是,他又开始做噩梦。
那是种什么感觉?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杰罗姆的那个惊悸的晚上。那就是他的征兆,即使并不是我的,我也本能地感到恐惧。
这是个漫长的夜晚,酒精让他短暂地得到了安宁。
我靠着舱门,烟头被海风吹得忽明忽亮,港口的喧闹隐约传过来:那些乌七八糟的吼叫和哄笑,那些颠三倒四的船歌和口琴声——
我要当面问个清楚,尽管我已经差不多算把自己说服了。但我需要他正式地说出来。即使他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账、恶贯满盈的凶徒,但我当他的跟班已经四年,我也分担过他的恐惧、欣赏他娴熟的技艺,而且大部分时候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他还至少救过我两次,当我在甲板上犯下愚蠢又致命的错误的时候。
是他而不是别人,把我从那地方带了出来,教我手艺,使我不至于饿死。我甚至有点好笑地想,假如他是我的弓头鲸,那么至少我应该为他做一道鲸骨门。
总之,星期二我不杀人,至少现在不。
一切等到天亮吧,天亮再说。
星期二我不杀人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