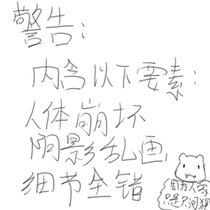三、碎镜相通
作为人类,长时间呆在纯色的环境里会开始感到压力和焦躁,会迫切想改变现状,想得到这里没办法拥有的东西。
而囚徒川的游戏又像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提醒你,嗨!你已经死了,但是你还能再死一次!玩笑一样的游戏和嘲讽一般的休息日把人变成了拉满的弓,背叛的选项就是弓弦上的利箭,一切都是看你的手用什么样的方式松开,是用利箭穿透呢?还是放开空弦?
神威鸟羽在第二日的时候去了礼堂,没有人的时候去的,也不能说没有人,奇妙的“转学生”坐在坐席上笑着和他打招呼。
白色的。
很奇妙,他没经过任何人同意,也不需要任何人同意,躺进了对应自己照片的棺材里,很宁静,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在想,如果棺材是黑色的那就更好了。
酒店是白色的,礼堂是白色的,棺材是白色的,白川奈奈是白色的,但是他是黑色的。
“鸟羽哥哥,你把我们的秘密告诉第三人。而且是半真半假的,你这是最恶毒的谎言。”
耳边传来的声音不是转学生的,转学生的声音有些健气,和她的外表一样,像是冬日暖阳,给寒冷的人能带来一点点温暖。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深入血肉、骨髓的熟悉。
是“八百坂白乌”的声音又不是八百坂白乌的声音。
他去父亲医院检查过自己,借着认识的精神科的医生做了简单的表格自查,虽然最后想办法删掉了那个结果报告,但是还是被父母知道了,统合失调症而已,他觉得并不影响任何日常生活,也不影响工作学习,只不过生活中偶尔会多上那么一个“人”。
她留下了一句话之后又走了,听起来有点生气。
下一次她出现的时候是在野餐会上,年轻人没办法在压抑了几天意识到自己死了根本不需要吃东西或者怎么吃身体也不会有变化之后能拒绝无限量的BBQ,或者是就像是广播说的,享受24小时休息的时间,宁静和平,哪怕脸被按到烧烤架上、被烤肉签子扎穿喉咙也不会死的毫无波澜的一天。
“八百坂白乌”出现在他给相识的几个同学送完烤串之后,她用《理想国》遮着半张脸,没有光华的眼睛盯着他,她说:“你背叛了我们的誓言,你说过只会陪着‘我’跳舞的。”
“我还想在这里暂时多‘活’一会……”
“鸟羽哥哥,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你已经没办法回头了,在这里你竟然选择合作?”
烧烤架的炭火发出细微的燃烧声,在嘈杂的摇滚乐里根本没有人听得见。
“八百坂白乌”还在问他:“你没选背叛的原因是没本事吗?”
真是刺耳的声音啊,哪怕她的语气那么平淡那么正常那么像她,但是还是让神威鸟羽把烤串签子扎进了手心里。
是啊,做着伪善合作的事情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仅仅只是因为没本事去背叛。
他想稍微为了那点不可能的事情多“活”一会,有机会看到电影落幕的明天就好。
“她”没等到神威鸟羽的答案,也不需要他的回答,像是樱花树飘落的花瓣一样消散了。
“如你所愿吧。”
签子从手心拔出来,带落了连成串的血珠,石榴籽一样的血把铺地的白色樱花染成盛放的血樱,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小小角落仿佛回归了正常一样。
遇到了两次前辈的神威鸟羽终于面对了一次同级生。
可靠的阳光的温柔的同级生——柏原亮太。
如果有挑事的……不对,不是如果,是确实有挑事的同学说过,“神威,你和柏原撞人设了吧?”
啊啊,努力的优等生和偏科的优等生,温柔可靠和温和稳妥、一样的乐于助人、一眼的眼镜仔、甚至连泪痣都是镜像的……如果不是白皙的神威看起来过于“柔弱”和被阳光眷顾元气满满的柏原气质上差别太大,真的会让人感叹一句镜子里相对的两个人。
神威鸟羽知道柏原亮太拿他没办法,有一些难以令人察觉出来的控制欲的人是不会喜欢把自己缩在堡垒里的人的,不踏出围城就不会被发现弱点。
其实看见对手是他倒是让神威好奇了一下,他一直觉得柏原很聪明,是会隐藏自己心思但是又在可控范围内透露出去的那种,感觉他们挚友组一直在濒临崩溃的边缘维持微妙平衡,但是这和他神威鸟羽有什么关系呢?
他只是有一丝在意透过他人眼睛看见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罢了。
“白乌”带来的压力让他决定了普通、中庸、从众是没办法的,那个人的手从深渊伸出来抓着他攀着他,让他越陷越深。
“柏原同学。”
“神威同学。”
两个男人站在巨大的镜面之前点点头,已经足够了解了,自己非他友人,不可能有天真的友情混杂在生与死的选择里;而他也非纯粹的好人,既不弱小可以骗取同情,又不强大到难以控制。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会合作呢?
神威鸟羽背过身去,推了一下眼镜进了选择的房间,虽然确实是没什么本事的人,但是也要尝试一下对吧。
红色的按钮像是昨天野餐会昙花一现的血樱,其实那朵樱花在他捡起来之前就没了,血色转瞬融入了白,更直观地说,像是被吞噬了,被囚徒川吞噬,把不属于这里的不和谐之音消灭掉,一如雪白,干干净净,谁也不知道积雪层下到底有什么。
“咔哒。”
按钮陷入又弹起,红色的、特别的、不和谐的按钮,然后身旁的桌上出现了一把银色的蝴蝶刀。
他把这把小巧迷人发着寒光的东西随手塞进制服口袋里,轻轻松松走出了房间。
“直面我最大的恐惧,拥抱三分钟?谁会抱啊。”
也许神威真的会拥抱,走出门的那一刻他看清了对面的东西,是个人影,是他无比熟悉朝思暮想甚至扭曲执念犯病到产生那个人幻影和自己对话。
八百坂白乌。对,没错,娇小柔弱阴沉的12岁的妹妹。
她,应该用“她”,身上还是国中那件黑底赤襟的水手服,系着松松垮垮的蝴蝶结,黑眼圈严重的脸上有着审视他的表情,手上提着一把和她身材并不契合的长条包裹,估计是武士刀吧,然后对着神威说;“我不会拥抱你。”
“对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神威鸟羽笑了出来,从喉咙里泄露的嘲讽的轻笑慢慢变成了肆意的大笑,他抱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眼眶周围的热气把镜片带起了一小块白雾。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眼泪看着对面,那个人的脸在失去了眼镜的辅助后那么模糊,但是他知道,对方一定在挑眉想,“我的恐惧为什么发了疯。”
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怎么能用这么可笑的方式让他最重要的妹妹出现在这里,即使有着那张脸,甚至声音都变得一样了,但是他没傻也没疯,那不是八百坂白乌,不是他的白,是他的好同学,提着刀会杀掉他的好同学。
“她”把包裹打开了,拿出了在他猜测范围内的武器。
他把手伸进了口袋,握住了比手术刀更加危险的武器。
奔跑的风声还没来得及在耳边呼啸就停了下来,神威下蹲重心弯腰欺近了“八百坂白乌”,蝴蝶刀尖细的刀刃划破了布料与皮肤绕开了肋骨直直埋入肌肉,他垂下眼帘,镜片之后的目光带着阴冷和狠毒,正当他打算扭转手腕准备发力让双刃的小刀更加侵入胸腹去划破脆弱柔软的脾脏时左手已经没办法动了。
冰冷的武士刀切进了他的身体,“八百坂白乌”借着神威刺到左肋的距离用力挥起了武士刀,对着他劈砍下来。然后他能够听见刀刃划开肌肉细微的声音,能听见左肩峰处的骨头发出痛苦的吱鸣,他的锁骨和肩胛骨努力卡住刀刃保护着他。
“滴答滴答。”
两个人的血液汇聚在了一起,红色的地面浅浅的反射着他们的身影,在对方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好好学生怎么会受过这么重的伤,过量失血造成体温急速流失,视线里时不时出现重影,连意识都有些模糊,身体也没办法支撑自己再站着,然后他跌坐在地上看着捂着伤口向门口离去的人。
回来!回来!看着我啊!!
愤怒的声音只能在胸腔响起,无力颤抖的嘴唇没办法把它吐出来。
看着我啊!你为什么没有发现我在……
最后的肾上腺素作祟,神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捂着肩膀和那只估计已经断掉了的左手扑向了要离开房间的妹妹。
“八百坂白乌”被抓住手臂,整个人被神威带倒在地上,回转过来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想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喉咙被沾满了血的手掐住,神威压在他身上,逐渐用全身的力量死死卡住他的气管,他想掰开神威的手却不知道那只单手为什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眼镜已经丢了,人也看不太清,肩膀的血顺着垂下的手臂全流到“八百坂白乌”的身上,神威的眼神里没有一点光芒,表情狰狞扭曲,加上脸上那些溅到的血,像是无差别伤人的疯子一样。
他现在确实疯了,只想把这个不是白的人杀掉,手指一点点收紧,身下的人快只剩下出的气了。然后他听见了有人在叫他,那张和八百坂白乌一模一样的脸明明已经没法发出声音,但是他敢肯定他听见了,他绝对听见了,听见了有人在叫他。
“鸟。”
手不由自主松开了一点,给予了对方一丝空气,也给予了一丝逃生之路。
柏原亮太喘息着,发狠把手指插进了他砍出来的伤口里,这是他造成的伤害,是他了解的地方,是他可控的地方。指尖捅着滑腻的肌肉触到了骨头,他掰着森森的白骨让神威痛到松开了自己,再补上一脚踹开这个混蛋,艰难地爬向出口。
身后的人死不死与他何干,他也想活着!
什么算是拥抱?是亲密的身体接触吗?那压制和掐算吗?半死不活的未成年人能完全让另一个人三到五分钟得不到空气窒息而亡吗?如果不能带来死亡,那能算是另一种“亲密”的接触吗?
囚徒川的房间永远是雪白一片,只有两条血路在这间房的镜子里缓缓消失,仿佛被这片纯洁的地面吸收了一样。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一个奇迹,你永远不知道迎接你的究竟是生还是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