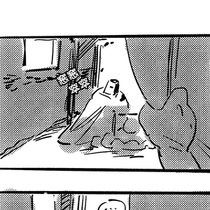-

不死之世-西多尔
-
如果你听了前一个故事,就认为我是个偏好吓唬人的家伙,那你可是大错特错。那只是故事,玛丽·莫里森也只是我故事中的人物,不过她是活生生的,我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除了——
你可以听听看这一个。
【空壳】
玛丽·莫里森来到达拉尔镇,她在迷宫花园丢了一把心爱的小刀。这把刀陪伴了她许多年,拥有武器的一切美德:便宜、好用且从不噬主。是她漫长路途上十分靠得住的一大助力。
其后一名穿着铠甲的高大家伙将之送了回来,他自称为西多尔·斯图尔特,可想而知玛丽有多感激这个铁大个儿了。“我应该如何回报你?”玛丽不喜欢没完没了的道谢,她盯着西多尔的头盔——那上面呈对称性地分布着一些孔洞,方便人呼吸,最上方是两条代表眼睛的狭长缝隙,能模糊感觉到缝隙后的视线落在她面上,铁皮隔绝了一切活人的气息。
“我有一座磨坊。”她提示,实际上她还有一些闲钱,有非常美丽的脸和躯体,作为一个寡妇她还有一个丈夫的名额。
但后者爽快地道,“希望你找回东西的好运气也能分点儿给我。”
“你丢了什么?”
“多年前,我与我的妹妹失散了,现在,我连她仅剩的画像都遗失了。”头盔之下的嗓音是年长的男性,听来稳重又诚恳,透露出深深的疲惫。“那是刻在木牌上的画像,不小心在迷宫花园把它弄丢了……我东奔西跑找了一整天,真希望有人看到告示后能告诉我它的下落,如果能够直接送回给我就更好了。”
“你的妹妹?”
“是的,一母同胞,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我母亲曾说我们两长得一模一样。”
“迷宫花园我去过,但木牌我倒是没瞧见,不过我来达拉尔镇以前也到过周围的几个村庄,倘若你能把头盔摘下来,让我看看你的长相,或许我能说清楚是不是在这附近见过她。”
那声音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头盔发出了声响,“啊,恐怕不行,你从我这里再寻不到她的样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还长得一模一样。”
“想必有一些缘由。”
她放松地靠在教堂的长凳上,他们有一整晚地时间待在这里。黑夜中一些蜡烛在燃烧,昏暗的光照下模糊的人影分散在屋内各处或站或卧,她能听到他们低声哭泣和轻柔的哀求声,长久而持续地回响在屋顶之下,而那些墙外的吵嚷、喊叫、骤然响起划破黑夜的哀嚎,则是这支小夜曲的协奏。
那个铁桶则在这样的开场之中讲他的故事:
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的妹妹是个美妙的姑娘,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她和常年随领主出征的骑士订了婚,原本这次回来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但有一天她突然哭着找我,说和骑士一同外出的同伴已经归来,但她的未婚夫却不见踪影。
于是我找到骑士的同伴,他们告诉我,有一天夜里,他离开了他们露营地的篝火,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离队之处是距离小镇只有两天路程的荒原之上,那里地势平坦,既没有什么可怕的猛兽,也不存在迷路的可能。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们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也只是猜想他可能突然想起有急事先行一步,大伙儿对他这鲁莽的行为有些埋怨,在确认了营地周围并无异常后,就匆匆上路了。
说来也奇怪,虽然骑士和我妹妹订了婚,但我们——我、我妹妹和我的母亲——完全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在当地有什么亲戚。何况当时母亲也已去世,对他可能的去处我全无头绪。我妹妹哭着恳求,我只好答应她去骑士离开之处再看一看。
于是我带上干粮,到了同伴所说的营地附近,周围既没有村落,也没有树林,假如你能明白什么是空无一物——
就是说,那上头丝毫没有人类和动物的痕迹,方圆几百里连一个活物也没有。只有枯黄干草成团地倒伏在地上,它们扭曲的藤上长着长长的爪形的根系,深深抓住有些沙化的泥土。而风,一阵阵酷烈的风,像是巨大的无形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地方四蹄翻飞,烟尘滚滚奔袭而来,带起可怕的气流咆哮!怒吼!横扫一切!
我不得不一边跟这狂野的怪风抗争,一边四处搜寻,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天,而且被这片荒原上的沙土和枯草疯狂侵蚀,但那处燃过篝火的坑还在原地,勉强能够辨认得出,仿佛人类留下的顽固遗迹。但也就仅仅如此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获,如同他同伴所说:并无异常。
事实是,我应当早做打算,马上就离开这要命的地方,那或许我在夜晚来临前能赶到一处农舍,在马棚里借住一宿。但一想到我回去将要面对悲痛欲绝的妹妹,我就觉得难以呼吸,她深深爱着她的未婚夫,而现在,我则是能找回他的唯一希望,假如我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她的绝望会活生生把我淹死,你大概不能理解,这是双胞胎之间特有的感应——
一种你能想到的最奇妙最古怪的联系,在双胞胎之间,*她就是我,我就是她*,有时候它是一根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蛛丝,它的两端分别牵着两颗心脏,哪怕是最细微的感情都会通过它而让另一人的心脏为之跳动。但有的时候,当双胞胎的其中一个陷入痛苦、绝望、疯癫,那么那种黏腻的可怕的感情就如同断裂的松枝上滴落的透明脂体,会彻底地把另一个层层包裹,他会失去自己所有的器官和感觉,而完全迷失在别人的情绪之中。
我和她之间便是如此,我不想她陷入这样的泥潭,于是我决定要尽最后的努力。我要在这里过一晚,碰碰运气,看看会不会再发现什么。我在深坑里燃起篝火,用的是随处可见的枯草团加上干枯的枝条,这个坑周围累着重重石块,这是前人留下来的福祉,能够防止风把火熄灭。
这样我孤身一人,等候着、等候着……
当黑夜笼罩,四周空荡荡但却充斥着不知何处不知何物发出的古怪声响,不是生物却又像是生物发出的呼吸和低吟,时远时近,既嘈杂又寂静——
而我明明知道在这荒原之上除了风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守在这一丛孤零零的火焰旁,半步之外就是被永恒黑暗统治的世界,这时,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盯着那唯一的热源在想——这难道不是一个邀约?
*一个古老的邀约。*
这个念头控制不住地进入我的脑子里。
*如果你在荒原上点燃篝火。*
这跳动的橙红的火焰,这温暖的燃烧着枯枝的烟气,还有在光源之下扭动的我的倒影,每一样都仿佛在招呼我看不见的孤独的在夜里跋涉的行者向我靠近。我脑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你呼唤牠们为你而来。*
接着牠们纷纷应和——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了!
到这里来了!
*到你身边来了!*
我不是个胆小的人,但我害怕极了。我毛骨悚然地感到有呼吸声在我的肩膀上,那些目光温热黏腻令人作呕地盯着我。
那头马鹿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在火焰产生的扭曲的烟火里,在黑暗之中,由远及近地显出它的轮廓,它哒哒哒踩着有节奏的步伐漫步走来,靠近你,靠近火。
这头雄鹿高大、灵活又矫健,非常年轻,肌肉健壮,雄健的躯体完美又优雅,一举一动都那么得体,眼睛又黑又大,带着点儿湿润的感觉,当它温顺地看你,就像是对情人低语。
而且它全身都散发着灵光,这是一种朦胧的淡淡的光线,柔和又令人舒适。你知道我多惊讶,在这个被神诅咒的暗夜,它是唯二发光的物体,神圣、洁白,它就这样像是救赎般出现在你的眼前!
*抓住它!*
我和他猛地站起身来!
*你必须抓住它!别让它跑了!*
我们向它走了几步,它站住了,深深地回头看了一眼,灵巧地转身就跑。他大叫着,然后像一阵风般追着鹿去了,于是我也不得不追着他们而去。
是的,和他一起,和那个骑士追着那只雄性马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那身铠甲,那个头盔,是的,我的妹妹爱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骑士,就是那个*新郎*。不知道从何时起,他就和我一起坐在那堆篝火边。
我记得我要把他带回去,我的妹妹还等着我。但骑士疯了一样追着那头鹿跑得气喘吁吁,他身上的铠甲严重地拖累了他,他拼命呼唤那头鹿,他全力奔跑,把碍事的铠甲脱下来扔掉。先是头盔,这没费多大力,然后是身上的披风、背心、靴子,一些部件让他不得不短暂地停留下来,但是一旦摆脱了这沉重的束缚,他立刻就再次往前飞奔,而且脚步越发轻快。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跑那么快的,篝火远远地落在我们身后,我为了追上他,学着他的样子,一件件脱掉身上的衣服,但那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变成在荒原里奔啸的风,你就要丢弃很多东西,我在融化,我的五官,我的脸,我的手和我的脚,我的脑子里挤满了各种声音和念头,像是有无数人用我的声音在和我说话,巨大的融合的狂喜充斥着我全身,逼着我脚步不停地奔跑、奔跑!
我就这样处在极度危险的崩溃边缘,直到——
我感到我身上的那根蛛丝拦腰勒住了我,在这速度之下,它几乎把我切成两半!剧烈的疼痛让我清醒,我正好看到——那应该是我能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了,我看到——
那个男人终于抛弃了一切,他赤裸地大步奔向那头雄鹿,周身都散发着同样的灵光,他一头扎进了它的深处,他发出呜呜呜——呜呜啊——啊啊啊——呃呃——
如此这样仿佛啸叫的可怕声响,随着风一起逐渐地融化在黑暗里。
铁桶叹息地道:“我站在黎明前那一瞬间,我丢失了……我也不知道丢失了什么,总之我感觉我可能是风,是沙土,是枯草,是荒原的一部分,但我还是人吗?我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在夜里是什么来到我身边?他是不是每一夜都在那篝火旁等待时机,终于在我来的这一天和牠们融为一体?
但我又清晰明显地感觉到我——我的意识还存在——我现在还站在这里,我是谁呢?我能到哪里去呢?我把他扔下的衣物、盔甲一件件捡起来穿戴整齐,当最后一件头盔遮住我的脸,荒原上的太阳升起来了。”
“我没有再回去镇子去,那种一切都被融化的恐惧,让我既不想成为荒原上游荡的魂灵,也不想回去见我的妹妹。我也担心,她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够从我心里完整地知道她的新郎的结局。然后她就会死在我面前。”
形形色色的怪事(中)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