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幻想风超能力学院企划——元素学院欢迎大家加入!目前企划一期已结束,番外筹备中~一旦开始会再次发通知,欢迎大家关注~
官方群号 256289636 强烈建议先加群!!!!!
第二章新势力群号372926917 想参加的先加群!!!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elementacedemic



“总之我先叫其他人过来,你稍微等我一下!”
说完之后,他立刻跑向房门处。
“要叫人的话打电话不就好了?”
“手术室里不能使用电话,这是规定。”
规定是吧?
“这里已经变成这样乱七八糟的样子了,也不用在意那些细节了吧?”
“不行,我……”
“看样子你对医疗方面的事情知道得不少啊。”
刚才他也通过自己的检查,做出了那几个白大褂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判断。
“我当过一端时间的医生,所以自然会懂一些——暂时先别管这些了,要赶快救人——”
“你先别走。”
“?”
“你看那边那张桌子。”
我依旧用眼神向他示意我所说的“桌子”是哪一张。
“就是那张桌子。”
“这里只有一张桌子……”
“……你看那上面,是不是有个记录本之类的东西?”
“是有一本。”
“那应该是手术记录或实验报告吧?我刚醒来的时候有看到,有个人在那上面写些什么。”
那个人写字的手也被我多戳了几根解剖针上去。
“你懂医的话,帮我看看吧,他们写了些什么。”
“这......这怎么可以......”
“他们都不告诉我要做什么实验,像这次,他们打开我的头在里面弄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能帮我看看吗?”
“要先救人……”
“身为实验对象,有知道实验内容的权力吧?”
“可是他们......”
“我也是伤者啊!我被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弄得动不了了,所以也应该先救治我吧?”
“......”
他似乎是屈服了的样子。
他走到桌边,拿起记录本开始翻阅。
在他阅读那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瞳孔,由小变大的过程。
最后——
“这......这是!!!”
——他的声音明显出现了颤抖。
这场景,这表情,这台词,都好像是动画里的内容啊。
作者麻烦有点新意好不好?
“洛基.菲克修恩......”
“嗯,是我。”
“刚才那只狼,是你元素能力的造物吧?”
“没错。”
魔元素。
将我所幻想的怪物制造出来的能力。
“元素使发动能力所做的造物是没办法永存的。”
“对啊,这我知道。”
赫尔、芬里厄跟耶梦加得,也只是因为我的元素神存有关于它们的记忆,所以我能瞬间制造出来,使得看上去就好像平时是隐匿身形,需要时再召唤出来一样。
“他们的实验,是想要打破这一规则。”
“打破?”
要怎么做?
要维持处于活动状态的我的造物的存在,需要消耗我的精力和体力,所以是有着诸多限制的。
比方说,至少在我睡觉的时候,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们的实验,是要把你改造成不需要睡觉的人。”
“哈?”
“他们想把你的大脑改造成海豚那样,通过左右半球轮换休息以消除掉人体完整的睡眠需求。”
“......”
如果我是不需要睡觉来补充体力的永动机的话,那确实,我的造物确实有可能能够永久存在。
一直存在,直到我死亡为止。
开什么玩笑啊?!
为什么我非得变成那种样子不可啊?!
不过是因为我是元素使,所以才同意参与你们的实验,但我可不记得有同意你们改造我的身体啊!
而且还失败了……
所以才不事先告诉我吗?你们知道我不会同意的是吧?!
“过分......”
一树颤抖着把记录本翻来又翻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看样子这些人果然还是得死。”
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事情败露后会被我给杀掉的觉悟呢?
不,我看没有吧。从我醒来后他们所说的话看来,他们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会有事。
我再次叫出芬里厄。
“统一一下,每个人,只咬掉左半边脑袋就够了。”
“不!不要!”
一树丢下笔记本,跑过去护着那些人。
“别挡路,你也看到了,他们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确实他们做了很过分的事,但也不至于让他们去死啊!”
“不下重手的话,他们根本学不到任何教训!”
“不需要重到让他们丧命吧?虽然做得不对,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啊!”
生命?
“一树君,你知道吗?”
“我的能力是‘创造出我所幻想的怪物’,是类似于——不,就是‘创造生物’的能力哦。”
我解除了对芬里厄的能量供应,芬里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并非‘召唤’出我的造物,而是‘消除再制造’。”
我再次发动能力,芬里厄再次出现在和刚才一样的地方。
“‘这一只’和‘刚才那一只’不是同一只哦,一树君。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元素神还存有关于它们的记忆,所以他们才能被瞬间以同样的形象再次制造而已。要这么说来,其实它们也不过是‘魔’元素神记忆的具现化和载体而已。”
“……”
“生物本身不过是生命的载体而已。生物本身停止活动根本就不能算是生命的丧失吧?他的生命应该也会在某处被保存着,等待着新的生物载体进行搭载吧?”
“……”
“所以说,生物体本身,其实怎样都无所谓。”
别说是那些白大褂了。
就算是我。
如果刚才的手术失败得再彻底一点,失败到我的这个身体再也无法醒来的话,我的生命也应该会在某个元素神或者上帝什么那里保存着,然后再以新的身体获得重生吧。
但是手术失败得没有那么彻底,导致我带着这种只能靠习惯去治疗的创伤苟活着。
今后我都得带着这副残缺不全的身体活下去了吧?
这才是我最不爽的地方。
“你的心理……到底是扭曲到了何种地步啊……?”
一树在低声说着什么。
“我无法认同。”
“?”
“生命只有一次!是应该被珍惜和敬重的东西!”
和他谈不来吗?
那果然还是只能……
“我能帮你!”
似乎是急中生智的样子,一树喊出了这句话。
“我的能力应该能帮你把大脑恢复到原本的样子。如果我成功的话,就请放过他们!”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记得他的元素能力应该是和治疗有关。
“如果失败了呢?”
“不会失败的!”
他的眼神里闪烁出了坚定的神情。
“好吧。”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你的大脑还是完整的,手术所改造的其实只有很小一部分,所以凭我的能力也是可以恢复的。”
一树再次检查了我的身体状态,舒了一口气,说道。
“不赖嘛。感谢啦~”
我扳弄着自己的手指,就好像我已经好几年没动过它们一样。
“那些人......我在帮你治疗的时候顺便给他们做了些处理。”
一树指着一旁,已经从墙上取下,身上的尖锐物体都被取走,一字排开放在被褥上的白大褂们。
“按照说好的,放过他们吧。”
“可以。”
被插成刺猬钉在墙上,这教训已经足够了吧。
不过,他们到底会学到怎样的教训呢?
是“下次别打改造洛基的身体的主意”,还是“下次要把改造洛基的身体的主意藏好一点”呢?
不清楚,我无法确定。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们也到本所来的缘故吗?如果他们不跟过来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想拿我的大脑做实验了吧。
明明上面只拜托我过来帮忙守门而已,这些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啊?
“洛基君是守卫吧?是哪一层的?”
刚好,在我正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一树问了我这个问题。
他是小心翼翼地问的。
“B2,一树君呢?”
他身为元素使却能在这里自由活动,应该和我一样是守卫吧。
“欸?!……和你一样,也是B2……”
“是哦?”
原来他是我队友啊。
“是队友啊。”
“是啊。”
“那请多指教咯,今后。”
“嗯……”
我把手伸出去想和他握手,但他却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那么,洛基君,你应该已经没事了,我要去叫人过来了。”
不等我回应,一树君就跑出了手术室的门。
留我一个人维持着伸出右手的姿势坐在病床上。
搞得好像我是笨蛋一样。
好痛。
我的头好痛。
头痛欲裂到痛死我了。
事实上它真的裂开过。
不,准确来说不是“裂开”,而是“被剖开”。
我刚刚被做了开颅手术。
开刀的是那些和我一起从乡下的研究所过来这里的研究人员。
他们说想借本所的设备来做个实验,实验对象当然就是身为元素使的我。
我原本以为只是和平常一样的常规实验,所以什么都没说就躺在手术台上让他们麻醉。
可是等我醒来的时候,迎接我的就是这阵像是永无止境般的头痛。
“抱歉,实验失败了。”
还有那些白大褂说出的这句话。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头痛——”
不只是“有些”好吗?
“——可能身体的运动也会变得困难——”
什么......我的手!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
“——我们已经尽量减少了对你的大脑产生的损伤,但还是有些不可避免的......”
大脑损伤?!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不过问题应该不大,你好好休息一会儿......”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就在我脑袋里乱搞,现在变成这样却只是这么轻描淡写若无其事地一笔带过吗??!!
“你......你冷静一点!快来人——镇静——啊————!!!”
我把他们都杀了。
他们现在都被手术刀和解剖剪钉在了手术室的墙上。
我叫耶梦加得把他们钉上去的。
好累。
不光要维持耶梦加得的存在,还要让它做出把这个房间内的所有尖锐物品找到并刺在那五个人身上这种劳动量超大的行动,消耗的体力可不容小觑。
虽然头痛一点都没有减弱的迹象,但是我也懒得去管了。
可能这痛觉永远都不会消退了吧,那我还是得赶紧习惯它才行。
就像我五岁的时候,习惯元素使每天都要接受实验这件事一样。
虽然一开始很难,但这是没办法的必须要经历的事。
“发生什么事了?我有事在隔壁房间,突然听到这里——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在刚才那一片混乱中被搞坏门锁的手术室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走进来的是个蓝色头发的少年。
我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见过他,我记得是叫做清崎一树吧……
“是青崎。”
“抱歉,懒得选字。”
……
“你们不要紧吧?振作一点啊!”
一树一走进来,就看到了满墙血淋淋的白大褂——我的杰作。
他很慌张地跑过去,检查他们的状况。
没用的,那些人已经......
“太好了,只是昏过去了,大家都还活着!”
欸?
“虽然伤都很重,不过所幸都没有伤到要害,只要赶快止血和治疗的话......”
被插成了刺猬居然都还没死?
是因为头痛的关系,导致我做出来的耶梦加得力量减弱了吗?
既然这样的话......
“芬里厄。”
“总共五个人,我一个人处理的话可能太慢,先呼叫其他人过来吧。————!”
“吃掉他们。”
“等等!难道是你——!”
不等一树“是你”完,我的芬里厄就冲了上去,一下把他撞开。
恶狼走到墙边,张开血盆大口,准备把墙上离它最近的那个失去意识的白大褂的头部咬下来。
“住手!”
被撞开的一树又大吼着冲了过来,挡在芬里厄和白大褂之间。
他从背后抓起一把霰弹枪,指着眼前的芬里厄张开的大嘴里的喉咙。
“快住手,我不想任何人受伤!”
说是这么说,但他的眼神却在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拼上性命保护那些人了。
话说那把枪看上去是特制的,是针对他的元素能力而设计的吗?
之前看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拿着这把枪。
他刚刚说他有事在隔壁房间。
会让他带着枪去的事会是什么事呢?
……
算了,这种事不去考虑也罢。
现在的重点是,青崎一树正举着枪,挡住了我的芬里厄。
“......”
芬里厄似乎因为眼前突然出现的障碍而产生了迟疑。
“算了。”
我轻声说道。
反正那些人无论死不死,都已经没用了吧。
芬里厄安静地闭上嘴,身影逐渐淡化。
待到芬里厄的身形完全消失之后,一树也放下了手上的枪。
“你这家伙,还真是乱来啊......”
一树看着我,如此说道。
“你穿着病人服,头上绑着绷带躺在床上......是在这里接受手术吗?”
“......”
没错,我一直躺在床上。
原因是我不但头痛,两只手也都动不了了。
后来我发现连脚都莫名地僵硬,所以现在的我只能躺在这里,完全不能行动。
“是啊,就是他们做的。”
我用眼神示意墙上那些人。
“对给自己治病的医生下如此毒手,你还真是过分啊。”
“不,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给我治病。”
因为我根本没病。
“那是?”
“是实验,这是以元素使为对象做的实验。”
“欸?!这个研究所会做人体实验吗?”
“他们不是这个所的人,他们是跟我从乡下一起过来的人。”
谁知道他们软磨硬泡了多久才获得许可使用这间手术室的。
“是吗......”
一树若有所思地说着,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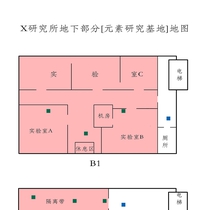




“都说了想要离婚没门!”
“你都快变成穷光蛋了还想让我陪你耗下去?呵呵,你当白日做梦呢?想都不要想!”
“你以为我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谁?!衣服首饰美容院,你当银行是你开的吗?”
“没钱养老婆有本事就别娶啊!为了这点小事唧唧歪歪的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
……
男人愤怒的嘶吼,女人尖利的叫嚷,重物坠地的钝鸣,玻璃碎裂的脆响,交织在一起从很近又很远的地方传来,却是和他的世界毫无关系。
安格斯安静的待在阳台上,周身围着一圈青色的盆栽,他对着阳光惬意的眯起眼睛,沐浴着这份温暖。耳边能听到风拂过枝叶的沙沙声,鼻尖能闻到树叶的香味,伸出手指去触摸柔软的茎叶,感受源自自然的一切。
这才是——他的世界。
所有的争吵与此无关。
所有的纷乱于此绝缘。
只属于安格斯的世界。
美妙的虚构的理想国。
*
夕阳收走了余晖,阳台上的温度慢慢消散,但还是能听到两个人在喋喋不休的争吵着。空空荡荡的胃叫嚣着自己的不适,安格斯一点儿也不想从这方天地里离开,但他的确需要给空了三餐而且前一段时间也没有怎么好好进食的胃填一点儿东西了。
——或许,稍微小心一点儿,就不会被发现?
——你看,他们吵得那么专心,小心点就好。
——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不会被发现的。
胃部的饥饿感战胜了恐惧。
阳台的门被小心翼翼的拉开了一个缝,安格斯透过缝隙张望,发现那两人似乎已经转战到了卧室,便努力将自己从不大的缝隙间挪出来,沿着窗幔的阴影缩手缩脚的向着厨房挪动。
只是,在他成功抵达沙发背后的时候,男人摔门从卧室里出来了。
他在刚刚与妻子的争吵中拉了下风,此时看见安格斯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对着卧室吼道:“你要是想离婚,就把你生下来的杂种一起带走!别让我看见他!”
女人迅速的从房间里出来,涂着蔻丹红指甲的细长手指对着安格斯,眼神却依旧在男人身上:“凭什么?这是你儿子!我还要嫁人呢,拖油瓶难道不应该是你家的么?这可是你们家的种,你不害怕绝后么?!”
男人怒气冲冲的上前拉住安格斯的手臂,指着他的眼睛对女人说:“他哪里是我儿子?除了这眼睛的颜色和我一样,半点儿都不像我们家的人!指不定是你和那个混账生下的小杂种,我凭什么要帮你养?”
——别碰我。
女人的脸色都气得青白了,她狠狠的咬着唇,恨不得能一指戳死这个讨厌的存在。
——别碰我!
好不容易扳回一局的男人却像是得胜的公鸡一样,拽着安格斯的手臂让他成功的夹在两个人中间,颐指气使的说道:“要么就带着他一起走,要么就乖乖的给我带待在家里,哪儿都别想去!”
——别碰我!!!
女人却神色变得惊慌起来,她伸出的手指都颤抖了起来,尔后便是扯破嗓子的尖叫声。
男人疑惑的低下头,惊恐的发现自己拽着安格斯的手臂变成了青色,他忙不迭的甩开手臂,孩子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天啊!你生了个什么怪物!”
*
男人的电话招来了一批神色冷漠的黑制服,安格斯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却毫无留恋的听话的跟着他们离开了。
——不难过。
安格斯不知道为什么男人的手臂为什么会变成那副样子,对他们恐惧的眼神变调的声音也熟视无睹。
——不难过。
他安静的从这所他待了十年的房间,带着身上的疼痛,带着空洞的心,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
——……不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