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0
Of Herfjotur And Spring
【真正的英雄注定被世人遗忘】
【瓦尔基里却永存】
“……‘Вишняк(维什尼亚克)’,春天出生的孩子。”
少女踮着脚,柔软的布鞋有些变形,少女绷紧了脚尖,旋转着向前进。
“我喜欢妈妈叫你的方式,那是怎么读的?”
“Spring”他说。
“妈妈家乡的语言好奇怪呀。”
“妈妈没有家乡,妈妈是流浪的民族。”
“妈妈在英/格/兰出生,就是英格兰人嘛。”少女的脚尖停下了。
“妈妈告诉我她是犹太人。”
“不和你说了”少女撅起嘴,脸颊鼓鼓的,“我就要走了,愿你能成为英雄吧。再见。”
“我会的,再见。”
少女又开始跳舞,她旋转着跳上了甲板,母亲站在甲板上催促她,雪白的船帆鼓了起来。
少年痴痴地看着船帆,那片白色渐渐淹没在海平线里,一片的海浪卷了过来,少女的笑声如银铃般,慢慢的远了。
他被维克多用钢笔戳了戳,他回过头,维克多告诉他他该听课了。
青年撇了一眼黑板,这是军备史课,老教授的俄文拐角飞起,几乎要穿过黑板,写到墙壁上似的。
墙壁后面有什么呢?维克多说那是教授的秘密教室,凡是违反纪律的人,就会被关进那个房间里三天,直到哭着求饶为止。
维什尼亚克向窗外望去,这个教室的窗户很大,到脚跟,可以看到外面的楼梯上,停着一排黑色的乌鸦。
乌鸦展开翅膀,往基辅广场飞去。广场上挤着很多人,人群的中心,是一张巨大的海报画,用鲜红的颜色勾勒了一个伟岸的红/军战士。
维克多拉着他,同龄人已经准备参军了,维克多比他高大些,他有一头乌檀木似的黑发和一双海蓝色的双眼,像雕像似的一个结实的青年。
他也拿了一份志愿表,虽然并没有参军的志愿。他有遗传的心脏病,他还在读大三,虽然也到入伍的年纪了,哦,他读的是军工,修枪补给还是可以做的,可是这样和没参军有什么区别?
维克多这样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他潇洒的选择了前线,然后搂着青年不够宽阔的肩膀往小巷走去。
维克多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妓女,说是妓女也不恰当,就是巷口超市老板*的女儿,每个月维克多这些大学生过来领月份的时候,她都会和他们调笑很久,似乎和他们当中许多都睡过。但是最近,维克多和她聊得越来越多了。
维什尼亚克没什么缺少的东西。维克多开始搬起面粉和油来,他们都是强壮的青年,背着这些回宿舍并没有问题。那个姑娘倚着墙,格外风骚地看着他们说:“都是不久要参军的人了,还拿这么多?”
“你可别担心,娜塔莉娅。”维克多说,“Spring吃得可多了。”
“那个单词我不会念,叫他尼克不好吗?”
娜塔莉娅朝他抛了个媚眼,扭着屁股回到了灰暗的超市里面。维克多意犹未尽地看着娜塔莉娅的背影,直到被维什尼亚克甩出很远。
维什尼亚克收到了信,从老家来的,称呼是尼克,那就是继母写的。他深吸一口气,把信继续读下去。
“……父亲病重,你若是参军,你知道,军人家属可以享受……”
灯有点不稳,他收起信,从袖子里拿出那张皱巴巴的志愿表来。
同龄人穿上军装的样子比我帅气多了,他想。维克多被分配到前方,他留在后勤,也的确应该如此吧。
“保重,Spring。”
维克多紧紧的抱着他,一颗年轻人的心脏隔着胸腔咚咚地响。
“保重,维克多。”
不再年轻的男人站在林立的墓碑前,雨下得很大了,黑色的伞缘流下一片模糊的雨帘。为烈士修筑的坟墓尽量从简,恨不得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成蚂蚁大小。
“维克•沙夏•基尔波诺斯,1906-1941,死于……战役”
娜塔莉娅并没有来,她随父亲下大牢了。一个前资本家的女儿是很容易下大牢的,在苏联。
对于维什尼亚克,这个世界上还会叫他Spring的人,已经没有了。
在乌鸦飞过基辅广场的第十五年,战争爆发了。*这一次,是男人拿着鲜红色的海报,在人群中招募士兵。岁月毁了维克多,却雕琢了他。相貌英俊的红军是很受欢迎的,至少,在不知道他十五年如一日的负责修枪,并且没有几个奖章或者头衔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头发有点长,眼角一颗泪痣,一双含水的绿色眼睛的英俊士兵,是很受欢迎的。
“胆小鬼,我们可要上前线咯!”
年轻的新兵叫嚣着,他们的面庞里都带着维克多的影子。男人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他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勇敢,却不敢拿起朝夕相处的手枪,冲进那个硝烟和血肉纷飞的战场。
离异的母亲和姐姐从两年前断了书信。母亲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带着姐姐搬去了法国,自那之后,来自母亲的书信几乎是一年一件。偶尔断了一年也不算奇怪。
但这次不同,即使他再怎么捂起耳朵不愿去听,也知道法国被占领的事实。他总抱着一点点的希望,希望母亲和姐姐能逃到英格兰,能逃回那个发音奇怪的国家去,他总是这么希望着。
直到德国人打进基辅的那一天。
德国人怎么会打进基辅?德国人怎么可能打到这里?德国怎么可能撕毁条约?农田被毁了,飞机被毁了,可是基辅不会毁灭。所有留在“后方”的人,已经被盘旋在基辅上空的飞机,搅成了一团浆糊。
我们不是什么后方了,我们是最后的人。他收到的消息,自己所在的营阵已经所剩无几,城里留守的人,再加上从前线退下的一群伤员,几乎可以说弹尽粮绝。从天上飞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来。
他拿起了枪。这不是需不需要后勤的时候,这是所有人都要为生存而搏斗的气候。不过说来可笑,这好像是修了十五年枪的男人头一次端枪杀敌。
一个德国士兵走过来了,他穿着黑色的衣服,端着步枪,应该没有看见维什尼亚克,他解开保险,将窗户拉开一条缝,端正,对准,扣动扳机,那个人很快就倒下了。他是个青年人,和刚参军的自己差不多大吧,看得出他有刮胡子,说不定还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他只是一摊血肉了。
维什尼亚克迅速的逃下楼,溜进那个巨大的教室,他现在藏身于自己的大学里,他打开墙壁的暗门,躲进了秘密教室。不一会儿,他被墙壁外丁丁咚咚的军靴声震得耳朵疼。
这就是维克多过的生活吗?
维什尼亚克抱住头,开始呢喃那些亡者的名字来。
“万尼亚,谢科奇,克拉克,莫洛斯,弗托里亚克,扎赫沃基……”
神啊,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幸运才是。
老教授的秘密教室大到足以让他和其他几个青年暂时修顿。开始几日还能接纳伤员,那些人死了以后,就干脆把它变成了最后的营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却没有变。不过是黑板变得光滑,玻璃变得混浊,世界变得硝烟纷飞,接受了教育的人类变得更加疯狂无知。
房间应该是化学教授或者物理教授的,男人很熟悉各种颜色的药品和奇形怪状的玻璃器皿。队伍里似乎只有他把大学里的东西记下来了,除了维什尼亚克,不会有人去碰这些奇怪的粉末。
这次围剿战打得比他所见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残酷。德国人在头几天还只是开着飞机盘旋,甚至接受投降。而现在印着十字架的坦克在广场上横冲直撞,把几天前的尸体碾压得一片模糊。
维什尼亚克从第八天起失去了最后一个队友,他躲在子弹壳成山的房间里,尽管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他还是选择在晚上躲进去,然后打开那些棕色的小药瓶。那里的黄色粉末味道很可怕,男人有些头痛*,他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开心。维什尼亚克决定出去走走,他不饿,他只是想了解那样一点外面的情况。
他出门,教室还在,两侧的落地窗被打得稀巴烂,一地的玻璃渣子。乌鸦穿过空空的窗户,像子弹一样飞了过去。就像十五年前,他托腮坐在窗前,看着乌鸦飞过广场那样。
一个德国士兵过来了,他不像第一个,他老了,像现在的自己,头发长了好多,脸上满是伤痕。德国人带了一排的士兵,举着枪慢慢的靠近维什尼亚克。
维什尼亚克笑了笑。身后的教室忽然迸射出巨大的橙红色的炙热花朵。
“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了)”
维什尼亚克闭上眼,往后重重倒去。
黑暗不知过了多久,少女银铃般的笑声传了过来。
“Spring.”
像妈妈的呢喃,像维克多的问候,像娜塔莉娅生硬的说出来的那个词,
“我是Spring.”
“我来找你了,姐姐。”
Spring忽然流下了眼泪,少女捧着水晶球走进他,她还是那个在甲板上跳舞的少女,穿着雪白的纱裙,却裹着军绿色的上衣,双目变为全白。
Spring已经不是Spring了,他读了大学,参了军,做了十五年的懦夫,不过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把几包黄色的粉末引燃而已。他是懦夫,他从来都不是英雄。
“维什尼亚克•葛利高里•伊万诺夫。”
“你被选中了。”
“虽然你不是战士,也不被历史所记忆。”
“你一直是我的英雄哦,Spring.”
少女的笑声如银铃般,慢慢的远了。
*(苏/联的超市非今日超市)
*(指1941-1945的苏德战争)
*(设定是非常不纯的TNT,(我可不希望儿子被TNT毒死……)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弄出一点TNT的就不要深究了。)

对那些自然衰老的人来说,所谓的“过去”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越是想要紧紧抓住,反而越快从手中溜走。
那么,对我们这些已经告别了“衰老”的人来说,又会如何呢?
总有一天,我也会把曾经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吗?
一如既往的,伊克斯在那凌乱不堪的小阁楼里醒来。
衣物、书本和各种杂物四散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也是一片狼藉。
她呆呆的坐在床上,任由十分不合身的睡衣从一边肩头滑落,原本应该盖在身上的薄被也只剩下一角还勉强勾在脚上。
大概呆坐了有五分钟,她才动作迟缓的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以一秒三帧的慢动作扭过头去,打量了一下窗外的明媚阳光。
似乎总算意识到已经是白天了,她终于慢慢的下了床。
在绊倒了好几次之后,伊克斯不耐烦的踢掉了缠绕在脚上的被单,从桌子上的一堆杂物里刨出了几块看来还能吃的饼干塞进了嘴里。
虽然瓦尔基里不进食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不过早上吃几块饼干算是从很久以前保留下来的最后的小习惯了……
……对,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伊克斯看了看墙上斜挂着的镜子,里面映出了一张很明显没有睡醒,但还算是可爱的稚嫩脸庞。
变成这个样子,已经有多久了呢?
298年?297年?
虽然一开始还会每天为了这张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惊讶,不过都已经过去了自己都懒得细数那么久的时间,对这样的姿态也早就熟悉了。
这么说来,今早我似乎做了一个梦……
……一个关于记忆的梦。
好不容易以龟速完成了早上的梳洗换装,伊克斯拖着还是有些像在梦游的脚步走下了阁楼。
楼下小教堂的部分还是一如既往的空无一人,虽然不至于像阁楼上那样有如遭遇了小偷入室一样混乱,不过桌椅上也都已经落了一层灰尘……不过伊克斯显然不打算去清理,反正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会来光顾这废弃已久的教堂。
倒不如说,搞不好都没人知道这里其实是有人住的。
她无视了已经有点歪斜的十字架,径直走向了连接地下室的暗门。
一片漆黑中,她摸索着打开了头顶的吊灯。
一瞬间,仿佛不该出现在这废弃教堂里的光景出现在眼前。
和头顶的哪里都不一样,这间小小的地下室里十分的整洁。
桌上装饰的鲜花,让本来空气不怎么流通的房间也多了些新鲜的味道。
伊克斯默默走向房间尽头,一尊小巧的女神像就摆在木制的台子上。
“我的女神,您今天也是如此的光彩照人。”
于是,伊克斯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今天的第一抹可以称之为“笑容”的表情。
自从将近三百年前,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虽然已经辗转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不过伊克斯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生活节奏。
每天向她的女神布伦希尔德问好之后,这一天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虽说当初为了适应这个身体也算是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不过在意识到瓦尔基里的形态比恩赫里亚的状态要有力很多之后,她基本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少女的样子过活了。
几乎连自己当初是否真的曾是一个人类男子都变得无法确定了……
……所谓的记忆,其实是个很不靠谱的东西,不是吗?
当年,伊克斯终于适应了瓦尔基里的力量,她便毫不犹豫的向那曾出卖、背叛她的人们展开了报复。
可是当一切结束,她开始不知所措。
在无所事事的游荡中,她偶尔去搅乱那些审判魔女的现场,偶尔在战后的荒野上闲晃,虽然也曾试着去发展别人成为瓦尔基里,但说实话,她并不在意最后的结果如何。
于是她开始选择偶尔在一些地方定居,而被选中当做她的住所的,都是一些远离人烟、荒废已久的房屋。
如果恰好那是个教堂,她就会运用曾经的知识和技能,偶尔也冒充一下“好心慈祥的神父”。
不过近几年来,人们似乎都变得不太需要神的开导,就算栖身于教堂,也鲜见有人来访。
他们似乎更愿意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也不曾留意那个穿梭于自己身边的年幼身影。
宁可沉沦于这些终有一天会消失的东西,却不曾看见布伦希尔德大人赐予的这永恒的姿态。
可怜的人们啊,这就是为何你们无法得到女神大人的垂青。
今天,伊克斯也照旧冷漠的看着一切。
……可是,总觉得我似乎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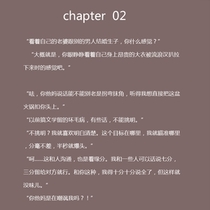

Chapter 1
00
Spring从梦里醒来,身边一台老旧的黑胶唱片机吱呀吱呀地叫着,机针快坏了,但是现在已经没人能修理它了。
他是一个要价高昂的雇佣兵,尽管他住在贫民窟里。他正为某个情报机关服务着。瓦尔基里的力量让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虽然带着面具,束着胸脯走路都不舒服,但是没关系,“她”有无与伦比的“异能”。
维什尼亚克•葛利高里•伊万诺夫。这是他“生前”的名字,被那个和姐姐长的一模一样的白眼女人带回“现世”,已经是第五年了。
他不曾变化过。他仍是那个三十五岁的英俊乌克兰军人,金栗色的头发和翡翠绿的双眼,眼角一粒泪痣,却看不到一丝新增的皱纹。
除了无可避免的瓦尔基里状态,他什么都很满意。Spring做了个很成功的买卖,他把瓦尔基里的力量出卖给人类,让“恩赫里亚”的自己足以维持生计。
他给自己倒了杯水,墙上的钟咔哒咔哒地响着,到时间了,他掏出一把枪,雪白的枪,看上去和工艺品差不多,它是一把白化了的英格拉姆*。他把它别在大衣里,然后走出门去。
01
“你听过Spring吗?”
那个男人梳着大背头,胡子拉碴,穿着松垮的黑色西装,右腿是义肢,一副黑道老子的模样。
谢科奇警惕地打量了这个男人一会儿,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近距狙击枪。
“告诉他!谢科奇。”
房间里传出上司粗重的嗓音和一片甩骰子的声音,松垮男笑了笑,谢科奇放下了枪。
“Spring是恶魔。”
年轻人面罩之上露出的双眼宛如黑曜石一般深邃,松垮男盯着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他有两把纯白色的猎枪,款式老旧得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了,但是他能用它们做任何事。”
“我是说,任何事,包括他是个半盲,必须借助猎枪来走路的事。”
“他说他可以用枪看到我们,就像正常人一样。他总是面罩遮脸,双眼也不会睁开,他就这样走在最前面,却躲得过所有子弹。”
“他不会和我们交流,他的面罩没有嘴部的滤网。”
“他是组织的秘密兵器。”
“很好,很好,”男人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抚了抚,拿出一沓钞票来,“谢谢你,年轻人。”
“我不能收钱。”
“你的奶奶需要,让我想想,她需要治病,是不是?”
“……抱歉。”
松垮男打量着谢科奇,不愧是特佣兵,完全不会质疑“客人”的情报来源。这太有趣了。
“我想你的奶奶经历过‘大清洗’,我没猜错吧?如果她精神好的话,请允许我拜访一下这位女士。”
“……”
“那让我换个说法吧,带我去见见你奶奶,我会替你负担一部分医药费,而你可以全程站在我和你奶奶之间。我想你不该怀疑一个嗜赌多年,右腿截肢的中年男人,会对一个经历过世纪沧桑的女英雄下手。”
谢科奇沉默了很久,轻轻地点了点头。
02
娜塔莉娅的病房在走廊最尽头,那里设施比不上之前的任何一个房间,但是足够安静,适合一个垂死的病人。
坎瓦斯悠哉悠哉地走在安静的走廊里,年轻人换上了普通的衣衫,谢科奇看上去十分文雅,却能感觉到他的肌肉透过薄薄的衣衫,发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年轻人回过头,眼神有些飘忽不定:“我的奶奶,似乎,有些不清醒。”
“哦,怎么说?”坎瓦斯挑眉。
“她一直在梦,梦见了一个人。”
“似乎是她少女时代的老朋友了,那时他还很年轻,在基辅读大学,她是百货店的女儿,几乎和每一个英俊的大学生都上过床,他那个纯良的小室友很想追她,她却喜欢那个他,就是说,她梦见了曾经的真爱。不过他后来参军了,她也下了大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她说他叫尼克,他没有老。”
谢科奇停住了,到了走廊的尽头,房门上写着花体的娜塔莉娅,谢科奇轻轻扣门,一个沙哑的声音叫他进来。
“那个,娜塔莉娅奶奶,我带了客人,说是采访您。”
“让他等着!尼克在这里呢。”娜塔莉娅似乎比听说的更为健康,她甚至对尼克笑出了声。
“奶奶,别犯傻了。您在做梦。”
“让我进去。”
坎瓦斯轻轻摁住了年轻人的肩,擅自推开了房门。
娜塔莉娅半躺在病床上,一个金栗色头发的男人守在她床畔,男人很年轻,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普通的母子。
“啊呀,你怎么擅自进来了呢?”娜塔莉娅像少女一样撅着嘴,转瞬又笑了起来,这一定是少女时代流下的影子,她笑起来那样充满了美好和挑逗,皱纹也无法掩埋美丽。
“不过,既然你来啦,你就一同采访我们两个吧,我是娜塔莉娅,他是尼克。”说着拍了拍床边的椅子,示意坎瓦斯坐下。
坎瓦斯没有坐下,他盯着尼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朝他伸出手来。
尼克对他笑了笑,他的眼睛是翠绿色的,像森林一样。他们友好的握过手后,坎瓦斯才坐下来,而谢科奇静静地站在一边。
“我只是附近的居民,似乎很像她的旧友,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尼克说。
“那么,您介意我问您的年纪吗?娜塔莉娅小姐?”坎瓦斯笑道。
“这真是不礼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1912年出生的,遇见尼克的时候,我才十五岁呢。”
娜塔莉娅伸出手想拍拍尼克的肩膀,却使不出力,尼克托住她的手,轻轻放回床边。
“嗯……然后他和维克多就参军了,他那样胆小,从不上前线,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男人。做英雄的妻子哪有不守寡的呢?我只要一个陪我聊天,带孩子的男人。”
“哦,在牢里那会儿吧,我的父亲……”
坎瓦斯认认真真地做下了笔录。采访结束之后,娜塔莉娅说她要睡觉,于是尼克和坎瓦斯就被谢科奇请了出去。
“你做的很不错嘛。Spring。”
坎瓦斯摊开那个厚厚的笔记本,前几页全是模糊的照片。一个带着白色猎枪的背影,很窈窕,似乎是个少女。
“我真不知道这些荷尔蒙缺乏的年轻人怎么了,你这样一个美人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么久,居然都没发现。”
“我说的没错吧?Spring?”
Spring盯着他,他也盯着Spring,那双绿色的眼睛终于软化下来,他说,“你要问什么?”
“说服军人还真是易如反掌,只要不涉及国家利益,他们就……”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问完滚。”
“我是你的同类,可以加时吗?”
坎瓦斯饶有兴致地看着Spring努力掩饰惊讶的表情,有些小得意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瓦尔基里,十六岁,是这些女神的年龄上限了吧。而且你的瓦尔基里,唔,叫什么?”
“布伦希尔德叫我海芙约特。”
“嗯,对,海芙约特,似乎很高啊,裹在面具和大衣里,还真看不出性别。”
“我需要知道一些你的东西吧?”Spring冷冷地说。
“行,这没问题,我的瓦尔基里叫做格恩达尔,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她和你一样,具有了不起的异能。”坎瓦斯顿了顿,然后压低了声音,“她可以改变你变身的时间。”
“想做个交易吗?我想你做佣兵一定拿到了不少钱,而且也知道很多的……”
“让我考虑一下。”Spring伸手示意他停下,“您居然亲自跑过来推销,我很感动,但是这笔买卖关系到我自身的存亡,我必须慎重。”
“当你可以任意切换身份的时候,你已经长生不死了。”坎瓦斯忽然又说,“这话题太无聊了,去喝一杯怎么样?布鲁克林有个不错的pub。”
坎瓦斯伸出手,他拿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黑发的年轻人的。
Spring深深吸了口气,“你说吧,多少钱,可以让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毁掉。”
“不多不少。”坎瓦斯笑了笑。
03
Spring穿着松垮的帽衫,这让他看上去和只熊似的,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进个鱼龙混杂的酒吧还是让他手心出汗。他不停地摩挲着伏特加的杯口,将自己的温度散发出去。他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在那把雪白的英格拉姆之下,是一捆砖头似的钞票。
“博伊尔先生,他在那里。”
侍者的声音淹没在鼓点之中,Spring被坎瓦斯的到来吓了一跳。
“你拿去吧。”Spring说,“把维克多和Spring的资料给我。”
“是什么让你不惜倾家荡产也要销毁你的老友?你喜欢娜塔莉娅小姐吗?”坎瓦斯抓过那杯伏特加一饮而尽,“这太令人好奇了,真的…”
“娜塔莉娅以为他还活着,她以为我活着他就活着。”Spring抢过杯子,把冰块倒在吧台上。“她想找他赎罪,她玩弄了一颗单纯的心。而我要继续活下去,就必须是Spring,而不是尼克,也不是旁的人。”
“……”
“你满足了吗,坎瓦斯,你满足了吗?”Spring的手指插到发根里,显出痛苦的神情。
“不,我很满足,感谢你的合作。”坎瓦斯提起那个笨重的旅行箱,往酒吧门口走去。
“好了,我做完了,放我走吧。”
Spring喃喃自语道,身边的侍者把空了的杯子重新满上了伏特加。
坎瓦斯站在酒吧门口,他的妻子站在对街的杂货店门口,就像以前他们夫妻恩爱时那样,坎瓦斯从鬼混的酒吧里出来,妻子买好了晚餐,两人一起哼着歌步行回家。
但这次不同,任何一次都与这次不同,她的妻子睁着雪白的双眼,带着莫名的压力朝他走来。
“靠。”
坎瓦斯骂了句脏话,迅速的躲进黑暗里。
FIN

马路的对面,那个影子在对自己露出笑容。
虽然只是一个看不清的黑影,虽然两人之间正充斥着车水马龙。
可是伊克斯确定,自己看到“她”了。
看到了“她”一如过去的微笑。
可是,“她”是谁……?
伊克斯最近一直能感觉到,曾经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出现了些许波纹。
他们以模糊不清的黑影的形态出现在不经意间,等想要仔细打量一下的时候却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可是只有一点伊克斯是知道的。
那些黑影,对自己充满了怨恨。
伊克斯对怨恨并不陌生。
很久很久以前,当他亲手把无数人或是送上火刑台,或是沉下水底,或是关进钢铁处女……他都能感受到对方深不见底的怨恨。
多年之后,当他变成了她,当她知道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拯救”只不过是欺世之言,她也曾觉得自己被怨恨也是理所应当。
只不过,伊克斯不喜欢这种“来自背后”的怨恨。
并不是说伊克斯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她只不过是不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影子隔三差五的在镜子里/阁楼角落/偶尔抬头看到的玻璃上/路上的水洼里……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地方冒出来……而且还总是一闪而过,这算是闹鬼吗?!或者说闹鬼搞不好都比这样有意思?!
如果办得到,伊克斯一定会找机会揪住这些影子痛揍一顿……这大约三百年来她都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很可惜这看起来是不可行的。
于是,在被这些黑影“骚扰”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反而渐渐习惯了这种诡异的生活。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瓦尔基里,适应力不高怎么行呢?
我的布伦希尔德女神啊,难道这也是您赐予我的考验吗?既然如此,就让我来努力克服他吧!
直到“她”出现在了眼前。
和以往的黑影不同,“她”一直站在那里。
直到站立不动的红色小人变成了绿色,直到身边的人开始了涌动,那笑脸才终于消失在了行人的潮水中。
……不,这或许也只是个错觉,其实“她”也和那些黑影一样,只是一瞬间就消失在了视线中。
只是对伊克斯来说,这一瞬间却是那么漫长。
直到周围的人潮停止又向前的重复了好几次,伊克斯才反应过来那个影子已然消失。
这是头一次,她对黑影有了不同的感觉。
她甚至开始怀疑,那个影子真的对自己微笑了吗?还是说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影子?
这么多年来,伊克斯早已对记忆这种东西不抱什么期待,就连钢笔写在纸上的字迹也会随着时间渐渐变淡消失。
她知道自己在遗忘一些东西,但那看起来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就一直对其听之任之。
可是今天,她第一次开始觉得恐慌,甚至开始怀疑几分钟之前自己的记忆。
但是她也知道,那个黑影并不是什么记忆混乱的产物。
“她”刚才,确确实实就在那里。
真正让伊克斯感到恐慌的是,那个如此熟悉的影子,如此动人的微笑。
……可是他/她已想不起来那是谁……
……美丽的奥莉薇娅,就让我来拯救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