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从旧街的重机械里发出声响,不卑不亢的急促的提醒着人们剧终。
一切剧终在1912,又全部从1912开始。
而活在当下的我们正渴望着未来的强大。
打破他原有的沉寂,从那历史的躯壳中逃亡,走出那条没有帝王束缚的道路。
那是我们崛起的时刻,无论结局怎样,脚踏实地的做好“我们”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拿起笔做武器,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战场。
将这份过于沉重的希望命名为——民主共和国!
【民国
叶洛他小时候总是听母亲说,江那每年都要死那么一两个人。
据说是有江神,也据说是有河童,说法各自不一,不过反正就是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在那江中死去,有些甚至连尸体都无法找到。
不过叶洛虽然是将这传说从小听到大,也真见过有个人家难得出了名人才却被那江神收走时哭天喊地的悲痛场景,他却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这个微小的家庭身上。
直到某一天为止。
“哥,爹娘呢?”天色已晚,他们点起油灯,父母却仍未归来。
哥哥拿着烟杆,看了看夕阳已经没去的天边:“他们下午说去河边玩了,现在还没回来。”说着,又拿起那烟杆吸了一口,搞得屋内乌烟瘴气。
“......”叶洛沉默着看着江那边,江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商船缓缓地从江上渡过,如往常一样。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江,叶洛心中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叶洛将电报放下,叹了一口气。
结果那不好的预感最后还是灵验了——那一夜不久之后,他便得知了父母死亡的消息。
父母的死亡对于叶洛来讲不仅仅只有心灵上的打击——更多的,是现实上的打击。叶洛他现在也就那么十几岁,还是个读书还没读成的书生而已;他只有母亲是本地人,而且也没多少亲戚;父亲是外地来的,年轻时叛逆,早早的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只有哥哥还和他偷偷联系着,自然也就没有直接来自家庭的援助了。
一般这时候都是大哥站出来承担起家庭的担子,可惜在叶家不能——叶家长子早早就染上了毒瘾,现在身子早就已经不行了,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年寿命剩,现在反而还成为拖油瓶——他们父亲的兄弟说要接兄弟两到上海,不过长子的身体早就已经承受不住过长的旅程了;而出于道德和兄弟之间无论如何都难以磨灭的情感,叶洛也就只能留在这里照顾他的哥哥,直到他的哥哥身体恢复到能够去上海、亦或者是死去为止了。
因为某些非法交易,叶家中倒还是有些积蓄,不过这积蓄也撑不了多久...‘这样的话,不行的吧。’
如此的,叶洛也只能叹叹气,将那些书本放回家中那已经有些年代了的书柜上,将那从来只有父母拿起过的账本翻开。
被那毒侵蚀了的人,终究不会有多长寿命。
叶洛将之前父母教的、做的、全部都从脑中挖出来,努力将自己武装成一个与他的父母一样的商人,连同那时候梧州商人的腐朽处都一并学来;他吃了不少他那时候还未能接触到的社会黑暗方面的苦,不过也总算是把这生意做了下去,换得钱财,能供生活,也能给他的哥哥买药护护身体,延长下那不知道何时会燃尽的寿命。
日子也就这么平淡而又不平淡的一天天过去,那乌烟瘴气也未曾在屋内散去;而父亲兄弟那边也是一如既往地通过电报来保持联系,电报中常常都是他父亲兄弟所写上的关切之语,偶尔还能看见那似乎是比他大了一岁的表哥写上的东西——应该是大了一岁吧,叶洛他也不大记得了。
他的表哥理应和他姓氏一样,不过实际上他的表哥姓白;他的父亲兄弟也姓白,据说是因为和家里闹了矛盾,便索性改名换姓了。
叶洛以前经常听他父亲叨叨父亲兄弟的事情,不过现在倒是经常在电报上看见父亲兄弟在惜叹父亲的死去了;而白里芬终究是个少年,写上的东西自然也不同于他的父亲,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少年气息;不过白里芬和白父的字特别相像,都一眼看上去给人种书生的感觉。
“最近又来电报了呢,哥。白里芬好像学的还挺好,以后说不定有出国留学的机会。”还真是让人羡慕啊。看着书柜上那已经许久没翻动过的书本,叶洛默默将剩余的话吞下了肚子。
而叶洛的大哥也如叶洛想象中那一般,对这件事毫无兴趣、话语中甚至有对白里芬这种人才抱有轻蔑之感:“哦,所以?你也想要那样?那么早点抛下我去上海不就可以了。”
“我没有那么想,哥...”
“哼,你之前不是很想读书来着的吗?天天抱怨都快要成怨妇了我可现在还记得——而且你现在不是经商吗?你也听那个家伙说了吧,商人也是去上海比较有前途的哦——”
听着自己兄弟的话,叶洛也只得沉默。
他的哥哥随着身体一天天变弱,脾气也逐渐开始变得古怪起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兆头。
‘...说不定这日子是要到头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什么妖怪上身了还是招惹到了哪路的神仙,叶家在短短一年内便死了三个人:两个被江神收去,还有一个是终于因为那外国来的东西而仙去。小小叶家也就只剩下了小儿子一人。
叶洛站在他兄长与父母的坟前,低垂着眼眸也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仔细一看便能发现眼圈都是肿红的,似乎是很厉害地哭过——谁都不明白这个毫无贡献的兄长到底有何处值得这少年如此伤心,不过他兄长气息断了的那天,他确实是哭过。
毕竟兄长已经是他最后一位关系谈得上亲密的亲人,而且.....
——“现在你就没有阻碍了吧,”兄长气息尚未断时,他忽然说道,“去上海吧,你。”
——“父亲他也,一定是这样期望着的。”
——“去吧。”
在那一瞬间,他终于再也止不住哭泣。
“我能够去你们那里吗?”
他最终在电报单上如此写道。
并获得了对方肯定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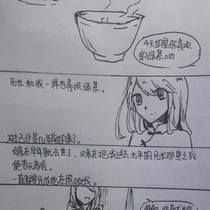
“楚老板,”茶房伏在楚薰耳侧,“今日那位藤野先生又来了。”
“请他进来。”楚薰正卸着头饰,藤野康信也不急,坐在后头看着戏子卸下一身行头。“今日我似乎来得晚了些。”
“你也不能日日往这梨园跑。”楚薰侧过头,涂着油彩的眼角微微上挑,本是清秀的面孔被嫣红的眼妆带出几丝媚色。“若是想听,哪日唤我去给你唱一曲便是。”
“楚先生的本领我自然是知道的。”藤野压了压帽檐,“上次的事,我也未有谢礼于你。”
楚薰勾起一抹极轻极淡的笑,而后又抿唇,一点点卸下面上油彩。“唱戏……便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事了,你若说,我怎会不答应。你且放心,昆曲我唱得,京腔我亦唱得,花旦那手扇子功夫,我亦是不差的。”
“那我便恭敬不如从命。”
楚薰长长的睫羽垂下,去了妆容的面孔犹如失了血色般素净,只亏了唇边那点痣,瞧起来才多了几分人味。
“楚先生,”藤野又开了腔,“我见外面天气不错,若是不忙了,出去走走可好?”
戏子点点头,便借着藤野伸出的手起了身。
“这两日雪停了,却有些寒意,添件衣服吧。”楚薰依旧点头,取了门口挂着的大衣披在肩上。
两人走在街上,除脚下踩踏雏雪时轻微的响动,倒也没有其它的声音了。楚薰本话不多,平日也都是藤野引导,此时藤野不开口,楚薰便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走了一段,藤野忽地在某棵树下停下了。
“我依稀记得,楚先生所在的梨园里,也有棵梨树。”藤野仰着头望着那棵被雪缀着的树,“我便时常在想,楚先生在那树下唱曲儿的时候……”
楚薰便起了个戏腔,“海岛冰轮初转腾……”腔调悠长绵转,楚薰的戏一直唱得极好,藤野有时觉得,这人或许就是为这戏留下,才不至于到诗中乘风归去的地步。楚薰侧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中也尽是戏,藤野仿若见到了那位媚态撩人的杨贵妃。
楚薰唱了两句便作罢,神色再次恢复到平日里的清冷,“不知怎么……忽然有些累。”
“我送你回去。”藤野笑笑,与楚薰并肩,“几日后再去拜访,到时将谢礼一并送上。”
楚薰嗯一声,只静静的听藤野讲他们那边的趣事。
几日后,小厮跑进来,楚薰刚上好妆,便开口询问,小厮只摆摆手道楚老板亲自去吧,他也只得起身去门口。
肯花钱捧戏子的不少,却少见这样的排场,饶是楚薰,见到那几车艳红的花也不禁一愣。转念一想,他便记起了藤野前些日子的话,然后又不禁有些犯愁,这花可放到哪里去好……
而后他去书屋找藤野,对方正捧着书,桌上的茶氤氲着热气。
“这谢礼,是否太贵重了些。”楚薰寻了几本戏本,藤野从书中抽出目光,为他包好戏本,这才开口,“这是日后请楚先生唱戏的花销,我倒是觉得少了些。”
楚薰不再说话,抿着唇笑了起来。




1922年大家的去向
[为了方便大家互动]
[没有说明地区的请评论我或者群里戳我我改]
[指的是主线开始的1922年这一年的时间请注意]
——主杭州——————26人
Voralyt 杭州
苏凛冶 杭州
周生 杭州
霍去病 杭州
湮辰 杭州
韩梅梅 杭州
许霂 杭州
许轩 杭州
乞丐 杭州
白琼 杭州
邹何 杭州
撸炮 杭州
君挽 杭州
黎 杭州
吃你 杭州
燕砸 上海至杭州
夏荷 南京至杭州
李柊 杭州
宣婳 杭州
宣顥 杭州
苏凛冶的管家 杭州
凌宴 杭州加天津
梁舟 杭州加天津
Sif 杭州及上海
李舒叙 杭州
晏玙咲 上海到杭州
——主上海——————16人
林悦 上海加杭州
谭鄂 上海加杭州
陈辞归 杭州加上海或全国
曲少游 上海
月丫 上海
徐云清 上海
刘言 上海
刘念 上海
叶剑碑 上海
苏明黎 上海
赵青釉 上海
赵青瓷 上海
王昭 上海
林碎 上海
黑川 上海
余耀华 上海
——天津——————2人
窕诋 天津
莫无魇 天津加外地
——北京——————4人
林清水 北京
朱笙 北平
林斌 北京
天弥 北京
——佛山——————1人
辛弃疾 佛山
——到处——————1人
夏清 听说哪里都可以
共计50人

幾個時辰前,滬上落了雪。厚而重的一層素銀裹覆在建築與道路上,使四處流溢著俗世之氣的街道生出一種奇特而莊重的美感。或許是因為天氣的緣故吧,街上並沒有多少行人,因而顯得與純白的街道相符似的寧靜,除此之外倒是有幾個頗為活潑的孩子在街上四處跑動,約莫是要打雪仗吧。藤野如此猜測著,心不在焉地翻看著新進貨的書籍,字的行跡模糊得要命,使他讀不進去。
偶爾也會有這樣的時候,無論什麼東西都讀不進去,大概是內心浮躁的緣故吧,不過藤野卻很難明白過來自己之所以浮躁的根源。或許是久違于美使自己的心難以沉浸在欣賞的態度裡吧——通常有這種感覺的時候,他會去找青樓裡的女人喝茶,欣賞她們那種慵懶又頹唐的美。
可藤野又隱約覺得這種空洞感與往日有所不同,單純地欣賞女性的美色,是不可能會治好的——非但不會治好,反而讓他有了如果那麼做,對美的感受會變得更為遲鈍的預感。雖然說不上是江郎才盡,但維持著這種感覺說不上是好事。
藤野闔上手中的書籍,走向書屋之外,素白色的街區上,幾個孩子正在奔跑,其中一個則一不小心撞上了路過的路人。會發火嗎?藤野想著,有些感興趣地看向被孩子撞到的男人,但那男人並沒有抱怨,只是將孩子扶了起來。隔著一段距離,藤野聽不清對方講話的聲音,不過,從對方的神色來看,並沒有發怒。
真是相當溫柔的人。藤野在心中默默做著評價,卻發現對方徑直向自己所在的方向走來。是書屋的客人啊。藤野反應過來後,默默地為對方打開了書店的門。雪天的客人是個十分纖細的男人,比自己要矮上一些,不知為何顯得有些怒氣沖沖的——是因為方才被孩子撞了的緣故嗎。藤野妄測著,將自己的視線埋藏在了書籍之後,坐在櫃臺後佯裝出在仔細閱讀的樣子。客人此刻正在挑選著書籍,是不是稍稍做些別的事比較好呢?藤野模糊地想到,注意力因過於乏味而開始注重起眼前的文字,白紙上的黑字有一半都沒讀進去,與其說自己在閱讀,倒不如說是隨意地眺幾眼、且理解只能浮在文字的最表面……藤野歎了口氣,將自己的後背安放在椅背上,好讓自己能更為放鬆些。
暫態,對方從書架處走了過來,手中抱著一摞書籍。客人將書籍緩緩攤在檯面上,藤野注意到對方伸出袖管來的手十分纖細,沒生多少繭——客人指著書,輕聲問道:“這本書應當還有第三冊吧?”
藤野聽到他的話,推了推眼鏡,看向客人所指的書。他拿著那本書站起身來,看向青年方才走過的書架,書是本探究文學的,也是他最喜歡的種類之一,應當進了不少。他看著書架,核對了一會兒,又將那本書還給了青年。
“抱歉,我去看看倉庫。”藤野說著,向對方微微鞠了一躬,好取得對方的諒解。他走到門面后的房間,卻還是沒找到那本書,不得已,只好再擺出一副笑臉回到門面上向對方道歉。
“書倉裡似乎也沒有,若先生您需要的話,可以在我這裡訂……實在抱歉……就這些吧?”藤野說著,將對方購買的書用印了康信書屋的牛皮紙包了起來,“您該怎麼稱呼?”
“李二。”男青年回答,“這些要花多少錢?”
“嗯……看您要用銅錢還是銀元付了。”藤野說著,擺弄起算盤來。他看向書屋外的街,雪霽天晴,有行人和人力車在往來。
之後,李二時常來光顧書屋。藤野常常看到青年站在書架旁,十分專注地讀著書的樣子。李二買的書,則大半是講曲藝的,也有不少是寫學問的。藤野時常會通過所買的書猜測客人的生活與個性,李二大概是個喜好中國戲曲的學究吧!他這麼想著,將對方預訂的書遞給對方翻看。
“這次就這些?”藤野問道,熟練地將對方欲購買的書籍包裝起來,臨到最底下一本時,他意識到那書似乎在之前運送的過程中變了形,“這本有點瑕疵,我去給你換一本。”
青年一語不發地點了點頭,藤野笑著將與瑕疵本相同的另一本書拿了過來,再包好。
“多謝惠顧。”藤野說著,向對方鞠了一躬,青年提著被牛皮紙包著的書離開了。望著對方離去的背影,藤野坐在柜台後思琢著該做些什麼——似乎偶爾去欣賞下中華的戲曲也不錯。
對戲曲,藤野說不上是行家,即便在自己的祖國也只不過是偶爾在節日之時對能劇、歌舞伎等稍作賞析的水平。不過,藤野對美麗的事物並不排斥,相反可說幾近渴求。尤其在異國,欣賞文化的璀璨無疑是件美事。
等到藤野閒了下來,便將書屋交付給了自己信任的店員,再去了戲園。大概是因為去的過早了吧,戲班才剛剛開始準備,台上見不到人。不停直視著戲園準備舞台,似乎是件有點失禮的事,藤野便將目光移開了。餘光裡,他看到一個身著旗袍、踩著高跟的婀娜女人——正是時下最流行的打扮。藤野看著那女人奔走,才想起過去似乎見過那張臉。是在哪兒呢?他也不確定,或許是在城裡的哪個地方見過吧。女人相當高挑,因為穿了鞋的緣故,並排一站,幾乎能追上藤野本人。除此之外,女人生得眉眼俊俏,春風嬌媚,無疑是個美人。約莫是意識到藤野在注視著她吧,女人回眸了一眼。
藤野一愣,這才想起是在哪兒見過女人的臉。是了,近些日子來,時常來拜訪書屋的客人裡,也有人有那麼一雙眼睛,只不過更為冷漠些。他想著,向女人走了過去,沒錯,那女人……肯定是李二……
藤野走了過去,脫下帽來,向對方輕聲問道:
“您……是李二先生的妹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