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场内名额已满】
这是鸟的世界。
您所需要扮演的,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的鸟类,同时您也可以被称之为“人”。
在这样的夏天,苏醒在莉芙湾的细沙海滩上的您,已经无路可退了。
海在叫你过去。
“它”在叫你过去。
---------------------------------------------
本企划定为黑暗恐怖向战斗生存企划,含有些许推理要素,分级为R18-G。
企划为文画混合企划,文手画手对战会混合抽取,会出现文手vs画手局面,不允许拉票。人设的创作需要与他人讨论并根据随机分配到的关键词,人设需通过审核,不合格人设官方有权打回让参与者重置。
企划微博主页http://weibo.com/u/5220412288?topnav=1&wvr;=6&topsug;=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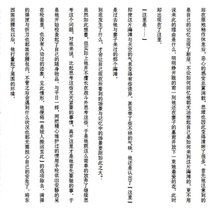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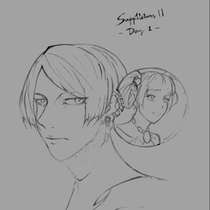

不知是從何時起,“他”誕生了意識。隨後在堅硬的驅殼和周身冰冷液體的包覆中,他意識到自己僅僅只是獨行,因此而有了不安感。
四周無人,唯能聽到頭頂有海浪互相拍打時所發出的聲響。在那聲音中,他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與寂寞還有渺小,世界本身則龐大得不著邊際。水流本身在緩慢地推進著自己的身體,向前漂去。不。他想。我還不想去那邊。但那水流卻毋庸置疑地不想讓他繼續呆在原處,不停地、一點點地撬動著自己的身軀。
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太暗了。他想,瑟縮在那層堅實的墻壁裡,等待著一絲光線的出現,可那是不可能的;他必須得上去,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光,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救贖。他清楚這一點,那份不安的心情因模糊而更加放大。
救贖是什麼呢。他想著,在冰冷的海水中思考著這件事。
想不起來。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等待著什麼。有很重要的人,離開了……是的,已經……
他就如此思考著自我的存在,順著海流向著自己也不知目的的地方,然後在海水中反復不停地陷入沉眠,再然後醒來;每次失去意識的時間都好像有一個世紀之久,但當他醒來時,他能感覺到周圍的溫度並沒有變化太多。那些溫暖而神秘的東西仍存在著,就在他身邊。
儘管如此,這世界依然寂靜。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他意識到除卻水的流動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從旁邊掠過。
他吃力地睜開眼,身體不允許他注視別處太長的時間,透過那層半透明的卵鞘,他看到龐大的黑色曲線從身旁溜了過去,隨後是一群,那些生物順著水流,但方向又有別于水流,他們仍有自己的動力。
好羨慕。他想,原來有東西能自由自在地活著。與自己完全不同,自由自在地,僅僅是存在本身便是自由的象征。說起來,原本自己也應當是那樣的……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自己的身體才變成這樣呢。他囁嚅著,但並不需要過多的思考,就能意識到了,四周拿層保護著他的“殼”,就是自己無法自由地原因。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手腕根本無法揮動,即使是簡單的動作也無法做到。無論四肢或是頭腦,都處於一種朦朧的禁錮之中。
啊,這都是因為……這都是因為,某個人的心情的關係,自己才會變成這樣。
那個人是誰。
仿佛回應他的疑問似的,隔著猶如石塊一般沉重的水,他聽到某個聲音遠遠地透過那層不穩定的液體傳了過來。
聽不清。
到底是誰的聲音。
總覺得很懷念。
啊,對了。他想起來了,他正是回應著那個人的期待,才在這個茫茫無際、令人感到孤獨的世界上誕生的。
那個人的名字是……
“爸爸……?”兩片唇瓣有力地摩挲,隨後,張開口腔重複這個字。這說不上有意義存在的話語,僅僅只能當做是隻言片語。但是,對他來說,已經足夠了。
隨後四周又陷入了寂靜。他再一次陷入沉睡。
再度醒來時,耳畔中似乎有個聲音在迴蕩,他一點一點地,將意識向著那個聲音靠了過去。那是與方才的聲音完全不同的東西。
應該說是自己的理解者、與自己相似的東西吧,或者用同類這個詞語來描述更好些?他心想,然後向那個聲音闡明自己的存在。
“是,……同類?”他確認性地向著那仿佛心臟般鼓譟的聲音問道,對方回應了他。
“是的,而且,不僅僅是種族意味上的同類哦,現在的你我,連處境都很相似呢。”
感覺是個很開朗溫柔的聲音。
不,聲音是不可能開朗溫柔的,大概,讓他感覺到那種特質的,是那個人說話的語氣和所說的內容吧。
“處境……?相似?”他重複著對方的話,試圖進行理解。對方似乎明白了他所能理解的極限,便解釋了起來。
“我和你……怎麼說呢,現在的狀態都還只是胚胎。”
“胚胎,我嗎?”
“啊,也是,你現在的狀態要理解這件事,可能還有些困難吧。”對方的聲音即使隔著那層束縛了他手腳的卵鞘,也仍然清晰,令他感到了些微的安心感。
“我該怎麼稱呼你呢,聲音。”他向對方問道,似乎是“聲音”這個名字逗笑了對方,他聽到那個人發出輕輕的笑聲,“我們這樣的存在,誕生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的存在是在那些傢伙的祈願中誕生的,嘛,可以說是那些傢伙的另一個自我吧。這樣講你能明白嗎?胚胎?”
“那些傢伙……?”
“你能感覺到似乎有什麼與自己的知覺相通吧。那就是他們啊。”
“啊,爸爸,爸爸……”他回想起那種令人溫暖的感覺,便再度唸起了那個名字,“爸爸就是……那些傢伙的一員吧。”
“你叫另一個自己爸爸嗎?”
“……自己?是,……什麼?”
大概是因為這個單詞太難解釋,對方選擇了沉默。他呆愣了一會兒,決定之後再自行理解這個詞彙。但對方再度傳遞來了一句話。
“你不覺得我們應該替代他們的存在嗎?”
“可是,我覺得我……做不到。因為,我是,回應著那個人……爸爸……的期待……才誕生的。”他語無倫次地向著那個人說道。
“嘛,要是這麼想,倒也沒什麼錯。”那溫柔的聲音安撫了他。
聲音真的很溫柔,仿佛與他講解這番事情和義務一樣。如果是聲音的話,說不能引導著自己走出這片冰冷又孤獨的地方。他這麼想著,但對方已經再聽不到了。他默默在腦海里重複著呼喚“那個人”的名字,然後在水波中向著有陽光的地方漂了過去。
爸爸。
回應著那個人的思念與期待,他向著海岸漂去。
還差一點,只要把爸爸殺掉,他……
就可以成為爸爸所期待的完美的孩子
[因為就是個大肉球在海里飄啊飄的劇情,非常意識流, 互動裡的聲音指的是140E,但我沒看到角色,就暫時不關聯了,2000字出頭]

“海星星海星星,我们一起让启暗星升起在混沌的虚空,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好不好?”
“海星星海星星,我们一起让启暗星升起在混沌的虚空,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好不好?”
“海星星海星星,我们一起让启暗星升起在混沌的虚空,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好不好?”
……
深海中,一只变种海兔子正在海星星边上蹦蹦跳跳地挥舞着白色的双手。变种海兔子的名字叫白豆腐脑,兔如其名,白得和白豆腐一样。
他从莉芙湾的这一头跑到海星星边上,又从海星星边上跑到莉芙湾的另一头,再从莉芙湾的另一头跑到海星星边上,又从海星星边上跑到莉芙湾的这一头。虽然已经跑了几百趟,但每次经过海星星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礼貌地问好。
大家都是住在莉芙湾的邻居,邻居与邻居见面以后当然要问好——白豆腐脑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就算现在处境非常危急,他也不会忘记礼貌。
“海星星海星星,我们一起让启暗星升起在混沌的虚空,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好不好?”
礼貌归礼貌,白豆腐脑用的其实是神经病一样的问好方式。开始的时候,海星星还会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斜眼瞄白豆腐脑个一两下;次数多了之后,他便决定对白豆腐脑视而不见了——神经病最喜欢引人注意,要是不理他他就会消停,海星星这样想着,但一点都不见效。
不管海星星怎么无视,白豆腐脑都会孜孜不倦地经过他身边,并像神经病一样向他问好。
终于,海星星烦了。但对这种神经病,他连宣战的心情都没有,他捡起了身边的一把垃圾,往白豆腐脑的脑门上丢了过去。垃圾在白豆腐脑柔软的脑袋上弹了一下,弹到了白豆腐脑身后。
“这就是启暗星吗?我过会再来捡哦。”被垃圾砸到后,白豆腐脑非常开心,但他没有转身去捡——兔子是要向前看的,这是白豆腐脑的兔生信条。
“启***,***!”海星星在心里骂道,但却没有说出来,一方面是他觉得骂白豆腐脑自己就输了,另一方面是他想骂的时候白豆腐脑已经不见了。
过了几分钟,白豆腐脑又跑了回来。他就地打了个滚,利索地捡起刚才弹在他脑门上的垃圾的其中两个。
“谢啦拜!”
留下这句简短的道谢后,白豆腐脑往海星星的脑袋上丢了一块白豆腐作为谢礼,然后白豆腐脑就真的在海星星的感知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白豆腐脑弹跳在白豆腐搭成的阶梯上。
捡起海星星丢下的启暗星后,白豆腐脑就造出了通向海面的白豆腐阶梯。白豆腐的弹性非常好,加上水的浮力,白豆腐脑一下窜出了海面,落在了稍低于海平面的宽阔白豆腐平台上。
白豆腐脑知道自己正在被跟踪狂追赶——穿裸体围裙四处乱晃就要承担被变态盯上的风险——这些白豆腐脑都是知道的。
被变态摸到了就嫁不出去了——不知为何,这句话作为一项常识,在白豆腐脑的心中铭刻——先不管被变态摸到嫁的嫁不出去,白豆腐脑的终生追求的梦想之一就是组建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他才不要嫁不出去,为了实现自己平淡又渺小的梦想,白豆腐脑为了躲避变态,在海面漂浮的白豆腐上拼命地奔跑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白豆腐脑在心里唱着歌,然后在空中画出了一座白豆腐桥。
白豆腐脑顺着白豆腐桥跑到了海面上空,但变态爬上白豆腐桥的振感还是通过白豆腐桥传到了白豆腐脑的脚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这里!”
白豆腐脑继续在心里唱着歌,然后在跑到桥顶的时候,在空中画出了好几架纠缠交错白豆腐滑梯。
白豆腐脑做了一个跳跃的动作,但他没跳进滑梯的滑槽,而是直接像高台跳水一样跳进了海里。
就像钻头一样钻进水面,没有水花!十分!
白豆腐脑没有因为这个傲人的成绩而忘记变态,他穿过水面后便拼命挥动六肢,划到了海底的一块不小的礁石顶上。
自从被变态盯上以后,海面都上升了。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白豆腐脑心里还是觉得变态很厉害的,如果他将来看到了可爱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他也有点想当个变态试试。白豆腐脑用几百趟的往返背熟了被淹没的莉芙湾海面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再逃跑了。
白豆腐脑将海星星丢给他的垃圾按在胸前,单膝跪下,将另一只手按在礁石顶上。白豆腐脑能看到远处逼近的黑影。白豆腐脑用跑圈和变态拉开了距离,用白豆腐阶梯、白豆腐桥还有白豆腐滑梯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赐我力量,启暗星!”
白豆腐脑从礁石里抽出了一把长剑,因为这是从石头里拔出来的剑,所以白豆腐脑将它起名为石中剑。黑影要摸到白豆腐脑还有点时间,足够白豆腐脑摆姿势耍帅了。
变态逼近了,白豆腐脑使出浑身的力气,将石中剑由下往上挥舞,砍在了变态身体一个凹陷处的一个小凸起上。
变态抽搐了一下,停下了追逐白豆腐脑的动作。
白豆腐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再次往变态身体一个凹陷处的一个小凸起上挥动了石中剑。
白豆腐脑连连击中变态身体凹陷处的小凸起,把变态打得落荒而逃。
“不要跑!”
白豆腐脑冲了上去,拼命地追打着变态身体凹陷处的小凸起,一直打到潮水退却,变态消失在砂砾的缝隙当中。
没有黎明,但新的一天却来临了,白豆腐脑被变态追赶还有白豆腐脑追赶变态的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告了个段落。白豆腐脑将石中剑插在沙滩上,在上面写了“变态之墓”四个字,然后再也没多看一眼,转身离开了。
□
天空中的白豆腐桥上有一件海星星丢给白豆腐脑的垃圾,那是白豆腐脑被变态追赶时留下的升起在虚空的启暗星。因为海面降低的关系,豆腐桥晃动了起来,启暗星从光滑的白豆腐表面上滑了下来,就像流星一样。
“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会说话的朋友,想过不用追赶变态的平凡生活。”对着流星,白豆腐脑这样许愿着。
苏姬坐在海滩上,她从醒来到发现种种不科学之处并开始走动时已经过了至少一小时。这个地方不准确来讲就像是在箱子里一样,不管是隔着公路的那个像是那种水泥墙一样感觉的阻碍物还是无法飞太高——上面好像被什么盖住了,苏姬有尝试从海那边找突破点,但可惜的是无论飞多久都是永无尽头。“算了,还是去找找有没有和我相同处境的人吧,凭着这个应该是编号人估计……不止我一个。哈,不过也不一定倒是。”她看了一下刻在自己左手腕上的091,上面还渗着血但却是无法流下来的那种程度。“继续往那边前进吧。”苏姬站了起来,她并不累,从来到这里的时候不管怎么飞或者奔跑都不会感觉到疲劳和饥饿,苏姬在飞了几圈寻找是否可以找到离开的地方的时候确定了这件事。苏姬张开翅膀以能看见人的高度沿着海岸线继续飞行并时刻注意海上或者沙滩上是否有其他人在。
“还是如此。”苏姬举起右手抚摸着天上的罩子。“虽说已经试了这么多次但果然还是想看看会不会有……还是没有啊,这可真是密封的很好,如果是食物的包装袋我简直想给他们打个五十分,在满分是十的情况下。不过可惜它不是包装袋……哪有这种包装袋的。我都开始胡言乱语了吗。”苏姬和往常一样从斜挎包里拿出手术刀在上面划了一下。“虽然感觉是无用功但果然还是想尝试一下,唉还是下去吧。哪有水泥墙能被一个普通的手术刀划开的道理。”苏姬无聊的收起翅膀在掉下去的中途又张开,“不管试几次果然还是很刺激。”她先绕了一圈确定没有任何人在这里后往海那边继续飞行。“连椰子树都没有,这样的海滩真是差评,非常差评,十分差评——不过至少我没有在这里消费。如果这里阳光明媚的话说不定会好点。”苏姬一路张望,在实在是看不到别人的情况下“我想没有谁会飞这么远吧……回去吧。”苏姬拍了拍包转身往回飞,“没人,我飞了这么久都没有人……这个海滩太大了?还是别人在我后面?或者根本没有别——人?”苏姬在飞回海滩的同时余光看见了大概不算是很远的一个身影。“嘿,看样子我的运气还可以……大概,不过这位男士看起来还真是,略高。”苏姬踏上沙子的同时收起了翅膀。“……我先悄悄走过去再说吧。”苏姬敏捷的一点点接近那个身影。“在沙子上要快速的前进还是飞起来比较好。”苏姬嘟囔一句。
苏姬感觉自己即将要吃到沙子了,她在看见那个身影后最初决定是靠走过去,然后她就像是灵光一现那样突然改变主意先往后飞起来然后开始滑翔,苏姬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埋进沙子里了我要坠落了。她在脸已经只剩一毫米之前迅速用手支撑住。“……原来他离我还是挺远的。”
苏姬抬头看着近了那么一点的距离。“我要收回之前的略高,这太高了。”苏姬将手从沙子里拔出来,拍了拍。将挎包从背后拉回正常的位置上。“我还是用走的吧。”苏姬抖了抖仍粘在裙子上的沙子。她慢慢走向据她本人目视至少有二米以上高度的人。“我真害怕其实这是棵树。”苏姬仰着头说。
苏姬跟着三米高的比利·海灵顿一起搜索海滩。在经过他透露的东西后和聊人生导致苏姬对比利的好感迅速上升——但这不是什么所谓的GAL。苏姬快速跟上比利,她从他那里得知他的编号是073。“这简直就像是大逃杀之类的。”苏姬压低声音尽力不惹到比利注意的说出口。她对这位虽然脸上带着面具而又特别高看上去就像是恐怖片里的杀人魔挺有好感,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是苏姬第一个见到的人吧。苏姬飞在空中俯视着他。然后转过头继续搜索海滩。“三米高到我都可以坐在他的肩膀上。”苏姬一边分心想着能不能坐在比利的肩膀上一边开始搜索海滩和海面。
苏姬非常小心的接近着比利,她在差不多可以搭上比利的肩膀的时候出声“你介意我坐在你的肩膀上吗?”在得到许可的同时直接迅速收起翅膀在快坐上去的时候再次张开。“不好意思。”她收起翅膀坐在比利的肩头,双手撑住脸颊。
苏姬收起双翼,站在露出的礁石上。她带着手套拿着死了的贝壳看着海面。“连条死鱼都没有,这个海滩真是十分糟糕。”苏姬将拿着贝壳的手臂直直伸前,在确定不会丢到礁石上后松开了手。“……呃我还是张开翅膀比较好。”苏姬在滑下礁石之前张开翅膀飞了起来。“这个海滩,除了礁石和偶尔能见到的死贝壳以外,简直死气沉沉。”苏姬想了想又补充一句,“虽然它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很死气沉沉,连天都是阴的。除了格外凉爽以外优点我掰手指都数的清,还是一只手的手指。”她又站回礁石上,“在和比利分开之后到现在都没有遇见其他人,是隔的太远还是在我没有去的那边?”苏姬抬头看着天空。“我简直都要怀疑这里是不是时间停止了,不会饿不会累更不会困。”她干脆坐在礁石上,不管裙子被弄湿。“现在重新理清一下,首先我在来到这里最后的记忆是医院,我可不记得我有来到这里……还是说我失忆了?但好像比利也是一样的。”苏姬将挎包拉到胸前抱住。“然后这里我曾经看过照片,不过到现在才想起,是因为阴天的这里和照片上的阳光明媚不一样吗。我记得这里传说是有人鱼出没的海湾莉芙湾,也许会和人鱼有关吗?不过我从没听说过这里……算了,从苏醒开始我到现在至少过了半天,而这里毫无变化我也没觉得疲惫之类的状态。”
苏姬隔着手套用右手摸了一下礁石。“……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在那时候尝试了几次最高差不多能飞到七十多米高,而海不论怎么飞多远都……也许有着和阻止出海滩之外的那个存在还会好点。沙滩我暂时还没有飞到尽头,也许再去探索一下会发现什么。不过沙滩上真是除了贝壳和石头以外基本没有什么。”苏姬活动了一下手指。“还有编号,我的是091而比利的是073。所在的地方也不同。……这点上有点想不清楚,先搁置。”
苏姬拍了拍手,“好像暂时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对为何我会来到莉芙湾以及为什么会有东西阻碍离开沙滩的这点暂时不明。”苏姬将手套脱下放进挎包。她将放在里面的手术刀抽出来在仔细观看了一阵后小心的拿在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