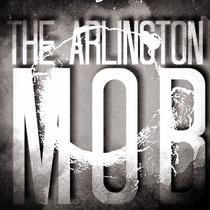
1950年,美国艾灵顿市陷入了一场危机,一颗子弹打破了多年以来黑帮与执法部门的平衡,黑帮头目迪·彼得罗被宣告死亡,暗潮涌动,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
企划简介:本企划重剧情与互动,是以1950年代的美国黑帮与执法势力制衡为主题的写实向企划。文手画手均可参加。本企划不设对战,以玩家人物“选择”为基础,重在发展自己的人物故事与剧情。
企划官博链接:http://weibo.com/u/5275215471?refer_flag=1005055011_
企划官群:595660494
(备注角色名与编号进群,私信企划主或官博审核人设以获取角色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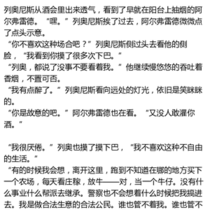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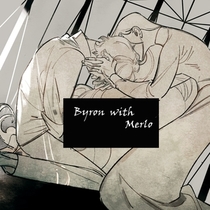

艾灵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办公室。
这间屋子狭小又杂乱,笨重的老板桌和皮圈椅占据了一半的空当,再加上一整排木板柜,陈年档案堆积如山,隔板不堪重负,随时可能崩塌,到时坐在下方的人可就要倒大霉了。除此之外,在桌对面只剩下一溜儿长方形空间,摆放着两根独凳。
室内的浅色百叶窗叶片常年半合,墙壁是由雏菊牌绿漆涂成的,在二十多年前尚算得上干净体面,柔嫩诗意的色调让人联想到初夏连绵的树荫。但现在好些地方已经剥落,斑驳不堪,漆皮像老妇人脸上卡住的香粉,一有什么动静儿就扑簌簌往下掉。尤其是位于门把手位置的墙面,被撞出的坑洞有食指指节那么深,露出内里白腻的石膏板,洞边缘布满了蛛网般的细小裂纹。
唐纳德·盖洛普快被逼疯,他才能平庸,但为人可亲,即使完全只是凭资历坐到了局长的位置上也没有受到来自同事和下属的刁难,是不可多得的好人一个。
而菲尔·雷斯和雷金纳德·洛克斯这对搭档是局里他最得力的员警,虽然眼下只剩一个,但绝对是最不好对付的一个。老天,你根本不可能说服一个玩儿枪的上帝使徒,唐纳德心想。
他一边揉太阳穴,一边试图让菲尔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都为雷感到遗憾,但杰洛尔的律师警告过我们两次了,必须立刻放人,发言人已经拟好新闻稿,只要超过零点就——”
菲尔尖锐地打断了他:“头儿,这是谋杀,彻底的谋杀。你知道,我也知道。”他指着窗外忙碌的警察,“要我提醒一下吗?兄弟被打死在警察局门口,我们就只能说——为他感到遗憾?让我们大家把这件事儿忘了吧,把该死的杀人凶手放了,给可怜的菲尔找个新搭档,万事大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注意言辞。”唐纳德并不想指责他话里的无礼,雷金纳德被一伙无名氏暴徒(并不是无名氏,他心底有声音悄悄这么说,菲尔说的对,你明明知道是谁)袭击,身中五枪当场死亡。而他们还不得不放走唯一的嫌疑人,因为检察官说——“证据不足,没有目击证人”——法官拒绝签发逮捕令。
菲尔瞪着仿橡木桌面,眼圈红了一片。“雷告诉我他查到了线索。”
唐纳德悚然起身,“关于——?”
他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菲尔一定知道他说的是谁。
“有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不想让我们插手这事儿。”菲尔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如果值得一个雷,也同样值得一个你。”唐纳德警告他,“你需要一个搭档,我们从不单干。”
“我不这么想——”菲尔咬牙。
“你应该——要——这么想——”唐纳德比他更坚持,“我们必须考虑到——你的处境十分危险,别急着反驳,也别告诉我你不想继续追查下去。现在雷不在了。”他做了个禁止辩论的手势。
“你的搭档势必也要参与到特别行动中,但我不敢让现有的其他人跟你一起,也不该让他们知道太多。不、我不想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不过越是这个时机,大家都越身不由己。”
是的,在艾灵顿,人情不那么容易还得起。他们起初通情达理,但你总会越欠越多,旧车应该更换了,老婆又想要买首饰,养孩子的开销永远高于预期,信用卡的还贷日每个月都比发薪日更早……日复一日,你深陷泥沼,拒绝他们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难以开口。
承诺是绞刑台的吊索,只要拉下拉杆,你就会一脚踩空,“一声脆响,向世界说再见”。唉,他还记得埃尔警员绝望的哭喊,愿地狱没有这帮狡诈的魔鬼。
他无法谴责在这片土地上的底层警察们,他们听得太多,见得太多,同样是随时挨枪子儿的职业,他们拿到的薪水袋都撑不起上衣兜。而杰洛尔之流却脑满肠肥,养得起轿车、豪宅,据他所知,他甚至拥有一个律师军团。
凶案就发生在警局门口,一个见到凶手的目击证人也没有。或许,这就是一次让步,一次容忍,一次封口费。他更不想让菲尔变成下一次的交易标的,最好是一个干净的、全无背景的搭档人选,而目前看来本·肖正合适。
“他上过战场,退伍前隶属第二步兵师,入职射击全优。他有这个胆子和能力在任何人脑袋上开个洞,不用顾忌任何人的想法。”即使是黑帮,也不会愿意轻易得罪一个美国大兵,也许平时他们身无分文、满嘴脏话、酗酒、烂赌,但惹到一个就可能出来一群,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只是一只容易被摁死的蚂蚁,但横行无忌的杀人蚁潮谁也阻挡不了。
菲尔厌恶地说,“我们还应该给他和杰洛尔颁个杀人奖章哈?”
“接受新人,菲尔,因为雷不会回来了。”他同情他,也知道年轻人的磨难远未结束。这对搭档共事多年,雷的死对菲尔来说就像断肢,你明明知道袖管里什么都没有,但你还是会痛得惨叫。“你可以试着信任他。”
信任另一个杰洛尔的想法激怒了菲尔,但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唐纳德提到接受——因为雷在他和其他人的心里是过去式了——警局收回了他的配枪和证件,纳税记录和人事档案销毁得一干二净,大家争着在葬礼上缅怀过他——因此这事儿,目前来说,就算完了,翻篇儿了。只剩下他的职位需要人去顶替,干永远干不完的活儿,现在、这儿、就有个现成人选,让杰洛尔去追捕杰洛尔吧,狗咬狗,多么精明。
但是——
“不!”他狂怒地拒绝,仇恨不会过去。雷流的血从警局门口一直淌到下水道,流进肮脏的阴沟里。怎么能忘记呢?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我要牢牢地记住这痛苦和苦涩的血味,直到——
最终的审判到来!
他会抓到人,遵守抓捕、审讯的规矩,配合检察官调查,在法庭上作证,等待法官作出裁决——接着杰洛尔就能开脱罪名,无罪释放——去他妈的程序正义!
“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逮住他的,不需要一个累赘!”
他面容狰狞,魔鬼在他体内咆哮,我会把他们都干掉,杰洛尔总该偿还血债,我要亲手送他一颗子弹!就镶在他脑门上!话就在嘴边迫不及待地想要往外蹦,但菲尔绝望地意识到自己不该说这个(至少不该大喊出来)。
“菲尔·雷斯!”唐纳德厉声道,后者愣了愣,勉强扭曲嘴角挤出一个可怕的笑容,好像那个丑陋的鬼脸附在他脸上共同地笑了笑。
上帝,原谅我,我在发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在发疯。菲尔惶恐地察觉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瞬间,他并非因信称义。是因为,我期望如神所说,一天之内,杰洛尔和他的国度的灾殃一并到来。
他羞愧难当,浑身发抖。
“去跟凯尔医生聊聊,他约过你,但你没去。”唐纳德提醒他。“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失去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的确相当难熬,但你会挺过去的——只是别再表现得像个混蛋好吗,雷和我也相处多年了,你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
“对不起。”但看医生没有用,正是因为他清楚唐纳德是对的,这事理应告一段落。
他撸了一把脸,深吸气。“好的头儿,我好的很,我保证,我只是……”
他摇摇头,“我根本不了解新人,对他一无所知。他能参与调查案件?我可不放心。去年我们抓的垃圾兵佬还少吗?一个月政府只给五十退伍津贴,黑帮能给他们五百,甚至更多。只需要他们拿枪干活,和过去一样。”
他瞄准唐纳德,扣动手里虚拟的板机,“嘭、五十块。”一次。
“嘭、再五十。”两次。
“杰洛尔杀人可能都没他们麻利,他好歹还得瞄一下准头。”
“得了,别说蠢话。”唐纳德打断下属的抱怨,“你必须得有个搭档,先从这个人开始。”他话音未落,可莱丝警员打开门走了进来,“头儿,有人找你。”
“就几句话了。”他偏头看了看,警员身后跟着一个金发混混,穿着廉价夹克,眼神像剜人的刀子,身上老远都闻得到穷酸味,不像是有正经工作,也许是专项整治案件的证人——那种需要调动警力保护的污点证人。
“让他等一等。”
可莱丝点点头,把人留在门口走了。
“你可以先试试……”他继续对菲尔·雷斯说,但这次打岔让他把那个新人的名字给忘了,他翻了翻手上的人事调令,“先试试这个本·肖。”
金发的外来者看了他们一眼,凑前几步,靠在门边。
唐纳德没当回事,“当兵没坏处,耶稣基督也曾招兵,你还能找到比他们更一根筋的吗。士兵需要被教导规矩,毕竟,比武场上非按规矩,不得冠冕。但你得耐心点儿。”
“我之所以没当成牧师,正是因为上帝告诉我缺少这玩意儿。”菲尔点出成绩单上的某个数字,“看看这个。”
“——噢,有意思,我多少年没见到这么低的文化分了。”唐纳德琢磨道,“上一个踩着及格线入职的还是1922年的艾格森,后来他调到四分局去了,凭良心说,艾格森是个勤奋肯干的好警察,但我们真不算特别喜欢他。”
“因为他真的又蠢又笨,只会拖后腿。”
“没准这个会好一些呢,诺,我答应你,如果他自作聪明搞砸了什么事儿,或者你发现了他有一丁点儿的品行不端,哪怕再小的一丁点儿,也算。再比如你觉得他身上有桑德尔那种苗头——就是去年西城区那起碎尸灭门案——不用你写长篇报告,我来替你想办法摆脱他。只不过有一点,你得发誓,你对他的评价要对得起你的良心和上帝。”
“那么,之后,我可以自己调查雷的死因?”菲尔确认。
“那么,之后,你可以换一个人再试——更多、更多的人选。”唐纳德挥舞手里的文件,有意重复菲尔的话,对对方的恼怒视而不见。
“嘿,别闹情绪小子,往好处想,这样当你有朝一日终于把自己玩儿进监狱了,起码有个搭档能代替你继续让我焦头烂额。就这么说定了,菲尔,你的麻烦事儿到此为止。”
“现在——下一个——”
“久等了先生。”唐纳德冲着金发点了点头。
后者笑了笑,“今天是我的报到日,先生,希望你没忘了。”
“但看样子我还有一场面试要过,是吗?”
“……”
“……”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本·肖,那个又笨又蠢、品行不端还可能杀人如麻的退伍兵。”
艾灵顿市南港区“一日威廉”是所有市长候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的地方,他们在大学学院、西城区商业街甚至牧师布道场装模作样地对市民福利、经济复苏和世界局势侃侃而谈,其狭隘的视界在人前突然就显得无远弗届,政治嗅觉更是比狗还要敏锐。
自打日本投降以后,沉寂数年的政治家心思又活络起来了。这类人名字后缀中总有军事家、律师、企业家、某某会议主席、某某事务特使等等一长串头衔。如果你听过这些无赖们的市长竞选演讲,他们对中国和朝鲜的无知以及装出来的愤世嫉俗的程度将令你大吃一惊。
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选民手里的绿色票票,这张绿色的通行证能让最谦逊的绅士肾上腺飙升,雄心万丈,感受世界尽在掌握的豪情。
可惜的是没人(没有一个候选人)对“一日威廉”感兴趣,就算它距离市政厅仅有一步之遥。这个街区像一块恶心的瘢痕长在市政厅的脸面上,在艾灵顿市市长的眼皮子底下,它曾是这座城市繁荣的象征,在它最辉煌的年代里,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挤破了头想要住进来。
不过如今已经是一片无主之地,只有最外侧的大楼还勉强保持着往日的外观,尽管它的红色砖墙有随时坍塌的危险,到处都是违章搭建,电线和晾衣绳在半空拧成一团,但仍然有不少寄居的租客,毕竟他们支付的租金只有其他地方的五分之一,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座巨大、空旷的废弃大楼还颇受欢迎。
在东边的街道深处,是没有外人敢进入的荒芜废墟,无家可归的妓女、酒鬼、流浪汉在残砖败瓦里游荡,像末日里的食尸鬼。每天这里都有人受伤或失踪,报警电话一晚上多达十几个,犯罪率高居全美前五名。但警官们不为所动,他们总是警笛长鸣、大开车灯地招摇过市,近十年来从未在此处抓到过一个嫌犯。
本·肖根本不在乎这点,他住在这座废楼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其他人叫它“弹坑”,因为它是城市爆发性增长后的遗留地,人们躲在“弹坑”苟延残喘,不知道哪天死亡的阴影会再次降临。
但他看不出来废楼和弹坑的相似之处,每个月本·肖要为废楼向州政府支付十美元的租金,这笔开支他心甘情愿。如果本·肖躺在弹坑里,政府将会向他的继承人(如果他有继承人的话)一次性支付三千美元的抚恤金,但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感谢罗斯福,它们丝毫不像。
今天是报到日,在第一道阳光照射进房间之前,本·肖就睁开了眼睛,床是标准尺寸,长度比他身高短了十几公分,床沿刚好卡住了脚脖子,这让人非常不舒服。但他仍静躺在狭窄的木板上,没有莽撞地翻身而起,毕竟从战壕里伸出头去的冒失鬼最后都吃了枪子儿。
清晨的“一日威廉”与夜晚完全不同,它来得寂寂无声,夜里的幽魂早已回归了墓园。贴在天花板上的1940年民众女神葛丽泰·嘉宝和出演《彗星美人》的玛丽莲·梦露并排向他微笑,床头放着花了他一美元买来的破收音机,摆弄到现在也只能收取两个台,其中一个军事频道相当怀旧,它收录了战争时期的所有演讲反复播放。
这时收音机正努力地滋滋作响,艾森豪威尔将军激动人心的战前动员从里面传了出来,当然还是1944年的那一次:“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潮流已经逆转……向胜利迈进。我对你……充满了信心……迎接……彻底的胜利。”
是的,今天是他去警局的报到日,东林区警局邮寄给他的录取信上戳满了红章。
“向胜利迈进”,本·肖意识到它说得没错,任何人在沮丧、绝望的时候都应当听听这个频道,这是人们为了让另一些人心甘情愿上战场送死而创造的群体智慧结晶,它们能够鼓舞人心,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能使人充满决心地去面对一切法西斯和共产党的炮火洗礼。
“彻底的胜利”,这又是一个过去常常听见的词,在每一场战役开始之前,他们都会这么说。偶尔他们也会打胜仗,但结果总是会死很多人,他面无表情嚼着卡拉威麦片想。卡拉威就是总在纽约时报上打广告的麦片品牌,他们那时候整个营地天天看同一份报纸,每个人都要摸摸这宝贝,广告又比新闻有意思多了。尽管退役回国后他发现这个公司并不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是“赢得了全面胜利”、“攻占超市全部有利地形”、“一盒等于一顿豪华火鸡大餐”的麦片之王。
它只是干瘪的糙麦片,稍微有点尊严的马都不会吃,并且只在廉价超市的角落有售,上面贴着红色大号特价标签:直降80%。但本·肖只买这个,大多数战后互助会的兄弟们都吃这个。詹姆斯大兵说:“我们都吃,这就是它胜利的关键点。”
他停顿一下,猛吼道:“希望它勇往直前,向前冲锋,直到消灭前面的一切敌人。“
他曾在太平洋战场为国杀敌,现在帮助他熟悉的卡拉威麦片、芝宝打火机、亨氏口粮取得辉煌胜利,成为了他神圣职责的一种投影。它们的排名在美国邮报的经济版面节节攀升,“更多的兄弟,更高的名次”,他每天要确认两遍它们在报纸上的排名,期望某一天能问鼎宝座。
他把所有的退伍津贴花个精光,再没有钱买报纸,幸好那时候“大个儿猫”提供十三种不同的报纸,后来逐渐提升到三十多种,他们会把大幅的广告页折在显眼的位置,让大兵们一眼看得到。
“大个儿猫”开在东首街,是唯一一家允许参与者不带拳套的地下拳击场,每日晚间十点开放到次日清晨,“死伤自负,不允许报警”的标语贴在擂台上方。詹姆斯是它的常客,他块头巨大,坐下能占两个卡位,在他身边一米八七的本·肖像个不足月的小鸡仔。“大个儿猫”暂停营业的时候,詹姆斯就以退伍军人战后互助会为家,他无亲无故,没什么可去的地方,对战友总是很亲切,但老虎艾伦除外。詹姆斯独来独往,既不招惹谁,也没有谁愿意招惹他。但艾伦是固守地盘的猛兽。
老虎艾伦在“刀尖”担任酒保,他高瘦,黑色短寸头,眼白多得看不到瞳孔,左额有一块蛛网状赤色瘢痕,颧骨高耸,方下巴。
艾伦的隶属部队没人知道,但这不妨碍他是互助会的一员,他专为不满管理局安置的退伍军人提供临时工作,保证活儿轻松,待遇丰厚,并且能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甚至不用进行岗位培训——考虑到这帮大兵擅长什么,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做到的承诺。
艾伦为本·肖开出了很不错的条件,但詹姆斯说得更得他心:“选警察,兄弟,当然选警察。工资社保,合法持枪,简直和我们过去的日子没什么区别。”
在他辛苦应付了四年鸡毛大学,终于拿到那本社会通行证之后,本·肖暂时不想让自己陷进烂泥地。尽管眼下他住在废楼里,吃两毛五一包的麦片粥,有轻微的应激反应,他不肯承认更多。
因为战争后遗症要么归类于精神疾病,要么被归类于歇斯底里,一旦确诊就很难再融入生活本身。前段时间有个倒霉鬼将民航线飞机的轰鸣声误认为敌军来袭,从十七楼往下跳,然后摔成了一滩肉泥,嵌入了道路缝隙里,清洁工用高压枪洗了六遍都没洗掉那股血腥味儿。管理局被迫在大门贴出告示,要求所有领取补贴的退伍军人应在规定期限内与医疗后勤联系。
没人和钱过不去,意外再没发生过,现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刮出碗里最后一点麦片粥,强忍舔干净碗的冲动,把空碗扔进水池。他打开水龙头,想把碗泡上,顺便沾点水捋捋头发好显得精神点儿,但龙头没有出水。
水管空洞地尖啸,滴不出一丁点水,这徒劳的呜呜声一瞬间让他心跳过速。他这才想起昨天楼下贴着一张通知,也许就是停水通知。如非必要他压根不想看到任何拼字,他一度认为自己可能会因为该死的文化课延毕,或者认真想想——看看他的垃圾成绩单——更大的可能是会被学校开除,这样就更糟糕,他再也没有机会能重来了。
但没关系,潮流已经逆转,他会向胜利迈进,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报到日也是一样,他将勇往直前,永不停止冲锋,直到杀光敌人,占领高地。
本·肖套上旧货店刚淘来的夹克,袖口和衣襟上已经磨出了毛边儿。一切都很好,没问题,他能坚持到下个月的发薪日。
他咔哒一声上了锁,手抄在裤袋里向外走,哼着熟悉的曲调。歌词在他脑子里回响:“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他们永不死。”
“只是归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