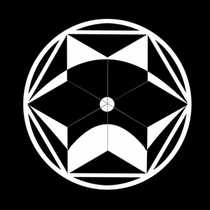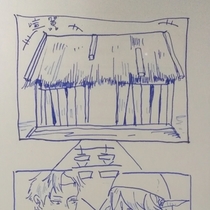子孙们,绝不要回头留恋过去……
——因诅咒而注定短命的一族,谁都无法活过两年。 他们将遗志托付给子孙后代。 纵使这孩子倒下去。 纵使那孩子也死了。 仍要向前迈出步伐。 由子传孙延绵不断的思念。 哪怕只是一小步仍要向前进。 一族的夙愿,不外乎肃清这禁忌宿命的元凶,为子孙夺回未来——
RPG游戏原作《跨过俺的尸体前进吧》的同人企划。接受玩过或没玩过的玩家。恋爱战斗日常探索等元素都可以随便创作的综合企划。主要可以生孩子。
神明人设截止日期:6月15
家族设定截止日期:6月15
人类人设截止日期:无截止日期,永久可投
在被久保怜人抓住手腕之前,不死原完全不觉得自己会被谁注意到。
也许久保怜人知道,他影响情绪的能力对不死原没有多大作用,但他似乎没发现,即使不使用能力,仅仅出现在不死原的身边,就足够影响他的情绪了。
“久保你…烦不烦?!放开我!”
本是神色平静地独自站在酒会角落的不死原,在久保靠近之后立马脸色大变,皱着眉头想要甩开他的手。
令人气结的是,抓着他手的那人完全没有要退缩的意思,只是微微皱起眉头扁着嘴,好像被欺负了似的。
不死原回忆了一下当初与久保初次相会时对方的姿态,想不明白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能把这个高傲又无辜的家伙磨出了没正经的性子。
但是能够确定的是,有久保存在的都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他被有着那样巨大转变的家伙看到过年轻时狼狈而脆弱的一面。
只是想到了这些,不死原就无法摆出什么好脸色。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能地驱使着他想要逃离一切,内心深处小小的不满和报复心却推动着他朝一条更加过激的道路走去。
全然不留情地将凶兆集中在久保掌心,不死原试图以“手掌要被刺穿了”的假信号驱使久保下意识松手,可某人似乎对这种手段产生了抵抗力,并没有当一回事。
一时情急之下,不死原有些恼火地抬起另一只手劈向钳制住他的那只大手,直到久保无可奈何地松手时,不死原才觉得压在心上的某种不妙的东西稍有缓解。
“果然今天就不应该来吗……?”
至少是安全逃脱了。不死原皱眉将还存着余温的手缩进宽大的衣袖,有些复杂的目光轻轻在远处人群中久保的背影上掠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向任何神明。
不知不觉间,酒会的宾客们大多与自己认识的神结成同伴,在席间聚成一个个小群体。不死原沉默地凝视着酒樽,淡色的唇只在酒液表面轻轻触碰过便不再动了,剔透如琥珀的液体倒映着神明重新平静无波的表情,眼中有着对自己所处局面的理所当然。
不死原黑鹤,本来他大可以坐看两派争斗,继续做他闲晃的“湖底神”,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也是相同的态度,可不知为何窜出来的一股恶意将这态度搅了个天翻地覆——在他知道其中有一派帮助的对象是人类之后。
“…。”
如果是做出那样的决定,倒真的是不来这场酒会也罢。
反正结缘这种事……也会不可避免的和人类交往。不死原黑鹤冷下了自己的面色,撑着纤瘦面颊如此想道。
不死原深知,以自己恶劣的待人处事方式不可能会适应人际交往,而且他对于那些从接近他的人或神身上传来的危险预感,早已见怪不怪。
但可笑的是,最令他不安的,却是和久保怜人待在一起时,自己内心产生出的依赖感。
细小的水声在气氛活跃的酒会中显然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白皙手掌五只张开承接着从酒樽中倒出的液体,有不少的酒液从指缝间流泻而出,滴落到地上。
不死原黑鹤面带懊恼地用酒冲洗着方才被久保怜人握过的手,试图用浓郁的香味掩盖那道已所剩无几的气息。黑发湿润的神独自坐着,心中将另一个正笑眯眯抚摸镜子的神骂了千万遍。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到底想到了什么。
“…我才不可能是为了那种家伙……!”
松之丞在自己正对的最后一只怪物身上重重砍下一刀时,刀刃发出了不祥的响声。
被冲力和疼痛向后逼退的小怪物并没有立刻倒下,仿佛垂死挣扎似的顺势抓住了松之丞手中打刀的刀身。
锋利的钩爪用人类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道捏住了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被用钝了不少甚至产生了些许裂缝的的刀刃——毕竟迷宫中的怪物不比寻常人类或是日常练习用的道具,武器的损耗程度自然是较往日要大得多的。
然后,还不等松之丞补上最后一击,半截刀刃就这么随着清脆而可怕的声响被迫从它的主体上分离了出去,映照着火光落入了岩浆中,顷刻间就没了踪影。
怪物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它那难以形容的脸上露出了不知是不是大笑的表情,口中滴着可能是血液的色泽诡异的液体,在捏碎了松之丞手中唯一武器的同时向他挥去了另一只钩爪。
在听到一开始的声响的同时松之丞就已经发觉了大事不妙,因此毫不犹豫地放开了刀柄向后跳去,尽管如此,怪物的钩爪却意外的长,夹杂着火焰和包着同归于尽气势的一击还是够到了松之丞胸前的护甲。
“喂你没事吧?!”
另一边的战场上传来了进之助有些紧张的叫喊。
原本这次作战是由松海和蝶间林两家组成了团队来共同攻略的,只是在陌生的迷宫里面对着源源不断的敌人,能够完整地保持着队形有序地按照计划战斗只有一开始而已。
现在其他人那里是什么情况呢?松之丞并没有进之助那样注意其他地方动向的闲心,因此也没有作出回答。也许像自己一样被冲散得只能独自面对敌人,发绳不知落到了何处,长发狼狈地披散下来被汗水黏在脸上,连武器都被折断逼入绝境;也许还能两三个人抱成团游刃有余地作战。无论如何要去找其他人汇合只有等自己眼前的敌人被打到才能考虑。
幸好退得及时,护甲并没被完全贯穿,然而被撕开了的焦黑的伤痕却极大,如果没穿护甲的话这一击就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致命伤。
以这护甲现在的状态,下一次再被打到就不能保证无伤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将护甲绑在身上的绳索已经伤痕累累,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因此松之丞在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后,果断地扯下了快要成为累赘的护甲,在怪物发出不堪入耳的怪叫声向自己冲来的同时将其扔向了怪物的面门。
投掷的方向非常准确,怪物也没有躲闪的意思,反而迎着这个向自己飞来的武器自信地将其扯成了碎片,没有丝毫停留就继续发起冲锋。
然而它的身体却与其意愿相反地往后倒去——在钩爪挥开的一瞬间,一柄苦无从碎裂的护甲间射向了怪物正大张着的口中,刺穿了它的喉咙并就这么把它钉在了地上。
“——————”
不知是出于震惊还是单纯从生理上无法再发出声音来,怪物的嘴巴就这么张开着无言地动了几下,而随即飞来的几枚苦无让它彻底停止了动作。
松之丞抹了一把脸上已经开始影响视线的汗水,等着这最后一只被打倒的怪物融化消失后才上前回收了还能用的苦无,纳入捆在身上的小型武器带中,顺便从已经彻底报废的护甲上扯下一段绳子来重新束起了那头过长的黑发。
护甲已经没了,因此他干脆脱掉了那身在迷宫中闷热得不行的外套,露出了贴身的里衣、绑腿、以及捆在身上的无数不起眼的小型凶器。
原先厚重的装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履行在团队作战中守护同伴的职责,然而这一切从此刻的松之丞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踪影。尽管团队作战在挑战迷宫时是比较稳妥的做法,自己也是自愿站在了这个挡在前面的位置上,可毫无顾忌不择手段地单打独斗才是他的本性。
捡起断刀插回刀鞘的松之丞回头看了一眼还在作战中的其他战场,转身走向了迷宫深处。
“一真,是不是有人跟着你?”
松海一真闻言转过身去四下张望,花了点时间才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看到有点眼熟的身影。作为一家之主的一真平时少不了和其他家族的人打交道,因此略微想了想才回想起那人是谁。
“内屋先生……?”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躲在石块背后的人影动了一下,然后带着尴尬的笑容走了出来,正如他所猜想的,是在祭典上捡到了扇子,又拉着自己到处打听寻找家人的那个黑肤青年。“我继续往前面走走,你快点跟上来吧。”松之丞见两人似乎认识,略微点点头打个招呼,便转身继续往迷宫深处走去,进之助略带着点好奇地探头张望两人,可惜走出来的并不是可爱的女孩子,因此看了几眼也兴致缺缺地跟着走远了。
“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和舅舅他们走散了,正好看到你想跟你一起走,不过看到你们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怕有什么不妥……那个,我真的没有什么不良企图。”
内屋衣御有点慌张地解释着,没说几句似乎察觉到自己的辩解苍白无力,挠挠头转开了视线,又忽然抬头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无敌意。
作为曾经被人类所“背叛”而灭亡的武家,在复活之后心存怨恨与怀疑再正常不过,尽管从刚刚松海家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对内屋的行为有明显的不满,却也只是表面上看来而已。况且就算是在和平的年代,这样鬼鬼祟祟地跟踪别人也是违法的行为,两个人还远远没有熟识到能够开个玩笑就将这件事翻过去的程度,如果松海一真因此发怒,恐怕……
想到这里,内屋衣御又是垂头丧气又是手足无措,慌张得几乎想转身就逃走,却又深知这时绝不能做的便是逃跑,最后他只能紧紧闭上了眼睛,等待松海一真的反应。
发怒也好,怀疑也好,觉得恶心也是难怪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在迷宫入口看到他时就大大方方地上去打招呼,怎么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内屋衣御的脑海中百转千回,令他瑟瑟的叱骂却始终没有降临,他只听到松海一真轻轻叹了口气,他说话前似乎总是习惯叹一口气,仿佛这短短的一声就能把万语千言都传达出来。
“内屋,你的手臂被烧伤了。”
最后得到的是一句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话。
内屋衣御抬起头,看到松海一真正在随身的小包里翻找什么,片刻之后递过一个碧绿的小盒给他。“……这只是普通的烧伤药,实在是有点寒酸,是我自作主张了……”见他呆愣着并不伸手去接,一真似乎误解了什么,有点窘迫地收回了手想把那盒药膏放回包里,内屋衣御这才恍然大悟,一边慌慌张张地摆手示意自己并不是嫌伤药普通而不收,一边想去拦一真,又觉得自己冒失,急出了满身的汗,最后索性心一横,一把抓住了一真比他细了一圈儿的手腕。
一真倒是不如他想的那样惊讶,只有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仿佛比翻滚的岩浆还要烫上百倍,内屋衣御又像摸了火似的赶忙松手,背着手活像是被父母训斥的孩子,左右思索半天,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对不起。
一真稍微睁大了点眼睛看着他,停顿几秒后还是伸出手,把那个碧绿的小盒塞到内屋衣御手里去,抓着他的手让他攥紧,不至于滑落,然后便微微行了个礼,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雷鸣般的心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