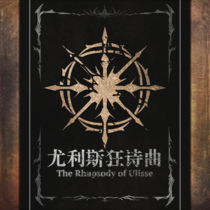
这是一个架空西幻背景的半养老向企划。
文手画手皆可参与,不强制跟随主线,打卡制度宽松,分场内外,最多可以创建两个角色。
请自由地编织您在尤利斯大陆的故事篇章!





哥哥这种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人生中,沃雷德时不时就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要说为什么的话,大概是因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安德斯少爷在私底下场合里,喊了他一句“沃利哥”。
……这应该只是少爷叫顺口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沃雷德却总觉的自己既然被叫做哥,那总该好好负起当哥的责任。
沃雷德作为孤儿,并没有兄弟姐妹存在,在他流浪的时候,他倒是见过一堆流浪的兄弟。那对兄弟在刚来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弟弟的身子并不好。对于流浪儿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一开始,那位哥哥还是非常照顾弟弟的——不准任何人欺负弟弟,还会抢东西给弟弟吃,沃雷德自己也曾经被抢过——只可惜,哥哥打不过他没有成功而已。
可是,不过也就几个月的时光,那位兄长就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辱骂弟弟,甚至开始对弟弟拳打脚踢。不过即便如此,哥哥也并没有丢下过弟弟去别的地方。
再发展到后来,他亲眼看见了所谓的哥哥在巷尾透了一点给老鼠吃的毒药,放进了给已经被病痛折磨弟弟吃的面包里……
沃雷德看的清楚,那位兄长眼里的疼爱、愤怒、哀伤都是真的。
所以说,做哥哥到底要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他思索了很久,总之,先陪弟弟做他想做的事就对了吧?
于是,诺尔练剑,沃雷德练剑。
然后诺尔突然不练了,跑去打铁。
沃雷德感觉那里不对,他突然觉得这不是哥哥,这更像宠物——主人跑哪他跑哪。
在这期间有一件比较庆幸的事情是,诺尔少爷后来有了一个妹妹——格洛丽亚小姐。
看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姐粉嫩的脸庞,沃雷德觉得自己心都要化了。他知道,诺尔少爷这下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长”。或许,他能给自己启发也说不定……
然后他看见诺尔少爷用十分不标准的姿势豪放的抱起小姐,开口就是一句:“不愧是我妹妹,看起来很强的样子一个能打十个的那种!”
沃雷德:???????
好的,不管少爷这个兄长到底合不合格,但是沃雷德这种兄长肯定不是他想成为的!!
女孩子,就应该穿着漂亮的裙子,在充满着蔷薇气息的花园里吃着可爱精美的点心,不是吗!
他看着渐渐长大,穿着漂亮衣服十分可爱的大小姐,内心甚是欣慰。
“哥哥,辛苦了!”他听着大小姐仿佛黄莺一般的声音内心十分感动。
“哦~格洛丽亚,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哦!”这是少爷欢快的声音。
然后沃雷德看见诺尔掏出了两个至少两个10公斤的哑铃放在了还不到10岁的妹妹的面前。
……他真想撬开少爷的脑子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但是不等他脸色发生变化,他就看见格洛丽亚开心的一手一个把哑铃拿起来,还颇有架势比划了几下,笑的仿佛太阳一样:“谢谢哥哥!这个重量太合适了!”
沃雷德·摸不着头脑·三观崩坏·克劳斯,今天也在绝赞石化中。
那之后,开始搭理生意逐渐忙碌,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就逐渐减少了思考。但是果然,兄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沃雷德至今也不清楚。
完成最后的清点库存,确认好今天的账目后,沃雷德打卡怀表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一点半了。
虽然账目上的红色的数字很醒目,但是比起这些,让少爷充分的休息才是最重要的。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安静的走向自己的房间,洗漱一番后也休息了。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在后悔自己为何没有先去少爷的房间巡视一下了。看看,看看这个年轻人的黑眼圈,问都不用问这肯定是通宵了。
沃雷德无语的看着诺尔飘忽的眼神,开始觉得自己身上应该带一面镜子,让他自己看看的话是有多么的不可信。
“少爷,下次说谎之前,记得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黑眼圈……当然,如果你想再被格洛莉娅小姐敲头,当我没说。”
果然一提大小姐,少爷就明显的怂了。有时候沃雷德也不是特别理解——小姐明明这么可爱,少爷到底为什么怕她呢?即使被敲头,考虑到小姐也是为了自己好,应该满心欢喜的接受来自妹妹的好意,不是吗?
果然“兄长”这种生物,真的很难理解啊。
他看着少年成长较迟的脸上露出稍有的凝重表情,诉说着自己的想法,心里不禁有一点点沉重——和少年不一样,他的人生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不管是练剑还是从商,都是他对当初救了自己一命的安德斯家进行的报答。若是少爷现在后悔了的话……沃雷德开始思考少爷重新回去练剑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他真的是想多了,少年其实远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复杂。这很好,他可以正式和他谈谈昨天晚上因为太晚被搁置的预算问题。
上一个月他绝对是鬼迷心窍了才会允许少爷自己出去买材料的!!沃雷德对当初那叠几乎要把自己这个月利润全都抵光的账单的时候,自己出现了意思心慌气短,手脚冰凉等老年人早上起床起猛的症状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仿佛刚发生在昨天。
尤其当他发现那些东西他几乎可以用一半的价格就拿下来的时候,更是坚定了他让少爷远离采购的决心。
控制年轻人不会讨价还价还乱买一气的坏习惯!怎么看也应该是兄长该做的!!
看着重新陷入沉思的少年,他不仅有些好笑。真是的,只是别让他进原料,又不会短了他,沉思啥呢。兄长这种生物,果然太难了吧,又要控制弟弟不乱花钱,又要能给够弟弟想要的。
他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微笑,记事本敲打着手心,安慰对方道:“当然,只要有清单就好,剩下的是我的工作……我可是财务经理,别小看专业人士。”


时间点约在主线一章的半年到一年前。
莫名ooc产物,相关设定请以oc主及企划主为准。
希尔是在那之后捡到那封信的。
“……我妈肯定是因为太忙了,”男人有点絮絮叨叨,希尔好不容易才把他坐起来的上身又推回床上去,病人却像小孩子似的还在嘟囔:“每到这个季节,她都有很多活要做,但要是她回了信,你可要第一时间就拿给我啊,医师小姐……”
最后几个词说得模糊不清,大概是刚刚的镇定剂开始起更深一层的效果,男人很快睡了过去,呼吸也逐渐安然起来。希尔揉了揉眉心,将口述的信折起来,塞进了信封里。某个整夜都在低烧和呕吐中呻吟的夜晚后,对方抓着她的衣摆,说他想给妈妈写信。希尔答应了。自那以来,她就一起做着记录和投递的工作。眼下已经是第三封。
这不是件轻松的工作。虽然要说“写字”和“去邮局”,相较之下她已经比男人轻松太多。她和爷爷的治疗手段都以用药为主,但极少数时候,诊所里也会留下需要住院看护的病人,他们很少会待过两星期。而男人就是后者。
忙昏了头的时候,希尔也有一瞬间希望过这次能快一点。因为她实在没法回应男人的期待。他的手有时还会试图抓住她的衣摆,最终却因为缺乏力气和疼痛,只是从布料上轻轻滑过。
“希尔小姐……有回信吗?”
“抱歉,还没有收到。”希尔也只能这么回答。
然后,当她为了前往邮局而推开门时,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就躺在门口的台阶下。
冷风之谷真正为了寄信的地方并不繁忙,毕竟很少有人会从这里通信。更多时候,工作人员更容易被临时分派去接管货物流通的工作,对这里而言,医药贸易更加不可或缺。
“希尔小姐又来了啊,”认识了她的人向她挥了挥手,希尔假装没让自己注意到他手臂上延伸得更长了的黑色纹路。“还是和上次一样?你还没拒绝吗?”
年轻的医师摇了摇头,第三封来自病人的信贴在她的口袋内侧,像是有温度一样灼得她皮肤发痛。她给对方看了在台阶上捡到的那封信。希尔并不认识会给她写信的对象,并且就她所知,收养她的爷爷更是没有。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字迹潦草,仿佛随便垫在什么地方写出来似的,而且仔细一看,根本就没有包含任何具体地址。
冷风之谷赫斯帕勒斯收。那上面如此写道。要不是确实有着遥远国度的信戳,她都要怀疑是什么蹩脚的恶作剧了。
“这个……是弄错了?”
对方似乎相当了然。“虽然确实是弄错……不过也不算吧。”
“怎么说?”
他说“让你看到实物更好说明”,示意希尔原地等待后,很快地离开拿回了一只纸盒。小箱子里散乱堆积着同样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抛开薄薄的那层灰以外,隐约能看到信封上洋溢着同样潦草的字迹。
“都是一个人,也都是一个样。”他耸着肩说道,“没有办法投递,就只这么放着了。你拿到的那封大概是哪个邮递员经过时不小心落下的……顺便一说,你要是感兴趣,这些都可以送你。”
面对医师“真的可以吗”的疑问,他露出了一个有点微妙的笑容。
“毕竟也没有人要。”他说,“而且,不觉得很像吗?”
希尔就那么收到了更多的信。她将堆满了医书和药瓶的桌子清出一块空位,然后将纸盒放了上去。
这确实很恰好,她心想,抱着说不上是想获得什么答案的疑问拆开了第一封信件。然而说不上是惊奇还是失望,信的内容很普通,或者不如说是随意过头了。既没有题头也没有落款,时而能装满沉甸甸的一信封,时而又短得几乎只有一句话。而内容只不过是每天的流水账,还写得东一头西一头的,不时忽然开始讲起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山野故事,时而又忽然抱怨起丢了重要的东西,拜托看信的人不要生气。希尔翻了几封便要被磨得失去兴致,刚巧,她的工作时间又到了。
于是她将信纸塞回信封,重新走下楼梯,去诊室看了先前的那个男人。一看到她,病人就问她:“希尔小姐,你刚刚去寄信了吗?”她一点头,他眼里就焕发出某种光彩。
“真奇怪……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给妈妈写信,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他轻而又轻地说,“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妈妈……”
那是希尔听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晚些时候,男人的病情恶化了。
某种程度上,希尔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患者的处境。能够逆转感染的治疗手段遥遥无期,一旦超过药物能够控制的范围,身体随时都可能迅速崩盘。因此,她的工作注定以死亡作结。
男人大约继续撑了两到三天,最后一天,他的意识早就模糊不清了,感染带来的剧烈疼痛几乎没有任何药物能压制得住,一整晚,希尔只能听着他的哭叫逐渐衰弱成干哑的呻吟,终于在凌晨的时候,爷爷对她缓慢地摇了摇头,然后将她赶出了看护室。希尔在院子里站了一会,亲手种植的药草上还残留着夜露的微光。她感到一种……寂静。某个呻吟声永远地停下来了,总是穿着黑衣的爷爷从门里走了出来。
“去休息,希尔。”他近乎命令地将她指向楼上的房间。希尔走上楼梯、推开房门,那只装着奇怪邮件的纸箱仍然放在从来没时间收拾的书桌上,那三封贴着衣袋内侧放着的信又令皮肤烧灼起来。
那个病人,那个刚刚死去的人的信,她一封也没能寄出去。对方给的地址是错的,她一开始就知道。确切地说,不是错了,而是……早就毁在魔物手里了。那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家人……“所以我无处可去,才来了冷风之谷”,这还是最初病人亲口告诉希尔的。当听到他要寄信的愿望时,她还以为自己的记忆出了错,但邮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了她,那边早就没人会过去了。
她真的无法面对男人对回信的询问,她甚至想过对方能快点离开就好了,然后又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悔恨。她总是不能忍受死亡的概念。我应该习惯了。她对自己说,可是如果我真的习惯了,那会不会很可怕?但如果有一天爷爷离开了……或者爷爷也将要让她面临这样的选择……她能够吗?
直到最后,她也只是每次都去到邮局,而无法带回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她想。是忘记了吗,还是记忆错乱了呢。她听着口述写下那些信,却深知能收到它的人早已不在。于是最后,这些东西就全都到她这里来了。而这个人……希尔看着书桌上的纸箱,甚至感到了一种茫然。这个神秘信的主人,他又在想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收到,也更没有人回复,可他还是在继续,继续寄给某个没有名字、没有地址、既无法接收,也没法回信的人。这不就、和自己的病人一样了吗。
……我想给他写信。她决定道。
希尔重新看完了箱子里所有的内容。尽管信封上没有寄信者的地址,但有了内容中提到的地名和信戳,很好判断出他就在埃吉狄乌斯王国的某个村落里……只要他从上一次提到地名起还没有搬过家。
她在书桌上铺开白纸。
<不知名的先生抑或女士,非常抱歉擅自打开您的信……>
她是第一次写信,字有点抖得太厉害了。可是她控制不住,但到了第二行,就已经好很多了。希尔问了他很多问题,大部分其实和那些飘飘忽忽的内容有关,于是多少也显得有点不知所云。比如<那个故事有没有结局呢?>,又或者,<最后您找回丢掉的东西了吗?>,当然的当然,还包括<如果还愿意继续和我通信、请告诉我的您的名字>。
最终,犹豫了很久,她在结尾加了一句,下笔前已经在另一张纸上重拟了好几遍措辞:
<您觉得……人为什么会给已经死去的人写信呢?>
<当然是因为想要收到回信。>
一个半月后,奇妙地没有辜负希尔每天的等待,照旧有点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就那么不慌不忙地躺在了门前的台阶下面。
有点草率的字迹、说不上认真还是随口的回答。他似乎根本不在意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却又确实回答了希尔的每个问题。然后、又是一如既往的流水内容。只是临到最后似乎顿了一顿——<你可以叫我索。>。
他如此写道。
最初那把匕首还有漂亮的刀鞘,刀柄的装饰简洁又精致,所以它和锻造师很不相称。后来,托勒自己做了更不起眼的刀鞘,随着使用,刀柄似乎也不再那么闪闪发亮了。于是锻造师就用得更加随意了。说真的,任何一个合格的铁匠,都会为其上乘制作和他使用方式之间的偏差而深深叹息,可他自己就是铁匠,于是管他呢。托勒用它开啤酒,开信封,给邻家闹腾的小孩雕奇怪玩意;然后又拿来拆开包裹,砍砍杂草和灌木;最后甚至拿去剖开鱼肚子,弄得刀刃上全是鱼腥味。也就是那一次,它不小心掉进了河里。锻造师赤着脚在下游的浅滩里找到了半夜,皮里斯在岸上喊他,喊他回去睡觉,他和苏珊娜明天会帮他一下子找到。
“那是什么啊?你一定要今天就找回来?”
“是旧东西——”锻造师拖着声音喊回去,“是我朋友的东西,我要还他。”
嘴上这么说着,托勒却好像已经放弃了似的,在河里哗啦哗啦地趟着水。于是最后,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找回来那把匕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