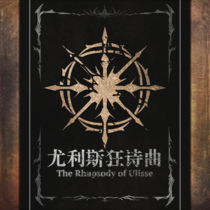
这是一个架空西幻背景的半养老向企划。
文手画手皆可参与,不强制跟随主线,打卡制度宽松,分场内外,最多可以创建两个角色。
请自由地编织您在尤利斯大陆的故事篇章!
萨老师的一些小日常。
柏诗可是萨老师音乐教室的学生,也冷风的一位下位治疗者,因为学的一手中医疗法,和主流的医学不同,所以一直不受其他治疗者待见。
========================================
“师父,我怀疑您缺乏求生欲。”
“有吗?”
“如果您真的想要治病的话,就应该让医生检查您的身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一团棉花。”
“棉花……在你看来我是一团棉花吗?”
“不只是看起来,摸起来也是,软绵绵的一坨,连骨头都摸不到。”
“你只是摸不出来,你的手指在按压我的手腕,这是千真万确的。”
“只有您感觉得到不行啊……”
说罢,柏诗可放下了软绵绵的伊萨卡璐,和之前的医生一样,在病历上写下了“不配合治疗,无法了解病情”。
“师父,我的确学习过一种不需要眼睛看就能检查身体的医术,但是这种医术仍需要触摸您的手腕,确切地说,我要摸到您手腕的血管,感受您血管的跳动,您现在这个棉花状态,就算是我师祖也检查不出任何结果。”
“抱歉,我不是想妨碍你们的工作,吃了那个药以后,我就很害怕光。”
“那个药根本没有那种效果啊……”
柏诗可叹了口气,放下了病历。她看不见伊萨卡璐的表情,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受到了某种未知的药物副作用。
“服药以后会降低魔法的精度,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怕光。”说着柏诗可用夹着木板的病历敲打了棉花的顶部,引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你这只是借口,你只是想妨碍我工作。”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一直很配合治疗,你们让我乖乖吃药,不要滥用魔法,我也照做了。”
“但在我看来,把自己变成棉花就是在滥用魔法。魔法的存在是为了让你们在这个魔物横行的世界里生存,而你却只是用它来烧命。”
“不,我怕光。暴露在光下我会死。”
柏诗可用尽了所有方法向伊萨卡璐解释,从来没有吃了药以后见不得光的先例。但不管怎么解释,伊萨卡璐都听不进去。


冷风之谷入冬后,伊萨卡璐换上了真棉花做的冬装。柔软的棉絮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需要用魔法隐藏的真实面目也只剩下了脸和手的那一小块。
伊萨卡璐喜欢冬天。
因为不怎么需要使用魔法,医生会夸奖他听话,药剂的用量减少之后,他也乐于用闲钱买一些木材和鬃线,以补充店里的乐器存量。
他将剔好的琴弦依次绑在琴架上。旋紧木钉,撩拨了两下。
音色正好。
一拨,又一拨,未上漆的半成品乐器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起初以为只是试音,但细细一听确是一首曲子。
“是上次黑帽子姐姐弹的曲子!”
“是黑猫姐姐弹的曲子!”
几个孩子听到曲声,跑进了乐器店里,围着伊萨卡璐摇头晃脑。
划上最后一个音符,伊萨卡璐才发现身边多了一群小棉花团子,他们在乐器店耳濡目染,也对把自己装扮成一朵棉花充满了热情。
“你这里都快变成棉花店了。”
柏诗可人群中唯一没有变成棉花球的。她护士的围裙里布裙变成了棉衣,但为了方便行动,她的棉衣很修身。
“哦,是柏诗可啊,来了就说一声啊,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你,不要在我这里偷懒啊。”
说着伊萨卡璐把手里的琴放到一边,起身给棉花球们端来了一碗玉米花。
“棉花球吃玉米花……也就你这里可以让人喘口气了……”柏诗可无力地坐下,从包里拿出了一小罐药,“没有其他病人,至少我这里,乖乖吃药的就剩你了。”
“哦……看来现在的时局很糟糕啊……”伊萨卡璐打开药罐嘬了一口,“可惜,我就算上了战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伊萨卡璐顿了顿,“我还给‘敌军’贡献了一把武器。”
“不是武器,是乐器,那时候谁都不知道圣艾尔弗里德会和我们决裂。”
“我觉得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她是宫廷魔法师协会的人,不是吟游诗人也不是巡回音乐家,是为帝国还有女帝效力的人。宫廷魔法师协会是做什么的,大家都知道。”
“但你不是抱着背叛冷风之谷的念头给她乐器的吧。”
“只要是喜欢音乐的人,不管是哪里来的,我都会给她乐器。”
“所以你才没有给敌军贡献武器,也没有叛国,你就是做了一个乐器行该做的事,仅此而已。”
“别安慰我了,我只希望你们别把我卖给她琴的事告诉其他人——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像你们这样原谅我。”
一阵沉默,柏诗可起身倒了两杯茶,拿起其中一杯,一饮而尽。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吃我的药了吗?”
伊萨卡璐没有回答。
“他们都在恢复魔力,想要为冷风之谷拼死一战。”
“因为大家都是从帝国出来的。”伊萨卡璐轻轻一笑,“人生的轨迹已经被破坏了一次,现在又要被赶尽杀绝,是人都不会乐意的吧。”
“他们是在燃烧生命!”柏诗可将另一杯茶也一口闷干,“可恶,本来这话应该是对你说的!怎么现在你才是最乖的那个!”
“因为我本来就很乖,我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什么荣耀,不是军人,也不是宫廷魔法师。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教大家弹琴,仅此而已。”
小棉花团吃完玉米花,乐呵呵地和老师挥手告别。伊萨卡璐收起盘子,也倒了两杯茶。
“伊莉丝,不要有事啊……”
伊萨卡璐小声地祈祷着。



(字数3842,剧情进展大概还是有bug的进展也有些突然,文笔太差,我坐牢了)
埃吉狄乌斯王国正准备着与冷风之谷联盟,一时间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惶惶不安中。有人想趁机大捞一笔,有人想要掺一脚政事,有人在热切地拥护自己的统治者。鱼龙混杂的愿望里,狄尔佩多依旧对这些没有兴趣,纵使有人看上她的能力想要拉拢,得到的都是一阵寒冰一般的眼神。她对这些毫无兴趣,国家之间的战争伤害的永远都是人民。如往常一样巡视了一圈城内,和很多居民闲聊了几句,让他们安心了以后,她开始参与支援冷风之谷的筹备里。
西奥尔多愿意向冷风之谷提供大量物资之后,这里变得更加忙碌了起来。城边的帐篷内一片嘈杂,突然集合起来的人们搬运起来配合的不是很好,摔碎了好几个木箱。狄尔佩多前去帮忙,将地上的东西都捡好重新码进空箱子里,看看木箱里的各种武器,估量着冷风之谷的资源究竟是何等贫乏。她听说过那里,像是一片绝望之地,但又因此谁都能接纳。她猜想,或许自己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将手上的几个箱子咚地一下堆到马车上后,她敲敲木头,示意车夫可以走了。哒哒哒的马蹄声踏得狄尔佩多心中更加纷乱,她其实知道待在这里什么也查不到,要是像以前一样跑遍整个世界,自然能追上那个人。她知道,她却也迈不出步子。
“没什么好说的。”
那是好几十次前狄尔佩多追上那个人后她说的话,直直戳进狄尔佩多心里,那个人说中了,狄尔佩多确实没什么好对她说的话。
因为一切都晚了。
因为一切都毁在自己手里了。
很久很久后的这次,她依旧想不到该说什么,她们既不像从前,是搭档,是朋友。现在?现在或许什么也不算,现在的两个人都怀着一身伤痕,一道道劈深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是我在一厢情愿地弥补吗?”狄尔佩多自言自语着。想着上次见面她的表情,希望找到那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也想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她的声音,她的面庞,她的名字,全都像搅进时间的浆糊里。狄尔佩多尽力地从那一堆糟糕透顶的记忆里握住她的名字。
理德琳。
哦,这个人总是不停的变装,总是在换身份名字,杀人利索的要命,一点感情也没有,从来都没有笑过的女孩子。
她努力不再继续想下去,以免勾出更多不该想起来的事情。既然找回了一点点对方影子,狄尔佩多将自己丢回现实里,跨上一匹马,慢了所有人一百步地挪出城。总之先做好现在的事吧,她想。承诺了的事就要做到,至少西奥尔多现在想做的事,她会尽力帮忙。
埃吉狄乌斯王国的人文还是很好的,狄尔佩多偶尔也会站在城墙上看看这片土地的样子,远处传来锻造叮叮当当的声音,商人们计划着下次的远行。这里犹如自己的故乡,那是被所有人围绕着的日子。她来到这里时就是被埃吉狄乌斯这样的氛围吸引,最近渐渐有些过于留恋了。她叹一口气,抽了马一鞭子拐向了冷风之谷方向的森林,回头又看了看红国还露出的一点点建筑。“再好终究也不是故乡了,我们的故乡只剩两个人了。”她想。扭头将自己没进森林的阴影里,不再看向后面。
据商人传出的情报,通往冷风之谷行商时总会遇见魔物,每次都有些许损伤,让他们很是头大。狄尔佩多很清楚,森林是魔物作为狩猎者最好的隐蔽所。之前有一队已经出发前往了冷风之谷运送物资,因此她独自前来这里想要清理障碍减少伤亡。倒也不是说她过于自大认为自己能单独解决,单单是独行惯了。和别人一起战斗反而会因为自己的狂野剑法妨碍别人施展拳脚。搭档这种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磨合出另一个的。想到这里,她再次确保了一下自己身上是不是带了伤药,万一受伤,能处理的就只有自己了。看到马上挂的满满当当的包,她稍微放心了一点,继续朝着原先确定的方向前去。
放低身体,将手摆出随时抽剑的姿势,慢慢靠近目标,一步,两步,咔嚓。“唉。”,狄尔佩多心中长叹一口气,一边感慨偷袭依旧还是不适合她,一边猛地闪避开魔物的攻击。魔物嘶吼着冲继续向她袭来,狄尔佩多此时还没来得及站稳,条件反射地用手去挡,被它撕开了一块肉。“啧,早知道直接打了,练什么潜行。”她稍微有点后悔,无视魔物的咬合力强行扯出了手,这一下带出了更多的伤口,但她随便看了一眼,便向魔物各处要害刺去,让动脉先破裂,接着让支撑部位失效,最后抬高姿势将全身力量压在剑上刺进心脏。狄尔佩多盯着对方,看着它渐渐不动,直到漫到她跪在地上的膝盖下的血洼也变冷时,松开了手起身对着头部再刺一剑作为保险,才捡起落了一地的东西晃晃悠悠地离开这处战斗地点。
她在森林里待了四天了,起初路程很顺利,还清掉了不少魔物,走了一半的时候马好死不死踩了个陷阱,她给磕晕了,醒来马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带的药等于没带一样,这让狄尔佩多颇为无奈。也多亏自己知道野外求生的知识,约莫再有个一天半也就到冷风之谷了,但架不住越往谷那边走,魔物越多,行走速度越来越慢。狄尔佩多心想自己扛过了这么多事,没想到栽一匹马手里了,真要命。
叹气归叹气,她还是找到了一个水塘清洗了一下血迹,随便撕点布裹了点她能力范围内能辨认出的草药捣碎了一起裹上了。所幸伤的是左手,最近已经不常用它摆弄武器了,痛归痛,也就一般的程度,她是这样认为的。她想起最严重的那次,可能全身就没几块没受伤的地方,躺了她一年半载的,对当时到处找架打的她来说就是慢性谋杀。
狄尔佩多找了一颗树靠着坐下,看着自己粗糙的包扎又是一阵无奈。说真的,她就是学不懂医术,纵使理德琳教过千万遍,她也只记住了理德琳编的顺口溜里的几种。当时她太自信了,认为理德琳会一直跟在她后面,会为她处理一切伤口,而她就站在前面不顾一切地破坏阻挡她的事物。
【医者难自医】狄尔佩多在很久以后才认得理德琳在某次叹气后给她写的这几个字,而她在理德琳写下它的那天,认为理德琳嘲讽她不识字而发了大火。现在她识字了,也不再性情暴躁了,就更想回到过去揍自己一顿,让自己回头看看理德琳的表情,要是自己但凡回过一次头,所有与自己人相关的人都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结局。狄尔佩多回想着这些,头疼的要命,连日的过度消耗让她精神不佳,更容易陷入回忆里。都说人类痛苦时会回想过去以抵御现今的痛苦,而对她来说,最好不要轻易想起过去的任何一件事,神能让她拥有悔过的机会,却不许她拥有忘记的机会。
她又让自己陷入了混乱里,在一片乱线一样的思绪里她睡了过去,但是因为后半段路程伤口治疗太差,全身的疼痛又让她噩梦连连。断断续续的睡眠过后,狄尔佩多猛地惊醒,抓起佩剑便开始防备四周。经验告诉她,是那种被猛兽盯上的危机感。她将后背紧靠在树干上,暗想那只死掉的魔物应该处理一下的。
她低头看了一下左手,布条近乎染红了,血的味道还是没法就被这一点点草药盖住,吸引了周围的魔物。这里离冷风之谷太近了,狄尔佩多盘算着应该会有三四只一上到这边来,自己敌不过这些没理智又不怕痛的魔物。还是赶紧跑吧,她想。做好预备动作,她立马向着谷的方向冲去,身后响起草划动的响声,她想提速,但体力因为四天的消耗有些力不从心,听着声音渐渐靠近,在身后一声嘶吼响起的时候,狄尔佩多同时急刹转身一剑贯穿魔物的身体,剑还没在魔物身体里时,左边又传来危险的气息。
“你们xx这么着急吃人干xx啊,上辈子xx怎么xx的我xxxxxx。”她气到把长久以来积累的素养抛了个干净,抬脚就向左边踹了上去,趁这个空档拔出剑补了前面这魔物一剑,跳开粗略环视了一下,确实有四只魔物,受伤的那只还没死,被踹的刚爬起来,而远方似乎还有一些影子,生生有一种自己要丧命的气氛。狄尔佩多怀念了一下和人打架的时光,人可比怪物好打多了。“xxx,吃不吃的到看你们本事xxxxx的xxxx的东西。”她说道,怒上心头抬手就砍过去,一如从前亡命之徒一样的架势,反正打架这件事,最后还剩一口气就行了,她这样想。
毫无目的地再挥一次剑,狄尔佩多机械性地再往旁边攻击,发现刺中的是空气,她才勉强看清四周,不知道地上倒了多少,现在的场面,浑身都是血的她才更像一个魔物。狄尔佩多不在乎这些,这么骇人的样子早就被人嫌弃惯了。她想再挪动步子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躺下了,森林里的光渐渐变暗,看上去就要进入黑夜。她能听见还是有魔物靠近,但她已经动不了了,狄尔佩多想:算了,这次就算了吧,让我好好睡会吧,咬轻点。
“这么久没见,还是一样能骂能杀啊,佩。”
狄尔佩多像是受了刺激,突然就有了力气向上望去,就看一个人影闪下来,刀刃的白光一晃几下,她便听见了四周一些东西安静地倒下。那人回过头来对她笑道:“看你不熟这些魔物的弱点,怕你先死了,给你解决一下。”狄尔佩多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站在她面前的自然是理德琳,她从没想过对方主动出现的情况,而且,还会笑,狄尔佩多一时间怀疑自己已经死了。
理德琳看她呆的和木头一样,也不惊讶,也只是简单再说了一句“给你处理。”便把人扛到了一处方便治疗的地方。显然对方对自己拥有这么大的能耐很吃惊,但理德琳懒得和她解释,本来这次出手就是计划外的事情。她没想到狄尔佩多还是会露出以前的样子,她以为这么多记忆的消失会让对方变成不同的性格。虽然理德琳这么想,但依旧在心底庆幸,她不希望狄尔佩多连她自己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在给她处理伤口期间,狄尔佩多一直盯着她,理德琳假装看不见。处理完很长很长时间,狄尔佩多依旧一直看着她,理德琳觉得这样太奇怪了,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不爱说话的人,从前完全是狄尔佩多在她耳边不停说话吵到头疼,现在狄尔佩多不说话了,她倒是特别不习惯。因为感觉太奇怪了,理德琳告诉了狄尔佩多安全路线,起身打算走人。而她终于开口了:“你……”
理德琳回头看着她,想知道这次她打算说什么。
“可是,你已经比我更能杀了,那我……?”狄尔佩多将头转向另一边,又道:“谢谢,没事了……下次……再见吧,我会去找你的。”
理德琳没有说话,良久她重新坐下,心想:也很久没见了,再留一会吧。
《关于那些失去的与尚未失去的》
*关于那些我没料到的和理所当然的。
工具人没投人设,反正是工具人,具体设定也没那么重要。
以为自己会画图就一直没发,结果最后也并没有画呢.jpg
***
“……是人为啊。”
“嗯……是人为。”
他这样说了一句,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哥……”格洛莉娅拉着他的衣角,轻轻地叫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眼眶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她曾试图用脂粉掩饰,可惜作为一个习惯了舞刀弄棒的骑士小姐,她根本就不擅长化妆这么精细的工作,反而看上去更加苍白又无助。
“哥。”她又叫了一声。
“……抱歉,格蕾。”诺尔仿佛大梦初醒一般转过头看她,“怎么了?”
她看着她的兄长,看着他眼下青乌的黑眼圈和眼中的红血丝,她犹豫了一下,低下了头。
“不,没什么。”她低声说,左手不着痕迹地在背后捏紧了手中的信纸,“不要太勉强了,我……父亲和母亲那边,我去看看,你不要担心。”
“嗯……我……抱歉,我想再呆一下,就一小会儿。”
她摇了摇头:“不,说抱歉的应该是我……那,回见。”
沃雷德的葬礼是诺尔主持的,按说这本应是他父亲的位置,但让那位几乎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老爷子出席这样的场面,未免也太为难他了。
诺尔很清楚,虽然名义上只是管家,但父亲对沃雷德是寄予厚望的。
嘛……毕竟,诺尔自己是这种散漫的家伙啊,如果没有个能干的助手,的确不太好……不,应该说很糟糕吧。年轻的工房长扯出一抹苦笑,自己都觉得难看,又耷拉下了嘴角。
他在第一时间雇佣了熟识的佣兵去调查了整件事,传回的第一份报告只有两个字:
人为。
轻飘飘字眼让他的五脏六腑绞在一起,直到第二份,第三份报告接连而至,才发现真相可以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
生命轻飘飘的,回忆也轻飘飘的,痛得久了,也就有些麻木了。
明明和魔物的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人类却依然在互相伤害着,低劣又自私的人性令人无言以对。
如今他站在墓碑前,对前来吊唁的人一一致谢,最后一个走到他面前的是个戴着眼罩的青年。
他看上去并不像来吊唁的客人,金色的独目带着几分凉薄。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大少爷?”他双手环抱在胸前,若他语气带上几分不耐烦或许还合适些,可惜这个人连声音也是冷冰冰的,在葬礼这样的场景下,显得格外异常。
诺尔抬起头,用那双浅绿色的眼睛直视着面前的男性:“两倍……不,三倍的金额,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也不要放过。”
“喂喂,我知道你对钱没概念,但这么大方,可太超出我的预期了。”听到他这么说,对方反而有些惊诧了,这让他的脸生动了起来。
“一个也不要放过,能做到吧。”
他无视了对方语言中的揶揄,自顾自地重复了一次。
“……我知道了,那就按你说的吧。”男人抓了抓头发,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家伙今天可不是吃错药了吧。
放在往常的话吗,或许诺尔会反驳两句吧,然而今天的诺尔没那个心情跟他争执,只是不置可否地岔开了话题:“来都来了,你也要祭拜一下吗?”
“……不了,你帮我放一支好了,再说……那个铁公鸡,也会比较想看我赶紧干活吧。”澄摆了摆手,转身离开,“等我消息。”
“嗯。”诺尔也不留他,只是静静地抽了一支花放在了墓碑前。
他并非出手大方,只是,不会再有人追着他问成本控制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任性了。
***
诺尔认识澄已经有十年以上了,他知道很多关于澄的事,譬如澄并不是他的真名,譬如他是圣艾尔弗里德帝国出身,譬如他的眼睛有残疾,只不过与视觉无关。
澄在十多年前来到了王都,瘦瘦小小的少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和一把有些豁了口的长剑,踏入埃吉狄乌斯这座钢铁的要塞,开始了他作为骑士的修行。与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不同,澄并非天生没有魔法才能只好离开故乡讨生活的人,正相反,他过世的母亲曾是一名魔法师,他是拥有魔法天赋的那一类人,只是他的右眼是天生的残次品,这对他的能力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诺尔曾有幸见过一次澄的右眼,那时他还是个见习骑士,在一次对练的时候挑开了澄的眼罩,那只眼睛仿佛最明亮的星辰般熠熠生辉,亮到有些过分。
“曾经有人说我的右眼会发光,但那不过是因为天生的残疾罢了。”澄停下来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他将长剑交到左手,用右手捂住了那只异常的眼睛,“只要接触到一点点光,魔力会逸散,就好像一个正在蒸发还漏水的桶,为了不让水流光,就必须盖上盖子,也因此不能使用魔法……在那边,我就是这样的废物。”
他顿了顿,又说:“还是你们这里好,只要有剑就能活下去了。”
仿佛窥探到了别人的秘密一样,诺尔莫名地觉得有几分愧疚。之后的日子一切如常,澄没再说过家人的事,诺尔也没问过,他隐约猜到那不是什么值得开心或怀念的故事。
再后来,先转行的人是诺尔,这不着调的小少爷几乎是欢天喜地地跑去当了一名铁匠,而澄在做了两年正骑士之后退役做了佣兵。这令人挺意外的,他看上去就是个没什么热情又怕麻烦的人,再加上他那种性格说好听点是心直口快,说直白点就是不读空气又嘴巴坏的KY,好在他做事一向干净利落,就算是铁公鸡如沃雷德也对他赞赏有加。
不过就算澄做事的速度再怎么快,他再回来也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
独眼的佣兵是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来到赫菲斯托斯工房的,他一脸嫌弃地从那些堆在地上的大大小小的箱子中间穿过,偶尔还要小心不要被勾到衣角。清晨的工房里人并不多,前台的店员正忙着和骑士团过来取货的人核对订单,也没工夫接待这个大概是进来挑武器的客人。
诺尔正在矫正熔炉的温度,他戴着护目镜,聚精会神地通过监视口盯着炉心跃动的火焰。熔炉所在的车间蒸腾的热气让刚从外面进来的澄不太舒服地眯了眯眼睛,他绷着脸拍了拍诺尔的肩膀:“你怎么回事,我去你家找你,阿姨说你一周都没回家了?就算工房再忙,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总得在家多陪陪她。”
“……”明明家务事不应该让旁人插手,可诺尔却有点心虚地移开了视线,“我回去也没用吧……格蕾比我会哄她开心。”
“哈?你不知道吗,格洛莉娅跟着骑士团的人去集训了,已经出去四五天……”
“你说什么!?格蕾去哪里了!?”
澄的絮叨被诺尔打断了,对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几乎是对他吼了起来。
“说是骑士团的集训还是什么的……我靠不是吧!?”让他这么一问,澄才意识到哪里不对。
集训,这是见习骑士出任务时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随口扯谎的惯用方式,这种前线吃紧的时候,骑士团哪来的余裕给见习骑士搞什么集训?
“……没想到她也到了会说谎的年纪了啊。”
澄沉默了一会儿,这样说道。
诺尔抬头瞪了他一眼,和某个反应慢半拍的佣兵不同,城里的供应商某种意义上是最清楚前线的情况的人群。
“你,跟我出去一趟,现在。”他扯下头上的护目镜,随手往桌子上一丢,从桌子下面拉出一个超大号的箱子,拉着澄就往外走。
“你干嘛……喂!”澄被他拽着,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被工具箱绊倒,他扶着货架站稳,听到诺尔跟旁边的工匠交代自己要出去几天,直到出了门才意识到这想一出是一出的少爷是在搞什么名堂。
“你,该不会是想去前线吧?”他猛地拽住对方,“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诺尔停下来,他转头看向澄,露出了一贯的理所当然的表情。
“我当然知道啊。”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