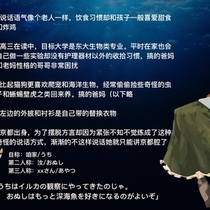十月的白令海峡,冰川之下,不曾为人所知的爱情戏剧拉开帷幕。
为了生命,为了爱情,为了那一位“存在”……
是荒诞的喜剧还是虚伪的悲剧,皆由身为演员的“您”来决定。
随机恋爱带恐怖元素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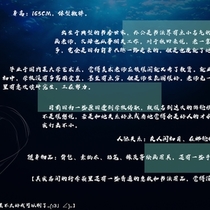
零、第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平平无奇的生活里总有一件普通的事让你意识到不对劲,接着一个又一个荒唐的令人浑身发冷的想法从你脑子里窜出来,你知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于是你从那里逃走了。
只有你活了下来。
……
但它是一只残忍的活猎狗,它会永远追逐跑掉的猎物,从此以后你在洗脸、吃饭、赶路时都能听到它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能闻到它带有腥味的体臭,偶尔还会在寂静的夜里听见响亮的犬吠,让你从睡梦里突然惊起。
尽管传说号上人人都会讲几个拿手的恐怖传闻,但我只从我的养父那里听他说起过一次这种事,当时他喝得烂醉如泥,跟其他水手大肆吹嘘他是如何摆脱那个丑陋怪物的追杀的,甚至还提到了我——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把我从那个苦寒之地带出来是有原因的。
他完全忘记了我也在场。
第二天早晨,当他酒醒了,他就不再说了。到他死之前他再也没喝过酒,我也再没有听他说起过。
我出生在因纽特人的聚集地图克托亚图克,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海港小镇,直到2014年之前甚至没有开通公路。冬天最冷的时候通往内陆的河流会上冻,大家就从冰面上驱车到最近的人类城镇里出售猎物,通常都是海豹制品,驯鹿皮衣、皮帽或皮靴子等等,再购入一些必需品,比如盐、汽油和一些机械零件。但一旦冰河化冻,不在任何航线上的图克小镇就几乎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只能靠直升机才能达到。
倘若有人生病的话,就只能期盼冬季的来临,因为呼叫直升机的费用十分昂贵,而脆弱的婴幼儿的死亡率比大人更高,在这里养大一个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除了有钱以外还得有充足的运气。
从我出生以来几乎就没见过什么生人,整个聚集地大约只有200居民,人和人之间都十分熟悉,聚会时没有一件新鲜事儿可以讲。因此当他突然出现在图克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开心坏了。大人们也全盘接受了这个遭遇海难的外乡人,他们给了他毯子、烈酒和深刻的同情,承诺他,直到他的船修好之前,他都可以住在这里。他的到来使得沉寂的小镇眨眼间变得生机勃勃。
我父亲招待他在我家住了一晚上,按照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说我母亲在晚上去了他的房间。
那天晚上,我和我父亲并排睡在一起,因为我的房间让给了客人。但我一直没有睡着,我听到我父亲发出的鼾声,窗户外刮起惊人的风声,还有永不停息的海浪声,和隔壁的声响。
我躺在我父亲身边想着那个外乡人的来历,要知道对一个12岁的因纽特孩子来说,聚集地就是整个世界。他从白令海来,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说他从月亮上来一样奇妙,我试图想象我根本没有去过和没有见过的地方,这给我带来独特的感受,因为即使我一无所知,但我也可以从一片虚无里体会到激动、快乐,这感官很难描述,不过对一个敏锐的孩子来说是切实的感受。
到了再晚一些,我听到有人从隔壁起身打开门,进入了浴室,水哗啦啦地从管子里流出来,接着是织物的摩挲声,关灯时弹簧板咯噔一声,然后我们这边卧室门开了,一个柔软的身体带着水汽躺到我身边,床垫向侧面陷了下去。我闭眼装睡,有一会儿来人屏住了呼吸,我感到她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她在仔细地观察我是否有睡着,但后来她终于放心地把头落在了枕头上,然后过了没一会儿,她带着香味的均匀呼吸就扑在我耳边。
她睡熟了。
那时——我突然发现,隔壁房间静了下来,静得可怕,我意识到从母亲离开那张床到现在,那个外乡人似乎是死了一样沉寂。我想象他躺在我的床上,但我想象不出来,因为真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没有走动,没有咳嗽,甚至没有呼吸声。我的想象力开始跟我作对,把我熟悉的地方扭曲得陌生又怪异。即使我的父母都在我身边,但——
他还在隔壁吗?他还活着吗?他是什么?
陷入恐慌之中,我甚至想不起来那间房间的样子,我听到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各种吓人的怪异事物在我脑子里盘旋,那时候我的所知还相当贫瘠,最可怕的经历也仅仅是有一次在玩躲藏游戏时我藏进了一条一角鲸尸体的胃里,切割人工作时差点把我一刀捅死。
而在我想象里最可怕的无非就是死亡和尸体,我听闻过莽撞的猎人冻死在1.5公里外的冰湖,每到冬季,他就在那条冰路下四处敲打路面,贴着厚厚的冰层就能看到他冻得青白色的脸,如果你看见他,他会张大嘴向你呼救,但没有活人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也听闻过被扒皮的北极熊活着追杀猎人的故事,它整个躯体都是红色的,冒着热气,它把带着熊皮逃走的猎人吞进肚子里。后来的救援者在那只熊的胃里找到了被融化了皮肤的猎人,他全身也是红彤彤的。我听说过最妖异的就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无法决定出一个我最害怕的景象来说服我自己。
或许比起那些东西我更怕的是那个外乡人本身,我害怕的是我和我的家乡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太过害怕了,我全身僵直,时间过得异常的缓慢,我以为我必须要这样躺到天亮。
但忽然我听到碎玻璃的声响,或许是风卷着什么东西打碎了窗户。于是港口的狗群大声地叫了起来,一声又一声,一家又一家的狗接连叫起来。
犬吠开始的时候,隔壁就传来了一声惊惧的喊叫,那个外乡人像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他从床上弹起来,害怕地呻吟了起来,然后疯了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接着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祈求什么。说来奇怪,当我终于听见他的哭声时,我就松了一口气,起先的那种恐慌无影无踪,我在我父母身边睡着了。
在住宿了小半个街区后,外乡人修好了船终于决定离开,临行时他向我父亲请求带走我,我当然也很想到别处去,这种渴望几乎让我把那天晚上对他的恐怖幻想都忘光了。
我父亲征得我的同意后,按照传统,满足了他的领养请求,并且以生父的名义祝福我,请求海女神席德娜降福于我,保护我和我乘坐的船,请求弓头鲸庇佑我,使我在危难中可以免于受苦和饥饿。
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年轻人决定坐他的船离开去外面看一看,等到冬天再回来。那可是一艘捕蟹的大船,装得下十来个人,更何况对这些早就想外出的年轻人来说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
他教我们如何检查船体、如何开船、如何看各种仪器和地图。可是我在船上越久,学得越多,就越感到蹊跷,在海上远行是一件多么疯狂而又辛苦的事?
在风平浪静的白日里还好,但到了夜里或是有暴风的日子,我们必须轮岗值班,时刻提心吊胆是否会有意外,或是船体的修补部分出现损坏,或是在无意中偏离航线,或是触到了海底暗礁,哪一个差错都会导致我们葬身鱼腹,到了最后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而从那时起,有一个想法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假如我们六个人要竭尽全力才勉强能应付这位钢铁美人,那么当初他一个人是如何做那么多事的呢?
或者,换句话说,他是拿了什么做交换才能一个人把船一直开到图克托亚图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