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ˉ)(《—'
÷+∑>∞√⌒±>∩∴△
△■■▲→▲△△■■■
■\@*@¥#〓←◎§□¤#☆§♂
¤▲▲
¤‰‰●○■■←
数据解析失败。
数据已存储。
本企划为凝津物语系列企划第7期,目前已结束。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关注官博@-凝津物语-,谢谢。


字数:3664
000
天野海斗一直看着天空。
他坐在长椅上,身旁恰到好处地留下了一个人的位置。孩子们在不远处奔跑尖叫,蝉鸣声也很吵。天野海斗什么都听不到,他从早到晚坐在这里,像一尊突兀的雕像。他保持着仰头的姿势,看向蔚蓝天空上的云层,眼神却空荡荡的,像是灵魂并不在此处一样。
天野海斗看起来什么都没在想,但事实上,他的脑海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理性与感性在他的大脑里厮杀,为了争夺他脑内回忆影片播放器的控制权。理性试图将其关掉,让天野海斗从长椅上站起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比如吃个午饭。而感性拒绝理性的提议,并且执意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同一频道的影像,这其中也包括了快速眼动睡眠时期。
这个频道的名字是,早津翔。
天野海斗今年二十二岁,认识早津翔十四年,他一半以上的人生里都能找到早津翔的影像。作为天野海斗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早津翔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时常出现。与早津翔有关的画面通常都是明快的,舒适的,只有一小部分充满痛苦,悲伤和绝望,一般出现在回忆的最末部分。天野海斗每每试图在想到这部分前停下,而理性却开始不依不饶,执意要把整部片子放完。
于是天野海斗又一次回到那个晴朗的下午,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沉闷的房间,早津翔的遗像在房间正中,笑得比阳光更加爽朗。画面在此处定格,从此以后的三个月零十八天都像是被浓雾笼罩般模糊起来。天野海斗开始觉得目眩,他已经感觉不到悲伤,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和空虚。世界变成巨大的雪花屏幕,天野海斗走进其中,他只剩下躯壳,切开皮肤也不会流出血液,取而代之的只有喷涌而出的黑白灰三色噪点。
“你还好吗?”
天野海斗回过神来,他迷茫地抬起头,看到一位高中生模样的女孩站在他面前。她略微俯下身子,露出关切的神情:“我看你在这里很久了,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我还好……”天野海斗开口,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哑得吓人,赶快清了清嗓子,“咳,我没事,我只是在想事情。”
他并不怎么习惯被人搭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肚子却擅自代他做了补充,拉着长音“咕噜”了一声。天野海斗顿时脸红了,他才想起自己根本没有吃午饭。
女孩欢快地笑起来,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个插曲对天野海斗心生厌恶。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补充一点糖分会比较好哦。甜味的东西对心情也有帮助。”
“谢谢……给你添麻烦了。”天野海斗低声道谢。自己的状态已经糟糕到高中生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吗,他苦笑着想。
“没有啦,我很习惯照顾人哦!在这方面我可是一流的!”
他们又讲了几句话,女孩便挥挥手离开了。天野海斗撕开糖果包装,把半透明的糖果放进嘴里。甜味让他感觉好了一点,他的饥饿感像是突然复苏似的,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上热气腾腾的晚饭。他摇摇晃晃从长椅上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慢慢拖着脚步离开了公园。
“你去哪里了?”
“散步。”
天野海斗低着头,把咖喱饭往嘴里送,不去看母亲充满担忧的眼神。她大概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心情,没办法开口说出什么劝慰的话吧。但是,他隐隐觉得,母亲看向他的目光里,总有些责备的意味。
“为什么还没有好起来”,“到底要多久才会好起来”,她大概会这样想吧。
“为什么还没有好起来”,“到底要多久才会好起来”,这也是天野海斗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对了,”母亲状似随意地开口道,“你不是喜欢小动物吗,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他们在招收志愿者。我看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我就帮你报名了。如果被选上的话,刚好可以去散散心。”
她没说下半句,但其中的期望不言而喻。
天野海斗点了点头。他没什么拒绝的理由。他自己也抱着期望,期待着自己能够不再执着于逝去的人,只是这一切会顺利吗?
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001
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时常失眠,做噩梦,半夜醒来动弹不得,有时还幻听。如果幻听的话,我更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但大部分时候我都只能听到尖叫。我有时候会想,说不定你现在就在我身边,在我耳边用我听不到的声音安慰我,鼓励我,可那不过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我试图让自己不去想你的事,但这有点难。如果你看到我这副样子,一定会很担心。我也并不是没有试着做一些改善现状的努力,可惜未见成效,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的魔力。这次来参加志愿活动,虽然并不是我本人主动报名,但我也对此抱有期待,期待与动物们共同度过的时光能让我获得一丝平静,至少能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很喜欢动物,我记得你也一样。
我们十二岁的时候,一起偷偷养过一条小狗。它是被人随便扔在路边的,刚出生没多久,叫声软绵绵的。我们想带它回家,可是家里人都不愿意养狗,只好偷偷地养。我们给它起名叫小吉,把它藏在神社后面,一到放学就去看它。小吉很乖,不乱跑也不乱叫,很喜欢舔我们的手。它好像跟你比较亲,因为这个我还暗地里嫉妒过你。只有一点点。
有天下雨,小吉不见了,我们打着伞到处找它,后来全身都湿透了。我们找了好久好久,才发现它就藏在附近的车子下面躲雨。因为闹出太大动静,我们的父母都知道了我们在偷偷养狗,一起骂了我们一顿。我们两个低着头,跪坐在你家的榻榻米上,趁大人们不注意互相吐舌头,小吉趴在一边的纸箱里,用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们。
后来小吉就是你在养了。你软磨硬泡地说服了家里人,这让我很是佩服,我就拿我的家人没办法。我们都没想到小吉会长得那么大,但我想你也跟我一样高兴。小吉很通人性,它听得懂人话,会握手,打滚,还会装死。有几次我们开玩笑说,有一天它开口讲话也不奇怪。前段时间我看到它,它还记得我,对我很热情,扑上来舔我的脸,但我不敢多看它,我逃跑了。我好害怕它突然开口讲话,问我:“海斗,翔去哪了?”
你去哪里了?我也想知道。我一直觉得你还会回来。
我也没想到,本来只是来散心的旅途,会变得如此诡异。我和其他的同行者一同被关在白色的房间,门外是人的眼球,内脏和碎肉,通风管里有人的尸体,白色的地砖里都是血。听起来挺像是什么电影里的情节,不杀光所有人就无法离开的那种。也许过一会儿会出现什么怪物,狂奔的犀牛或者哥斯拉,随后超人从天而降,把哥斯拉一拳打倒,带走这里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儿,其余的人就被埋在垮塌的建筑物里。我的大脑看似在理性思考,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理性的范畴,往胡思乱想的方向狂奔了。我觉得我在做梦,我还没有醒来,这样超现实的情况不可能是现实,到处都是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但我无法醒过来,门外的血腥气息更加浓了。
我开始呕吐。明明是梦,人却会呕吐。一想到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待在房间里,我没有真的吐出来,害怕我的呕吐物会在这个密室里陪我好几天。我试着思考开门的方法,忍着反胃感思考如何把门外的眼球取进来的时候,跟门口站着的男人对上了视线。
我意识到他意识到我也在想和他一样的事。
“伊藤林叶。”他突然开口跟我说话。
“啊,你好。”我慌乱地应答。
我这阵子都没跟陌生人讲过什么话,社交能力快要完全丧失了,因此就算想多说两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你也在这里,一定能很自然地跟伊藤先生说话吧。事实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伊藤先生有些眼熟,名字也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可是我不想去思考这件事,这意味着我又要想到跟你有关的事。我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暧昧,虽然我很清晰地记得许多事情,但那就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一样,轻飘飘的,没有实感。就好像走在路上的时候,鞋底离地一公分似的。看似踩在地面上,实际上却是行走在空中。你离开之后,我每天都像这样走路。
如果你在就好了,我第一百次这样想。
伊藤先生十分可靠,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并没有丧失理智,还尽可能地照顾其他人。他把拘束带递给我,我试了试,没能碰到眼球。事实上,是因为感到太恶心了,我没有非常努力地伸出手去。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会比我做得好。你会安慰哭泣的孩子,平复他人的恐惧,让身处困境的人团结起来,不像我,我什么都做不到,只会跟在大家后面说一些没用的丧气话。我后知后觉地想起,伊藤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也应该报上自己的名字。
费了些时间,我们还是把门打开了。门外是碎肉遍布的走廊,比从门缝里看到的更加令人作呕。我感到强烈的反胃支配了我,一瞬间我感到天旋地转,只能努力地撑着墙壁不让自己倒下去。我没办法控制自己,把白天吃的便当全都吐了出来。我感到自己就要死了,有怪物袭击了这里,不然无法解释满地的碎肉和那些粗暴的抓痕。我已经知道这不是梦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无比真实,我现在只想喝水,我的嘴里都是恶心的酸味。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如果我在这里死去的话,我就可以见到你了。
我其实想过很多次去死,但都没有真的打算去做。如果我就这么死掉了,又要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你呢。我想过这样的场景,我死掉之后,见到你的鬼魂,你歪着头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海斗,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死去了啊?然后我低下头,老老实实地说,我死于卧轨,跳楼,服毒,溺亡,烧炭,或者别的什么我还没想到的方法。你肯定要皱着眉头,生气地呵斥我:你把你的生命当成什么了啊!明明你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走呢!
在这里死去的话,你就不会责怪我了吧。如果我说,自己是被什么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怪物碾成了泥,就这样凄惨地死掉了,你一定会露出无奈的表情,温柔地说,是吗,那就没办法了,你也辛苦了啊。
所以,老实说,我虽然很害怕,但我的确也是对此抱着一丝期待的。
没有想到,我预想的恐怖电影展开并没有发生,但这整件事的恐怖意味更加浓重了。我觉得你这辈子肯定没见过身上画满了彩色〇〇的裸男,我也一样。这家伙的出现摧垮了我紧绷的神经,我放弃了思考,开始觉得怎样都好,甚至期待立刻出现一个什么金刚异形铁血战士一脚把这里踩成废墟。这样的展开事实上与梦境的构成相差无几,混乱,无序,毫无逻辑,梦中出现的角色也像是毫无理智似的,所有东西都一团乱。带着扫地机器人出现的男人,抱着扫地机器人的少女,面不改色的小姐少爷,仿佛什么诡异的事都没发生似的,在令我足足呕吐了两次的场景里谈笑着。高中生们三三两两谈起了学业,好像这里不是满地血肉的研究机构,而是他们学校的走廊。
我原先觉得这不是梦,却又觉得这就是梦。我恍惚地拿走了一串钥匙,把自己锁进房间,蒙在被子里,想逃避这里发生的一切。
只是,在这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梦境。
如果这是我的梦,怎么可能没有你在呢?
t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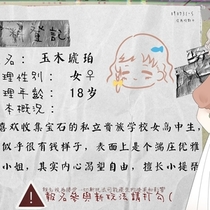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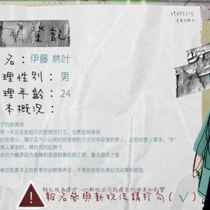

【About ***】
*
*
*
字数:2750
“乔邦尼是……哪个故事里的什么人来着?”
8月1日,晚间9点,伊藤林平躺在单人间里努力思考。
8月1日上午,11时,伊藤还对乔邦尼、康贝瑞拉这两个名字还毫无概念。
当时他满脑都是对于狮堂真莉夜生活环境的困惑:她家里好像没有母亲,父亲作为监护人显然也疏于照顾,以至于她流落这种场合也完全没想起家长。
但,怎么会这样?爱哭的狮堂真莉夜虽然容易慌张,但总体而言分明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再夸张点可谓天才——至少在三维空间想象力和记忆力方面是这样——平时完全没有人监管,却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光靠和同学一起学习也能考到年级第八。作为父母理应以她为傲、多多关心才对。怎么会冷落到让她比起家人更依赖学校里的老师?甚至从体重来看……真莉夜多少有些营养不良,恐怕家长疏忽到连饭食都没有给她好好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真莉夜还能成长为这种不骄不馁好相处的性格,实属不易,不知是受到了什么人的引导。
是那位来栖老师吗?可更早期又是怎么样?
而到了8月1日下午,伊藤林叶有生以来第一次目击了干瘪的人类尸体、而且还是死状可怖的整两具,不再有精力去考虑其他。尸体中的一具是在不知何处被干掉后塞进了采血机、另一具看得出努力躲藏过,但大概遭遇了玩捉迷藏时时间不够的问题,在找到合适的掩体前就被捉住了(要是他能成功去到第一具尸体的藏身处,说不定现在能多一个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的人)。
谋害它们的凶手是一条拥有巨大口器、皮肤比皮革更坚韧、同时还具备强悍攀爬能力的巨虫,但,就像灾难片中常出现的手法一样,它好像只是影片开端的一道前菜,在拥有1~2个机位的镜头后就没了利用价值,成了具侧面衬托真正的怪物有多可怖的尸体。
真莉夜有提到过“这里躲着许多人,要小心他们。”这样想来,虽然巨虫头部的伤痕一点都不像是弹痕,但一定有谁带着极为罕见的热武器躲了起来。
也或许是已经出现的人?那个白发的……叫什么来着。
第二具尸体的口袋被掏空了,不过根据对方蜷成一团的姿势来看,伊藤并不认为那里原来藏着武器……可能是员工身份卡?
【想要得到卡的话,从原主人的身上拿不就可以了吗】
……绫小路良平?
但究竟是他从某个人手里取得的,还是自己去从尸体身上捡的?
伊藤问过绫小路是否有在这里任职的熟人,不过单刀直入的问询并未得到正面回应。想来也是,自己一行人与这里的研究者们可说是天然的敌对关系,要是绫小路真有个交好的就职者,怎么都该为他打掩护,而不可能随意透露。
虽然如此思考,伊藤还是问了许多。
“绫小路君,请问你是不是来过这里?”
“是有在这里任职的熟人吗?”
“你的衣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临近的关押室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
“你是有……穿墙的超能力吗?”
——在伊藤看来,无法证实的猜想是最无意义的东西,绝不要沉溺其中。而与此关联的错信与错枉间,错信远比错枉要好。
可惜,绫小路良平虽然毫无被冒犯的愠怒,却也没给他错信的机会,而是模棱两可地反问了回来。
“伊藤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我很害怕。伊藤坦白道。
绫小路良平是镇定的,几乎没有表现出恐惧或不安。他一个人寻找睡眠场所、一个人穿过迷宫般的地下回廊去到三楼、还去探查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而后,冷静地独自应付抛出一堆问题的伊藤。
可这种违背人类本能的镇定正是伊藤一系列怀疑的根源,同时,他也担忧着绫小路自身是否正面临某种更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分不出半分疑心给恐惧。
……我能做些什么吗?
伊藤想。
“在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表现诚意的方法很少。刚才冒昧说了不少,如果绫小路君有什么疑惑,尽可问回来。”
伊藤说。
电视节目中扮演丑角的人正引导观众哄堂大笑。
绫小路良平的嘴角向面颊两侧绽开:“伊藤先生既然会来单独找我提问题,那想来是发现了许多不合常理,值得怀疑,甚至有些危险的地方。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为什么伊藤先生还会孤身一人,单独来找我呢?”
伊藤注视他的双眼,知晓他对问题的答案有所期待。可这对依循以往习惯就这么做了的伊藤来说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他不想敷衍面前认真提问的高中生,于是不得不在欢声笑语中盯着手指,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词汇。
“你是有过去及现实生活的另一个个体,”他想着绫小路,也想起另一个真实的、生命刚开始绽放的少年人,“不该被迫成为他人,哪怕我自身怀疑与恐惧的载体。如果不经任何交谈,擅自就将你定位为反派角色、幕后黑手之类的……”
他抬起头,“我不认为应当那样,也做不到。”
……或许他不该抬头的。
“伊藤先生有注意过自己的表情吗?这个表情的话……是因为想起了过去认识的什么人吗?”
绫小路扯开了话题,可那并不是因为对伊藤的回答产生了某种感触。
他只是在打量他。
以一种……同希望观众发笑的喜剧演员眼中一样强烈的渴求。不,应当是相反,更像观众在等待黔驴技穷的演员作出最后挣扎。
伊藤没能明白绫小路在那之后的比喻意味着什么,仅仅模糊感知到他的欲望。不过,这也已经足够了。
某一位母亲、某个班的同学、某桩流言的散布者……伊藤见过太多双探究的眼,即使不知比喻的出处也能给出回答:“你们没那么像吧。如果拿故事来说,你会是更亲近的人,比如狮堂同学的康贝瑞拉吧,而不是我的。”
我不是康贝瑞拉,也成为不了康贝瑞拉。绫小路微笑着说。
既然用了故事中的人物做比,你又会是哪个故事中的谁?伊藤问。
恩……秘密,这是不能告诉伊藤先生的事情。绫小路回答。
他们没再深入地交谈这个话题,可准备就寝时,漂浮于伊藤林叶脑中的疑问从尸体的来历、狮堂真莉夜的家庭关系、无法打开的研究所大门、食堂的物资储备等变成了这么件坐在沙发上时随口听来的事儿。
“伊藤先生看起来就像是被留下的乔邦尼一样。被康贝瑞拉舍弃,不得不一个人回到现实,可怜的乔邦尼……你的这份关注,又是想要在我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呢?”
我在从绫小路身上寻找清水寺吗?
伊藤把胳膊枕在脑后,看着空无一物的洁白天花自问。
清水寺和绫小路都是班长,都有着会受女孩子喜欢的端正长相。除此以外,他们的共同点还有什么?受到同学的信赖?遇事时的沉着态度?
可即使姓名相似、即使生活环境别无二致甚至一模一样,清水寺还是清水寺,绫小路良平还是绫小路良平,伊藤所想起的“清水寺”只会有那一个。
如果把清水寺的事情写成文章的话,按伊藤知道的量大概能写八页B5,绫小路良平的则只能写一页,其中还有一半要画问号。但再怎么说,把关于清水寺的书页插入到绫小路良平的书里去是不行的。
所谓相似性……只是两条直线的“交汇点”。伊藤伸出手,望着白纸般的天花比出一个十字,随后是一个空心圆圈。
——如果是两条很短的线,“点”看上去会额外巨大吧?但那是在两线长度相当的情况下。清水寺的生命线已经两端固定,而代表绫小路的直线还会继续延长……光是这一点,他就已经和清水寺完全不同了。
说来绫小路比17岁的自己要矮一点,不知道会不会也在尝试各种口味的牛奶。
“像吗?不像啊……”伊藤得出结论,手掌拍回不算柔软的白床单上。
……
今晚能睡个好觉吧。
晚安。
*
*
*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