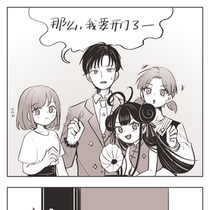阳光正好,从白色矮架中投射,穿过开得正好的粉色爬藤月季,终于柔和地罩在正在说笑的二人周围。两人长相一样秀丽,留着差不多的短发,衣着都偏向中性,一同坐下时默契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有心人却能看出,一人无忧无虑更加开朗,一人老成持重更加坚毅。
一人手舞足蹈讲述什么,另一个只是温和地听着,丝毫没有察觉到更远处有人无聊到和猫聊天。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耽美?”马何戎上半身都靠在栏杆上,看着眼前两个俊美的人举止亲密。
被大家称为管家的黑猫甩着尾巴喵喵叫了两声。
“说实话,长得好看的人站在一起确实赏心悦目……”但是其中一个人是和他同屋而眠的学弟,再想到昨天晚上奇怪的氛围,以及还余留在眼角下棉麻衣服的质感,“学弟的取向果然是那边?”
黑猫努力地想要给他翻一个白眼,奈何面前的人根本注意力完全在别人身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极力否认的喵喵声。
“你说得对,我昨天晚上的反应太大了。”马何戎有些懊恼地甩了甩头发,“我不讨厌,甚至……”
感觉非常温暖。
你是害羞了吧,管家的表情似乎在说。
马何戎伸手,按在了猫咪毛绒绒的黑色脑袋上揉了几下,把它的表情揉得远远的。想一想啊马何戎,以你引以为傲的逻辑思考能力。
喵喵。
“男人和男人也可以恋爱但是。”
喵喵。
“我知道男人和男人也可以结婚但是。”
喵喵!
“好,好,男人和男人还可以领养孩子。”
“噗,啊,对不起非常抱歉。”还没有回应,旁边突然出现的男人就自主完成了道歉。
“不,没事,是在公用通道里大声和猫聊天的人有问题。”马何戎泄气地把手从黑猫头上移开。
“我叫钟意。”
“马何戎,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那么我就先……”钟意正准备离开,旁边的黑猫纵身一跃就挂在了他的肩膀上,他也不生气只是问,“你也要跟我走吗?”
黑猫顺着钟意的手臂又跳了下来,重新坐回到栏杆上。黑色的尾巴轻轻地拍了两下地面,然后转向不远处的二人组。
拜托了,帮我好好解释一下。猫咪似乎这么传达着。
钟也随意地靠坐下来,看了看那边:“白儿茶和安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安好住在一间房。”
不远处的安好打了个喷嚏,白儿茶关切地递上纸巾。
“是,我和安好是校友,我大一届,所以一起住了。”马点了点头,“安好是个很好的室友,爱干净晚上还不打呼噜,和我以前大学那群衰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有人不知道猫咪着急时候的叫声,那么现在管家的声音就是。钟意连忙给管家顺毛,就像拉住侏罗纪公园里逃出栅栏的迅猛龙,又道:“冒昧地问,你觉得安好出现了性取向的问题?”
“我……并不想评判同性恋,但是什么男人恋爱结婚,还是很艰难吧。”马何戎径直走回了直男逻辑怪圈之中。
“那可不是‘什么男人’。”钟斩钉截铁地说,猫咪闻言舒心地叫了一声,开心地蹦蹦跳跳。
“你的意思是……”
“你要想那是安好。”猫咪已经蹭起了钟意的手背,完全把他当做了伙伴看待,“比起‘男人’做什么,‘安好’做什么更让你在意吧。”
“……是这样。”马何戎非常认真地想象了一下,“‘安好’和男人谈恋爱让我烦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钟意试探。
看着白儿茶和安好挽着手,完全没有男性间的社交礼仪。他与那两人物理上的距离是三十步,心灵上的距离却是三十光年。他怀疑起昨晚电影幕布下的拉近,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还是他半梦半醒间的杜撰。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是我。”马何戎从心底吐露出一个答案。
点头,鼓掌。钟意和猫咪像是好不容易送了一个问题学生毕业,心中是骄傲和感动。
“谢谢你,钟意先生。”马何戎留下一句话,就往他的学弟那边走去。
“加油小马。”钟意挥着手目送他越走越远,转头和管家说,“会馆是支持每一种性取向的,对吧。”
的确如此,猫咪舔毛认同,又觉得哪里不对,狐疑地抬头看看钟意。
“祝福小马和他学弟两情相悦。”
不对啊!黑色猫咪仰天长啸一声,人类的眼睛就这么不好用吗?心灵受伤的黑猫,三下两下蹦下栏杆,懊恼地钻进了矮灌木中不见了踪影。
钟意看了一会儿远处的三人,确认有在好好地聊天,便也匆匆离开了。
斯万觉得那诡谲的厄运又悄悄缠上了自己。
那天他正下班回家,被一只猫吸引住了目光。那猫长得颇为有意思,浑身漆黑,脖子上却有一块状似领结的白色斑纹,他跟着走了两步,却看见了一间婚礼会所的橱窗,模特们身上穿着礼服靠在一起,红红白白的气球和丝带装点在四周。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快步离开这个地方,脑子里却挥之不去。
婚礼,鲜血,纱裙,尸体,枪声。
更糟的不在这里。
没过几天却又收到了某间会所寄来的信笺,拆开时他的手都在抖。半饷,才猛地把邀请函扔进垃圾桶。
是谁在恶作剧?这个城市有人知道我的事了吗?人们一旦知道就会开始谴责,哪怕逃的这样远,也无法逃离那里是吗?
……又或者,是凶手的戏谑?
如果他冷静下来,肯定能判断这一切不过是巧合,但这个男人此刻已经在恐慌的边缘,他猛地拉开衣柜,把寥寥无几的几件衣服往床上扔,又拿出皮箱和各类证件,准备连夜去往下一个地方,哪怕他都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就这么收拾了大半夜,外面不知何时开始大雨倾盆,雨点与阁楼窗框的激烈碰撞声让他清醒不少,斯万突然安静下来,抱着头坐在床沿,像一尊被抽去了灵魂的雕塑,雨声愈发响亮,没有人会听到屋内传出的呜咽声。
……
雨依旧下着,几公里外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正站在路边,似乎毫不介意,把玩着手上的一张纸。
很有意思,自己在此地落脚还未超过一天,只四处逛了逛,却于今晚收到了一份措辞诡异的婚礼会馆邀请函。
来到一个新地方,勒查查第一件做的事,便是了解当地婚丧习俗。出生、结婚与死亡,是人类总绕不开的生命纪念碑。对于他来说,没有比看到人类露出喜悦或悲伤更让他有活着的感觉了。
勒查查回味着上一次的婚礼,那是个郊外的小教堂,阳光很好,透过彩窗打在新人的脸上,在新郎的眼睛里闪烁,在新娘的脸蛋上流连。
然后他掏出了枪。
等十分钟后逃窜的人群散去,教堂大门敞开,只剩下他和尸体。彩窗的玻璃也被打碎了,白色纱裙被染的一块斑斓一块黑红,他才发现新娘也在死亡之列,旁边却没有看见新郎。
“太可惜了。”他轻巧地蹲在女孩的头边温柔细语。“新郎丢下你跑了吗?”子弹射中新娘胸口,她还保持着一脸惊恐。
尸体不会回答,勒查查最后吻了吻新娘没有沾染血污的额头,向她告别似的轻声祝福:“新婚快乐。”
婚礼是个美妙的词语,每次听到都会让他不由得从灵魂深处开始震颤,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爱情总是短暂又经不起考验,这就是勒查查不太满意的地方。
勒查查手一松,卡片顺着水流落进了下水道,变得肮脏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