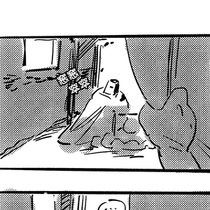如果让阿诺德·施特拉德形容自己的人生,想来他只会用一句简单的短语:
“向来如此。”
老阿诺德实在是太老了,连森林里的狼都换了几茬,他却依然是那个严肃又沉默的猎户。能记得年轻时的老阿诺德的人可不多了,能记得他已故的妻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甚至于老阿诺德偶尔会在擦拭墓碑时恍然意识到,他已经不记得她的脸了。
他们年轻时并没有太多的故事,猎户与农妇,也算是门当户对的爱情,好像他们生下来人生就已经定格了一般。爱丽,对,他妻子的名字,是一名像她的名字一样普通的女人,每天只知道围着田垄转。但他们的孩子却自命不凡,或许从他向老阿诺德央求一本书时,他们之间注定无法相互理解。
神啊、教义啊、经文啊,在老阿诺德看来都是教会拿来骗人的玩意儿,但爱丽执意要让孩子去读书。好吧,好吧,看看他读了些什么东西回来?满腹经纶,却连锄头都挥不动。自从识了字,那孩子的心思就不在田里啦,每天就知道对着路过的马车发呆,好像这样就能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一样。
最终,他走了,和他所谓的真爱一起。他们跟着贵族鞍前马后,只留下还在襁褓中的帕梅拉在这里。大约也是从这时起,老阿诺德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爱丽,他终于意识到爱丽已经不在了——哪怕那已经是数十年前的事了。
照顾孩子对老阿诺德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就像他把儿子拉扯大一样,不过是再重复一遍原先的过程罢了。他对帕梅拉也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期待,反正她在不会成为累赘时就会离开,去过那所谓的好日子去。
他不曾幻想,也想不通除此以外的人生有什么不得了。人都是会死的,像所有生命的必然。一把匕首、一瓶毒药甚至是一场流感,都会让人死去。他也曾远远地看过那座城堡,高大,宽敞,可是这究竟和他的农舍有什么不同?
离巢是动物成年的标志,生命就是不断迁移的过程。像他离开老家在这里定居,像他的儿子去给贵族做骡马来换取一枚又一枚的金币。他本以为生命如此,他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如此。
但当帕梅拉用无邪的眼神看着他将一头小鹿拆解时,当她说出她想成为爷爷这样的人时,老阿诺德意识到,有什么不一样了。他开始无法忽视这个孩子的存在,他开始不时感觉焦躁。他的脾气一天坏过一天,就像他那已然不再年轻的身体。
而后,这场长达三年,或许还会更久的闹剧开始了。这里的人都疯了,或许他也是其中的一员。每一天都是过去的一天,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一切都在变化,一切也没什么不同。
“爷爷!你看!这里有牛犊!”帕梅拉一天天地长大,和三年前相比,却只是个子高了一些。她善于躲藏,会用陷阱,但她最喜欢的却依旧是这群沉默的畜牲。老阿诺德总是跟在她身后,不知不觉已经变成这样了,明明她笨拙地追上他脚步的日子好像还在昨日。
帕梅拉依旧把这里发生的事当做游戏,她透过门板缝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对上一双又一双的眼。所有人都把她当孩子看,因为她还没学会欺骗和隐瞒。她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单纯,好像这里的一切就该如此。
“要不要去那边玩?”老阿诺德记得,说话的人叫维尔利多,是那个铁匠铺的小铁匠。他和那个叫丁香的医生明明先前还在讨论杀人的话题,却在发现帕梅拉之后立刻换了表情。他们变得柔和,变得亲切,变得像帕梅拉一样清澈。
维尔利多帮帕梅拉打开了门,里面是抱成一团的孩子们——像冬天里相互取暖的雏鸟,这样并不能让他们度过严寒,却可以让他们多撑一天。
他们排斥帕梅拉,在三年之前就是如此。母鸭会把一起孵化的鸡仔当做自己的孩子,但当那只小鸡不能下水时,它的谎言无法再维持时,它就会被它的“兄弟”们疏远。即便如此,帕梅拉依旧和他们挤在一起,说着故事,说着教会,说着这一个月发生的事,好像一切如常。
是的,向来如此,这座城镇向来如此,这里的人向来如此。
没人会苛责一个孩子。
人们用此来掩盖自己的虚伪,好像这样便能抵消自己全部的罪孽。
也许这也是他不信神明、不敬神明的报应,老阿诺德心想。他只是想让帕梅拉快乐地长大,即使终究他或她有一人要先一步离开,她会出落成大姑娘,用她的精明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那么聪明,她那么欢快,她会有自己的新家,她会成为幸福的新娘而后有自己的子嗣,就像生命的必然。
即使她离开他也无所谓,即使她迟早会忘记他也无所谓。他已经很老了,他在这里呆了一辈子,他还能去哪呢?
可她不一样。
“帕梅拉,你不能永远这样。”他用布满粗茧的手拍着她的肩膀,最终抚上她的脸颊。他的语气如此虔诚,或许这是他此生唯一一次祈祷:
“神啊,我祈求你。”
他折断了她的脖子,很快,甚至不需要耗费什么力气。帕梅拉走得很快,没什么痛苦。她靠在他的怀里就像睡着了一样,甚至来不及听清爷爷最后念叨的究竟是“原谅(Forgive)”还是“遗忘(Forget)”。
钟声敲响了,这一轮游戏终于结束了。老阿诺德抱着帕梅拉向家的方向走去,他想,希望太阳再度升起时,一切不再如常。

自从死人会复活,我认为总的来说世上发生的怪事并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得更少。有人反对我,他们说人死了之后还会喘气这还不奇怪吗,想想这样的情形吧:一个人指着因为犯下谋杀罪而被公开行刑的人说,看啊,这人杀了我,他马上就要被处死了!但被这凶手杀死的可怜人不但在人群里围观,还能和其他人议论纷纷呢!而到了第二天,哎呀那个身首异处的死刑犯居然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仿佛他是个崭新的人似的!世上平白无故多了两起凶杀,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死掉,这还不是怪事吗?
而且假如再也没有人死掉,那灵魂——我们的灵魂又怎么办呢?那些在荒原上、在古堡里游荡的呜呜咽咽的游魂,和我们死掉的祖先们,他们又去往何处了呢?我们不再害怕走夜路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绝无可能死得掉的,再也没有什么可敬畏之事!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安眠!就连教会收税都不再会提起给你留一块墓地这种话了!
啊,对了,我们也不再有什么审判了!多怀念从前,万事万物的对错是多么笃定?假如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用火来烧!倘若有人被大火烧死,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倘若他没死,那他一准儿是恶魔!可现在人人都会死,然后人人都会活过来!我们再也不能证明这个人是好是坏!也没法知道哪些事儿是魔鬼干的了!
现在!死亡、幽灵、魔鬼都统统消失了!反对的人言之凿凿道,依我看世上的怪事哪一件不是因这三件事而起的?既然它们都消失了!那么怪事的总量一定是变多了,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变多了,他非常有把握地说,那就一定是变得更少了!总之一定有所改变!
但我要说的是,世上发生的怪事总量并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少,我将为我说的话负责,你们总能在我这里听到形形色色的怪事,从前我每天讲三个,现在我也每天讲三个,因为世上发生的怪事总是不多也不少。
【可爱的小径】
死亡——
当然,大家都晓得现在人们已经不会死了,虽然杀人这个古老的可恶的罪行仍然时有发生,毕竟不管是为钱财还是为享乐,人们都是乐于自相残杀的。毋庸置疑,绝大部分的死亡总是人类所造成的,但你需得知道这世上有极少极少的例外,即:有些土地是会吃人的。
你随我来看,在达拉尔镇的陋巷,让我来给你布置一个这样的处所。我一边动手干活儿,一边告诉你这个故事。
我,玛丽·莫里森,喜欢郁郁葱葱的植物,因此我到了此地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迷宫花园。顺便一提,我在那里遇到了可怜的埃米尔。不过比起达拉尔镇中埋藏尸体的迷宫花园,我还见过一个更可怕更恐怖但又更加美丽的地方。
一个春日,我正要去一个陌生的村庄,走着走着,我发现路边有一条细小的分岔路,那是一条可爱的小径,铺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圆润鹅卵石,两边长着郁郁葱葱的矮树,树上爬着翠绿的藤蔓,藤上长满了野花。
当时日当正午,时间还早,而且距离我的目的地也不远了,我左右看看,四下无人,周围没有什么路标指出这条小径去往何处,那尽头又是什么。我心想,玛丽啊玛丽,你既没什么要事,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为什么不顺从心意,沿着这条可爱的小径走走呢。或许在那里面会有小妖精做馅饼呢。
于是好奇心驱使之下,我心情愉悦地踏上了这条岔路,两边的花儿簇拥着,争先恐后地散发出悠悠香气,绿色的植物生机勃勃旺盛地生长,既没有人工修剪照看的痕迹,但也不会显得杂乱,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呀!只有铺得整整齐齐的鹅卵石让人知道这是有主人的了。
走了一会儿,我远离了大路,越往前走,树丛就更加茂密起来,我注意到在树丛里还有些长得大大的莓果,一串串儿,有的黑黝黝、有的红艳艳,沉甸甸地点缀在绿意之中,时不时从树影中传来或清脆或嘹亮的鸟鸣,我甚至能想象那副小鸟取食的可爱景象。
我不断地走,但我总也没有见到一只鸟儿,这实在太奇怪了,我只听见它们起劲儿地在周围叫嚷,但我什么活物也没瞧见。更为奇怪的是,我已经走了好一阵了,原先日头还在正中,这会儿已偏出一个角度了。我和普通的姑娘可不一样,我长得高大,脚程也快,这样一段时间,我应当已经走出好几里地了。照理说,若是有什么村庄、庄园之类的早该到了,可只有树呀花呀莓果呀,和我脚下的鹅卵石!除了这些之外我什么都没瞧见!
我认真打量四周,这些景象!这些景象!几乎和我走入小径之中时一模一样,只是树更高!花儿更大!莓果更繁密!
我向前看,在我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仍是那样,无数的树、花和莓果,它们静静地立在鹅卵石的两旁,向远处不断伸展,伸展——
我又回头去看身后,我已经走得太远,远到那条原先看来可爱至极的小径在我身后仿佛被猛地拉长了,无限地、无限地向我身后延伸出去,在那两旁也长着那么多的树、花和莓果!
要不是我能碰到那些植物和石块,我甚至都以为我是一副画里的人,被框在画框里,钉在墙上,而画的内容就是一条无边无际、无头无尾的小径,而我则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小径中央,回头去看身后——
一种异样的寒气从我背脊直窜到脑门顶,但我安慰自己,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不过是走了很长一段的路罢了,只是这条路没有拐弯,没有分岔,又长又直——是啊,它真的太长了,太直了,到底是谁?有什么必要修这样一条路?有个声音在我心底小声嘀咕——你只要掉转头往回走,就最多再走和刚才那么一会儿的时间,你就能回到大路上,到那时你就知道,这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小径罢了,和其他普通的小径一样,没什么不同。
于是我转身往回走,但来时悦耳的鸟叫现在让我心烦意乱,起先我还压抑着心底怪异的感觉,逐渐地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像是有人追在我身后似的,最后我终于跑起来!
我慌张地跑,跑啊跑,跑啊跑,一直跑到跑不动为止。我已经失去了距离感,但幸好我还能看到太阳,比起我往回走的那时,日头又落下去了一点儿。按这时间算,虽然小径仍然没有变化,但我应当距离路口很近了,我实在跑不动了,但又不想停下,就还是往前慢慢走。
假如我就这么一直走,走出了这条路,这个故事也没什么好讲的了。何况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些该死的好奇心,要不是这样的好奇心我也不会偏离原本的大道拐到这条小径上来了。
于是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但脑子却出神地想着一些事,一些古怪的事,比方说——
我想到,比方说,我怎么竟然连一只鸟儿也没看见呢。明明它们就在周围!明明它们叫得那么欢快!而且鸟的叫声此起彼伏,倒像是相互之间在传递信息一样。我越想越奇怪,越奇怪越想,最后竟停了下来,我看着道路两旁的矮树,树非常密,层层叠叠,但如果非要往外走的话,如果我一定想要去看看那些鸟儿的话——
也不是不行。我只要掰断一些树枝,就可以从这小径之中脱身而出,进入矮树林,甚至更远的地方,或许那些鸟儿隐藏在那里面。
我一想到我马上就要回到既定的大道上去了,那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又变得悦耳极了,于是我开始掰那些树枝,我想,玛丽啊玛丽,你不看个仔细怎么能安心呢。
我力气很大,很快就在矮树丛上弄出一个能容人通过的洞口,我想我只要进去看一下,就看一下,然后我就回到小径上来,再也不回头,一直走到大道上去,然后在夜晚来临前,我就能在我的目的地美滋滋的睡上一觉。
我打定主意就只是去看一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觉得那是个好主意,总之我往那个缺口踏出了一步,又一步——
又一步——
矮树丛之后连着更高大的树木,树木挨着树木,进入森林之后光线骤然暗下来,而我好像是撕碎画布的老鼠,从画的破洞又钻到了深处——
更深的地方——
我快走几步,抬头四处张望,树木的高枝儿上什么也没有,没有鸟儿,没有其他任何的生物,这里安静极了。
那豁开的洞口是一个联通外界的通道,光从洞口透进来,在幽暗森林里十分耀眼。而我正借着光四下里走着,找那些该死的鸟儿们,我只需要看一看,只需要看一看,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它们全躲起来了,就好像刚刚叫个不停的鸟儿突然之间全死光了。
我自顾自找着,那光却逐渐暗了下去,我回头一看!这才发现那个洞口——那个洞!它正在变小!
我不太确定,但——
更多的树叶正从它边缘闭合,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有什么生物正在蚕食那光团,周围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我来不及细想就往洞口冲去!但那两三步的距离却随着光的消失,越变越长了!我拼了命地跑!我从没跑得那么快过!但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每过一刻就变得更小一些!很快就从一人高的洞口,缩得只有一个木盆那么大,接着缩成一个拳头大小——
眼看就要消失在我面前了!
越急越乱,陡然间我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猛地绊倒!狠狠跌在地上!
当那团光消失的最后一刻,趴在地上的我终于看清楚——
在那洞口周围,在我踩着的泥土两边,在树叶下,全是牙齿!全是牙齿!全是牙齿!全是牙齿!
牙齿!牙齿!牙齿!牙齿!牙齿!
我的天啊!巨大的牙齿!密密麻麻的牙齿!
一些埋在泥里!一些露在外面!露在外面的部分圆圆的,白白的,洞外透过来的光照在上面,闪闪发亮,就像沾了水的鹅卵石一样!
在我失去意识之前,我身下坚硬的泥土和头顶的树叶都翻腾起来!阴影交错!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嘴正要咀嚼!吞咽!它的食物!
故事结束了吗?没有!因为——
你还记得吗,如今死人会复活。
要是三年前,恐怕我和我的故事都要血腥地结束在这里了,不过当日头又升起,我从最近的教堂睁开眼,坐起来,发现我只是回到了上一个镇子,距离我的目的地仍然是只差一天的路途。
当我向人们谈起此事,我发现当地的失踪案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赢得英格兰那会儿,甚至——
或许——
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第一位国王,第一位骑士之时,就发生过无数次了。我想,可能一开始它只有短短的几步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失踪人数的增加,那小径越来越长,鹅卵石越来越多。
可是随着神的旨意降临,死亡不再是终点,随着死人从这片饥肠辘辘的土地上逃走,传闻也越来越可怕,逐渐不再有人踏足此地。
而我呢,我,玛丽·莫里森向来是一个固执的女人,即使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但我还是要去我的目的地,我甚至在半路上又撞见了这热情好客的老伙计,还带走了一大把鹅卵石呢!
现在,我的朋友,我可给它找到用武之地了,假如你想杀掉我,你就尽情来追猎我吧,而我要布置一个致命的陷阱:我要把这只怪兽带到你面前来。
为什么要来学校呢,可能自己也有一颗追逐知识的心吧,逛过了城堡,再逛逛学校,一切之前独属于上层人的区域现在毫无保留地向所有人敞开,这怎么能说不是神的馈赠呢。
学校的氛围和城堡截然不同,这里充斥着年轻的干燥的气息,或许还有若有若的血腥味,当然,在现在这世道,这是非常正常的。
莱昂没有带兜帽,反正他足够年轻,就算混进这里也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异常。要是幸运地碰到识字的人,还能问问他昨天拿到的药剂瓶上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整个一层居然连个鬼影都没有。
在城堡中尝到甜头的莱昂,看着空无一人的教室中的柜子,兴奋地搓了搓手。他舔舔干燥的嘴唇,挨个搜寻了过去,只不过没有什么收获,都是些不值钱的边角料,甚至连书籍都没有。
而下一刻,他的视线就被一大片红色占据,那是一大把红色的长发,它细腻又艳丽,如果长在哪位美丽的女士的头上,一定如同绸缎般炫目。
可是现在它出现在这,是被谁割下来了?
莱昂自己就有一头耀眼的金发,所以对类似的东西都格外感兴趣,他轻轻用刀尖拨弄着这些散落的头发,虽说这种质量的头发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但是莱昂并不打算这么做,要说为什么的话,大概是自己也有类似的东西吧,不想把自己切割成块,打包放在称上称量。
随意搜寻的时候,莱昂惊喜地摸到了几把钥匙,耗费一些时间,终于打开了其中一个木柜,里面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瓶养护油和一把钝器。莱昂叹口气,随手拎着钝器走来走去,只能说总比没有要好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楼上隐约传来了歌声和踏步声,莱昂仔细听了一会,声音只是在同一个位置响着,而且听起来有很多人,很热闹的样子。
但在上去之前,莱昂一拍手,用钝器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然后把红色头发编成两条粗长的辫子放在笑脸两旁,看上去扭曲又可爱。莱昂对自己的作品满意极了,随意地甩着新找到的战利品去寻找声音的源头。
通往二楼的楼梯踩上去就发出腐朽的吱呀声,未凝结的血液淌到了他的脚尖前。
莱昂抬头向上看,正好和一个头颅的双眼对上了视线,只不过它已经从身体上被分离了,胳膊则在不远处。
莱昂顿了一下便踩上了被血浸湿的楼梯,黏糊糊的血液粘在鞋底,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奇特的声音。
一路上,尸体在增多,而歌声的源头也近在眼前了,那歌声是那么快乐,莱昂喜欢热闹!他摩拳擦掌,想要加入他们,来吧,一起演唱这庆典的,赞美的歌声!
但还没等他走到最热闹的房间,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就从房间里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莱昂皱皱眉,他不喜欢这种被酒精支配而失去理智无法沟通的家伙。
“你!就是你!”
莱昂歪歪头:“我!就是我!”
“混进我们之中的小贼,你偷了什么!”
莱昂随意地甩着手中的东西,偷确实是偷了,但可不是刚才,看来在自己之前还有别人来过。
他真诚地给出建议:“你看看你丢了什么不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来问我?”
“你假装跳下去又折回来!想偷更多东西!这些都归我们了!我们抢到了!”男人得意地叫嚷这,但听在莱昂耳中无异于野猪嚎叫,难听极了。
他连刀都没拔,直接用手中的钝器做武器和他周旋,一边打一边想,这个做法怎么感觉有些似曾相识呢。
不过要撂倒这个大块头,还是费了一些功夫。莱昂晃了晃有些眩晕的头,骑在对方身上,像敲西瓜一样把他的头敲烂了。
“唔……衣服脏了……”敲烂一个人的脑袋可是个体力活,莱昂气喘吁吁地站起来,准备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选了个最近的安静房间,但是为什么,这个房间会有一口大箱子呢?这难道不是在诱惑他探索吗?
莱昂遵从了神的旨意,打开了这个箱子。
他并没有做什么防备,于是在箱子被打开的一瞬,雪亮的刀光照亮了他的瞳孔。
距离太近,根本没有办法闪避,莱昂只来得及微微偏头,就被刀擦着脸颊划过去,紧接着就是涌流的鲜血和尖锐的刺痛。
而下一秒,他所在的房间房门被踹开,一个持刀的男人速度极快袭来。
“啧……”莱昂迅速抽刀迎战,短兵相接的一刹那,莱昂看清了对方的脸,瞳孔都因为兴奋而缩小,“基兰!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