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要选他。”
站在跪伏在地的他前面的是领主的女儿和领主的骑士们,在稚嫩女声的话音落下后整片田间无人做声,而他只是将头紧紧地贴在地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农奴只能弯下他们的脊梁或是低下他们的头颅,他们绝不可直视他们的主人,那是大逆不道。
但是他清晰地听见了骑士老爷们的声音,坚硬沉重的细长物体戳了戳他的肩膀,“抬起头来。”
他十一年的人生中第一次看清了那些尊贵的人,高大的男人们穿着坚硬的铠甲,身披绣着复杂徽章的披风,而站在他们之间的那个女孩——就是领主的女儿。
她身材纤细,有着柔软的银色发丝,看起来像只刚出生的柔弱兔子,但是这只小兔子拥有可以让他的父母弯下他们身躯的力量——她的地位。将来她会代替她的父亲成为他们的主人。
他直起身子,而他的父母们仍跪在地上。
“我要选他。”女孩又说了一遍。
骑士们的眼神中似乎多了些迟疑,他们的视线在女孩看不见的头顶交换着他不明白的信息,但这些让他隐约察觉的女孩的决定让他们十分为难。
这时母亲的声音忽然爆发出来,尽管她仍然低着头。即使他们的声音稍微惊扰了那些贵人们也算是罪过。
“大人们!如果您需要……需要我们的孩子……”
“闭嘴!”他听见父亲的低声呵斥,或许过一会儿母亲会挨一顿毒打,但她没有停下,她甚至也直起身紧紧扶着他的肩膀。
“您看看,这孩子长相不错,也很机灵!不管你们需要他做什么他一定都会去做的!大人们!你们再考虑考虑……”母亲的手在不住地发抖。
女孩水晶般的黑色眼睛眨动,粉色的嘴唇再次张开,这次她的话语终于成为改变他命运的锤音,“我要选他。”
最后骑士们将他带离了父母身边,跟着骑士们的他被女孩紧紧牵着手,他偷偷回头看向那破旧的小屋,父母已然哭作一团。握着他的手的那只柔软的小小手掌握得更紧了些。
这是发生在基兰十一岁那年的事。
2
五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足以让瘦小的农奴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玩伴及护卫。基兰站在窗户下面,当树叶被风吹动,从缝隙间落下的光线也在他的脸上晃动,他微微眯起眼睛,向上方举起双臂。
“安琪!”少女的身影正在二楼的窗台边缘犹豫,茂密的树影掩护了她的动作,“我接着你,下来吧!”
“你真的能接住我?这里好高,基尔……”比安卡坐在窗台边缘,频频四处观望,她眉头微蹙,仿佛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
“我会接住你的,相信我,安琪。”
忽然少女转头看向身后的房间,她脸上的神色从犹疑变成了惊恐,“基兰……”她的声音也开始发抖,“有人——”
“快跳下来!”
最后比安卡闭上眼睛,身体在窗台边缘倾斜,而后她在基兰金色的眼眸中坠落,他立刻向前迈步,在衣裙掠过的声音中花朵与香料的味道溢满他的怀抱,比安卡投入他的臂膀,他立刻抱住她的身体,轻轻亲吻她的发丝,而后将她小心地放在地面。
“走这边。”他抓住她的手,带着她沿着墙根按先前他已经探清的路线离开随时会被人发现的窗户底下,而就在他们刚刚离开那里后查看情况的卫兵从窗户探出头来四处张望。
在躲过巡逻的护卫时,比安卡油然而生出一种新奇的感觉,她漫步在自家的庭院里,却要躲过那些平日里对她毕恭毕敬的骑士与佣人们,因为她现在正在做一件不能被发现的事。而那些人会将他们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的父亲,这可不行。比安卡觉得自己正在变成那些爱情诗集中为了爱情昏了头的傻女孩,要是哥哥们知道了一定会笑话她的。
她的手被基兰紧紧握住,她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握住这只手时,这只手要小得多,却已经布满了劳作痕迹,变得伤痕累累。现在这只手几乎完全可以将她的手掌握住,尽管上面仍满是伤痕,但温暖又可靠。
基兰,她自己选择的玩伴,他现在也已经变得高大,十二岁之后他们的身高都猛地成长起来,但当她回过神时基兰几乎已经比她要高出一个头。他就像她的哥哥们一样可以轻易地抱起她,而这几年里他就像他的母亲说得那样——
不管她需要他做什么他都一定会去做。
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基兰的出身表达不满,但是他只是看到了他的出身,他不知道基兰对她的感情。或许比安卡自认为不会受到父亲的话语的影响,但有时已经对世事稍加了解的贵族少女还是会思考基兰留在她身边究竟为何。
今天她会知道一切。
基兰可以理解父母曾经的举动与决定,即使只是一个护卫或是宠物一样的玩伴,他的生活也照比农奴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需要卑微地伏在地里耕作土地,期待着永远不会属于自己的收成,也不用一家人可怜地缩在破旧的房屋中用残破的布料御寒。高大宽敞的城堡中会有一张属于他的床铺,上面铺着柔软厚实的垫子和被子,他可以和那些骑士们一起学习骑马,剑术和射箭。有时比安卡还会教他写字和读书,不过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领主是不愿再让他学习识字的。
他和比安卡已经有了许多秘密,那些铺满歪歪扭扭的字体的羊皮纸记录了他们的心照不宣。
但是大部分的时光都在他们的心中,就像今天。布鲁特家族的庄园大到可以容纳下一个小小的山坡,这里过于靠近庄园的边缘,因而无人打理。青青野草在这里肆意生长,随着他们的走动掠过他们的脚边,比安卡时不时地会停下看看路边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野花。
“你经常来这边吗?这里离训练场还挺近的。”
“是啊,”基兰接过她摘下的粉色花朵别在她的耳边,这让她苍白的发色间多了一点活泼,“以前这里偶尔能看到野兔,后来园丁们想办法把野兔都赶走了。”
“原来你喜欢兔子?”
当比安卡忽然凑到基兰面前时,他听见一声巨响从自己的胸腔中传来,甚至盖过了周围的风声,青草与树叶的低语也为之停下,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这原来是他的心跳声。他的擂鼓般的心跳声震耳欲聋,比安卡也会听到吗?银白色长发的少女睁着漆黑的双眸看着他,像一只好奇的小兔。
“嗯,我……喜欢……”他点到即止地回答了主人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了,他必须到此为止,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好了,对他来说他必须满足于此。他只能满足于此。
“是吗?我也喜欢,”比安卡收拢裙摆蹲下,基兰跟着单膝跪在她的身旁,顺着她的视线他看见一只睡在花蕊中的甲虫,“不过我也很喜欢小狗,但是爸爸只肯让园丁养那些猎兔犬。我想要属于我自己的小狗,基兰。”
她的意有所指让他的心情再次慌乱起来,基兰不知道应该对此作何反应,他能做的只有撇开眼神,用手指拨弄身旁那支无辜的小花。
“基兰,爸爸总是说我应该和配得上我的身份的人一起玩,但是我只想要你……”
“小姐……”但是不等他说完,忽然他的身体被推动着失去了平衡,当他倒在地上他的视野中只剩下了比安卡——他的主人。他的肩膀被比安卡的手压着,尽管他可以轻易挣脱她的压制,但基兰不想这么做。
“基兰,告诉我,你不会离开我。”
“我……”
“永远。”
他本不应说出的答案,他本不应逾越的鸿沟,现在在她的注视下他已经不想再去想那些了,对他来说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词汇,但是如果他的主人想要一个永远,那么他愿意将永远背负在自己的命运上。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比安卡,”他说,“我爱你。”
“我也是,基兰,我爱你。”
当比安卡吻上他的双唇,他将手环上她的腰间让她的身躯贴近自己的胸膛,好像她奋不顾身地投入自己的怀抱。
直到一切结束,他们也不愿与对方轻易分开,如果他们就这样离开便又要回到那被礼教与阶级束缚的城堡中,他们不得不对彼此装作无事发生,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最后是基兰先牵起比安卡的手,他使得比安卡离开自己的怀抱,像个护卫该做的那样,他拘谨地亲吻她的指尖。
“该回去了,小姐。”
比安卡只是垂着她黑色眼眸,细密的睫毛在她的眼中投下一片阴影遮挡住了里面的光。最后她摘下耳畔的那支小小的野花,娇弱的花瓣落进泥土,很快便无处可寻。她握住基兰的手,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裙摆与头发。
“我们都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她看向远处的城堡。
“……是的,”基兰走在比安卡的身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3
只有这片本就无人打理的小山坡一如既往。基兰站在山坡的顶端,白色的小花在他的脚边盛开,但很快被他踩进了泥土。他踏过青草和土地,荒芜的训练场出现在他的面前,失去护理变得锈蚀的铁剑歪歪斜斜地放在架子里,原本平整的训练场的地面现在坑坑洼洼。骑士们都已经失去踪影,野草、昆虫与野鼠占领了这里。
每一处人类的废墟最后的下场。
他对那些生了锈的铁片子半点兴趣没有,于是他径直穿过训练场,绕进花园的小径。花园,现在倒不如说是荆棘的迷宫。没了管理和修剪,蔷薇的枝蔓四处缠绕、攀爬,比爬山虎更具侵略性地占领了这片土地。但这些蔷薇对他来说称不上是什么具有威胁的守卫,基兰拔出短剑轻易地砍断这些干枯的植物。
他再次站在了这座城堡的脚下。带着满身的伤疤。他感到脖子上的伤口隐隐发痒。
自他被比安卡杀死过去了一年左右,布鲁特家族以超出他想像的速度迅速衰落下去,以至于当他终于恢复到可以回来寻仇时,这里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城。就连领地里的农奴们也不见踪影。曾经给了他与父母一个庇护之地的小小房屋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
谁都不在了。
脚步声回荡在布鲁特家族城堡空荡荡的回廊中,不间断的回声仿佛在指责他干扰了这里的清静。他对城堡的低语熟视无睹。
没有人做他的向导,也无人告诉他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那么多的人究竟是如何一夜蒸发让这里空空荡荡,那些蒸发的人又究竟去了哪里。不过基兰对这些事也并无兴趣,他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只有一个。
他的记忆是最可靠的指引,他轻车熟路地来到这个房间的门前,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他也是如此站在这里。他推开这扇门,梳妆台,小雕像,床铺……除了蒙上了一层尘埃这里没有任何变化。
不,还有另一个变化。
她也不在了。
比安卡·布鲁特成了杳无音讯的遥远回忆。只有每晚的疼痛与窒息提醒着基兰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比安卡·布鲁特的人,她是他曾经的爱人,她是夺去他姓名的凶手,她是……给予他痛苦的人。
他金色的眼眸转向下面,地毯上除了尘埃没有任何污迹。蒙尘的痛苦之神默不作声。
基兰关上房间的门。
夜色将至,基兰来到他曾经居住的房间。或许他死了之后这张床被分配给了别人,但一切都无从查证。他掀去被灰尘侵蚀的床单,下面的铺盖仍干干净净。他不在意上面的霉味,能有一张床供他休息已实属不易。
忽然他想起什么,但他的动作却忽然犹豫着要不要继续进行。过了片刻,基兰的手指还是摸到床头垫子下的隔板,上面的缝隙似乎等待已久,他毫不费力地撬开这块木板,里面已经泛黄的纸张出现在他的眼中。
这是他们的秘密,无人知晓,无人发现。甚至在基兰离开后也无人在意这个死去的护卫、宠物究竟同他的主人一起藏着怎样的秘密。
记录着歪歪扭扭的字迹的羊皮纸被撕碎丢进火盆,火石砸在火钢上迸溅出点点火花,落在写在纸片的角落里的名字上。
基兰。比安卡。
阿诺德·施特拉德是知名的怪人。
达拉尔的人每每提起他,总会在最后加上一句叹息。达拉尔的老人不多,活到阿诺德这个岁数的更加罕见,好像只有老糊涂的汤姆还记得有关他年轻时的只言片语。
无可否认,老阿诺德的陷阱从不落空,他制革的手艺也是一流。但就像达拉尔居民的那一声叹息:
“他好像永远都不太高兴,我就没见他笑过!”
虽然老阿诺德是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脾气,但相比之下,他的孙女帕梅拉可就讨人喜欢的多。周围的商户都喜欢她,被她用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盯着,人总是会情不自禁要给她些小礼物。
人们总说帕梅拉什么都不懂,就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其实帕梅拉懂的可多呢。一头牛能做四双鞋底、一个包、和两条腰带,这些制品拿出去就又能换一头牛;还有一壶牛奶等于三个鸡蛋、一只母鸡能换一袋小麦粉,但把牛奶和小麦粉混合起来,做成的食物就能换一块咸肉……
那群精明的商户总想着和帕梅拉做生意是最轻松的,但他们不知道,帕梅拉的小脑袋瓜转得比他们还快呢!
但是商户家的孩子们却没有那么喜欢帕梅拉,因为和帕梅拉玩游戏是最没有意思的。让她扮演领主,她下的命令总是让人不知所措;让她扮演骑士,她又总爱刨根究底;至于让她扮演敌人,哦天啊,她的力气可真大,一不小心就会被她的木棍打伤!
老阿诺德是最不屑于管这些事的,向他告状只会被他反问:
“你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也要向对方领主的爷爷哭鼻子吗,骑士小子们?”
久而久之,孩子们就再也不愿意和帕梅拉玩了,可帕梅拉也不太在意,因为跟爷爷去打猎可比念台词有趣的多!
帕梅拉在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在阿诺德身边学习如何做一名制革匠。垂垂老矣的工匠总是坚持自己剥皮,他对自己出手的作品有着异乎寻常的挑剔,必须从第一道工序开始掌握,这样他才来得舒心。随着年纪的增长,阿诺德的偏执越发严重了,但或许正是这种偏执,让许多达拉尔之外的商贩都慕名而来向他提交订单。
年幼的小工匠对这门手艺的认知,是从尖刺穿过一只野兔的头开始的。灰色的生命蹬了蹬腿,很快就融化在了红色的浆体中,捧在手里毛茸茸的,搔得手心有些痒。起初它在怀里是滚烫的,但慢慢的,就只剩下恰到好处的重量,好像抱了一条毯子,软软的,很舒服。
这也是帕梅拉第一次直面死亡,她并没有哭闹,也许是这个过程带给她的震撼远远大于恐惧本身。大约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已经是个十足的施特拉德了。
她问:
“为什么?”
而阿诺德答:
“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谋生的手段。”
阿诺德没有教她敬畏,但却告诉她要心怀感恩。皮革匠的商品源自于死亡,而她只需要明白:
“我们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罢了。”
兔子的肉成为了晚餐,而帕梅拉在爷爷的教导下,将它的毛皮做成了一顶小巧的帽子,卖给了一名和她年纪差不多的贵族女孩。时至今日,帕梅拉依然会想起那只兔子,还有阿诺德把她的酬劳放在她的手心时,对她所说的话:
“孩子,我们并不比这些畜牲优越太多。我们本质上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动物。”
这番晦涩的话很难说给了帕梅拉什么触动,她还太小,前不久才刚刚换了门牙。但帕梅拉最听爷爷的话,既然爷爷这么说,那一定就是这样。
原来这座城也是一座农场,我们做出来的皮革也是一种牛奶。我们进食,我们生产,我们成长,一茬又一茬。当我们老了,无法再履行自己的职能时,我们就会被分解,而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一套朦胧的概念在帕梅拉尚在成长的头脑中成型,不过帕梅拉自己尚不能理解这种认知。她只感觉在那之后,她看草棚中的牛犊更加亲切了,当爷爷教她如何把皮剥下来展平时,她对这个过程的理解也顺畅了许多。
那爸爸妈妈呢?他们是被卖到了更大的农场吗?帕梅拉问,但阿诺德没有回答,也没有纠正。帕梅拉没见过她的父母,她只是从邻居的只言片语、还有一些写着好看但难懂的字母的纸片中知晓,他们应当存在。
阿诺德很少提到他们,如果一定要说些和他们有关的事,那张麻木的面孔就会皱得更紧。
阿诺德只告诉她:
“幼崽长大了都会离巢的,你也不例外。”
日子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老皮匠的咳嗦越来越严重,甚至一场秋风都会令他卧床不起好一段时间。帕梅拉依旧奔跑在城镇每一条街道上,老阿诺德总是抱怨,她的衣服刚刚做好,很快就又要做新的了。
邻居说,神将奇迹恩赐于达拉尔的子民,只要诚心祈祷,失去的便会回来。
双手交叉握紧,跪在地上,向天空念叨着感恩的词语就可以?帕梅拉有学有样,问神自己掉落的牙齿可不可以一下子就长出来?阿诺德想笑,但这让他咳得更加厉害。到了第二天,帕梅拉的虎牙依旧是个黑洞洞的豁口,汤汁会顺着那里流进嘴里,她便也不再祈祷。
冬天过了,在小麦还没出芽的时候,老阿诺德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大人们说,他死了。帕梅拉并没有哭,因为爷爷教育过她,这是必经的循环,她记着呢。
但是又过了一天,浓汤在帕梅拉醒来前就被煮好了。爷爷回来了,帕梅拉却感觉有些困惑。她们家的院子里最多只能养一头奶牛和一头小牛,如果被分解的作物又回来了,那不出一个月,家里就会全都是牛啦!帕梅拉可养不过来这么的畜牲。
“乱套了。”阿诺德也这么说,“全乱套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小小的家并没有被不断膨胀的牛群占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越来越多的人闭门不出,他们看帕梅拉的眼神不再充满怜爱,渐渐地,他们恐惧,最后是憎恶。
他们问:
“神啊,这个孩子难道被魔鬼附身了吗!?”
他们说:
“一定是她招来了这场灾难!”
爷爷说过,如果想捕获雏鸟,就要趁成鸟外出觅食时下上笼子。在阿诺德去打猎的某天,混乱的大人们将帕梅拉丢进了燃烧的柴堆里,渴望以此能够结束这场闹剧。火苗很快融化了皮肤,烤化的油脂冒出了好闻的香气。帕梅拉想到了爷爷做的肉排,也是把食材一整个丢进炉子里,区别只是它们被送上餐桌前要被剥下皮毛。这道菜很奢侈,准备起来需要很久,只有新年才能吃上一次,连生日都不行呢。
然后,她醒了,她躺在冒着青烟的柴堆旁,余烬非常温暖,她好像只是睡着了,做了场噩梦。爷爷的手里拿着一柄斧子,血滴答滴答地顺着边缘淌了下来,大人们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像极了她吃过的苹果馅饼。
在那之后一切就好起来啦!城上的大家每个月都要举行庆典,以往只有丰收的日子才有呢!游戏总是有输有赢,但帕梅拉玩得很开心,因为素来疏远街坊的爷爷也会陪她一起玩。
但是阿诺德却好像并不开心,他再也没抱怨过帕梅拉的裤脚怎么又短了一截,恰恰相反,他对帕梅拉说:
“你不能永远这样,孩子,你不能永远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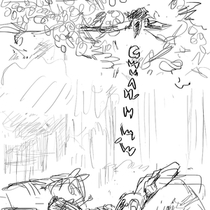
警示TAG:死亡、暴力、血腥描写,G警告。
主要内容:玛丽莫里森在迷宫找到一具尸体。
——————————————————————
达拉尔镇,迷宫花园。
玛丽·莫里森跟着乌鸦找到了一具尸体。
这就是你想给我看的?她瞥了一眼那只鸟,它站得挺高,东张西望,尾巴翘起,跳了两下,飞走了。
一个被人奸杀的小姑娘,下身赤裸,两腿张开,裙子被拉过头顶。玛丽把她的裙子放下来,露出一张原本年轻漂亮的脸,但此时她面目狰狞,皮肤青紫肿胀,脖子上还有可怕的勒痕。
今天她肯定是说不出话来了,虽然她的身体还很柔软,但死人的舌头没法告诉玛丽自己的名字。
没关系,我叫你埃米尔。玛丽把外套脱下来盖住她,玛丽·莫里森比男人还要高大,她的外套足够把埃米尔整个包住,只露出乌黑的头发、纤细的脚脖子和一双可爱的红鞋。
在这个潮湿的花园,在太阳没有温度的下午,玛丽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冷,是的,风呼呼的吹,从异常高大的灌木丛缝隙里钻过,密布的叶片在泥地里投下阴影。没有外套她应该觉得冷的,但她感觉自己在缓慢燃烧,一种恼怒的情绪从她身体深处升起,烧尽的木炭里还燃着雪白的火,她整个人都热腾腾的。
埃米尔明天就能坐起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到河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回家,大家只会知道她死了一次,不会有人发现她是为什么死的,死之前如何了,但发生过的事会在无人的地方,在众目睽睽下,在白日,在夜里,找上她,勒死她,我聪明可爱的姑娘会变得疯颠,怨恨,丑陋,再也不能得到平静。啊,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埃米尔,我们就应该让畜生得到惩罚,就像我惩罚那些不听管教的丈夫一样。
埃米尔还很软,杀她的人还没有走远,玛丽心想,她仔细地听,能听到落单蜜蜂的嗡嗡声,枝条树叶的摩擦声,虫子的鸣叫,鸟儿飞起带来的风,以及……她感觉到有人在迷宫里移动。
而且在那潮湿柔软的新鲜泥土上有一些脚印,这就足够了,对于经验丰富的玛丽来说足够了,被她逮到、死在她手上的男人们完全可以为她作证。
杀死埃米尔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两个。这也很正常,折磨是一门需要精进的手艺,羞辱、掠夺的过程很有趣,他们当然会一起分享,就玛丽的经验,神很喜欢女人走投无路的绝望和恐惧,不过——
神也会享用她提供的美味:
她无声又迅速地接近,举起巨石从他们身后直接干碎了其中一个的后脑勺,被打中的男人一声不吭,直挺挺地栽倒在地,鼻子砸在坚硬的石头上,向里陷进了脑子,再也没爬起来。
另一个被同伙飞溅的脑浆崩了一脸,僵在原地,他剧烈地发抖,转身想跑腿脚却软得像烂泥一样,摔倒在地,四肢并用拼命往前爬,想要从这个可怕的女人身边逃开,但玛丽一脚踏断了他的小腿,他发狂的在地上翻滚,哀嚎、挣扎,因为舌头不听使唤,他发出的声音像野兽的哭号,谁也听不懂,她毫无怜悯地举起石头——
之后,他就再也动不了,但他还没死透,他还有呼吸,只是牙全碎了,嘴不成形状,血咕噜咕噜往外冒,像鱼一样吐出红色的泡来。
她扯下灌木叶仔细地擦手上的脏污:“啊呀、你这就要死了,太快了,太快了,我不喜欢。让人死前痛苦是很不错,生气的时候砸碎人的脑袋也很爽,但简单的死,比如说砸死、砍死、勒死,切断四肢被捅死,死后分尸,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时间足够,我更愿意看你慢慢去死,这不是说我会在一天之内折磨你,看你咽气。我想——”
她瞟了他一眼:“我会让你保持呼吸,从脚指开始,把你一寸寸砸烂,然后把碎骨头渣捡出来放进石磨里,你见过磨小麦吗?我有一座磨坊,你会喜欢的。
你先是在地上爬,然后连手也没有,只能躺在地板上,没有事情可做,身上长出疮来,皮肉一块块烂掉,老婆孩子朋友,凡是认识你的人,都会把你忘了,只有老鼠围着你吱吱叫。
我想要的不是你一时的痛苦,我想要你烂成一滩肉泥,烂成骨头架,我想要你连呼吸都带着地狱灼热的温度,我想要你全身溃烂活活饿死,我想要你要么恨不得死掉,要么已经在死的路上,神会允许你在痛苦之后有片刻安宁,但我不会。我会守着你,每天早上时候一到,你就会准时睁眼——”
他瞪着玛丽。
“你发什么抖呢?”她把一把叶子扔在他脸上:“害怕了?别怕,我不会对你这么做,现在不会。埃米尔不认识我,但我明天就去找她,让她喜欢我,我要告诉她我的好主意,教她我拿手的,我特意把你和你朋友留给她,她肯定会很高兴收到这份大礼。
你就等着吧,等着有一天她来找你。哦,对了,到那时你也可以求求她,就像她曾经求过你一样,我看她长得漂亮人必定也很善良,说不定你求她,她就会给你一个好死!”
我做错了什么?他手脚抽搐,那双鼓出来的眼珠子无声地质问这个残忍的女人和她描述的地狱般的景象。为什么是我?
玛丽·莫里森柔声说道:“你没错、你没错,乖乖,只是你今天不走运罢了。”
她把石头举起,然后用力砸下去——
他哼了一声,从胸腔里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叹息。
然后她把他们拖进了灌木丛的底部,往里踹了两脚。
她深吸一口气,一些带着水汽的空气被她吸进肺里,听见炭火在她胸腔滋滋作响,太阳差不多要落山了,她这会儿觉察到风里带着些凉意了,达拉尔的夜晚将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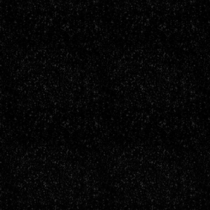
这事发生在不久前,在诺福克郡,也可能不在诺福克郡。这是那种夜晚在篝火堆里燃烧又在人们嘴巴上滋滋作响的故事。
我在赶路途中听别人说来,别人又是听别人所说,虽然给你们转述时会提到“我”或“我们”,但只是指事情发生时在场的人们,并非是我本人,也因此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我都没法给你们证实,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这事儿发生之前,死人不曾开口。
不久前,在诺福克地区,据说有一对新婚夫妇,妻子肩高高过门框,不低头都进不了自家屋舍,我见过的男人没一个能比她更魁梧,但她肤白貌美,身体丰腴,和镇中心立着的女神雕像一样高大又美丽。只是比起那样坚硬、冰冷的青铜造物,这个活人更香更软,像去了麸皮的白面包。
她的丈夫威尔·乔是当地的自耕农,谁也不知道他打哪儿找来这女人,有人从庄外打听,说她是南边来的寡妇,也有人自称有朋友在荷摩的娼妓街上见过她,对这种不敬的猜想,没人会有疑问,因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子肉欲就是比处子的芳香还有滋味。
在农闲时再也没有比这更引人注意的话题了,她一出家门那些男人和少年就总是偷摸看她,想想吧,当这个女人在床上舒展四肢,温热、洁白、巨大的身躯绵延起伏如同丘陵,啊,那时我们一致认为夜里她的男人在她身上耕耘想必如同牛马在肥沃的土地里耕耘般快乐。
哪里有农夫不喜爱农田呢?我们喜欢她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萨维比我们还要喜欢她。
萨维是那种很坏的女人,看谁都不顺眼,从前打骂孩子管教丈夫给她带来乐趣,但现在也不能再使她快乐了。不过自从那个女人来了之后,萨维像是取食的雀鸟,在她的门前晃来晃去,如果她看到有少年在那女人门前踟蹰,她会拿着棍子赶人离开。那女人一次也没出来阻止过她,就这样她每天比前一天距离那女人更近一些。终于有一天她进了那女人的家门。她去了一次就忍不住一去再去,她给她有力的怀抱,像母亲般的安抚,她身上有一种香甜的食物香气,让萨维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少女时期,甚至比那更好,因为那时她还要为嫁人而发愁,而在那女人热烘烘的怀里,她只需要如同黄油般融化,全然不再考虑任何问题。
当她回来时,她就变得好相处多了,就连萨维的丈夫都时常建议她,你何不去威尔家里和那女人待上一会儿?这就足以见得,尽管威尔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透露出古怪,眨眼之间他就结婚,又因为妻子的父亲年事已高,全要靠她带一名丈夫回去继承家业,眨眼之间他又必须变卖家产背井离乡,但我们都很欢迎她,盼望她能改变主意,和她的丈夫一起融入到本地快乐的生活之中来。
不幸的是,悲剧发生了。
在他们将要离开的某日清晨,有人没命似地敲钟,我看那口钟上一次被敲得这样响还是在海盗登陆英格兰东海岸的那天。等我们急忙跑到广场上,敲钟人大声又凄厉地宣称威尔家遭了盗了,于是我们又跑到威尔家一看,我的乖乖,全是血。全是血。威尔被敲碎了脑袋,他头冲外倒在门口,啃了一嘴泥土,从房屋到门前全是搏斗的痕迹和被袭击的证据,一切都砸得稀烂,但没有见到威尔太太的身影。是的,那是个健壮的女人,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啊。我们一致认为她凶多吉少。穷凶极恶的盗贼会把抓到的女人拖拽过河流密布的绿林,在冒着黑气的沼泽里淹死,沉到烂泥里发酵,让她们的骨肉也化成烂泥。
萨维简直哭得快背过气去,但我们发现得太迟了,凶手早就带着威尔的财产和女人跑了,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也没什么心情收拾可怜的威尔,他没有什么别的亲戚,就连农地也卖得精光,由于他生前欠缴税款,不管是墓园还是教堂都不肯收他,于是只好把他和他那颗烂脑袋装进棺材,当天就下葬了,就埋在他自己那栋农舍背后。
倘若只是这样,那完全不值当我给你们讲这件事。
过了一段时间,竟来了个外乡人,这个村庄在诺福克是最普通不过的村庄了,耕种的乡下人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客人。可他远道而来,在村里东走西走,找人聊一些诸如收成如何的闲话,我们心知肚明他一定是憋着什么屁事儿。到了傍晚他终于忍不住了,走到我们面前来问是否见过一个女人。
我们这里有诺福克最好的农妇。
不,他说,我找的不是农妇,这个女人橘色头发,眼睛碧绿,她高得出奇,但她很美,鼻梁上的雀斑,因为皮肤很白,所以格外显眼。
他说的是那个女人!是威尔乔的妻子!
外乡人道,原来她在这!带我去见她!
我们不得不指着威尔家的方向,告诉他那女人的下场,她丈夫已经下葬,她也被盗贼带走不知所踪,即使是往最好的方向去猜测,也肯定死得不能再死,因为我们还没听说附近有人见过这么高大的女人。一个人除非是死了不然怎么会如此无声无息呢?
外乡人听了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愚蠢!愚蠢!她不会死!我要找到她!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们完全听不懂他的疯话,但害怕他闯出什么祸来,也只好跟着他跑。
外乡人两条腿飞快地倒腾,转得像是疾驰的车轮,我们紧跟其后,啊,那间农舍还立在那儿,它逐渐地从远处显现,因为失了主人,区区十来日就显得破败起来,杂草丛生。
他越跑越快,我们都快要追不上了,太阳将要落下,金橙和血红色的光笼罩住这片土地,刺目的光芒逐渐收拢,阴影爬上了地平线。
接着我们看到他在靠近那座农舍的一瞬间,就在他跨过门的一刹那,他身体突然变得四分五裂,像是个因为奔袭速度过快而散架的板车,手在激烈的挥舞中高高甩脱在空中,然后腿从裤管儿里掉了出来,鲜血飞溅流得满地都是。
我敢打赌那块地上的杂草因为有这灌溉都应该长得更高些才对。
等我们围拢,他还没死,他还没咽气,他衣服染得通红,因为痛苦而不停尖叫!
这事发生得措手不及,我们像是受惊的兔子呆立在农舍前面,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种有韵律的沉闷的声响,从那屋舍后面传来,从地下传来。
咚咚咚——
从威尔的坟墓里传来。
咚咚咚————
不知是谁拿来了锄头,把那块土挖开来,那棺材震颤着,我们听到里面有人在喊叫、拍打,等我们把棺材撬开,我的神——
是威尔!
他活生生地从棺材里蹦出来,大叫:她杀了我!她杀了我!你们把我埋了!
我们目瞪口呆,但这已是白日的尽头,太阳最后的光芒在他脸上转瞬即逝,萨维首先开始尖叫,然后是我们所有人:威尔的头扭曲变形,一下,一下,又一下,在那天夜里发生的没有人目睹的凶杀在众目睽睽之下重现了!
他后脑勺猛地瘪了下去,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无比高大的人用钝器猛击了他的脑袋!他整个人剧烈地往前倒了一下,然后是第二下!
他倒在棺材里!
第三下!
血从他的眼睛鼻子里冒出来!
生机迅速地从他头上的破洞流逝而去!再没了呼吸。
好了,现在你们都应当知道,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死人不曾开口,但从那一天开始,神的旨意改变了,而愚蠢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把可怜的威尔埋进了地里。不过威尔最终原谅了我们,自从那时候起,威尔每天都会在广场的大钟旁给我们进行这场真实又血腥的表演,顺便说这也是在节日游行中最受大伙儿欢迎的节目之一,毕竟我们其他人都死得太普通又乏味啦。
手脚横飞的外乡人在第二天也恢复了原样,原来他是被用斧子砍死的,可不是,那女人臂膀的力气大得惊人,他坚信那女人一定还活着,他一定要找到她,也是因此,他才会寻着女人留下的痕迹找到了我们村,救了威尔一命。要不是他,可能过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发现威尔还活在地里头。
故事仍未结束,从那之后,又陆续来了好些外乡人,有男有女,有少年人也有老头子,死状千奇百怪,现在我们知道那女人确实还活着,我们这儿只是那些外乡人在夜晚来临前停靠的某一地罢了,我们在火堆边烤火,喝着热气腾腾混了黄油的啤酒,讨论他们新鲜离奇的死状。而这些活死人们,至今还在外面到处游荡,寻找心中那个残酷、恶毒又美丽的女人,不知道是要向她祈求欢愉还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