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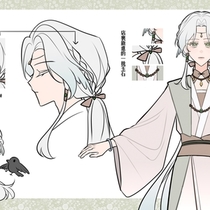

癸卯拾肆第一次去陆景维家里的感想是——
不如镇安司。
院子不如镇安司大,房子不如镇安司多,水池不如镇安司广,还没有操练场。
这种想法在他看见陆景维的房间后戛然而止。
“这么大一间,你一个人住?”
“对。”
“这桌子椅子,你一个人用?”
“嗯。”
“这一架子兵器护具,都是你的?”
“是。”
“我能拿下来看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拾肆摘下一把长刀,托在手里细细端详,用手指抚过雕刻着花纹的刀盘,发出细小的惊叹声。
陆景维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被这样赞叹,他还怪不适应的。
忽听得前院一声呼喊:
“孩子们,出来吃饭咯!”
拾肆收刀入鞘,放回原处,哒哒哒跟着陆景维出去了。
第四章 予你华裳,许你安康
癸卯拾肆啃着羊骨头,眼神不老实地四处飘,想着陆家究竟是怎么出来陆景维这么个人的。
明明父亲和兄长都是出口成章的文人,身上一股墨水味儿,母亲和嫂子也都是温柔随和,善解人意,总笑眯眯的人。
唯独他,佩着刀,冷着脸,步步生风,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冷冽气息。
不过,人各有志。拾肆深知自己没资格评价陆景维。他们是同一种人,舞刀弄枪,日日与钢铁打交道。
所以这样温暖的,软绵绵的时光,拾肆格外珍惜。
“来尝尝这个,我新学的油糍,可试了好多次才成呢。”
“别噎着了,喝点这羹,一碗下去身子都热乎着。”
拾肆倒不客气,什么好吃的都照单全收。饭桌上不少好东西他见都没见过,今天可算开眼了。
“谢谢伯母,谢谢嫂嫂。”
“我们持光很少带朋友回家的……怎么样,他在司里和你们相处都还好吧?”
说话的是陆景维的兄长,陆景荣。拾肆进院儿时远远望见过他靠着栏杆看书。
“嗯……挺、挺好的。”
拾肆简要地聊了聊陆景维在司里的近况。当然,关于一些陆景维乱摸异人同僚耳朵尾巴导致被抓被打的事情,他知趣地没有提及。
酒足饭饱过后,拾肆在陆宅院子里参观。时值立冬,花圃里有一层薄雪。拾肆就蹲在院子里玩雪。
陆嫂递来一条披肩,见拾肆衣裳单薄,又想起曾听陆景维说这孩子是个孤儿。
“你这孩子,还没有冬衣吧?”
其实拾肆也不是没想过买衣服。只是他先前在司里安顿时欠了不少债,平时吃的又多,每月发下来的俸禄不是还钱就是进肚,根本余不下什么买衣服的钱。
他现在身上还是从火场里穿出来的旧衣服。平时如果换洗,就穿官服,再不济就去镇安司库房捡一件伤员穿的白袍子。
看着拾肆身上的衣服,粗糙的布料被搓洗得发薄,嫂子当即决定给小狗添件新衣。
拾肆几乎没逛过成衣铺,倒显得有些畏手畏脚。一方面是他对穿衣确实不讲究,选不出个所以然;另一方面是怕价钱太高,让人家破费。
见拾肆支支吾吾的样子,嫂子直接一手包办,全身上下,通通翻新。
陆景维平时的衣裳似乎都是哥嫂操办,两人选起衣服来驾轻就熟,一边选着,一边聊起过去的事。说些什么我们持光这个年纪时要高些,长得飞快,衣服半年就要换之类的琐事。
拾肆只顾着听,全然没在意自己身上的东西越套越多,最后——盖了一件毛茸茸的披风才算结束。
“看看怎么样?”
拾肆回过神来,看看镜子,心里欢喜,眼睛亮亮的,一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他怕弄脏新衣,但又想多摸摸这样柔软的面料。小狗把袖口举到鼻尖前嗅,心说不愧是好衣服,连味儿都是香的。他又想起陆景维身上也有一样的香味儿。
“喜欢吗?”
拾肆点头如捣蒜。他想摇尾巴,但背上的披风太厚重,压住他的尾巴,摇不起来。
陆景维奇怪道,他练武,整这些不是拖地麻烦么。
嫂子嗔道,再废话把你的披风变成三层。
陆景维不说话了。
陆伯父和陆伯母这时也回来了。两人先前不知去逛了什么,脸上带着笑意,背着手,神神秘秘的。
“呀,这么好看!还怕我们选的不合适,搭配不上新衣怎么办。”
陆伯母从背后拿出一把长命锁,挂在小狗脖子上。
“现在看来,选得正合适!”
双线银圈儿底下坠着一把精致的小锁头,上刻云纹,下串银铃,摇晃起来叮当响。
拾肆傻了眼,他哪见过这东西。一边摆手,一边忙说太贵重,不能收。
陆伯父笑道,谈何贵重,太过客气。
陆景荣说,还麻烦你平时在司里多照顾我们持光。
拾肆怔怔,说道一般都是他照顾我呢。
一众人都乐了。陆景荣又问,你觉得持光这人,如何。
拾肆看了一圈和气的陆家人,思躇了一阵,缓缓道:
“棉花堆里冒出来的铁块子。”
陆景维皱眉,怎么也想不通为何是这种形容。
陆景荣乐了,说有的铁块子也是空心的,你敲开来看,里头都是棉花。
那他也是棉花?拾肆歪头。
陆景维大手一挥,使劲按了一把狗头,顺便搓了搓狗耳朵。
他说。就你贫。
赶紧回家,明天当班。
小狗跟上去,脚步哒哒响。身上的饰物摇晃起来——
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响起来了。

拾肆今儿不巡街,被徐止拎出来。
他俩脸上都跟坏了一样,面无表情,能不动就不动。猫眼狗眼,都只转一转。拾肆说,你其实很适合来镇安司,坏人一看你,容易吓得不敢跑。徐止有来有往,说,你也适合收破烂,客人看了你,通常会不要钱,放下就走。拾肆很少听这样的话,居然老实问,为什么?
徐止想了想,从善如流,说,因为你可爱。
他俩还没走,仍在镇安司门口。曹石路过了,问,吃饭啊?徐止说,捡破烂。曹石说,那在下先告辞了。徐止叫他别走,曹石不解,这猫说:我捡捡你。曹石给他扛起来放墙上去。
拾肆哒哒哒跟过去,又问,你捡破烂还捡人啊?徐止说,有些话本来有趣,你如此认真,显得我十分缺德。我只是捡曹石,但曹石不让我捡。拾肆说,哦,那他毕竟不是破烂。徐止说,你真可爱。拾肆说,你也是。徐止叹一口气。
吃烧鸡吗?徐止拍拍灰尘,边走边问。拾肆眼睛一亮:吃。但转念一想,很担心:捡破烂的钱,够不够吃饭?徐止说,比之镇安司,实在差很多。拾肆说,难怪曹石每每问我,都是叫我请客。徐止说,要不咱俩去摸他的钱包。
拾肆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这如何可以?
徐止头头是道:我若是摸到了,咱俩吃一顿,你将我抓起来。我若是没摸到,就躺在地上,讹他一顿。
拾肆说,你开玩笑的吧。徐止说,是啊。拾肆说,你真可爱。
徐止说,你是故意的吧,拾肆说,是啊。
=
要过年了么,仲秋提前准备些腊肉。
做吃的她其实不算擅长,照顾大小姐的时候全靠厨娘。但非要和赶制冬衣比起来,那还是做吃的容易些。
如果有自己的小院子就好了,不用这样和衣服们挤在一起晾晒。她这样想道。但回头看看,正是因为镇安司的官服遮挡,麻雀们看不到自己来了,所以才心安理得地继续偷啄腊肉。腊肉本就是多做了一块给他们的,白天是鸟雀,夜晚是野猫,分配合理,如果多拿,就被暴打。
被谁暴打,仲秋不知道,只奇怪怎么大家如此有序,一次一口,彬彬有礼。
前阵子回温,来的小鸟更多了,乍一看以为春至,其实还有得熬。仲秋把官服抽出来,灰色的外衫不庇佑麻雀,该去守护百姓了。她看一看天,鸟雀呼晴,觉得阳光很好,实在适合晒被褥。
真正到镇安司时,还没到她换班的点,但听到门口有吵闹。她走过去看,见曹石拎起个小孩,正摩挲下巴那没刮干净的胡茬,难保不是昨晚又通宵了:“小徐兄弟为什么喜欢来镇安司摘桂花?”
徐止挣开曹石,猫一样蹲在墙头,振振有词:“此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德俱尊,四季平安,没人来偷,无人敢抢,连桂花都开得很茂盛。”他停一停,回头看到仲秋,问:“镇安司的绿树是对公众开放的吧?”
仲秋愣一下,却看向曹石:“仲秋不知,要问前辈。”
前辈。徐止嚼一嚼,这老家伙要是着急点,年纪可以做你爹。仲秋思考了一下,说,可是小白你好像只比我大一年。曹石问,要红包吗?徐止尾巴上的毛竖起来:……给多少啊让我多个长辈。曹石认真想想,塞给他二十一文。
=
1
=
“卖糖葫芦咯!”
卖糖葫芦咯。徐止跟着他嘀嘀咕咕,被赵弘义听到了,一转头,可是那猫耳朵躲在草垛子后面,什么都看不到。赵弘义不信邪,把草垛子往左,猫也往左,赵弘义把草垛子往右,再往右,咚一下,看见猫头,击中猫头,猫头蹲下。
“……哎哟徐兄,不好意思,我以为见鬼了。”
猫头捂着脑袋蹲半天,面无表情爬起来,手里居然有一串掉了的糖葫芦,他说,你不要了吧。赵弘义说,呃,可以不要。你头没事吧?徐止说,还能用。赵弘义说,我给你点药?徐止高看他一眼,问,你还随身带药?赵弘义说,万一呢,总有人用得着。徐止说,你倒是随时助人为乐。赵弘义道,人活着么,是这样的。
徐止偷偷把糖葫芦吃了,说,我随时准备入土为安,你路过可以帮我埋一下吗?赵弘义若有所思,说,赵某拄拐杖不太好挖坑,坟头放一把糖葫芦算吗?
=
2
=
有个小孩买糖葫芦,一路往北跑,结果铜板掉地上了。赵弘义看得见够不着,正要喊,也不知道去他去哪里,只瞧个猫耳朵,鬼一样窜下来捡了。
“小徐兄弟!来得好。”
——好个屁,他还没说话,那猫把铜板揣自己兜里了。
赵弘义扶额,说,小徐兄弟,你腿脚快,能不能把这铜板给刚才买糖葫芦的孩子送过去?徐止面露不舍,说,都掉地上了。赵弘义劝道,那也是人家的,我请你一串,你帮他一把。
十分划算。徐止露出点笑:好啊。
这厮居然起身就走,目标明确,三两步消失巷口,没多久便跳回来,抬着他的伞,说,给他了。赵弘义想,是不是又被这贼猫坑了。
贼猫还在笑,心情很好,挑了串小的。赵弘义问,你今日不开店?徐止道,开不了,朱雀大街死了人。赵宏说,难怪旧日同僚如此忙碌。徐止道,我也忙碌,如何不见你称赞我。赵弘义看着他吃第一口糖葫芦,说,你本可以不忙碌。
他俩慢慢往前,话题东倒西歪,徐止吃到第二颗,居然又看到那小孩跑回来,他指了指,说,街头李家奶奶的宝贝孙子。
赵弘义大惊:“她哪来的宝贝孙子?”
徐止道:“我也觉得奇怪,但你上个月说二狗媳妇丢了娃,死活找不着,鼻歪,眼斜,家里人也不在乎,官都不报,只有孩子娘哭天喊地。”
赵弘义听出弦外之音,说,我们去看看。徐止吃完第三颗,转了转眼珠:“我帮你把他抬过来,你再给我一串?”
这是什么缺德买卖。赵弘义问。徐止说,你看,这镇安司要是看见了,我是说我捡垃圾,还是说我拐卖人口啊?赵弘义说,你想说你拿串糖葫芦过去是送爱心吗?猫说,那先谢谢赵老板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