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苏鲁/修仙/G向
本企为g向企划,以Q群、eflartworld双平台运行,需要在eflartworld官网进行人设创立,并进行主线打卡
g向内容发布e站需要全年龄封面,打码处理
荒界之中,源气断绝,修仙之路即将行至尽头,万民呼唤只等新的飞升者存亡续绝!二十五年前灵台飞升的失败者,如今再度被邀请,只待你重探秘境,重回巅峰,并寻找真正的飞升之道……
本企预计将于2月7日晚八点结束人设投递并开始审核,文画皆收,中审,有主线,有撕卡要素,预计时长两个月,审核群群号:923224245,静候诸位修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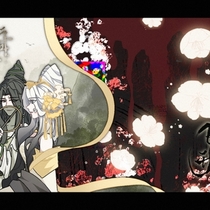

欢宴夜硕鼠惊好梦,晚月下故人再相逢
不知何时变得破败的房间内,血的味道让五感都变得迟钝,唯独落下的月光依旧轻柔,也因此显得眼前人的一头白发耀眼如流银。他穿着我熟悉的漆黑长衫,整个人仿佛融入夜色的芦苇,只有在风吹时才会稍显身形,但风一吹,他就会消散。而那道背影和记忆里无二,消瘦,苍白,只是站在那里,好似被潮湿的海水淹没,无法呼吸。他回过头,依旧是那副威胁般的微笑,他道,点点。
很少有人会用这个名字唤我,只因这两个字的来历太远太久,也太过亲昵,我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世界上最爱这样唤我的只有两人,我已经死去、尸体都没留下的母亲,和微生万仞。我和微生万仞的关系并不好,无非是我受缚于他,而他随心所欲威胁我取乐的糟糕关系,偏偏在某次他得知我的乳名后,不论我如何威胁,也坚持要用这个名字称呼我,我拿他没办法,也没有资格反抗,后来也就习惯了。
突然出现的、会说话的诡异老鼠的话还萦绕在耳边,出现的人应当是我最重要或者最珍爱的人,我本以为会出现父母、家人、或者师父与同门,最多不过是年幼时关系最亲密的玩伴,却偏偏出现了一个我都快忘记样貌的人。至亲至爱?我和微生万仞绝非此种关系,也许我会称我与他之间为孽缘,也许只是萍水相逢,但绝不应该——
“点点。”
第二次。他再次出声唤我,我抬头看去,微生万仞还是那副模样,他擅长用笑容来威胁我,我们实力相差太大,在他面前,我毫无胜算,因此只得缴械投降、忍辱负重。在我们相处的为数不多的那几年里,他从来如此——一个阴晴不定、只手遮天的人,我被迫跟着他,从最初整日想着该如何逃跑,到后来干脆利落地放弃,耗时不过七天。
老实说,我并不了解他,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将来、现在,我们对彼此的认知都太片面,我充斥偏见,他满是轻视,直到最后离开的那日,我才稍微对他有所了解。可我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思及至此,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已经过去很久了。
那是距今约摸有数十年的事情了,我同师弟们因为在山上炸了一次厨房,被罚下山游历,行至某处称不上繁华但绝对富裕的村落,听说了此处妖魔作祟的事情,秉承着打响本门名声的想法,一致决定留下来帮忙。我就是在这里遇见微生万仞的。
村子里的人说,那妖物屡次出现,带来灾祸,本地人苦其良久,最后他提出要定期献上新娘作为祭品,这才消停下来。寻找线索未果,那么只能引蛇出洞,办法很简单,我们之中谁结个婚、穿个喜服、坐个轿子,成为他的“新娘”,自然能摸到他的老巢。于是问题来了,谁来当这个倒霉蛋?谢景宣道,我太高了,不行,我也不要穿那种东西;柳拂衣道,如此看来,我应当也不合适;林凤道,我倒是不介意,但是我毕竟是男子,恐怕轻易便会被认出;最后三个人齐齐看向我,我心道不好,要被卖了,转身欲跑。可毕竟我四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太久,彼此之间知根知底,我正要转身,靠我最近的林凤摁住我的肩膀,柳拂衣果断拉住我的手,谢景宣更是直接,拔刀威胁道:师姐,来都来了,出点力如何?我动弹不得,更是敢怒不敢言,只得干笑着答应他们。身为大师姐,却毫无尊严、任人鱼肉,实在可悲!
那天晚上,原本作祟的妖物没能出现,我却在“洞房”里见到了微生万仞。上马车前,我的师弟们千叮万嘱,把能用上的防身器具全部塞给我,告诉我一旦找到地方就立刻联络,不要作任何停留,可我被送到那里,半晌过去,仍旧毫无动静,我实在按耐不住,怕有异变,正准备掀开挡住我视线的红盖头,却看见一只苍白的手停在我面前,接着,视线一片清明。
出现在我面前的瘦弱的男子身着黑衣,一头白发长到快要曳地,烛火晃动着,映在他惨白的脸色,他脸色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失去了全部的情感,整个人也冰冷得察觉不到一丝温度,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良久,我终于回过神来,不对啊?不是说是个长着三只眼睛的妖怪吗?这又是什么?虽然长得挺帅的但是好像连呼吸都没有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鬼吗?
这是我与微生万仞的第一次见面,我把他认成鬼,他把我当成那只妖怪的同伙。解释开误会之后,微生万仞告诉我,他是在此地闭关的散修,被那只聒噪的妖怪吵醒,实在忍无可忍,出手解决了,又发现此处有别的动静,这才来看一眼。也偏偏就是在这闲谈时,我们忽略掉那妖怪一息尚存,于此时发动攻击,微生万仞反应迅速,却还是与我双双中招,这妖术诡异得很,没能对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却将我二人绑定在一起,甚至不能分开太远。
他提出要带我去找人解决,但不想再带着柳拂衣几人,一开始,他们三人自然是反对的,我却安慰道,没关系,就当是我下山游历,不必担心。谢景宣眉头紧皱,问我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柳拂衣目光担忧,欲言又止,林凤盯我盯了老半天,最后应当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道,好吧,师姐,我尊重你。
我并非相信微生万仞,甚至觉得这妖术实在蹊跷,答应与他同行,无非是确定现在他不能伤害我,并且想明白他到底要做什么。从我修行至今,我极少露面,以我的实力也无非是治治小病小伤,最多称一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必不可能招惹到仇家,他却对我如此关注,显然有别的原因,我甚至……怀疑与我父母的死有关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但也不算对。从一开始,微生万仞就在骗我,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甚至这一路上,他都在刻意引导我,落实我的猜测。即使那都是虚构。
后来那几年的事情,我未曾同我这三位同门讲,只是在某一天,我回到扶摇山,出现在院子里,林凤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也是第一个看出我的疲惫,他什么都没有问,而是和过去一样,问我要不要去看我离开前种下的花,春日已至,如今开得灿烂。师父没有问,柳拂衣和谢景宣也没有问,甚至一同忽略了微生万仞这个人,久而久之,我也觉得自己把他忘了。
微生万仞于我,谈不上爱,谈不上恨,我一直当这几年都只是一段遭遇,一次经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在离开那天之前差点死在他手上。
我至今记得他伸出的手,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我因此摔倒地上,那些长发垂落下来,落到我的身上,即使是在暖色的火光下,他的皮肤依旧苍白得像是不属于此地的鬼魂。他反反复复地质问我,却不给我回答的机会,好像只是在逃避,他不停地问,你要走了?你是不是想离开?你是不是想走?他看起来愤怒又慌乱,分明是生死存亡关头,我却忽然意识到他看起来像要哭了。
真是奇怪。我忽然不想反抗了,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们都像个笑话,他编造出谎言,为了我至今不明了的目的强行留下我,而我在明知道他有诸多破绽、毫不可信的前提下却还是因为那一点可能性选择跟他走,所以我没有挣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平复自己剧烈的呼吸,看着他逐渐泛红的眼眶。那是我第一次称呼他的全名,我问他,微生万仞,你为什么要露出这样的表情?骗我的人是你,想杀我的人也是你,错的分明是你,为什么却是一副被我伤害了的表情?
他的手开始颤抖,在我平静地询问下,他闭上眼睛,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对他毫无利用价值,最多算是个逗乐的宠物,可我毕竟不是动物,不会摇尾乞怜,有自己的亲人与朋友,所以我想要离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手里握着的匕首是许久以前林凤送我的礼物,送给我的那天我不客气地要求他再送我一根他的孔雀毛,他倒是欣然同意,反复强调这是他攒了一年的钱才买来的,我也因此一直留在身上。这匕首轻巧灵便,尽管我至今不会用,但仅仅是握住它,往前一刺,扎进心脏,这并不是难事。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匕首,刺进微生万仞的身体。
忽地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直到眼前的一切被泪水模糊,我再也看不清他的样子,我才发现我哭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或许真的很想他,原来我也会因为他的离开而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