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吉商店街是一条位于京都市,昭和2年成立,由60个中小店铺组成的小型商店街。每间店铺的人都是熟识,互帮互助着度过一年又一年。
可是,繁荣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时代变迁,人吉商店街也走向了衰退,不少店铺都出现了营业危机。
1964年的7月,生活协同组合会决定:如果到10月底,本商店街的销售额仍不达标,就要彻底解散,并在这里建造百货大楼?!
这可是大危机!该怎么办呢?!
【创作交流群:643560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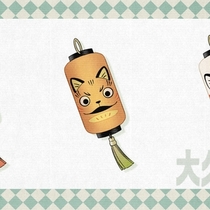

//加班之中极限滑铲……
//精致哥斯拉海报在悠凛那里:https://elfartworld.com/works/9485124/
//本次滑铲含有一些未知的东西。
清晨七点,小张太郎翻身滚到冰凉的地板上清醒过来。和往常并无什么差别,他半睁着眼睛洗漱,下楼的时候仍然浑浑噩噩,最后一脚踩空,在摔下去之前总算被悠凛拽住了后领,方才避免了脸部着地的惨剧。
随后,悠凛便在二楼的沙发上坐下,豚豚不知道躲在哪里,地板上的茶茶伸则了个懒腰,跳到她的双膝之上蜷缩起来,同样是半睁着眼睛。
“门口有很多垃圾,还有昨晚的那些,我先去处理一下哦。”
小张在一楼喊道,他先是花了点时间打扫店内的环境,紧接着,便一手拎起需要处理的垃圾走出门外,将近四十分钟后才回来,将店里的灯光点亮。
八点三十分,小张将豚豚和茶茶的早饭端出厨房。炖烂的鱼肉白嫩嫩地拌着搅碎的熟内脏,在两个画着诡异图案的陶瓷小碗里堆成小山,顶端洒了些木鱼花,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豚豚扑过来便卷走了一口。
厨房内仍有咕嘟咕嘟的声音,似有若无的香气开始急不可耐地往外飘。小张放下猫饭,转身回去,再出来的时候便如夜间居酒屋的服务生一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姿态“端”——或者说捧出了三个托盘。
他将这些东西潦草地放到悠凛面前的小几上,在悠凛的注视下,又手忙脚乱地重新摆放。
首先是两碟酱油白豆腐,切成大小正好的方块,酱油淋了满头,颤颤巍巍地顶着一身翠绿的葱花,好似将将从冰箱里取出来一般散发着微薄的凉气。
接着是热油喷香的煎秋刀鱼,几处花刀将焦香的鱼皮切开,露出柔软而饱满的粉白色鱼腹,盐粒被均匀地洒在上面,此时看来仍未完全融化。
最后便是昨晚便已炖上的味噌鱼汤,用来炖汤的鱼已经入了两只猫崽的肚中,加了味噌之后,汤色奶黄而醇厚,切成小块的汤豆腐、海带漂浮其中,其余的葱花、虾米、木鱼丝,便一应皆是作配,稍尝一口便是鲜而回甘,犹有余味。
待到两碗雪白的米饭亦安稳地放到小几两端,小张方才坐下,将筷子递给悠凛。悠凛与小张同一时间合掌,喊出一声重合的“我开动了”,室内才安静下来,除了豚豚索要食物的叫声以外,一时无人说话。
半小时后,小张将碗筷收拾到厨房,他要在厨房内完成一应的清洁工作,悠凛则在这段时间内回到柜台,处理那些“对小张来说有些太过超前了”的文书类杂物。当小张全部收拾好,洗干净手回到一楼时,悠凛要做的事情也基本上告一段落。柜台上只留下她那顶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宽檐帽,漂浮着大丽花与小菊花的水池前,悠凛本人半倚在一把藤编的靠背椅上享受自橱窗洒进来的日光,披散的黑色长发搭在椅背后,像一块只应出现在富贵人家的上好洒金缎子。
小张便拿着檀木做的梳子,以及架子上成分不明的护发精油,走到悠凛身后盘腿坐下,开始给她梳头发。
十点钟时,小张出门倒垃圾。垃圾很多,也很沉重,皆因为擅自来找麻烦的百货公司,一夜之间竟多了那么多麻烦事。当小张气喘吁吁地撒上最后一铲子土时,那些碍眼的垃圾也终于全都消失不见,但愿今天不会再有更多的垃圾了,不是每一天都适宜处理这类大型垃圾。
小张在一个小时后回到店中,开始整理柜台,准备安排下午的工作任务。悠凛束起头发,戴上她的宽檐帽,不知道去了哪里,等到中午的时候,她才施施然从楼上下来,温和地提醒小张到了休息的时间。
十一点半,小张将两个人(以及两只小猫)的午饭从厨房里端出来。先是一碟酸甜开胃的柚子汁渍白萝卜,再盛上两碗和早晨相同的味噌鱼汤,最后端上来的则是金黄香甜的煎蛋卷,并两碗生鱼盖饭。醋渍的米饭散发出甜香,新鲜切出来的肥厚鱼片围着碗边堆了两圈,中间则堆满了色泽鲜艳的鱼籽和海胆,皆是小张托捕鱼为生的友人买来的平价海货。
午饭后是短暂的休息。下午一点,悠凛留在店内,小张则提着清扫工具出门工作,按照今天的排单逐次上门清扫。其间发生诸多杂事,不一而足,直到傍晚天色擦黑时,小张才重又回到商店街。
那时已经是晚上六点,他在路上买回了晚饭:悠凛喜爱的生牛肉刺身,各式各样的什锦蔬菜天妇罗,纸袋装的串烧小吃,还有罐装的啤酒、汽水,拎了满手晃晃悠悠地往家里走。他的手上还握了一束杂七杂八的野花,没有什么包装,也说不上来什么品种,就这么和那些塑胶袋子一起抓在手掌心,裹挟着夕照的金光带回了昏暗狭小的店铺之中。
二十分钟后,小张把带回来的食物与冷饮放在桌上,招呼悠凛来到三楼,打开电视一起吃晚饭。电视上正在播放山本富士子出演的爱情电影,小张看得津津有味,问悠凛喜欢什么样的类型,悠凛想了想遂答道,今天的生牛肉很好吃,小张能学习一下做法吗?
于是此话题到此结束。
晚饭过后,小张继续负责收拾、洗碗,这时间几乎不会有客人上门了,但他还是回到柜台前坐下,一边守店,一边进行一些自认为专业的手工活。悠凛在楼上看电视,没有下来,等她再次出现时,就能看到小张对着八月份的业务清单苦思冥想,专心地在海报上描摹一只哥斯拉。
差不多到了筹备盂兰盆祭的时节,本月业务顺势而设,秉持着清洁、舒心的服务宗旨,通灵家政推出了墓碑清洁——以及相应的一系列衍生服务。一旦说到盂兰盆节……
小张竖起拇指:有鬼,有亡灵,正是名副其实的怪物节!
八点过,小张完成了海报,在悠凛的鼓掌声中喜滋滋地张贴到店外,随后便关上了了店门,挂上了打烊的牌子。他计划剩下的时光喝着啤酒,不知道第几次观看他珍藏的《哥斯拉》录影带,当他向悠凛发出邀请的时候,悠凛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几分钟后他回到房间,便看到悠凛坐在最舒适的位置上等待他。
嘈杂的声音是在两个小时后响起来的。
小张看了看时间,和昨晚近似的时间,令人烦闷的垃圾开始大批量地出现在店铺后门。鬼鬼祟祟,蹑手蹑脚,更多的垃圾堆放在前门,有的甚至伸出手,试图撕掉他今天才贴上的海报,破坏他精心绘制的哥斯拉。
小张和悠凛交代了一声,下楼清理垃圾。
等到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垃圾全数消失。守卫了哥斯拉的小张在后院新种了些夏秋季节的花,松了松土,又浇了浇水,弄得脏兮兮的回到屋子里,立刻便钻进了浴室。
悠凛在外面记账,之前什么表情,等小张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表情。
深夜十一点,小张收拾好床铺,准备睡觉。悠凛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许还在店里,也许已经回了家。微醺的酒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他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睛,平静顺遂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间章-
【■※▒卍■※篇】呪い日々に・零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什么都看不见。
这并非一种隐喻的修辞手法,没有任何代指心灵或是神智蒙昧愚昧的含义,我什么都看不见,此为物理意义上的实质存在的,肉体的盲视。
我的双眼无法看到任何东西,就好像它并不存在,连黑暗都虚无缥缈得像是我百无聊赖的想象。有时我甚至心生怀疑,我是否还拥有“眼睛”这一类器官?但额头下方连带着内里神经的疼痛又常常警告我,我不应当产生这样的怀疑,我的眼眶里存在着一对触手可及的眼球,它们是真实的,绝非我的想象。
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周遭的一切都变得异常敏感。这也不是指我本身,而是环境产生了异变,空气不再平静,山间的水流由缓慢变得急切,就连院子里时有时无的气味,都变得经久不散,仿佛要永远在这里扎根下来,非得像这对眼球一样逼迫我承认它的存在。
对此我保持了怀疑的态度,我的父亲很早之前就评价过我,固执己见,冥顽不化,不会听从任何人友善或仁慈的建议。他们不明白我的主意都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什么人的指点,或者,又是从什么样的书籍中学来的?
但这个问题我也很难回答,无论他们怎么追问我,我都找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因为我不读书。
在那段我无法睁开眼睛的日子,烦人的噪音充斥着我的耳朵,但是我对此毫无办法,且哪里都去不了,便只好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里。榻榻米虽然散发出竹制的草本气息,但实在难以盖过院子里的气味,我便尝试拜托好心前来照顾我的奶奶点上家里剩余的熏香,虽然有些陈旧,但总比令人难受的臭味好得多。
白天我只能发呆,凭空想象一些无趣的生活琐事,晚上——应当是晚上,算起来是每日第二顿饭食的一段时间后——则会有人到我的房间来,和我聊天,陪我打发时间。
我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怎么安排的日程,谈话的时间定在夜晚,这是什么地方才有的规矩?不过考虑到我许久未见他们二人,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也说不定,来陪我说话的人或许并非得人授意,有可能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也可能仍然是我想象中的某个形象,例如山里的樵夫,打鱼的渔夫,或者路过此地没事可干的学生,反正我什么都看不见,是什么样的人都无所谓。
我只是和他们聊一些没有内涵、无甚趣味的话题,时间会在这样的对话中逐渐推进、消散,等待第二天来临时,双眼的疼痛或许便会消散几分,进而变得麻木,笼罩上“一切都会好的”这种自我欺骗的幻梦。
但是到了第二天,一切仍然像是没有终结一般行进,循环往复,比此前那些我不得不做的功课还要烦人。不过相比较而言,不用做功课总算还是好上一些,只是之后应该如何?我却一点也想象不出来,未来我还需要完成更多功课吗?还是再也不用做这等毫无意义的小事?
即便到了夜晚,也没有人回答我。
我那时便是如此急切地期待着痊愈的那一天,尽管我什么都不想瞧见。
你瞧,我现在几乎想不起来那时候的事情了。但要是到了夜晚,当我重新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曾经陪我说话的人——应当是,他们找到了入口,便有可能重新找上我。他们和我聊天,我只能当那是做了噩梦,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把那时候的事情讲给我听。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但他们永远记得,于是,我便因为这些没有意义的谈话,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时候的事情。
那是什么样的地方?阿寒湖边,他们叫它雪雾山,当你顺着公路……不,根本找不到公路,它在一个很深很深,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
只是无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你要知道,我完全、压根、一丁点都不想瞧见。
为什么我非得亲眼瞧见不可呢?
在遥远的某个过去的午后,某个山坡上,低矮的草丛被太阳晒出微醺的热度,风拂过树梢背面的阴影,年幼的阿多尼斯•布鲁斯鼓起脸颊,靠在他的哥哥,威利姆•布鲁斯身边,对着自己手中歪歪扭扭的泡泡棒吹了口气,于是透明液体膨胀、鼓起,摇摇晃晃的飞向空中。
泡泡在他们的目光中随风漂浮,然后在触碰到天空之前破碎。
“这应该是目前做过稳定性最好的配方了吧?”威利姆把手搭在阿多尼斯的肩膀上,看着他用金属棒搅和杯子里泛着泡沫的液体。
“差不多,回头让爸爸看一下。”
泡泡顺着风从山坡上滚落,将他们俩的视线一同引向远方,那蜿蜒的,消失在低矮房屋中的公路,往后是他们居住的独栋,往前,是父亲回来的方向。
他们数着来往的车辆,当太阳半没入地平线之下,厚重云层的阴影压在屋脊之上。当熟悉的车牌印入眼帘时,阿多尼斯发出一声欢呼。
“今天是单数,我赢了。”
“好吧,我早该知道不该和你赌这些,好运的小子。”
威利姆抱怨着,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扔给他,随即从草地上跃起:“走,去接老爹去。”
风带来一股让人怀念的味道,缠上了阿多尼斯的脚踝,拖住了他起身的动作,仅仅迟疑了一瞬间,威利姆的身影就已远去,他看见那辆属于他父亲的湖蓝色小汽车停在院子里,他的哥哥迎了上去。
之后父亲会打开手提箱给他们看他带回来的礼物,然后带着未拆开的礼物去找他们的母亲,礼物盒里装的是一支玻璃吹成的玫瑰。
他知道这一切……因为这是他的过去,他现在应该呆在远东小岛的某个阁楼上,而不是英格兰的山坡,被夕阳熏染的天空之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梦。
当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察觉到某种冰凉的液体没过他的脚背,潮湿的腥味瞬间涌进他的肺部,几乎让他窒息。
不是英吉利海峡,不是大西洋东岸,这是,日本海,宫津湾,他苏醒时的那片沙滩。他的舌根仿佛又尝到了那个夜晚里苦涩的海水的味道。
自然的,或者说命运一般的,他抬起头,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威利姆,他身着海难发生那一天所着的靛蓝色西装,站在比阿多尼斯更靠近深水区的地方,海水没过了他的膝盖,浪花卷起细碎的泡沫拍在他身上。
阿多尼斯只觉得心脏膨胀起来,如同不稳定的泡泡一样一触即碎,他几乎忘记这是一个梦,想要走到威利姆的身边去,去问他到底在哪,问他过的怎么样,去拥抱他,如同年少时他们所做的一样。
然而这只是一个梦,他的身体拒绝听从他的指挥,木然的站在原地。他看见威利姆像是说了什么,风从他们俩之中呼啸而过,翻起层层浪涛,拍击在海滩上,淹没了威利姆的声音。
在阿多尼斯搞清楚威利姆说了什么之前,风势弱了下来,轻柔的抚过他们的身体,然后,像带走一片浪花一样,吹散了威利姆的身影。
布鲁睁开眼睛,仰躺在床上,望着空白的天花板,呆了好一会,才缓缓起身。
从出事那天算起,已经一个月余,他依然没有威利姆的消息,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水野屋分给布鲁的这个储物间,大约有8个平米,之前听佑里歌说,这个大小在日本被称为“四叠半”。现在那些杂物被堆在另一侧,靠墙的一侧铺上了被褥作为他的床,最初睡得他腰酸背痛,如今也慢慢习惯了。
“いただきます。”
完成了餐前祷后,他照葫芦画瓢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念了一句,别扭的拿起了筷子。
食物……也渐渐开始习惯了,当他意识到食物被臼齿捣碎后谁也没法分辨这是来自英格兰的土豆还是来自日本的梗米,他就成为了整个水之屋吃饭最快的人。
在他放下碗筷准备起身时,水野屋 前叫住了他:“对了,布鲁,今天上午不需要看板,听佑里歌说你已经差不多熟悉这条街(人吉)了?”
布鲁瞥了眼佑里歌,后者正专注的挑出铺在烤鱼底下的青椒,并且试图趁着水野屋不备塞进他的盘子里——或许已经成功了几次,因为水野屋那盘烤鱼的鱼腹可怜的隆起,杂乱的青椒丝从烤的焦黄的鱼皮下漏出来。
这副光景让他忍不住露出一个微笑,于是水野屋立刻顺着他的视线发现了佑里歌的动作,操起筷子拦住了她。
“喂!说了好多次都要好好吃干净吧!”
佑里歌鼓起嘴巴瞪着水野屋:“我妈在的时候从来不管我那么多!”
眼看着两人马上又要开始一轮日常的斗嘴,布鲁将话题拉回正轨:“说起来,前你刚刚准备和我说什么?”
“啊,对,”水野屋顿了顿,啧了一声,显然意识到他是在给佑里歌打掩护,但还是接着说了下去,“最近不是要****了吗?我准备了一些新商品的传单,这里有一些需要上门取衣的客户,你去取衣服的时候顺便发一下传单吧。”
或许是布鲁的迷茫太过明显,真琴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角,缓慢的重复了一遍那几个音节,不过就算是他们三人接力解释,也仅仅让布鲁搞明白,他们在说一个和死者有关的传统节日罢了。
“所以你让我准备的那些肥皂原料是为了这个?”
“啊……嗯,”水野屋显得有些意兴阑珊,一边说话一边把青椒夹回佑里歌盘子里,“随便做点茄子啊黄瓜之类的肥皂进行节日促销吧,唉,可惜没有做出来会动的架子安在底下,那才是真的酷。”
那个酷在哪里?
到底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布鲁接过水野屋列好的清单往楼下走去,听见背后传来水野屋对着真琴纳闷的低声询问。
“他刚刚是不是翻了个白眼?”
“咦,谁?布鲁吗?你看错了吧。”
水之屋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真琴说之前这里会写着每日料理和清洁当番,慢慢的变得随意起来,等到他来到这里时,它已经变成了像留言板一样的东西。
大家会随意的写下自己准备去买的食材,在黑板上隔着时空交流。今天黑板最上方是真琴娟秀的字迹,她购买了些小麦粉和蔬菜,准备做乌冬面。
【但是我想吃咖喱】
混着一些平假名的字迹,应该是佑里歌留下来,后面画了个生气的小薰。
【哦,那我去买点牛肉,正好昨天好像还剩了土豆】
水野屋的字迹很好认,他留下的粉笔痕更重,收笔时棱角分明。
没有多加思考,布鲁拿起粉笔,匆匆留下了一句【咖喱乌冬面,听起来很有意思】,便提着包出门了。
死者……吗。
或许是因为月初那些闹事的混混,又或者是因为这个节日,他走在这条街道上,很明显的感觉到与上个月略带躁动的氛围不同。尚未完全复原的街道,行人沉寂的脚步,无不传达出那股不稳的气息。
他出神的思索着,机械的做着水野屋交代的事,脑子里却在想着完全不想干的东西。
这一个月来,他尽力去避免想象那个糟糕的可能性,但是当一个人独处时,杂乱的思绪无所顾忌。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开始祷告,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绝不能再失去自己。他蜷缩起自己的灵魂,让福音隔绝了一切杂音。
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意外的平静,既没有想到可能的不幸,也没有把自己投入信仰之中,只是单纯的,固执的回忆。
他在回忆昨天那个梦里,威利姆最后说的话,他没有听见,但是他看见了口型。
那到底是“好运的小子(Lucky boy)”;
还是“再见(Goodbye)”?
布鲁回到水之屋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早上带去的传单一个不剩的发了出去,包里也妥帖的装好了客人们送洗的衣物,这显然是一切都在良好运作的信号——如果他没有看见站在水之屋门口的那些人的话。
他认得那身制服,是不远处那个警察局的人,他站在门口当看板时,偶尔会看见他们在这条街上巡逻。
【主啊……】
那两位穿着警服的人很快注意到了他,他们有些不自然的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在他靠近时,摘下了帽子,朝他搭话:“请问,你是阿多尼斯•布鲁斯氏吗?”
他在心里发出了一声近乎绝望的叹息。
“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可能属于你的哥哥,威利姆•布鲁斯,能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辨认一下吗?”
【主啊……请予我慈悲吧……】


*盂兰盆节创新菜谱:冷汤素荞麦面
随着拉门声步入店铺的年轻人,有着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庞。他先是目光巡视了一圈店内,在店员的欢迎声中浅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挑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坐下。
“可以先看看菜单,墙上的这些都是可以点的哦!今天的特供菜是冷汤素荞麦面,堪称炎炎夏日的降暑利器!”
真辉一边给隔壁桌子上菜,一边热情地对这位初来乍到的小哥推荐。今天龙之介请了假,他一个人要忙整个食堂的招待、跑堂与布菜工作。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他跟龙之介的现学现卖,他还挺喜欢的,反正“发明人”也不在,他跟着说也没问题。
“选好了就告诉我哦——”
放下一杯冰水,真辉又去收拾刚空出来的吧台。年轻的男性偏偏脑袋,开始认真研读墙上贴着的菜单。纸条新旧不一,不少都泛起了黄,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菜品和价格,旁侧还挂着块写着今日特供菜样的小黑板。
现在是比通常饭点略微晚一些的时候,这家食堂基本每张桌子上都坐着人,空气中充斥着各类饭肴的香气,男人用食指轻敲桌面,看上去陷入了选择困难。
“怎么样?”重新回到男人身边的真辉问,他的口气多少有点不像正式的服务员,不过他意识不到这点,食客们也都不在乎。
“或者你也可以点菜,食谱之外的也可以做。”
男人的表情亮了一下,他语气温和地开口:“什么都可以吗?”
“唔,差不多?”真辉用笔戳了戳后脑勺,“你想吃什么?”
“宗之说这里做什么都好吃,推荐我来的。我好久没有吃鱼了,有什么建议吗?”男人胳膊撑于桌面、下巴搁在交叉的双手上,面带微笑,“比如黄狮鱼刺身之类——”
“咯噔”,是铲子磕在铁锅上的声音,这突兀响起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大声交流的常客声中。
“咱这儿没这鱼呢!换一个呗?”
真辉爽朗地开口,继而转身对着料理台大声询问:“幸二,今天还有什么鱼吗?”
“只有竹荚鱼,不过刚才都卖光啦!”幸二抬手用胳膊蹭鼻尖上的汗水,眼珠一转接着又说,“不过还有‘那个’。”
“哦哦——‘那个’啊~”真辉也跟着转动眼珠,显出几分狡黠,“你运气真不错,这本来是熟客送给我们自己尝鲜的,都不在菜谱上!不过看在你是第一次来、又是宗之小弟介绍的份上,特意做给你吃吧!如果觉得好吃今后要多多光顾我们家哦!”
男人像是被两名少年打哑谜的模样逗得有些忍俊不禁,他的笑意更深了,用右手的大拇指蹭左手虎口处的皮肤:“那还真是谢谢你们,也多亏宗之弟弟了。还请务必拜托给我来一份‘那个’,以及再来一份今天的特供饭。”
“好嘞!”真辉在小本子上扒拉了两下,随手把笔插进围裙的口袋,“今日的隐藏菜单与特供饭各一份——”
男人点过餐后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了材料,他时而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时而陷入沉思,当他思考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去摸手腕上的那只表,用骨节分明又修长的食指与拇指绕着表盘转动。绢代将全部都尽收眼底。像,实在是太像了,那两颗痣所在的奇特位置,她曾经也认识这么一位故人。她的心脏怦怦跳,从看清那男人的面容起她的心脏就怦怦跳,这种奇妙的、混杂了不敢置信与疑惑的心情在男人说出“黄狮鱼”的瞬间攀抵了巅峰。
“绢姐,能麻烦你帮我抹盐吗?”
幸二一无所知,只当刚才锅铲与锅子发出的噪音是正常现象,甚至根本没往心里去。绢代抬起眼睛的同时已经挂上了笑意,她乐呵呵地接过已经被穿刺好的若鲶,轻轻拉开它们的鳍涂抹上粗盐。她的余光瞥见幸二正在准备炭烤的小炉子,又扫视着低头看材料的男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谁也不会再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就算是“他”也会忘记的。在自我宽慰下,绢代的心逐渐向下沉,终于回到它应该在的位置。
没等多久男人点的饭就上齐了。他将铺在桌面上的报表拢好、依次收回包里,同时对布菜的真辉道谢,然后才礼仪周全地双手合十轻声说:“我开动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了餐桌“半壁江山”的的冷面,健康的深色荞麦面被埋在冷却的高汤中,上面一层满满当当摊着豆芽和切成丝的黄瓜、胡萝卜、鸡蛋以及木耳,色彩缤纷鲜明诱得人食欲大发,另外还有半颗正在流淌汁水的溏心蛋卧在正中央。
接下来上桌的是今晚“重头戏”盐烤若鲶。这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佳肴,金黄焦香的若鲶头尾齐全浑然一条,除了盐巴之外无需任何调味点缀。酥脆的头部与柔软、鲜嫩的鱼肉相辅相成,略苦的口感在反复咀嚼后又迸生出回甘的香甜。腌菜与白萝卜泥负责唤醒沉溺于享受中的味蕾,时不时吃一点爽爽口再接着品尝鱼肉又是与先前不一样的、层次递进的美味。
男人品尝的同时发出喟叹,他半眯着眼睛赏味,看起来满意极了。站在吧台后侧的幸二用毛巾擦着手,他的父亲生前喜欢欣赏食客品尝自己制作的料理,将它视为自己的追求与乐趣。幸二也乐得如此,还能有什么比令食客满足更有成就感的吗?
“真不错,虽然来之前已经知道很好吃了,但真是意料之外的美味。”男人欢快地说,他还称赞了腌菜,并表示腌菜好吃的店做饭绝对值得信赖,这也是他率先品尝的第一道菜。
“要不是被介绍来,真是容易错过呢,没想到在侧路上还有这么一家店。”
“是吧是吧,”真辉与有荣焉,他立刻就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跑堂也能兼顾过来了,“好吃就多吃点!”
“啊,这么说,我听宗之说,咱们店之前推出了全豆宴?听起来好厉害,搞得我也想试试了。”
“可不是!我当时还在想豆子哪能做这么多菜啊,可我们还是做出来了!不过那分量可不少,你还能吃得下吗?”
毫无疑问用评估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男人,真辉心里有些犯嘀咕,这人看起来也不胖啊?
“那还是有些难度的,不过只试试一道菜应该可以?好像是之前七夕的特供——啊,真不好意思,都是特供了,现在也没了吧?抱歉,忘了我说的话吧。”
男人立刻表达出愧疚的神色,无论在任何人看来他都正在陷入自责。
“应该可以吧,又不是什么麻烦的菜。”
真辉大手一挥,开开心心地去后厨帮男人加菜。男人在等菜的间歇无所事事,貌似无聊地环顾了一圈食堂,对每一个对上视线的人点头代替打招呼。
共同的喜好极易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常客们很快就因为得到了认可、并打心底为食堂受到喜爱感到开心,大家也纷纷对男人表示了亲近。
“小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给你说千代的咖喱味道特别独特,其他地方吃不到的!有机会你一定要试试哈!”
“咖喱?听起来就很不错,我最喜欢了,等天气凉一点了我一定要试试!”男人兴致勃勃。
“还有老板娘亲自酿的梅子酒和米酒,哎呦,配上下酒菜那才叫一个绝!”
“是吗,可惜我不太喝酒,不过量少一点也没什么吧。等哪一天手头的工作都处理完了,我再来喝一杯,到时候我请客,大家可不要拒绝呀。”男人稳妥地回复。
绢代低垂着眼睛,她看上去依旧在忙厨房的事情,但却竖着耳朵将大家交流的点点滴滴全部收集。
“久等咯——‘番茄冷豆腐’,轻慢用。”真辉将红白相间的菜肴摆放在男人面前,有些得意地蹭蹭鼻子。来吧,问问为什么这道菜和七夕沾边,这样他就可以讲讲创意,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多么用心、这里又是多么值得光顾了。
可是男人却只是说:“原来如此。”
“是采用了‘红叶桥’的典故吧,或者‘鹊桥’,真有趣呢。老板娘千代真的是蕙质兰心呀!”
真辉愣了一下,心直口快的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提醒,就已经有常客调笑了起来:“小哥你还不知道吧,虽然叫‘大众食堂千代’但老板娘实际上叫绢代!以后可要多来几次,千万分得清人啊,你说是不是,阿绢?”
绢代露出了一个极为标准化的笑容,她攥着抹布,关节都握成了白色。
“山本先生,您就不要打趣新人啦,”绢代提着一瓶酒出来,走到山本面前为他斟了一小杯,“也是我们店的招牌太有迷惑性,大家都有第一次嘛。”
山本哈哈哈笑了起来,他白得了酒心情愉悦,已经不准备再拿这件事说叨,但新人却猛地站了起来。
“绢代?你……是铃木绢代吗?”
笑容犹如焊在了绢代的脸上,她不敢太用力捏酒瓶,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当真抓碎了它,但她又随即自我嘲讽这是不可能的,如同她想完全逃离过往一样不可能。
眼前的男人就是证明。
深呼吸,绢代努力做出回忆的神情,虽然在她看到那两颗位置古怪的痣时,就险些快要回忆起男人了。
“是我啊,栎我久都!”
好吧、好吧,不论如何……
“哎呀……真的是栎君?”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认识的人?”
得到回应的男人激动地双手按在绢代的肩膀上,店里的其他客人开始交头接耳。幸二搞不清缘由,但还是径直来到绢代身旁,我久都见状立刻收回了手,他甚至整理了一下领带,再次恢复彬彬有礼的微笑模样。
“当年你搬家后我们就断了联系,真没想到还能再遇见你……这位是?”
我久都的目光从幸二过度到绢代的无名指,他佯装震惊地问:“难道是你的孩……”
“绢姐是我嫂子。”幸二主动回答。真是的,哥哥怎么就留下孩子呢!哎呀不对,有了孩子绢姐不是更伤心嘛,还是现在这样更好。
绢代注意到了我久都的小动作,从男人自报家门开始,这个名字就好似一把钥匙,开启了她特意尘封的全部记忆。她当然明白男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我久都君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还是邻居呢。”
“那不就是青梅竹马嘛!”山本起哄道。
幸二的眉头挑了起来,他有些不悦,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如此。
“当年搬家后我也尝试联系过你和大家,我有写过信,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呢!看来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就让我来请在坐的各位都喝一杯吧!”
亲自给喝酒的客人们都倒上了酒,店内的气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绢代知道不过明天她有个青梅竹马的事情就会传遍整条商店街,人人都会知道他们的关系。这种小把戏她尝试过,当年正是他们一起这么做的。
关上拉门,绢代走出食堂,不出她的意料,我久都已经候在了门口。她猜他应该有很多话要对自己说,特别是指责的。她等了会儿,只是与对方互相直视。
片刻后,绢代笑了,我久都随即也笑了起来。先前几乎凝固的气氛再次流动。
“谢谢。”绢代轻声说。
谢什么?谢对方在所有人面前没有拆穿自己?配合她做好所有的准备与铺垫?这简直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但我久都只是说:“我来把你忘了的东西还给你。”
他将两样东西放在绢代手里,最后说:“下次见,小月。”
绢代低头,那是块难以看出模样的木雕,还有一枚之前试胆大会的奖励硬币。
我久都走在夜晚的小路上,他感到愉快且满足。他的胃轻飘飘又沉甸甸的,有种醉了的微醺感。他当然记得自己未曾喝酒。
“阿姨,你拿着的东西太沉了,我送你回家吧?”
百坂光一如既往地帮助看得到的、需要帮助的任何人,他站在昏暗的路灯下,把中年女人负着的重物扛在自己肩头。
我久都看也不多看百坂一眼,只是与他擦肩而过,哼着小调走进黑暗里。
今日菜谱:盐烤若鲶、冷汤素荞麦面
炭火的烧烤不仅带来了酥脆也留下了余香,无需过多的调味装饰,只是盐就可以将“清水之女王”的美味凸显得淋漓尽致。再搭配爽口降温的凉面,看似朴素但却绝对不简单,多重色彩的食材组合给予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冲击!
你也快来“大众食堂千代”品尝一下吧~!
TBC


華乃音所说的这家百货商店位处四条,在这京都,可算得上是最繁华的地方了。我们二人还没入内,便能听到西洋风的流行音乐朝外流淌。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至于为何而来我并没有过多过问,毕竟是華乃音,她总是想到做到,对她来说,做出这样的举动本来就不需要理由。姑且以现在的情况的状况推论,是我的状态实在是过于糟糕。
似乎是避免被人群冲散,她小心地拉住我,有些急冲冲地朝着内里探去。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丰富,到是让人有些看花了眼、但大体上来看,百货商厦以种类分区,不同的商家会按照划分的区域格子售卖着自家的商品。
而现在光顾的区域,卖的都是些装饰相关的小物件。
“哇,快看,是在杂志上见过的眼镜牌子!好像宣传图是当季的新品!”
華乃音抬手指了指面前的柜台,但没有太凑上前去。
我对所谓的“时尚”并不了解,只是狐疑朝她说的那边看过去,“但是我们没人近视吧?要过去看看吗?“
“不是啦,也有没有度数的墨镜和装饰用的眼镜。带上眼镜,也会给人成熟的感觉对吧?“
華乃音踮着脚,朝着稍稍高处的地方看了过去,“你看,那个小姐带的就是这次的新品,是不是很有大人的感觉?不过真漂亮啊……”
“漂亮?是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吗?"
"恩,你看那个……“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但并没有朝那边走过去的意思。反倒是顺着楼梯上到了二楼。二楼是女装的专区,我以为她会在此多多停留,专门慢下脚部,但好像她对此不以为然,只想匆匆略过。只是发现我动作慢下来,才停下了脚部。
“不用停下看看吗?应该会有和刚刚一样,在杂志上看过的时尚衣服?”
我朝着其中的一套指着,话虽如此,自己对于这种碎花的连衣裙或是有着厚垫肩的西服外套实在是不太能了解。
華乃香回过头来,只是摇了摇头,抓着地手又微微用力,把我往前拉扯。
“没关系的!之后我会和香药姐一起来的。这次就来帮竹音哥看东西就好,而且就算什么都不买,只是来逛逛就很开心了。”
“话虽如此,我似乎也没有什么需要新购入的东西。”
“恩——男士的领带之类的呢?或者是正装,在或者是新的草履配饰…“華乃音列举了一堆,但好像看出了我对此没有什么兴致,只好选择作罢,开始左顾右盼地看起了女装。
我们两人站在这通往楼上的阶前,而谁都没有迈出新的一步。
只是选择了适时地放开了手。
不过我终将要放开那双手的,来往于这里的家庭很和情侣很多,免不了想到之后,她将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景象。想起之前父母所寄来的信里也常常提到催婚之事,或许离那日并不远了。
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些愣地出神,想要抓住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不过也确实什么都没有,只是空气和痕迹在弥散消失。
身后传来了熟悉地气息,被人从后面用力抱住,然后慢慢松开。再从身后慢慢探出她的脸庞。
“别发呆了!真是的……我看了一圈回来,竹音哥你还在这里傻乎乎地站着呢!”華乃音做出一副生气样,但一下子又恢复了先前的担忧。
“待会儿我们再去顶楼看看游乐场,然后再家庭餐厅吃个饭……”
“去吴服店看看,我想好要买什么了。”
虽然为时尚早,但还是送些首饰给華乃音吧,送个同她发色与这身衣服所相称的发簪。
似乎是误会了些什么,她的表情变得雀跃起来,又一次地拉着我的手,去往了专门的铺子。一位优雅的女士接待了我们,小声而亲切地询问着需求。
是在是分不出什么哪些种类,只好将所有的问题抛给对方。
“那样的话,最近细工花饰卖的很好,您看看这几款如何呢?全部是由匠人手工制成的、不过您想要送给谁呢?面对不同地客户群体,适合的颜色风格都有些不同啊。”
虽然不确定推荐的是面向谁的,但是艳丽而亮眼的红色映照在整个眼眸。
是红色与粉的梅,透着玻璃制地柜台也能清晰看出正绢的纹路。
“这是我们这里的人气商品。”
“啊,麻烦换一下。她并不太适合这种颜色。“
紧接着,展示的是紫色的菊。“紫色是高贵的象征。虽然也没有那么艳丽,但也很称人。而且这个紫色颜色很多人都适合佩戴。”
回复对方的仍是摇头。
这回答似乎让店员也有些犯了难。“恩,是给稍微可爱一点的客人准备的吗?那样的话我们还有珊瑚色和朱鷺色混搭的款式。如果还不合适,或许去我们店的本铺更合适,那边的种类会更多一些,这边准备的都是些热门款啊。”
我没有回答对方,只是朝着華乃音的方向看去,对方倒也心领神会,拿出了由一片叶与花组成的发髻。淡粉和白色的樱花在叶和淡紫葡萄与奶油黄的小田卷衬托下显得格外可爱。
“那么这款呢?和那位小姐的风格很称。也是最近的人气产品,就算是没用过这类饰品的客人也能够轻松搭配。“
似乎是在一旁等着不耐烦了,華乃音在柜台看了一圈后又凑了过来好奇地盯着,眼里写着尽是困惑。
“恩——可爱是可爱,但是这个是给谁的呢?啊,难不成竹音哥你交了女朋友了?是谁,我有没有见过?用这种风格的发簪感觉会是年下的孩子。嗯嗯,想不出来……”
我并没有回复对方,也没有做出解释。只是叫店员将东西打包好,在華乃香慌慌张张地寻找那优惠券地时候,就结束了付款。
“恩。要送人的祝福,还是这样圆满的比较好。”我轻轻拦住華乃音,小声说道。
華乃音好像有些担心价格,嘀嘀咕咕了两句,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但毕竟是给她以后准备的,我想名家的优品才算是过得去。但,这件事我还需要瞒下来多久呢?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在休息的那几天里是不是有旁侧敲击地催促,想到这些又有些耐不住神来。就连之后在家庭餐厅吃了些什么,在楼顶的露台游乐场玩了些什么都有些记不清了。
回去地路上,我喊住了她。
分开的双手又在一起被牵起。我有些恍惚,这一幕好像和七夕那时相似,只是换了地方,夕阳为人蒙上了黄昏色的纱。
“怎么了——?”華乃音抬头望向我,不太理解这番举动的意义。
我将刚刚打包好的袋子递了过去。她惊讶地看着,又一次地抱了上来。
“啊,居然是给我的吗!谢谢竹音哥——“她欢呼地接过,似乎是因为刚刚的困惑被解开而显得愈发高兴了。
“但平常的话,不都是送些吃的玩的过来吗?怎么这次买这么贵重的东西?生日礼物也拿到了,完全~想不出什么需要送礼的理由啊?”
或许没有比现在说出口更好的时机了。
“这个,是给你约会时候准备的东西。”
“约,约会?”她惊讶地有些手舞足蹈。
“恩。父母之前向我问过,似乎……再没有动静,弄不准会让你相亲或者是直接订婚了啊。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心爱的人就是了。哎呀,倒也不用那么正式,觉得想的时候,合适的时候戴上就好。不管做什么决定,哥哥都站在你这一边。“
似乎刚刚的内容给她的冲击太大,她甚至没有道谢和便匆匆跑开。不知是不是在夕阳的映照下,她的脸颊印上了微微的红晕。
在这恍惚之间,我好像也意识到,自己的琴音有何而来。所追寻的那阵风,究竟为何。
——那是写有人的,人の音。写有人与人羁绊的,温柔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