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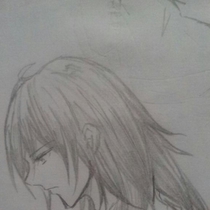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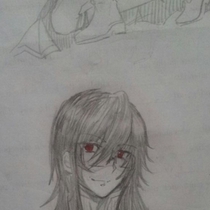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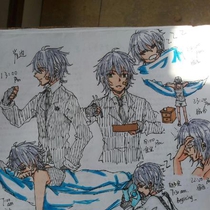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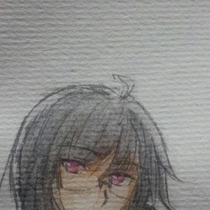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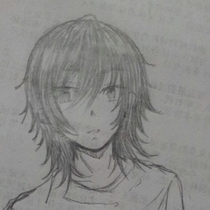
事情简直开始的莫名其妙。
李殳那家伙差点吓得我许久不犯的起床气旧病复发,真该庆幸房间里没什么凶器,他也没在我睡着的时候进来——否则我铁定把他当成那个梦里的奇怪家伙徒手掐死。
开玩笑的。在他用来历不明的钥匙开了我的房门,把我拖进房间并且占了我的床铺之后,我只有搬板凳坐在床边听他鬼扯,不时嘲讽他几句的份了。我们并没有聊多久,那种没有营养的话题简直让我煎熬,好几次我都想给那个像死了一样瘫在我床上的人一脚,结果都是无奈地看看天花板表示作罢。
最后李殳终于换了个话题。他说:“我们下去。”
去哪啊?我皱着眉刚想问他,还没出口一个字就已经被拉了出去。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什么也不说,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轻松。托他的福不久前差点被领去电疗,这回说什么也得问清楚再行动。我甩开他的手站在楼梯口死活不走:“先说明白这回要干什么。”我的药还留在房间里,这种状态跟他乱跑很危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幻觉。来自楼梯下的风吹的我脊背发凉。
他仍旧是烦躁地催促我走,不做任何解释。
两个人折腾了半天也没搞出点所以然,结果我耗不住跟着他去了一楼。接着他直奔休息室,休息室里那个柜子。
他在那个足两米多高的柜子前又是踮脚又是上蹦下跳的,还是一无所获。我在一边抱着手臂看他,李殳比我高上三厘米,他拿不到我肯定也拿不到,也没兴趣多做尝试。不过我比较好奇,柜子顶上到底放了什么。
“蹲下。”我没好气地命令李殳,并且抱着一种轻视他智商的心态坚持不给他解释。最后他还是乖乖蹲下给我垫脚,看着他那条干净的衣服我没忍心踩,于是借着他的肩膀够到了柜顶。幸亏李殳的力气还没大到可以一口气站起来,不然我肯定会撞到天花板。我抬起眼看着不低头就会顶到的上界限,心里暗自庆幸了一下。
柜顶放着一台老旧的留声机,别无他物。留声机结着蛛网,还积了不少灰尘,像是很久没有拿下来过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那家伙应该就是要这玩意吧。
我用手扯掉那些蜘蛛网,端住那台古董想要把它拿下来,掉以轻心的试了一下差点没拿稳。留声机还是很重的,我好好使了点劲才取下来。一手托住底部,我几乎可以预见那边袖口蹭上了多少灰尘——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脏。
我掸了掸灰尘,心满意足的看着那些灰掉到李殳脸上。爽。之前被吓和被拖下来的气消了不少。
下去之后我把留声机放在一边桌上,李殳从怀里掏出一张黑胶唱片,看上去和留声机一样有不少年头了。他很熟练地把唱片放好开始播放,我也安静下来想听听这唱片里有什么玄机。
一时间休息室里只有唱片转动时和振针摩擦的轻微声音以及外面的风声。我猜也就只有我和他每天发神经一样在病院里到处探索。哦,差点忘了,我们本来就是精神病啊。
正在我出神的当儿,留声机出声了。
是女人的声音和令人难受的杂音。那声音莫名的有种熟悉感,似乎在哪听过。那边李殳晃了晃脑袋,刚才听录音时他像是被魇住了似的不知道想些什么,我想问他这张唱片哪儿来的,又迟疑了一下改了口。
这个声音的确耳熟,和那个刚死不久的女病人有很大的相似度,我见过那个女人,那才是真的疯子。她癫狂地告诉过别人什么,但我没放在心里,已经记不清了。
本来她死了也倒和我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这一连串的奇怪事情放在一起看却有了什么端倪:疯子女人,不散的腐臭,不准进入的地下室,奇怪的梦……还有这张黑胶唱片。我隐隐感觉有一件大事正在悄悄编织。
“既然咱俩还算正常,就出去吧?”李殳向我提议。
我暂时没给他准确答案,而是反问了一句。他点头。
说实话,我越想越糟糕,心里那种惊疑警告我不要轻举妄动。这种事情不是简简单单逃出去就能解决的,我这样想,回绝了李殳。
逃出去被发现就是死,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能逃脱,我不想被处理掉也扔进那个恶臭熏天的池子。
出于自身安全,我没有提醒李殳我心里所想。
没等他再说什么,我转身就走。病院开始有人走动的时间已经快了,我不想被其他的任何人发现。走到楼梯拐角的地方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待在休息室里,盯着唱片。
真是造孽。我放轻脚步跑回房间闭上了铁门。
滴答,滴答,滴答。
我在延绵不尽的水声中转醒。那见鬼的水声恐怕又是幻觉中墙上蠕动的肉块缝隙里滴落的脓血。恶心之极。
趁着意识还清醒,我一边想着这次安眠药的药效差到家了,一边想要伸手到床头柜上拿镇定精神的药物——可是我动不了。手和脚都被结实的皮带捆缚着,绑得非常紧,几乎勒住皮肤扣进血管里,稍稍一挣动就会感到刺骨的麻痹感和血液不通的疼痛。
F**K。我暗骂一声睁开眼,看见的却不是想象中那个血肉模糊的世界。一切都很正常——又或许并不是,我奋力抬起仅可以自由活动的头吃力地看了看四周。
陌生的地方,自己所在的担架床在正中央。墙壁老久破败,头顶惨白的日光灯少了一个灯管,仅剩的那点灯光也不稳地闪着。房间正右侧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木质的桌子,角落的木料似乎是经过了严重的撞击,里面的木板起着毛边看起来很扎手。【这时候我不得不感谢一下那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神秘人没把我的眼镜拿走】桌子上放着奇怪的玻璃器皿,似乎是化学实验要用的器材,一堆横七竖八放着的试管中间有一个锥形瓶,瓶身有一个一角硬币大的洞,正不停的流着浅蓝色的溶液,水声也是溶液从桌沿滴下发出的。
房间里没有别人,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从溶液流出的速率和瓶中的余量来看,神秘人才刚刚离开不久。因为瓶子总不会平白无故自己碎的,对吧。
于是我试着用力挣了挣想要摆脱皮带的束缚。可惜动作太大,带着小轮的担架床一下子滑了出去。这回糟糕了,我想。一声巨响,床撞在了放在一边无影灯的支架上,撞倒了那个麻烦的大物件,我该庆幸的是床没翻。
继把我吓了一跳的事情之后,我从鼓噪的心跳声里听到了走廊外隐隐约约的脚步声。深呼吸,我努力让自己别太激动,房间又恢复了寂静。一定是刚才那个动静让那家伙听见了,现在正在赶来查看。伴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能听出那步伐的节奏忽快忽慢、忽轻忽重,显出虚浮的样子。有一双颓废的眼睛从门上的小窗试着往里看,接着治疗室的双开大门被他大力推开,门板摔在墙上的发出十分扰民的响声,簌簌掉下几块焦黄色的墙皮。走廊上一片漆黑,从这里透出去的灯光虽然微弱,可是足以让我辨识出走廊上纠结着肉瘤的墙壁和在地上积起浅浅水洼的血。
我看见那个人带着口罩、黑色的短发也仿佛很久梳洗过结着白色的污垢,穿着衣摆染血的白大褂,黑色皮鞋上沾着碎肉块和红色的液体。他右手攥着一把手术刀缓缓向我走近,那对眼睛疲惫不堪,下眼睑有着浓厚的黑色阴影,血丝几乎使他原本的瞳色被遮盖而看不出来,那些细小的毛细血管爆裂,血液在他的眼白上蔓延。
他把手术刀越握越紧,站在我身边蓄足了力气双手捅下来。
我本能的闭上了眼睛——
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我感觉喉咙本能的干涩,味蕾的感觉还是被药物的苦味占领。
做了一场噩梦啊,今天又和昨天不一样。
灌下一杯水之后那种苦味缓解了些,我悄悄靠近封闭房间的那扇大铁门,从门上的铁窗往外看。
走廊对面蹲着一个人,正看着我这里。
这件事把刚才噩梦中惊醒的我惊出一身冷汗,暴躁地踢了一脚铁门:“我靠李殳你在我门外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