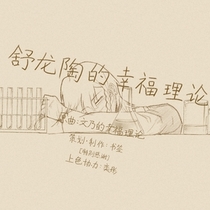他偷了我的翅膀然后飞走了。
对,便是这样。无论是非必需品的饭还是非必需品的酒还是非必需品的药,还是非必需品的其他,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睡到午后两点起来然后头脑放空地在角落抱着书靠了三个小时,才想起又是吃完饭的时候了。窗外的天空变暗了,在我什么都还没做的时候。
明明前不久才吃过的。我的厌食又严重了起来。
我没有病,可能是少掉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反而感觉自己轻松的很。正因为我轻得让我一时无法适应,所以我像氯化银——为什么是氯化银不是硫酸钡?——一样沉积在房间的角落里。我有点迷糊地想象自己一站起来,就会像氦气球一样轻飘飘地浮起来,“气球的重力忽略不计”。我擦掉了那个向下的箭头。我丢掉了我的翅膀。至于有没有丢掉更多,我让自己拒绝思考。
这句话我只敢当作一个诗歌的象征来讲。流亡在远方的人,是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再回去的了。
究竟要多少剂量才够把这样大的一个人麻醉住?上次把透明的吗啡倒在玻璃沙漏里,我跟他毫无征兆又顺其自然地谈到这个。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假如他唱一首歌给我,我就可以勉强获得五分钟的深度麻醉。他可以一边唱歌一边拿走我的翅膀,这样我们便都是幸福的(太暗了,我得站起来打开灯)。我们习惯从麻痹与幻觉里找到幸福,麻痹与幻觉与药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的话也不是那么不健康。或者说幸福和健康不是之间从来不会有因果关系(这的确是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没有拒绝迷幻剂的理由,是吧。世界上这样美好的事物可不多了。我们把费洛赛宾粉和麦司卡灵粉还有沾着麦角酸二乙酰胺的方糖搅拌在一起。我们是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回去的。
突然暴躁了。
虽然除了丢了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不幸发生,但是我还是暴躁起来。在看着相对论的光锥图时我一边狂暴地抓着自己的手背一边流下眼泪来,于是我走出房间去把半瓶黄樱倒在碗里(我忘记怎么走路了,走姿相当的业余),喝进嘴再吐出来。真浪费。白墙和玻璃窗发出风的空旷的声音。我抬头看到玻璃窗上的影子,没有梳头也没有换衣服,被一大口只有二十度的酒刺到两眼满是泪,“委屈的哭了起来”,我在我的影子下面意念加上这些字。
就算有翅膀我也不能真正地飞起来。
我想到这些,终于沮丧下来。
这个笼子怎么飞也飞不到头。“哪里有笼子?”他说。哪里也没有,但是我们活在笼子里。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拥抱我们的互相的伤害我们的血我们的活着和死了都是笼子。给了我翅膀的话我便可以俯视人间的彩虹了,彩虹还有高压线,然后一直看到停止呼吸。现在他也有了翅膀。幸福。如果他还会回来的话我要找个时间这样严肃地上一课。想要幸福的话首先要带上可以逃跑的翅膀,就算无论怎样也逃不出这个笼子,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向着自由的逃避飞行的。
将幻想与药当成翅膀的我们从痛苦的自我里找到了幸福的影子。为了伤害而相遇,为了遗忘而记忆,为了逃避而生活,在没有人记住的地方搭起玻璃的房子。在没有人记住的地方我便可以做一切我想做的事,离开所有人,说着不是所有生命都有活着的权利,随心所欲地杀掉我想杀掉的东西。
过去,当然这是过去。
他偷了我的翅膀然后飞走了。
现在我在整个世界的边境,突然有了一种不知道怎么回去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感觉。管这么多干嘛,我活着从来不是为了活的(又倒下半瓶边喝边咽边吐),我狂妄又无理地沾沾自喜着。把水龙头打开冲着水槽,自来水的味道温和又冷淡。我当然没醉了,哎。
把昨天的衣服套上,插上耳机,锁上门,老实地从路上走过去。
得到回报的人生没有那么多,嘴里的令人不快的酒味刺得我有点反胃。我不能飞起来。我感觉我被自己抛弃了。被我所期望的自己抛弃了。没有下雨也湿淋淋的地面,在这样的梅雨天气里,期望的自己再怎么坚强完美,大概现在也该生锈了。我抓住空气,在手心中捏出了水珠。
“无论怎样你就是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什么都没在想。”
电车的声音。
“话说现在这个时候樱桃刚上市的吧。有一大袋那么多,樱桃还是车厘子,还很便宜,这样说来我又想用舌头打结樱桃梗了。”
想到这些句子,于是我买了樱桃,一大袋。插着耳机,沿着人行道,在身旁交错的车流中一颗颗地塞在嘴里再把核咽下去。我依然是没有食欲的,只想花一笔钱满足一下无理的败家欲。我不想回去了。我有点想像他一样带着我的翅膀流亡到永远永远永远不用回来的地方,于是我沿着电车轨向着终点站走过去。
踩在地面上的感觉是陌生的,我说过我忘记了怎么走路,但是我跌跌撞撞地走着,从在夏天就落满枯叶小路上晃过去。海鲜小饭店里亮着黄色的光,人类共同的幸福。共同的幸福,像是一个梦,我坐在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的火车上,火车坏了停了,乘务员打开广播讲笑话给我们听,一切都是那么幸福美好,只是在我中途下车的时候火车忽然又开走了,带着所有人的幸福,把我一个人留在雪地里,远远看见的是新年的烟火。——新年的烟火,市中心的霓虹灯。冷风迎面吹过来,让我忘记现在是六月。耳机里的音乐随机到了The scientist。我还能继续往前走。穿过路中央的电车轨,在昏黄的路灯还没染上玫瑰色的时候,我们两人只是沉浸在互相孤立的幻想里,焦躁地寻找着爱情存在的痕迹。想到这里,我跟着音乐,口齿不清地唱起来。
让我们回到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
回复。
今年份的狂气。我想想对他还是不用认真遣词造句比较好,反正我自己写我自己的事只要随手写出来就行了。流水账一样记些私事。
其实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最后那句,scientist好听。
标题勉强和去年的凑了一个系列。
“今天又下雨。”
Sion把茶杯搁在桌上,里面的开水已经温了。白水这种东西就是该要么冷要么热,温的算个什么东西。该再放一放,摆到和外面的湿淋淋的空气一样冷才能喝。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啊就算不下雨也是个好沮丧的日子。”
迷迷糊糊打瞌睡的Verite咕哝道。室内空气居然闷到这家伙打瞌睡了,真是一场妖雨。
“不是因为星期一,所以下雨吧。”
“啊对,每一天都有下雨的理由。”
“不是这个。”总觉得哪里不对,Sion话说一半终于还是觉得不要讨论星期一和下雨的必然联系比较好。虽然刚刚四点半,但层叠的乌云已经把实验室笼罩在一片灰黑的阴影里。水滴砸在玻璃窗上,里面浮出雾气来,室内温度高于室外使水汽液化,窗玻璃的热传导系数……“你带伞了吗?”
“没带。我要睡在这里。”
“不准睡在粒子碰撞机实验室里。拿出你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的朝气来。”
他拖着Verite的衣领硬是把他拉着坐正(“我已经下午四点半了嘛!”Verite嚎叫起来)。两个老年人在下雨的实验室里……感觉并不是很有趣,明明应该坐着躺椅晒着太阳插着收音机听经典流行频道的。夕阳红啊夕阳红,夕阳是晚开的花是陈年的酒,半死不活的甜蜜人生。
“我觉得,只是我觉得,你就挺适合窝在与世隔绝的小盒子里做做实验的。”
清醒过来的Verite又开始话多。
“把生物钟调慢九倍去做,做他个一年半,然后出去看看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听上去有些意思的,只是我搞不了,我的时间不如你那么多到可以随便浪费。”他撑着下巴看着窗外,摆出一脸憧憬的神情说。“适合那种……我刚做了这么个梦,你在一个长十米宽十米高十米的盒子里面,盒子是白的,里面除了你什么都没有。——啊,有一点,还有墙上一只黑色的蜘蛛。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你,还是幼女的你,不过你想想那个,像恒温孵化器那样的……
“对的对的,恒温孵化器。话说上次,他们把海龟的蛋放到孵化器里孵……”
Sion又试了试茶杯里的水。好像凉到了可以喝的程度。
“水母又不产卵。”
“啊,是的,水母也没有心脏。不过海龟的心脏很有意思,有的海龟——是绿海龟吧,Chelonia mydas,因为水的压力大到没法呼吸,所以它的心脏九分钟才会跳一次,于是它们可以活那————么久。”Verite伸出双手比划道。
“我的心脏一直是很正常地跳着的。虽然它用什么速度跳我不是很在意,反正无论试多少次它也不会停下。”
“我觉得吧,你这么稳,真的像一只九分钟一次的海龟呀。——还是说你觉得你有心脏和没有是一个道理?”
雨一直下。空气有点闷了,气压大概有些大。
“心脏九分钟才跳一次的不应该是你吗?”
“才不,我的心率正常得很,一分钟也有八十一下的!”
“比正常稍快了点。”
“因为我过得比你们愉快嘛!愉快了心跳大概就会快一点的,对我而言这不是,很正常的数值嘛!”
靠在窗前的不锈钢栏杆上,Sion朝窗外望过去。隔着被雨打得模糊不清的玻璃,依稀能看到灰白色的天与灰白色的楼与灰白色的路。都是灰白色的,树与水与在雨云里露出一点点的太阳。这层楼离地面太高了,在不下雨的时候Verite会趴在栏杆上往下看,轻松又专注,专注到Sion总觉得他是想把这一整片风景记到脑子里回去学某个人画全景鸟瞰图。
只是白亮到发蓝的路灯开了,远方的灯火浮在水迹上。
好像在俯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丢失自己之于世界的归属感是常事。世界之大与自身之小的同时叠在眼前便招来了矛盾,在不能调节的疏离与矛盾中,人会陷入混乱。这是谁的句子来着,忘了。
“我们已经在与世隔绝的小盒子里了。”
Sion说。
“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们在离地五十米的半空吗?五十米的半空与五十米的水下,隔绝体验大概是同一个强度吧。”
“你高估我的文艺细胞了。我指的是普通意义的与世隔绝。”
“那是什么样的?”
Verite快活地踱到他身旁。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只是想到了一些东西。
“我是说,参考系。μ介子会以0.98光速的速度运动,而它的半衰期是2.22微秒。在曾经的观测里它在运动中经过了不止一个半衰期,但它的数量远比预计值要多。毕竟用劳伦兹的式子去算,在这个速度-时间的时间膨胀实验里,高速移动的μ介子衰变速度会比静止的μ介子慢五倍。”
T=T'/√(1-v²/c²)
在蒙着水雾的玻璃上,Sion把算式划了出来。“虽然这是最简易的。”他念道。
“等下,我没有那么高速的,这一定不是我平时很嗨的缘故吧。”
“虽然自身的高速是时间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前提是膨胀之于惯性观测者双方而言是对称的。只要是两个观测者以相对接近光速的速度移动,那么他们的观测结果都会是对方的时间变慢了。所以有时可能不是人用高速把世界拉开了,而是人以外的所有都在高速飞行,把静止的留在原地。……如果以他们为参考系的话。我说过这是相对的。
“这样世界看你是慢速的,你看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它总是沉闷得跟不上你的激情的话。”
盯着玻璃上的算式,Verite偏过头估算起来。九分钟一下与一分钟八十一下,一比九的三次方……嗯。是个有点糟糕的速度。——不是用这个算的,傻瓜。“这要画图的吧?”
Sion在算式的上方画起坐标系来。
“闵可夫斯基时空图。”他在横轴与纵轴上分别标上x与ct,“大概画图比较容易思考,为了方便把所有的空间轴并成一个x就差不多了。如果名为Verite Ox的参考系是这个正交的直角坐标系的话,我们现在讨论匀速运动的世界。将你以外的世间万物并成一个质点,以速度v在图上运动,世界线便是一条相对于ct轴斜率v/c的直线。这是另一个惯性参考系。”在直角坐标系上用同一个原点,他又划出了一个歪曲的坐标系。
“所以你觉得,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他把声音压低了些。至少Verite听来有一点。天色好像比起刚才昏暗了许多,Verite转头找了找开关,在实验室的另一头。太远了。“嗯,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严肃的回答应该是arctan(v/c)。”他伸出手去标出了两条时间轴之间的夹角,“不严肃的话我能不能回答91厘米啊?”
“怎样讲都没错。反正这终归是我忽然想到的一些东西。”
“噢——像我忽然想到绿海龟那样的吗,虽然说起来的时候没什么理由,不过好像有没有理由也没问题。——虽然有点玄幻,但你讲出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好像歪歪扭扭的器官冷藏柜。”
“没什么共同点吧。”
“有……有一点?”
Verite好像自己也忘了为什么说出这个比喻来。里面是暂停的心脏?他想。
“你的比喻系统真是正常人过三百年都搞不懂。”
“不管了,不懂便让他们去不懂。反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好的吗?”
“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看着对面一脸没心没肺没脑般的夸张表情,Sion感到一种说什么都敌不过他的热情的无力,——啊这样也的确挺好的。他把窗上的图连着水雾一起抹掉,雨刚停。他忽然想起天色明明并不是很晚。
“没带伞也可以走了。”他指着窗外说。
“我还想再等干一点嘛。”
Verite又趴在栏杆上看起了他的风景。Sion起身把桌上留下的半杯冷开水一口气喝掉——讲那么多话有些累了。他想。这家伙平时究竟是补充了多少水才会这么话痨呢?反正总归是敌不过他的。这次大概是一败涂地了,不过并不算沮丧。
“我觉得下雨并不因为是星期一。”他放下茶杯,对Verite说,“应该是夏天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