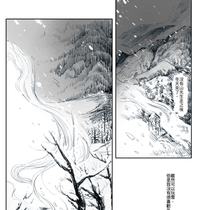更新补完!!
===正文的分割线===
新年伊始,街头巷尾各家各户都沉浸在忙碌而愉快的气氛里。七海家也不例外。从十二月开始七海家便不再接待新的住客,连带着「海味」也开始半放起了假来,每天只在早晨开上一会儿就早早收了铺子。无论是旅店还是水产铺,招聘的帮手都是本地人,所以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假期,但毕竟是新年,他也乐意让大家都过得轻松些。
七海看着站在身边闭着眼,安静地许着愿的织原,感觉自己的整个心都被一种温暖的感情所盈满着。
织原睁开眼,放下合十的手侧过头,不出意外地看到七海正望着自己笑着。
“冷吗?”七海拉过他的手,拢在掌心里呵了口气问道。织原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却也没抽回手。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还仿佛冬日里呵出的气一般,带着一丝丝暖意却无比朦胧,而现在却可以这样站在他的身旁。七海在恋爱这件事上并不顺利,甚至在遇到织原之前,他都有些快要放弃了。而当两人真的开始交往以后,关系进展之慢也一度让他觉得“可能就这样了吧”。他对所有人都很好,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人,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愿,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要求对方向自己妥协什么的。
—— 一个月前
「如果得不到心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这段时间总是忍不住想着之前同森美月聊到的话题。森家的先生离开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看起来柔弱的女人实际上无疑是非常坚强的。大部分时候他们聊天的话题通常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趣闻琐事,但偶尔也有这种情感上的问题。
七海并没有去打探森美月问自己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原因,非常难得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试着去探查对方的偏好倾向,而是直接了当地顺着自己的心思给出了回答。
佐佐木冬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自己跟他是邻居的关系——不不,还要比那再多一些。是十年前还是多久呢?曾经看着那个少年成长的那段日子。毫无疑问七海对佐佐木是有好感的,也不知道这种好感到底是发展到哪一步了,突然之间就成了恋人的关系。
只是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短暂。他们原本就认识,像是很好的朋友,又有些像兄弟。一旦这种感情变了味,要升级似乎就成了非常容易的事情。——发展太快了。当时的七海并没有这个意识,佐佐木当然也不会有。…也许不会有吧,现在七海也有些搞不清楚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佐佐木似的。
之前意外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两张松竹梅剧院演出的票,好像是临时有什么事去不了,才转赠到他手里。七海本来想约上织原一起去看看,那刚好织原那天也因为约了人聊一些工作的事而抽不出时间。浪费一张票总比两张都浪费了的好吧,就这样想了,他便一个人去了剧院。
是万万想不到会在那里遇到佐佐木冬树的。
同一天、同一场演出,……邻近的座位。
真的是太尴尬了……七海想。
他尽可能的没有把这种尴尬表现出来,但恐怕并瞒不过佐佐木吧?好在对方似乎也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只是简单的打了个招呼便各自入了座。本来留给织原的那张票在这个时候可真是派上大用处了,七海坐进自己的座位,和佐佐木之间刚好空出了一个人的位置。
怎么就那么巧呢、怎么就那么巧呢…这次是这样、之前在祭典的时候也…这个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人。
七海还记得几年前这个人的不告而别,之后便杳无音讯。他不是没有试着联系过佐佐木,但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好像是石沉大海,请人带的信也从未得到回应。不过他也没有真的坚持太久,从客观角度来看的话,对方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的很清楚了吧?
是自己被讨厌了。
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在开头的一两年时间里七海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把两人交往的那些回忆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里重复播映,却找不到任何不愉快的回忆。
……啊啊,是啊,当初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一段恋情。
一定要说的话,大概是自己真的太黏人了吧。
喜欢一个人,喜欢和他在一起,想要触碰他的身体…即使是对七海这样看起来温吞水一般的人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如果对方是跟自己两情相悦的,多一些这种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也不会觉得为难吧?但说不定真的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如果自己会为了喜欢的人而压抑一些冲动,为什么会认为对方、不会为了满足自己而勉强做一些本来并不喜欢的事呢?
所以说真的是做了什么让对方不愉快的事情吧…但已经被那么直接地斩断了彼此的关系,七海也没有真的厚颜无耻到去找佐佐木问个究竟。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自己再想起他的时候,心里也没有那种酸楚的感觉了。
就如同眼前的演出一般,好像是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只是刚好自己知道一切的过程罢了。
他一点也没有去看坐在身边、刚好隔着一个人的距离的佐佐木,也理所当然地觉得对方不会看自己。
所以当剧院的大火燃起,自己手忙脚乱地帮着疏散人群,来不及发现即将砸落到身上的断木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想到佐佐木会过来救自己。
“…护——!!”
“……你知道我去过医院了吧?”七海坐在一旁,看着身上还裹着些绷带的佐佐木。那天他站着的那个位置上方突然开始坍塌,周围太嘈杂了,人群的呼喊和尖叫声此起彼伏,他分不清楚那些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更无暇去判断是哪里的木块正被火烧的咔咔作响。直到听见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他才发现佐佐木不知从哪儿窜了出来,一把揽下他的肩将他扑下。他分明看到砸落在佐佐木身上的那些东西和他额角渗出的血,却做不出半点反应,直到佐佐木自己挣扎着起身,他才赶紧一起帮着搬开那些杂物。或许是参军的关系吧,他和佐佐木互相搀扶着的时候他才发现当年的少年已经成长得相当健壮了,在为自己抵挡危险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曾经像“弟弟”一样存在的人了。佐佐木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后又立即转身去帮助更多的人,他本来想在外面等他,却无法留在现场。等火势得到了控制,他再想去询问佐佐木的下落的时候,只得到了一个“看起来没事,已经走了”的答复。
…怎么可能没事、怎么可能没事!
他好不容易打听到佐佐木所在接受治疗的医院,再跑过去的时候,这家伙却又已经不在了。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到那个自己几年来都刻意避开的地方,果不其然佐佐木早早出院后就回了自己家。
“不是多重的伤,没必要一直待在医院里。”佐佐木笑了笑,说道。
七海皱着眉头看着他。
本来只是想着作为曾经认识的人、作为朋友,对方在那样的情况下救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应该探望一下、当面道个谢,如果没有亲眼看到他好好的,自己是决定不可能安心的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这都是人之常情不是吗?他本来准备了不少探病时安慰人的客套话,这个时候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个人在祭典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只是喊着“七海先生”,但是从口气里完全听不出“厌恶”的情绪。这些年来断开的联系毫无疑问地拉远了彼此的距离,但七海现在却突然隐隐觉得,好像是自己误会了什么似的。他就这样盯着佐佐木的脸看着,眼前的佐佐木散着刘海,脸庞同当年相比确实是成熟了多的,他试图从对方若无其事地说着“责任”“义务”“刚好看到有危险就帮了一把”之类的话的脸上窥探出一些秘密来。他尽力让自己只去听佐佐木嘴里说出来的话,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但最后无奈地发现,自己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听他说得越多,自己心里的问题也越多。
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丢下我?
为什么连再跟你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吗?
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看了吗?
他的眉头越皱越深,不是因为佐佐木说的那些话,而是因为自己心里在想着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很多年了,有时候、有意无意地它们就会突然蹦出来,占去自己一些时间。在他心里一直有着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叫嚷着,去问个清楚啊;另一个声音则低诉着,随他高兴吧。
随他高兴吧、随他高兴吧……他太习惯顺着别人了,以至于连表达自己的心情这种那么本能的行为都几乎要忘记了。
这世上唯一的、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个人现在就在自己面前,与自己四目相交。
佐佐木停了下来,看着一言不发地七海沉默着。他脸上的表情也不再那么轻松了,逐渐变得有点沉重,甚至是有些紧张。
七海忽然觉得,佐佐木或许是在等自己说话。
可他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他心里的那两个声音,无论哪一个现在都不存在了。他又望了佐佐木一会儿,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叹出来,嘴角扯出一个并不太好看的弧度。
这些年来,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他心里的某个角落累成了层层叠叠的蜘蛛网,事到如今要不要撕开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
原本应该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属于这个名叫佐佐木冬树的男人的、叫作「爱恋」的心情,早就已经腐化成灰了。
佐佐木看着他,肩膀忽然颤抖起来。
“…七海先生,您现在过得很好,是吗?”
他的声音也颤抖着。
七海点了点头。
“…那拜托您、以后能不能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佐佐木几乎是哽着喉咙说出这句话,有几个音听起来显得特别重,又有几个音几乎轻不可闻。七海当然知道这种感觉,虽然现在自己的心情不是这般,但如果自己现在开口的话,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他仍旧只是点了点头。
缓缓地低下去、又缓缓地抬起来,非常深得、重重地、点了两下。
佐佐木不再看他。七海在点头过后站起来,微微鞠了鞠身,便转身离去。在他关上佐佐木家门的那一刻他知道,两人之间再也不会有什么联系了。
佐佐木还喜欢着他。
七海也是刚才才从他的眼神里读到这件事的,也是同一时刻,他也通过眼神向佐佐木传达了自己的心情。
没办法了。
如果再早一点…三年…不、或许两年就够了,在自己还牵挂着他的时候,在自己还想跟他要一个答案的时候…但现在太迟了,迟了太多了。
早在遇到织原之前,他便已经无法在想起佐佐木的时候有任何“困惑”以外的感觉了,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有了织原。
织原…白星。
光是在心里默想着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出他的样子,七海都觉得会有一股说不出的暖意从心底涌出来一直蔓到四肢、连指尖都仿佛能感到一阵酥麻。要是多想上一会儿,心跳就会逐渐地快起来,「喜欢」的心情慢慢地挤在胸腔里,几乎能压得人喘不上气。
如果说恋爱是糖的话,那一定是很甜很甜的糖吧,偶尔会让人觉得甜得发苦。但正是这份苦涩,才真的让人更珍惜、更迷恋它的甜。
七海一边往家的方向走着,一边胡思乱想,他走得很慢,不知不觉便过了很久。忽然他停下脚步,有些意外地看着出现在身前不远处的人。
“……白星?”
金色余晖落下,细细地洒在织原的身上,他整个人都被笼在一层柔软而温暖的光里。七海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却仍是看呆了。他无论看到织原几次,都如同第一次见面一般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目光被这个人牢牢地吸引住,心也跟着一起。
织原看着高兴地向着自己快步跑来的七海,微一笑道:“你去哪儿了?”



愚人节也不忘追赶进度的我……然而进度依旧缓慢(倒地)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96266/
=====================================================
临安.千金堂
田知甚走近时,有人正轻轻哼着小调,声音恬淡舒和,从朦胧树影中悠悠传来。
此处是千金堂中颇为冷清的角落,种有大片腊梅,如今尚未到花开时节,淡黄色的花苞纤纤点点的凝在枝头,悄无声息的将这冬季的萧瑟抹去了几分。
这几日田知甚暂留千金堂养伤,不过随意散步至此,并未掩藏脚步声,他既无意偷听,也懒得寒暄,正打算悄然离去,岂料那林中之人似有所觉,缓缓转了出来,她乌发素髻,青衣淡淡,手扶花树而立,犹如画中之人。
“原来是田郎君,”见到田知甚,她并不惊讶,意态闲闲的笑道:“这曲是我一位好友所作,可惜我只记得的这一小段,让田郎君见笑了。”
“音律由心而发,虽只有一小段,但可知此人率性。”田知甚评道,他在千金堂盘桓数日,见过这女子一次,虽未有过交谈,但听仆役提过,她是千金堂少东家郑曦之友,名唤阿羡。
“确实呢,我这位朋友虽然唱歌音准不佳,却能作出好曲调来。”
她生得温眉秀目,看起来格外舒心。
田知甚觉得有些好笑,回想了一下那曲调:“羡娘子的朋友倒是很妙。”
“是啊,”阿羡秀眉弯弯:“此人最是有趣,喜欢到处乱跑,上个月他还跑去太湖画了一副长卷,我戏言让他送我,他竟说我不懂欣赏不肯相赠,你说这人是不是很小气的很?”
田知甚闻言一怔,她说的朋友是……费丹。
那日从地宫出来后,众人在附近的天龙寺借住了几天,多亏柯行之的师弟郑曦及时赶到,将大家的伤势稳住后立即回转千金堂,百里姐弟伤的较轻,很快便带着两柄“芳菲剑”道谢离开,说要尽快告知轩辕会有关地宫中峨眉派所遇之事。
然而费丹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地宫中的那一剑居心恶毒,刺穿右肩后旋拧而出,导致其肩肌撕裂筋脉皆损,尽管竭尽千金堂数名大夫之力,也只能将外伤缝合,却无法续接破碎的细小筋脉,从此连握笔抬手等事都甚为艰难,更莫论挥毫作画。
他也曾私下问过郑曦,可有转还的余地?
然而回答是,即便华佗再生,费丹的右手想要恢复如初,也是渺茫,千金堂百年名声,下此结论应是毋庸置疑。
如果能拦下那一剑,哪怕再偏一点,都不致如此。
然逝水如斯,莫可追挽。
正当田知甚神思微飘之际,一名垂髫童子从另一头急急奔来,见到阿羡如同见了救星:“羡娘子,原来你真在这,快同我来!”
阿羡被小童拉着往前走:“金枝,怎么了?你家郎君怎么说?”
金枝清秀的小脸皱成一团,苦兮兮的摇头:“不行……郎君说谁也不想见,但郑大夫说郎君的伤非治不可,说要踹门呢!羡娘子快去劝劝吧! ”
田知甚闻言皱眉,这金枝是费丹的书童,数日前费丹清醒后便召来金枝,要告辞归家,但郑曦以费丹伤势未愈为由不允他离开千金堂,费丹伤重无力,身边又只有年小力微的书童,自然拗不过,索性闭门拒见,没想到今日已到如此地步。
“一个是这样,两个也是这样……”阿羡叹了口气,又朝田知甚笑笑:“田郎君,那我……”她本想告辞先走,不料田知甚点头道:“我也去。”
千金堂.西院
“少东家稍安勿躁啊!”老大夫颤巍巍的劝阻:“费郎君受此重创心神不定,我们当用些安神的药才是……”
“命都要没了,还安什么神,王伯你且让开。”
少年笼着袖子站在紧闭的房门前冷声道,他眉目俊秀,缓带轻裘,袖口领口都镶着雪白柔软的貂毛,一派富贵斯文的模样,然而说话间锋锐尽显,正是临安千金堂的少东家郑曦。
侍女捧着药箱,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静立在侧。
“费丹,你再不开门,我可就进来了。”
郑曦扬声下了最后通牒。
然而,房中依旧静如死水。
田知甚等刚行至院前,就听见数声大响,那客房的镂花木门四分五裂的散了一地,老大夫躲得老远连连叹气,柯行之面色淡淡的立在门外,竟任由郑熹拆了自家房门。
金枝服侍费丹时日颇久,对主人忠心不二,见郑曦当真破门而入,大喊一声就要往房间里跑去,阿羡一把将其拉住,他也不敢发狠挣扎,委屈的抽噎起来。
只听见房间里传来碎裂之声和隐约的只字片语,片刻后郑曦的声音逐渐拔高:“总之,你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今日不好明日继续,明日不好后日再治,直到好了为止,飞雪,拿药箱来!”
门外侍女应声而入,田知甚心下愕然,只听说逼着大夫治病的病人,还从没见过这般强行给人治病的大夫,他正欲迈出一步,一只淡青色袖子轻轻横了过来,那袖子的主人凝视着破碎房门,语气温和:“田郎君若是朋友,就不应该劝阻的。”
“难道你不是费兄的朋友?郑大夫虽是好意,但如此强硬,恐怕适得其反。”田知甚不以为然,在地宫数日他也大约知道费丹虽是一介书生,但性格狷狂,强硬手段虽可压制一时,可心病比身上的伤痛更难痊愈。
“费郎君为人纵情任性,若是顺遂他意,只怕他不愿瓦全。”阿羡闻言瞧了他一眼,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不愿见朋友求死,所以不能让他顺心遂意。”她笑了笑:“虽然这很残忍,但世上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不是吗?”
田知甚一时默然,阿羡说的没错,然而这番说辞和她温言笑语的模样重叠在一起,让他心中涌起一股奇异的不协调感。
见田知甚不再有所行动,阿羡放开眼泪汪汪的金枝:“金枝,你若再哭,你家郎君就真要成仙了,快去厨房看看,等会儿端些吃的来。”
“可,可郎君说他不吃。”金枝垂着脑袋闷闷的回答。
“他说不吃你就不端吗?你呀应该一天端个十七八回,说不定哪一次他饿坏了想吃了。”
“真的吗?”小童半信半疑的问。
“当然,千金堂的药膳可是有名的。”阿羡摸摸金枝的小脑袋,又将一小包东西放在他手中:“喏,这是糖糕,只给不哭的金枝。”
“羡娘子待金枝真好,”金枝不过是个心思单纯的十岁孩童,连忙擦了擦眼泪,脸上又有了点笑意:“待我家郎君更好。”
阿羡笑眯眯的点头:“那是自然,因为我们是朋友。”
听着这些稚气的对话,田知甚哑然失笑,方才心中浮动的奇异感觉渐渐消散,他轻呵了一口气,看着那团白雾聚了又散,离开蓬莱岛不过区区数月,心境似乎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既然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那么是该回去了。
======================================================
Ps:
1.此篇发生在十一月十六日之后(十一月初十出了地宫),一行人在天龙寺住了三日稳住伤势后立即回到城内千金堂,冬至后田知甚离开临安,回转蓬莱岛。(田田: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2.郑曦态度强硬除了性格所致,也因为是郑熹通过阿羡,找了费丹担任柯行之下地宫寻人的向导,所以她和柯行之都认为是因为保护不力间接导致费丹有此结果,无论是作为医者还是朋友,都应该将费丹治好,然而费丹是个任性而且活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