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夏至的独白。
一条咸鱼怎能忘了咸鱼楷模【
————————————————————————————————
『日日重复同样的事,遵循着与昨日相同的惯例,若能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的来袭。』
这本书是我十六岁时,雨季的某一天,从旧书店里买来的。
十六岁时的夏至与二十岁没有什么分别,天空总是下着阵雨,凉月那柄透明的伞也总是挂着透明的水滴。
与真正的夏至读音不同,作为白鸟夏至的我出生于初春。如果真的出生于黏腻的夏季,或许性格也就不会是这样了。
「白鸟君,还没吃饭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父母又不在家。
「父母不在家也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凉月似乎总是能听到我的心声,就算不通过语言,也能交流。
但他实在太过敏锐,所以这份感情也必须更小心才行。
「又在看这本书了啊。」凉月笑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些太早了?」
「……还好。」
我和书中这个人不同,我放不出逗笑的烟幕弹。在和凉月相处的时候也只能不知所措地结束话题。他一定会觉得我无趣吧。
雨季空气中的水含量使人感到溺毙般的舒适,耳中凉月平和的声线混杂着雨声,没有比这舒适的环境了。
有时凉月在纸上演算题目,袖口带着沾染了潮湿的淡淡烟草气味。这种味道于我而言等同毒品,清淡而镇定心神。
很少回家的父亲每次见面时,身上都会有烟草的味道。与时段场合挂钩,每种烟草的气味有些微不同。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能分辨很多种不同的烟草烧过之后的味道了,但凉月身上这种,我之前却没能闻到过。
我想或许我知道这种烟草,只是它出现在凉月身上才使我感到这股陌生的舒适吧。
我将脸贴在桌子上,从垂直的角度注视着凉月滑动的笔尖。
「累了吗?休息一会也没关系。」凉月停下了笔,钢笔尖划过的轨迹还没干透,一条泛着光的弧线一直连接到笔尖的尖端。
「这样就好。」
如果这样不好的话,凉月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喜欢上比自己大十一岁的人,该怎么办呢。
-
「啊,你又在看这本书了。」泽木抱着电脑盘腿坐在沙发的另一半。
「恩。」
泽木身上有时候也会出现烟草的味道。和凉月的完全不同,他身上出现的烟草味似乎更容易沾染在身边一些其他的东西上。仿佛本身就带有侵略性一样。
和凉月的关系就像是一条渐近线,无限趋于相交却没办法相交。和泽木之间却像是周期函数,习性与性格都相去甚远,却总能找到最合适的交点。
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如何都不想被他知道。
我将头枕在泽木腿上,呼吸着那毒品一般的烟草味,找到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并将他的抱怨视而不见。
二十岁的夏至和十六岁时也没有什么分别。我知道有人是爱我的,但我好像缺乏爱人的能力。
『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害怕会失去,害怕会怀念,害怕以后会痛苦,所以选择了沉静。』
因为标题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文艺就只好放着日文啦!!!
直译是「代表开始的尾声」
白鸟和浅光两部分文风非常不一样【立派的白痴和立派的文艺】
明明只是序章就给给的,不愧是恋爱小组,直入主题【。
擅自决定了季节!以及只问了对方说话的习惯【。】所以如有OOC请大力打我并指出来orz
————————————————————————————————
01. 浅光悠斗
浅光悠斗,男,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两年无业,大学期间曾经在便利店做过兼职。
与简历上稀少的字数相符,朋友的西装穿在他身上显然过小了些,悠斗在身后拽了拽袖子。刚刚及胯的上衣边角不合身地翘起,显得悠斗甚至不像是个一米七出头的矮子——或者只是让人深思这套西装的主人有没有成年。
「有照顾过小孩子的经验吗?」
「有有有我有个弟弟是我一手带大的!」虽然不如说是他一手打大的比较确切。
对方上下审视了他最后一遍,合上了那算上标点符号都不到四十个字的简历:「你明天开始过来上班吧。」
浅光悠斗,男,二十五岁,明天开始成为幼儿园的保育员。
-
「嘟——嘟——嘟——」
浅光有些兴奋地想把找到工作这件事显摆给什么人看一看,结果在手机里从あ翻到了ざ,才找到那么一个不是代打工作的联系人。
泽木冬树,大学时候的同一个社团的学弟,现在的……饭友?
说是饭友,但是浅光大概已经被对方身边的人当做了狐朋狗友,而他自己作为比对方大上四岁的社会人,却也没请人家吃过几顿饭——更多的是蹭蹭他家的饭菜或者带他去小酒馆喝个酒,吃吃回转寿司。
不如这次就请他吃一顿不回转的寿司吧?
「喂?」听筒里传来了对方的声音
「今晚我请你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浅光语气里带着得意,生怕这个噱头没能做足。
对面的人显然是一幅不太信任的样子:「又是回转寿司?」
「你想吃什么我都请!」他一口答应下来。
明天的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电话那头闷声笑了起来,浅光也懒得反驳他。
「毕竟这可是我前半段人生的结末【エピローグ】啊!」
02. 白鸟夏至
泽木电话里传出的句子似乎令白鸟十分不爽,他的手指反复拨弄着书签绳。如果是一本新书的话,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摆弄封皮了。
「夏至——我出去一趟,你走的时候记得锁门哦——」
「唔。」他从喉咙里发出了悲鸣一般奇怪的声音,像是想说什么又被一口咽了下去一样,随即拖长了尾音回道,「是是——」
泽木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便开始对白鸟直呼其名。虽然后来他了解到自己的确是比泽木年龄小一些,也并没有什么因为被这样称呼而感到不舒服的缘由,但却总是无法适应。
每次从那张嘴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总是有一种溺水的人被揪出水外,又像是电流从耳朵电击过大脑一样。
既不愉快又有些痛苦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自己从没有过被这样称呼的经历吧。
「怎么一脸不爽的样子?」泽木一边换衣服一边笑着问道,白鸟仿佛还沉浸在书里脸脸都不抬一下——虽然泽木明白他只是懒得抬。
「尾声【エピローグ】就是尾声,放在中间的尾声只能算是休止,放在前面就要叫做引言了。」
「为什么偏偏在这种地方较真啊?」泽木又笑起来,「话说回来你是怎么听到的?!」
白鸟叹了一口气,声音一如既往地没什么力气:「所以我才不用手机那种东西啊……哪有什么隐私。」
「这是意外啦……」谁叫悠斗那家伙喊那么大声,泽木刚想吐槽出来,便在鞋柜边发现了白鸟类似上个世纪风格的翻盖手机。
他顺手捡起了做了个翻开又合上的动作,一气呵成仿佛手机是自己的一样:「如果家里着火了果然还是要打电话给我啊——」
「是是——」白鸟的语气像是对待麻烦的老头子似的,想把他快点赶出屋去。
屏幕上一晃而过的新着信,写着一个泽木也没听过的名字。
森永凉月?
03. 浅光悠斗
「悠斗!」泽木一路小跑着来到和浅光约好的居酒屋,看着浅光身上那套小了一号的西装,噗地一声笑了出来。
「臭小子笑什么笑!」悠斗不客气地趁他笑到弯腰时往他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好歹我也是个社会人了,好好叫我浅光前辈啊!?你这样几年后踏入社会会被老板当做没礼貌的人的!」
「不不不你是最没有资格对我说这话的了吧!别这种时候才装出大人的样子啊?」泽木笑得抬不起头来,却还是伸手比划了一条从悠斗的额头到自己下巴的直线出来,「就算从身材来看也叫不出前辈这个词啊——」
浅光撇着嘴,拽了拽短小的袖子,似乎想要逃避这个问题:「这个话题讨论得够多了,给我闭嘴。」
-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啦?」看在多年的交情上,泽木还是只点了一碗盖饭,现在正单手撑着下巴,一边等待上菜,一边盯着右边的浅光。
「我啊……」浅光吊胃口似的十指相对,支在桌上,一脸严肃又不舍的表情。
看对方少见地如此认真,泽木也变成了端坐的姿势,等着对方的下文。
「我……」
趁着浅光还没说出口的这段时间,泽木再次上下仔细分析了一番对方今天的穿着。
特意从哪里借来的小西装,比平时少卷翘一半的头发,领带似乎还是现场学会怎样才能打规范的……
「不会吧……」泽木将头向右探了探,挑起半边眉毛问道,「你要结婚啦?」
「哈?!」浅光拼尽全力强行制造出的严肃气场瞬间散了个干净。
「这身衣服……难道不是去相亲的吗?!」
如果他们坐在两人单独的小桌上的话,现在桌子肯定已经被浅光掀翻了:「我是去面试的啊!面试!!」
「不,这比结婚还不可信哦。」说着,泽木掏出手机来。
「你翻什么?」
「查查十一月份什么时候多出来了个愚人节。」
下一秒,泽木的鼻子差点被拍进老板刚刚递出来的猪排盖饭里。
「所以?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保育员了?」
好不容易听完了来龙去脉,泽木又捂着脸,一幅阴郁的样子。
「有这么难以置信吗?我也是带大了一个弟弟的人啊!」浅光往嘴里吸着面,口齿含糊不清。
「我是在担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说着泽木指了指他的脸,「就这种吃相该怎么教育小孩子好好吃饭啊?」
「那里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啦,那种事就由礼仪好的人来教咯。」把嘴里嚼着的面条好不容易都吞了下去,「我只负责男子气概的传授!」
「我看人家是把你当保镖请去的吧……」
04. 白鸟夏至
天色已经暗到连书页的编码都看不清的地步了,但白鸟实在懒得走上那么五米去开灯。门口静音模式的手机似乎闪了一次亮光,但是他也不想走上那么十米去拿。不如说,就算它被带在身边,白鸟也不会想要回复——除非是凉月的消息。
这样想来,凉月在他的心目中好像和别人都不太一样。虽然泽木似乎也有什么不同,但不像凉月那样能清晰地分辨出来。比如凉月在身边的时候,就会像是变回了七岁的孩子一样,忍不住和他亲近撒娇。
凉月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将书扣在自己胸前,缩进沙发的角落里,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和另外的骨头交错地硌在一起,虽然很疼,但在黑暗中又格外有安全感。
凉月很温柔,这是一定的。没有任何一双手比他更能传递温暖了。他的温柔虽然发自内心,但是却还是能让人觉得有什么别的东西正缓缓地从他内心的缝隙里渗透出来,而被淹没在众多复杂的感情里了。白鸟依赖着凉月,凉月却似乎没办法依赖着他。
也是。白鸟叹了口气。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有什么理由作为别人的依靠呢。
凉月总是一幅操心劳碌的样子,虽然泽木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凉月的等级要高上许多——况且泽木平时就给人一种精力用不完的活泼感。凉月只是安静地做事,做完之后又默默的给自己加上别的日程。保育员,酒吧的代理店长,照顾妹妹,甚至还养狗,明明做着那么多事简直就要累死了,白鸟想,如果换做是自己的话,说不定那样的生活,第二天就要体力透支而死。但是凉月总告诉他:「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啊。」
啊啊,明明都只是人类而已。
而且,明明只是人类而已,为什么不能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啊。
天这么黑都有点困了。
为什么要发明电灯啊。
开关还离得那么远。
白鸟想着想着,脑子里就只剩下漆黑一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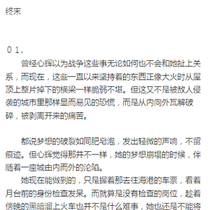
一个没忍住,我回来走兄妹线了【。】
所以被我跳过的秋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笑)说不定会补吧。总之先打个卡【。】
安定而矫情,很短很短,没头没脑没封面的一千字。
———————————————————————————————
01.
「我出门了!」心辉胡乱地把围巾绕在脖子上,连父亲的回话都没有听全。和服正装使得每一步都迈不开腿,但她还是用尽自己最快的速度向神社跑起来。
现在正是战争吃紧的时候,哥哥能如约来参拜神社已经是奇迹了,更别奢望能待长一些。
到达鸟居的时候,心辉怀疑从别人眼中看到的自己,大概正从袖口脖窝里冒着白色的水雾。凉气从围巾的缝隙灌进身体里来,提神醒脑的功效甚至让她觉得有些舒服。鸟居前的阶梯下有不少在等待的人,年轻人们脸上挂着的那份期待使人不难猜到在等的是谁。
心辉一时有些慌了神,但细想想,那个人也不太可能在这紧要关头出现于人潮攒动的地方。
「心辉!」
正在心辉为被高个子的家伙们挡住视线而着急的时候,煌己似乎看到了她的耳朵。
02.
「哥哥没有穿上次新买的和服吗?」
「不知道会不会打起来,穿旧的打坏了也不可惜。」
这番回答着实让人难过。
「哥哥在请御守的时候许了什么愿望吗?」
心辉在煌己背后问道,而他当然一个字也没有听见。
「今年就将我的运气都转交到哥哥身上吧。」
「又是樱色?」煌己手中握着和他本人不太相符的鹅黄色御守。
「每年都是这样嘛。」
只是些没有意义的话题就让心辉从确定不了心情的不知所措中安定下来,大概是哥哥特有的力量吧。
03.
神社枝桠上堆积的雪才刚因为人群的聚集掉了个干净,天空就又飘起雪花来了。
「不愧是真冬啊。」心辉把脸颊往领口缩了缩,正这样感叹着,脖子上便又暖了一层。
哥哥普兰色的旧围巾甚至有些起球,实在不是什么适合新年参拜的配饰。
但是普兰色却正好能压住不断涌现的猩红回忆呢。
她将鼻子整个埋进围巾里,身体也向哥哥的方向靠了靠。
「我决定了。」她说,不知为什么却被哥哥听了个正着。
煌己看着她,等待着那句她本来并不想此时说出口的下文。
像是被挡住脸颊会感到安心似的,心辉不敢抬起自己的脸,但这样的决定如果不能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一定会让人以为是逃避而已。
「舞藤小姐和茨木小姐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我自己也认为,或许那样才是正确的。」她紧张地抿了抿嘴,「我打算去海外研习钢琴演奏。」
心辉从来没在一句话中说过这么多「我」字。能让一直以来避免着主观看法的她以这种方式说出来的句子,让煌己意外得有些心慌。
心辉似乎还没有说完,鼻尖却皱了起来:「所以哥哥一定要在战事中活下来啊。」
「哥哥能安全回到家里才行。」
「在哥哥回家之前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不想让永远不能见面的人再多一个了……」
「哥哥……」
心辉一股脑地说出来之后,再也收不住在眼眶打转的液体,用袖子挡住了脸。
煌己一时不知所措起来。上次遇到这种情况的记忆已经几乎被时间冲刷干净了,脑子里像被铲了个干净的神社地面,连一片白花花的余地都没有。
他像小时候抱住更加幼小的妹妹那样安慰着她,右手还时不时像拍着襁褓中的婴儿似的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膀。
心辉所恐惧的事情再寻常不过了。但就算是这样普遍又简单的请求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得准。
也许就是这种时候才能感受到战争的实感吧。心辉想着,也像多年前一样,一头将脸扎进煌己的怀里。
04.
心辉把从神社里求到的签工整地折好,放进随身的本子里面。
和这枚纸签夹在一起的,还有一片已经干燥,却仍然鲜艳不肯褪色的红叶。
以及一份戛然而止的初恋。
「运势中吉
学业顺利,出行平安。旧缘已尽,争端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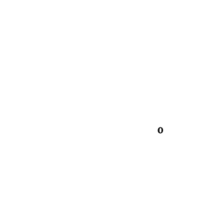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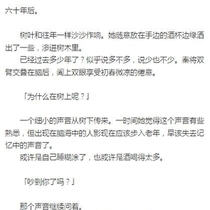

我从小就喜欢读龙应台的文字。初中时在作文里用过最多的句子便是她『目送』里的那句,「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虽然这句原文我至今还能背得出,但当时的我不懂政治,不懂台湾,甚至连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都都记不清顺序。我对她的喜爱也仅限于文字上。我喜爱她的文字简单却又深奥,每句话都能直击心灵,对于爱的诠释也显得平凡而真实。
当时的我也喜爱鲁迅,像大多数初中生一样喜爱鲁迅那耿直尖锐的文风,但我也是今天才明白过来龙应台的尖锐并不在鲁迅之下,而她的思维方式,为了维护这份尖锐所作出的选择也都是我所欣赏的,同时也是值得欣赏的。
四年左右之前,我在作为文学社社长的时候曾经收到一篇「从文学角度解读龙应台」的投稿。那位作者当时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对龙应台的认识就算在四年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仍然叹为观止。她在自己的文章末尾写道:「龙应台,在看过她的文字的每一个心中,都应该有那么一面镜子,正面是她,背面是你,她的心声,也映衬着你自己。」当时的我甚至只是觉得这位小作者的文字很好看,很透彻,而至今才觉得或许那是一种语言的天赋,而我大概是达不到她那种境界的。只能希望她没能被这些年的应试作文教育堙没了自己的才能。
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今天所看到的那一篇文章,说的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前半的标题叫做『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看过的人大概也就明白后半的标题为什么不能打上来了。
冰点事件当时虽然曾一度在网络上销声匿迹,但现在已经是百度都可以显示出来的过去式了。只是龙应台这封『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质问文章,至今还无法从中国网站上找到原文,搜索出来的大约只有零零散散对这篇文章的反对与批评。
或许你也可以说我是被资本主义或民主国家对中国负面的介绍蒙蔽了双眼,但我认为我能明白怎样算是正面,哪样算是负面。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也不是什么难分清的事情。中文课上讲起这些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老师是在推销自己台独港独思想,也有根本没读多少就睡了的,有读了也读不进去的,也有读一句反对一句的,主要是因为爱国心,我也不能不表示理解。或许就连我,能读下去这样强烈政治指向的文章也全是因为曾经狂热地喜欢过龙应台的文字。
她在文章开头提到马英九先生的那句话使我十分诧异。或许是丢下中文太久,我甚至连反讽都认不出来了。但也正像龙应台自己在访谈里回答的一样,不同立场的人对他的文字各取所需,各自解读,或许所指的不是这句,而我却疲于读懂这种文字了。现在再来分析这封信里的政治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毕竟这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信,而那位领导人,虽然不知道是否还在后台有所行动,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公众来看,也的确是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
我很欣赏龙应台那种清晰又模糊的态度,这是一种敬仰的欣赏,也是价值观的欣赏。她将「家国认同」和「价值认同」分得很清楚,许多生活在自己家国之中的人反而分不清这两点了。我想这大概是漂泊者的特权吧。她自己也在信中反问,「我到底是独派还是统派呢?」
如果两边都符合她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
这时我联想到,两岸的价值观真的相差甚多吗?
在人物周刊的记者对龙应台提起济南拆除德国人修建,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漂亮老火车站时,龙应台回答那位记者的是她在台北政府做事时经历的相似事件。台湾银行要以相似的理由——「殖民痕迹遗留」,作为拆除古建筑的借口。
同样,两岸对待自己历史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去掉对自己政府不利的东西,留下有利的教育后代。这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普遍的。
两岸的人在思维方式甚至处事上,都是归于相同的根。如果没有治国方针和两岸群众的主观仇视因素,或许人心是一种更容易联合,而不是被用来作为政治武器的东西。
也是在同一篇采访里,龙应台曾说,她为了可以写对于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批判文章,一直不办德国护照。我想这并不是大多数批评家可以做到的。虽然这其中必然有立场和情况的具体不同,每个事件也需要独立分析,但我想,如果处在相同条件下的自己是绝对无法做到这种事的。「身为一个境外的人,我所冒的风险不能跟境内的人相比。」当被问起为何不轻易下笔批评大陆时,她如是说。也正是因为这份风险,使得她对台湾政府的评论显得更加中肯,也更有分量。比起现在网络上整日信口雌黄又因为拿了别国护照而不怕受到风险的人,龙应台的这种方式也给了她更多支持的声音——虽然她并不愿意活在别人的眼睛里,也不愿意为他人而写。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多数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而莫言虽然在作品里有影射到社会问题,却在自己的为人处世上颇为圆滑,每当被问起政治相关的问题时都会巧妙地躲避开来。我个人是不太欣赏莫言的文学的,但是对于他的圆滑却不得不表示赞同。他做不到像龙应台一样身处某个国籍却还能挺身说出自己对政策的看法,这当然也是成长环境而决定的,但是他做到了对他来说最保守,最安全的做法。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莫言型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言多必失,非礼勿言。
接下来的这些大概是我的闲话。
龙应台在访谈中提到,一九八零年代她再读大陆的作品,认为「句子的结构都是翻译体,不是纯净的中文,连文体都改了。」我便开始担心起来。若是当时就有文体改变的话,我这个一九九零年代才出生的人,一路所看的,所听得,又都是怎样的中文?这样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我们所写出的又该是怎样的文字?只能靠着毫无营养价值的网络小说来充实文字世界吗?
龙应台说,在她读大学的时候曾用过「蔚蓝的天空」这个词,但朋友问她,「蔚蓝」的「蔚」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她却回答不出。朋友接着问,既然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为何用它?
她还提到了爱默生的那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她说,文字,要触摸得到。
大家又是何尝不懂这些道理呢。
但是文字的魅力又是什么呢,小时候做好的词句摘抄,多数是找些自己不懂得的华丽辞藻,摘抄了,就学会用了。而它到底是不是亲民,又有谁会去想?现在被称作文豪的人,多是用着「精英的词」。之乎者也云里雾里,就连之前提到的能从网上搜到反对龙应台那封信的文章也是一样。我读龙应台的这封信,思想清晰有条理,而且很容易让人理解——虽然被同学之间极端的人说成「台独还写的这么花枝招展。」这类同学显然是没能理解信里那段价值观的文字——反观那篇反对这封信的文章,道理讲的很空洞,只是不断重复老子庄子,逻辑也是想到哪写到哪,反而让人看起来累得很。
这大概就是功底的差距,文字的魅力吧。
「如果没有好的伴,那还不如寂寞呢。」
这是我在整篇采访中最受感触的句子。虽然是怎样的感触我无法名状,但总觉的那是一种境界。她说,「我永远还有一双眼睛从别的地方看过来。」她可以做到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样的高处都能客观地面对自己,我想,这也是她能做到客观地面对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原因吧。
到底有多少人能客观地看待自己,又有多少人能客观地看待世界呢?
2016年3月1日
又是写给自己的MEMO,如果真的有人互动的话也可以参考试试看?
填完了之后亲妈自己对心辉的认识也更进一层了www
1.角色的父母是谁?角色是否由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不是的话又是由谁抚养的?
父亲永藤龙之介,家庭煮夫的类型,家里便当都是爸爸做。母亲没有设定名字总之是个任性的猫又半妖画家。
2.角色有从小时候就是死党的好友吗?有兄弟姐妹吗?他们现在在哪里?角色和他们还有联系吗?还是已经分开了?
哥哥久宫煌己,从小都在一起,一年前参了军不过还是保持着频繁的书信来往。对哥哥十分信任,除了认路这方面。
3.角色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平静宁和还是动荡不安深受创伤?
生长在外表平和的年代所以度过了安稳的童年,导致她对于危险的认知也不是很足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
4.角色有什么钦佩的偶像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
从前就十分喜欢『异言』上名为雾隐藏之介的作者。并且十分钦佩那位将受伤的自己从雪地里救回无铭会的人类。但是并不知道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人。
另外很崇拜班里会转钢笔的二之宫晴彦,因为能把钢笔转得很漂亮,而且和心辉一样是个比较安静的人,处在同一个学习小组的时候觉得很省心。
5.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角色是干什么的?是谁训练了角色学会现在在做的工作?
是学生。只是学生。
6.角色的道德观和宗教信仰是什么样的?为了维护他的信仰,他会做出多大的努力?是谁或什么事情教会了角色接受这种道德观念和信仰?
因为家里是放养的模式,所以形成了很独立的思维方式。并且习惯性地进行客观思考。对于人的死亡甚至大规模屠杀都会以客观的角度分析两方利弊而不是感情用事。或许是信奉稻禾神的吧,或许不是也说不定。本身希望处于无阵营的状态,但为了安全着想加入了无铭会。虽然挺有主见的,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有时候还是会有幼稚的想法或考虑不周的地方。
7.角色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爱好或者体格特征吗?旁人一般对此有何反应?
爱好小动物【。】喜欢充实的时间表。安静地从这里移动到哪里做着别人不太清楚的事情,行动之前也不大会和别人说。或许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吧,闷声不吭地就完成了很多事。遇到小动物的时候就挪不动步了。
8.别的角色对你的角色的态度如何?从你的角色的观点来看,他们为何会有这种反应?
因为心辉本身不会主动去接触别人,所以就连同班同学对她的态度大概也只是混个面熟,不会很经常地打招呼。角色本身认为这样就挺好的,不想和别人相处因为会不知所措,所以也就维持下去了。
9.角色能杀人吗?他/她为什么会做出杀戮的行为?他/她有什么敌人吗?角色能杀他们吗?
如果经过一系列的利弊考虑的话,杀人也是会的吧。不过因为想要置身事外,所以应该不会这样做。敌人没有,无铭会的敌人或许会成为她的敌人吧。随便杀(笑)【←这个亲妈怎么回事】
10.现在角色的人际关系如何?他/她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吗?或是仇敌吗?如果有的话是谁?原因是什么?
故事开始前的人际关系的话,和久宫煌己是兄妹;和编辑部有着每月一次的信件交流;给【——】(自主规制)写着十分日常的信;和二之宫晴彦是同班同学;被秋叶沧海救回无铭会。
11.角色在精神心理上有麻烦吗?有什么恐惧症的对象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
有点害怕雪的触感,因为曾经被砍伤倒在雪地里。附近有雪女半妖或者妖异的话可能会比陌生人更在意一些。其他都没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12.角色平素是怎么对待别人的?他/她容易相信别人吗?还是特别不容易相信别人?
因为思考方式独立,大概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不过要用洗脑一点的方法的话,大概就会相信了。毕竟还是孩子嘛。
13.角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她有什么伤疤或是纹身吗?如果有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
耳朵上有被砍伤留下的豁口,右肩到右胸也有伤疤,是与雪地的记忆同次留下的。
14.角色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这种规律的生活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打断了他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大体作息是十分规律的,但是个起床困难户。日程倒是不一定有多规律,因为总喜欢把日程填的满满的所以随时可能塞进新的事情来。
15.角色曾经历过这个世界上的什么重大事件吗?他/她的经历对角色有何影响?
从人类变成半妖了。坦然接受,并且在渐渐适应身体发生的变化并对此进行运用。
但是尾巴不让摸。摸了会脸红所以不让摸。
16.角色有任何声名狼藉或是名声显赫的祖先吗?他/她做了什么?当人们知道了角色有这样的祖先后他们会有何反应?角色的行为是为了提升这种声誉,降低声誉,还是忽视之?
并没有,母亲也没什么名气。心辉只是喜欢母亲所用的颜料。不过也算是被母亲的西洋化所影响,最近突然喜欢上了某种西洋乐器。
17.角色的理想或者说人生目标是什么?
故事开始之前还没有人生目标。在故事发展中会有的。
18.他/她是怎样追寻目标的?故事中描述的冒险经历对完成这种梦想有何作用?
等剧情(笑)
19.角色有过建立家庭的想法吗?如果有的话,他/她心目中理想的伴侣是哪种类型的?
青春期的少女也不是没有想过这种事,但是因为印象太模糊了所以全部作罢。目前所希望的大概是不要指出自己的婴儿肥就好吧(笑)虽然实际上也没有多肥。
20.角色考虑过他/她死亡的可能性吗?他/她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没有考虑过。还年轻嘛。但是考虑过自己远行的可能性。具体措施还留着剧情来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