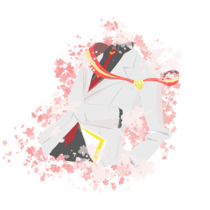二十三岁的时候,讨厌小孩子的我,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接下了照顾小孩的工作。
委托人是一对姓柳沢的夫妇。
“啊~小忍冬不知道吧?毕竟你从中学开始就离开家乡了嘛…那个「柳沢」在我们这里还挺有名的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叔叔正转着沙发椅满办公室地绕圈——电话那头传来的滑轮声是这样告诉我的。这个人向来不正经,可偏偏又微妙地在某些方面吃得很开,又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从事着便利屋的工作吧……就结果而言没有被划入废人的范畴真是可喜可贺。
啊,忘了说了,我那会儿姑且算是失业在家。记得一月的时候叔叔不知从哪里的楼梯摔下来伤着了腿,于是唯一有空闲的我就被抓来充当救兵。但是话说回来,若将照顾小孩的这类工作交给叔叔,我想用不了两天柳沢家里的地板上就会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划痕吧。
“…是哪个艺人或者官员吗?”
“啊啊,不是哪种方面的。说白了只是普通人而已,普通到跟学生时代的叔叔我坐前后桌的那种关系哦?放轻松,放轻松啦。”
叔叔如此宽慰着我,而我的神经却因为他话中的某个词而绷紧了。
“请等一下,所谓的「有名」该不会是因为什么见不得人的原因吧?”
“啊……在叔叔说明了与柳沢家的关系之后小忍冬你是这种反应还真是伤人啊。完全不是那样!!只是稍微、稍微有一点点与众不同。打个比方来说的话就是混入拉面的乌冬面条。”
“我要挂了。”
“他们夫妻都是专业的旅行家,是那座真藏学院的OB。两人刚好差了一届,因此同样拥有「超高校级」的头衔。”
这么一说,我也渐渐回想起来了。
叔叔的记忆稍微有一点差错。柳沢夫妇出名的时间大约是我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那个信息不如现今发达的年代,地方报纸、地方广播乃至地方电视台,不知为何连续多日都在重复播报或谈论「高中生二人组首次徒步穿越无人区」的新闻。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判断其背后还藏着别的什么事吧。但当时我却只记得“励志”的那一部分了,并且是以作文题的形式。
不过在那之前,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某个清晨目击到女高中生像猫似的在围墙和树之间跑跑跳跳,以优美的身姿连续非法入侵多家住户现场。这场面太过于魔幻,使我犹豫了很久是否要继续按下已经拨了一半的报警电话。后来那张脸我在新闻上也见过,正是那位旅行家女性。不是嫌疑人真是太好了。
挂断电话,我打开网页键入「柳沢」、「旅行家」并检索相关词条。
“嗳……居然在20岁就已经结婚了,年轻人真是了不得……啊。”话一出口,我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太对。
好在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人紧抓着我话里的漏洞不放了,偶尔的失言也没关系。我继续滑动网页。与父母不同,女儿的信息在网络上仅有寥寥数语少得可怜。重复输入几次不同的关键词后,仍然没能搜到任何有效信息。
会是怎样的孩子呢?眼前不知怎的浮现出了那个猫一样的少女的身影。
隔周的周六便是上门拜访委托人的日子。
柳沢家现在的住宅位于城市的另一端。不过由于我之前就在那一区工作,外加叔叔也住在那附近,所以纸片上的地址看起来也并非完全陌生。或许是职业原因吧,柳沢太太对方位的描述简洁易懂,纸片的背面还附上了徒手绘制的地图。
“……「走过便利店之后右转进小巷,大约两分钟后会看见向上的阶梯。」”
站在石阶之下的我找茬似地抬起手腕检查时间,现在是02分。没记错的话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我有听见整点报时的钟声。真是可怕的女人。
“唔…然后……我看看,似乎石阶的最上面就是目的地了呢…「路比较陡请小心。」……”
我抬头目测石阶的长度,稍微有点后悔穿着长裙与高跟鞋来拜访柳沢家了。
“啊呀,难道是北斗的侄女吗?”
正当我准备踏上第一级石阶的时候,路边的灌木丛后突然冒出来一个穿着polo衫的男人。我先前完全没有注意到,动作凝固了一瞬。
“……是。”
北斗正是叔叔的名字。我故作镇定地与他握手。“您是柳沢先生吗?直接叫我忍冬就好了。”
“啊啊,你好呢。一路找过来还顺利吗?”
男人这么说着,迈开腿从灌木丛回到正路上。随着他的动作,几团影子也从那个地方蹿出,这时我才发现他另一只手里提着的猫粮。
“我记得你们事务所离这边还挺远的吧?内人担心你找不着路,所以让我在这里等。抱歉吓到你了。”
我露出公式化的笑容:“没有的事。”
“从这边上去就是我家了。内人今天和朋友出去玩了,不过日花里倒是在。她跟我们都不一样,即使有休息日也不愿意出门,总是窝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做什么……”
柳沢先生一边走在我的前面引路,一边向我介绍着家里的状况。他似乎是有意识地特意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转头看向我像是在确认我的状况。不愧是在野外工作的人呢,才走过了一半的石阶,我就有些喘不上气,完全没有做其他事情的余裕。
“如果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会儿吧。”
“抱歉……”
“没事没事。日花里也总是这样,经常抱怨我跟她妈妈为什么要买这里的房子。有时候还会撒娇让我抱着她上去。”
“这我可做不到!……我是说抱她上去这件事。”
柳沢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跟北斗也说了同样的内容,当时他回答我的是‘不如你也抱着我上去呗’。不过在那之前他就已经从这里摔下去了。我是在医院里和他说的。”
“……”
原来如此,难怪这对夫妻对我体贴得有点过头。破案了。
“北斗最近还好吗?我昨天才回到日本,还没来得及去看他。”见我休息的差不多了,柳沢先生再次迈开步伐。
“……挺好的,摔伤了腿之后沉迷玩转椅。办公室的地板被划得快不能见人了。”
“哈哈,日花里也有那样的时期呢。虽然很快就厌倦了。”
这个对话好像有哪里不太对,但我决定忽略这一点。
“您刚才说……‘日花里总是窝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做什么’?为什么会不知道呢?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小学教书,遇到的家长们都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些过度…”
“……关于这个,说来也惭愧。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千明,也就是她妈妈,没有办法像其他家庭那样一直在她身边……”
“所以回过神来就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我替陷入内疚的柳沢先生把话说完。
“算是这样。”
“那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单纯在你们不在的期间照顾日花里?还是……解决家庭内部矛盾?”
柳沢先生又笑了。
“只要照顾她日常起居就好,还有在学习的方面帮帮她……这个你很擅长吧?我当时说道这点的时候北斗就极力地向我们推荐你。这方面日花里也有些反常,比起玩乐反而对学业更加上心,尽管我之前说不清楚她在做什么,但多半都是在看书。”
我失礼地朝着柳沢先生的脸的方向盯了一会儿,很难想象这样的双亲会有一个书呆子类型的孩子。
说话间,我们终于爬到了石阶的最上面。
“到了。”柳沢先生直接伸手推开一间住宅的门,似乎原本就没有上锁。我跟在柳沢先生身后穿过前院,正在这时,一个古怪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牛奶拼图」这种东西呢?顾名思义,那是纯白的拼图。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将那个古怪的东西命名,我想那就是「牛奶魔方」了吧。可尽管二者都是益智类的游戏,进到小商店里也多半摆在同一个货架上,魔方却不比拼图,六面全白本身就使它存在的价值大打折扣。
资料上从未说过柳沢夫妇对行为艺术也有所研究。我的脑袋隐隐作痛。
那之后我就开始接手柳沢夫妇的委托。出乎意料地,柳沢日花里并不是个很难照顾的小孩。没有赖床的习惯,也不会吵着不去上学,甚至每天每日会按时间表——听柳沢先生说那是日花里自己制定的——规划日常生活。
先前也提到了,我上一份工作是小学的老师,不是没有见过自律的孩子,甚至其实,我小时候差不多也是这般模样。但叔叔听过我的汇报之后却神经兮兮地压低声音:
“你说,小日花里「打开」来该不会装着的是机械的内脏与设定好的程序吧?”
“……是要从哪里「打开」啊?!”我连忙拽住叔叔的领子,欲将违法的芽苗掐死在摇篮之中。
“只是打个比方、比方。说来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抬手看表,距离日花里的小学放学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差不多是该走到路口了。出于一些原因,我不太方便直接去日花里的学校接她,于是只约了在距离学校两条马路远的停车场见面。
“那我先走咯~虽然挺想看看那家伙的小孩是个什么模样的。”
我用凶狠的视线催促叔叔赶紧离开,奈何拄着拐实在快不起来,走到出口时,还与日花里打了个照面。这人最近康复了不少,好不容易拿到了外出的许可,几乎天天都会在这附近遛弯。
日花里看见我,微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自觉爬上了后座系好安全带。她一言不发,无论是为什么刚才的怪叔叔莫名其妙地冲她笑,还是为什么由我来照顾她的起居,甚至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在这里碰面,她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直到那一天。
我曾预感这份工作不会做太长,毕竟柳沢先生与我签订委托合同时是以周为单位续约,想来也是为了能够在离开的时候及时中止。果然,几周后我在去学校的路上接到了柳沢先生的电话:
“钥匙的话就直接留在桌上吧,我已经发消息通知日花里了。”
“我明白了。”
还好还好,不需要通过我去传达这个噩耗。我多少也猜得到日花里究竟在为何而苦恼着,可是很遗憾,我并不能为她做些什么。
——但是她会当面质问我这点却是我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做完家务之后辅导日花里的功课,快要到离开的时间时,小姑娘却突然趴了下去:
“…………为什么呢。”
我耳力很好,也正值壮年,非常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听漏。我并不认为日花里是个会因我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的孩子,这不合逻辑、也没有理由。如果这会儿她告诉我她其实是个害羞内敛重感情却不擅表达的人设我可能会汗毛直立。所以,我十分直白地“啊?”了一声。
“为什么连你也…!”
从书本上爬起来,日花里不满地瞪着我,我不由得伸手摸摸自己的脸,一头雾水:
“我?我怎么了吗?”
“我听见了喔。班上的家伙,说你是「英雄」、是最好的老师。”
啊。
好夸张!
秘密被揭穿可真让人害羞啊,但我不是会轻易脸红的类型所以没问题:“哎……?你搞错了吧?”
“……。”
日花里的眉头依旧锁得紧紧的,我可真怕她小小年纪就皱出抬头纹来。
“这样啊,你知道了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又不傻……倒不如说觉得瞒得住的人才是真的傻吧??”
唔,非要说的话应该是成年人的傲慢吧。我在心里默默纠正。
“所以呢?我在做便利屋的工作之前,确实是在你们学校当过实习老师啦……而且特别巧教过你的班级……但那又怎么样呢?你该不会是怨恨我没有告诉你学校的八卦吧。”
“……。”
“而且我申明一下,我并没有隐瞒的意思。没有说只是单纯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值得一提了。”
“……。”
“呃,反正你明天就转学了那我姑且悄悄告诉你哦?其实你们班主任五年前上过相亲节目,那会儿他还是个地中海。”
“那种事怎样都好吧!”
似乎终于厌烦了我生硬地扯皮,日花里忍不住呵斥出声。但我可不是为了转移话题就诋毁他人名誉的糟糕大人,刚刚的八卦绝不是我临时瞎编的,有视频为证。
整点的钟声又敲响了,是该道别的时间了。我将辅导材料摞成一摞,将橡皮屑从桌面扫进垃圾桶:
“虽然不知道你听说的是什么内容,但是抱歉啊,我想我并不是你期望中的「英雄」。”
“……。”
“我是不会「救」你的。”
“……。”
“……。”
我差不多对解读省略号的游戏失去耐性了。于是日花里终于开口:“……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不是教师了。”
“这没有关系吧!”
“有的哦。就像名人在外要注意举止一样,教师在学生面前也必须伪装自己啊。把糟糕的、市侩的、势利的一面藏起来,只展露世人所认为的「好」的一面。我帮那个孩子作证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已经超时了,我放弃打太极,准备速战速决。
“…可是……………”
“可是,就算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怎么会有人做出简直就是自我牺牲的事情,对吧?可事实上,我本就临近试用期尾声,也并不打算留在那所学校里,做这种事也不过是顺手罢了。
“你也别误会了,我并不是找不到工作才来接照顾你的委托。但说到底我只是负责照顾你的起居偶尔辅导一下学习而已。其他方面…像是处理家庭内部矛盾,这并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我应该已经拒绝清楚了吧?日花里的学习能力不错,我想她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差不多可以放我走了吧?
然而日花里的反应还是出乎了我的预料。
她说:
“我知道了,给你钱就是了吧。他们雇你的时薪是多少?”
「他们」指的应该是父母吧。我随便比了个一般小孩应该给不出的数字,然后就看见日花里拉开抽屉,从一沓钞票里抽出几张:“给。”
“……你要委托什么?先说好,离家出走之类的计划我可以帮你做。但我只提供计划,协助实施要加钱。”
“我只是想要普通人的人生而已。或者让我爸妈变得普通一点。”
我把几张纸钞都塞了回去。
“许愿的话我比较建议你去神社,那里只要五円就够了。”
“这就是你对雇主的态度吗。”
“你适应得倒挺快。说到底,你认为的普通究竟是什么啊?”
日花里没有回答我,托着腮陷入了沉思。她似乎没有注意我,这或许是个溜走的好时机……不过,还是算了。
窗外传来猫的声音,我已经过了装成猫回应它的年纪,倒不如说,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阶段。日花里或许也是这样,还有这世上不曾见过的千千万万个孩子,这其中应该也有一定比例因为某个原因从未学过猫叫。
“总之……就是像普通人类一样……”
半晌,日花里没什么自信地小声给出了个有些奇怪又像是什么也没说的答案。她看起来不太知道怎么用语言准确解释清楚。
我有些好笑,同时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少女时期的柳沢千明。于是我下意识脱口而出:
“可是直立行走的猫才更加奇怪吧?。”
“?????”
再后面的对话我记不太清了,或许我解释了些什么、或许也没有,毕竟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教师,也终究无法担任育人的工作,正因如此当年才会选择及时止损。所以我想,我应该没能给予那孩子什么有价值的指导吧,只隐隐记得自己似乎最后说了句,“与其怨恨为什么没有成为人,不如就按照猫的方式前行吧”,但她是否听得懂这种比喻,我却无法保证。
再后来我就没和柳沢家接触过了。听叔叔说,在搬到新的城市以后日花里似乎还曾写过几封信给我,但因为他不小心把「日花里」这个名字和我教师时期班上的小孩搞混,所以直接帮我丢掉了,于是也便不了了之。
怎么样,这是个很无聊的故事吧?
忍冬说完这句话,将马克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她身边的人——也就是她现在的监护对象,则将烤串的竹签当成指挥棒在空中划着规律的轨迹。
“哈啊……真是无情呢。”
“是吗,我反而觉得,免费延长工作时长已经仁至义尽了喔。而且这还超出了我的工作范畴。”
“别~那么死板嘛!”
英气的女性直接上手去戳忍冬的脸颊。或许是酒精发挥了作用,忍冬一时没能躲开,只能任其随意揉捏。好在对方很快就停下了:
“……啊。”
忍冬朝着同伴发愣的方向看去,电视里女主播正在播报夜间新闻。她的声音埋没在酒馆的嘈杂之中,只能看见底下的标题打着「真藏学院97级入学名单新鲜出炉!」的字样。
“真藏学院……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吧?”
“啊是。说起来,今年也到了公布新生名单的时期了啊。”
忍冬随便敷衍了两句,然后又点了一杯啤酒。她抱着杯子,鼻腔里充斥着令人心醉的香气,正想押下一口的时候,胳膊冷不防地挨了一肘。
“阿冬你看。”
“什么啊。”
忍冬眯起眼,再一次朝着电视的方向看去,然后,她整个人都僵住了。
——「超高校级的酒店试睡员,柳沢日花里」。
猫找到了它的路。
=====
两年前一时兴起脑的故事,最近突然又想起来,在完全不记得我当时到底想表达什么的情况下顺手给摸完了。
我讨厌说教的情节,也努力想减少&避免,但好像不太成功。要说的话,忍冬也不是最适合说教的人,不必勉强x
是的不必勉强,日花里最后还是长成了肆意妄为的孩子,我想这或许就是她过早的意识到了自己注定与众不同,不必勉强和别人一样,不读空气、不看眼色、不试图融入。但她本质还是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是了。
死得早想补全只能补点以前的事情了,但我又觉得写爹妈好无聊喔所以用了日花里的某个时期里的短暂过客为主角进行叙述,这么任性真是不好意思——虽然没有真要道歉的意思嘿嘿。以及我还蛮钟意纯白魔方的梗的~本篇没有实现好遗憾啊!
那么最后还是,感谢阅读!有缘再见!(……)
那天晚上,索菲亞·查普曼決定穿上她最為滿意的裙子和大衣去參加舞會。等她化完妝時,乳娘已經有些等不及了,站在她房間門口敲了第四次門。
“小姐,那小子已經來了有半個鐘頭了。”
“叫他再等會。”索菲亞站在她的鏡子前,開始挑選合適的女帽,紅色的太張揚,黑的顯老氣,她有點挑不過來,“他沒急吧?”
“倒是沒有,坐在客廳裡看書呢。您看我要不要給他點喝的?”
最後她挑了一頂紫羅蘭色的,這正是令她滿意的答案,她在鏡子前擺弄了一下帽子,覺得合適,於是便高聲回到:“不用,到了晚上有他喝的。”乳娘似乎明白過來什麼,很快就下樓了,從樓道傳來中年婦女重重的腳步聲。
索菲亞又花了點時間檢查了一番,才算打扮完了。等她輕巧地走下樓梯時,乳娘已經點了燈,她的舞伴蓋因尼斯·坎貝爾坐在沙發上,正看著一本雜誌,看到她來了,抬起眼睛來笑了笑並起了身。
蓋因尼斯·坎貝爾身材高挑,一頭紅髮,時常瞇著眼笑,給人種狐狸似的感覺,但你要是和他對視,他又會用年輕人真誠的眼睛看著你,正因如此才不會叫人覺得猥瑣。他出身英國,是哪個沒落貴族的小兒子,至於具體是哪個,索菲亞並不在意。她也知道,蓋因尼斯身上出過不少流言蜚語,可哪個都沒鬧大,以至於到後來人們都忘了他所謂的緋聞對象是誰,不僅如此,這些緋聞還為他本人平添了點奇特的魅力。誠然,他不是最佳的舞伴候選,可也不是最差的,至少在索菲亞能接觸到的人裡可以排個亞軍。
“在看什麼?”索菲亞問他道。
“這個月的《克萊爾》。”蓋因尼斯答道。
他們上了車。乳娘在門口看著他們離開,索菲亞看著她黝黑的皮膚化成路燈下一個剪影。蓋因尼斯話不多也不少,恰好叫他們不至於限於尷尬沉默的境地。等他們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天已黑魆魆的,蓋因尼斯為她開了車門,好叫她不必。
“挽著我的手。”索菲亞說。
“遵命,查普曼小姐。”他照做了,但兩人身體間恰好隔著一拳的距離。他們受到宅邸主人歐文·達德利的招呼,迎接他們的還有侍者手上的香檳,前者很快就對這兩位年輕的客人失去了興趣,轉而招待其他人了。此時,第一支舞還沒開始。
“你哥哥亞伯拉罕為什麼不參加舞會?”索菲亞因為酒精洩了口氣,她倚在希臘柱上,匿在蓋因尼斯身後。他們倆看著處在門口的達德利和招呼來的客人。來人也是一對舞伴,女人黑髮,帶著一頂漂亮的帽子,男的還很年輕。
“藝術家天生內向,不過我想,他本想邀請一位小姐的。”蓋因尼斯眨眨眼。索菲亞不大相信,但這話聽起來頗為受用,她因此稍稍恢復了些活力。
“那他該親自來,而不是讓他的弟弟過來代替他受氣,他的畫怎麼樣了?”她問。
“來靈感了,去了康尼島。”蓋因尼斯側過臉去,望著不遠處喜形於色的達德利,“那位小姐是?我第一次見。”
“是太太,霍爾·詹姆斯先生的夫人,她開了一家帽子店,我的帽子也是從她那裡買來的。很漂亮吧?”索菲亞道,她的男伴聳了聳肩。
“確實漂亮。”
那兩個初來乍到的客人進了舞廳,詹姆斯太太走路的步子十分優雅,像只高傲的貓,達德利則是隻聒噪的鴨子。至於年輕男伴,看起來雖然清秀,卻沒什麼存在感。
“當真?”
“嗯,人和帽子都是。”蓋因尼斯說,索菲亞被逗笑了,她不好意思地推了推蓋因尼斯,前者沒收了她的酒杯,讓侍者拿走了。
“聽說她在和她丈夫鬧離婚呢。”
舞會已經開始了。詹姆斯太太的男伴欠下身去,邀請他的女伴起舞,兩人的動作自始至終帶著種生分的遲緩。蓋因尼斯意識到那份距離感反倒使她顯得更為高貴,又或相反,因為她本身的高貴而產生距離,畢竟,人怎麼會因為同伴的生分而顯得高貴呢。
“怎麼說?”蓋因尼斯問索菲亞道。
顯然,他的女伴精於此道,但偏要裝作一副不甚了解的樣子,好留下一個好印象:“我平時對這些不怎麼感興趣,這件事是從我朋友那裡聽到的——詹姆斯先生沾花惹草,給詹姆斯太太丟臉了,可那位太太也不甘示弱,一來二去鬧得啼笑皆非。”
“可她看起來並不像是丟了臉的樣子……罷了,並不重要,您願意和我跳舞嗎?”蓋因尼斯伸出一隻手來,隔著手套吻了索菲亞的手指,後者咯咯笑著應了他的邀請。
“當然樂意。”
他們進了舞池,蓋因尼斯引導著索菲亞在人群中起舞,他跳得快活優雅,在那些隨著音樂地甩動四肢的美國人中顯得獨樹一幟,把舞伴也襯得粗俗。索菲亞緘默不語,頻頻踩上他的腳,不知是因為技藝不精還是出於報復。
在不協調的小號頻頻衝破薩克斯風的旋律後,蓋因尼斯開始放慢腳步。他不經意間瞥到了站在酒席上的太太。這次有了點新發現,一是詹姆斯太太的頭髮其實是暗紫色,只是因為光照容易看成純黑;二是她的高貴一般來源於神秘感,一般來源於一個他未踏足過的領域——兩者常被混同,但本質上相差甚遠。
他的好奇還未滿足,詹姆斯太太的視線便追了過來,這讓他出於禮貌移開了視線。恰巧,索菲亞踢了一腳他的小腿。蓋因尼斯並未追究,他照例以一拳的距離若即若離地環著索菲亞的手臂,兩人從舞池的中央旋轉著來到無人注意的角落。
“你哥哥,亞伯拉罕他擅長跳舞嗎?”索菲亞問,她在最後一段薩克斯風的獨奏中轉了個圈,他配合著做完了一切,隨後樂聲在一聲犀利的長音中戛然而止。顯然,這才是她真正關心的問題。
“沒我擅長,但也不錯。”蓋因尼斯眨了眨眼。
“你太惹眼了,搞得我有點緊張,於是跳得更糟。罷了,待會兒要是有人邀請我,我就繼續跳。”
她散伙的信息已經傳達得很明顯,他也就沒必要糾纏了,更何況他本就是為了頂替自己的哥哥邀請一位小姐才來的。蓋因尼斯於是走出了舞池,他聽到薩克斯風和小號變得更為悠揚。在明亮過頭的燈光下,詹姆斯太太還站在那兒看著舞池,她蒼白的臉上帶著一種虛浮的微笑,一如隔著一層薄霧。
蓋因尼斯深吸口氣。或許他該去問問那位太太——很難描述清楚是什麼驅使他這麼想的,間歇是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好奇心。如果他被拒絕,那也無甚不可,當然最好是被接受。她沒跳第一場,但氣質應該會很適合交際舞。蓋因尼斯這麼想著走了過去,在那位夫人面前鞠了一躬。
“詹姆斯太太,請讓我邀請您共舞。”
“不需要用那個姓氏稱呼我,那太生分了。”她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多爾瑪麗,他們通常這麼叫我,當然……只是太太也可以。”
他意識到她並不喜歡那個姓氏代表的含義,這反倒讓他產生一種怪異的歸屬感:“那麼多爾瑪麗小姐,請讓我邀您共舞。”
他伸出一隻手,多爾瑪麗答應了他的請求,女人的指尖帶著股淡淡的煙草味兒,但並不像那些男子的煙味那般味道粗俗,反倒有股甘甜的香氣。在達德利金碧輝煌的大廳裡,又一首新舞曲演奏了起來。他們跳得很緩,像在熟悉彼此,又像似曾相識。他環著多爾瑪麗的臂膀,在對方裙擺的旋轉中意識到了什麼。
他知道他對她的好奇源於哪兒了,二十四年,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人——不光是出於她的神秘。他生在歐洲,見過無數故弄玄虛的吉普賽人,滿腹經綸的神父,還有那些因瘋狂而無法理解的人,他們都是神秘的,但她不同。常人神秘是因為他們是未經開墾的處女地,而她本身便處在另一個世界。即便他再探尋下去也不會找到什麼結果,他有這種預感。
在不斷盤旋的音階、在逐漸趨於高潮的旋律中,他看到她的眼睛,她也在看他。多爾瑪麗有雙奇異的綠色眼睛,或許是之前離得太遠了,他現在才注意到這點。他聽到有人在驚呼窗外遙遠的煙花秀有多漂亮,可他並不那麼在意了。
“您的眼睛很漂亮。”他說,幾乎是句脫口而出的無心之言,多爾瑪麗笑了笑,拉著他的手完成了一個漂亮的旋轉,她跳得很好,優雅又充滿生氣,並不像一般的美國貴婦那般單純地隨著樂曲擺動手腳。
“抱我。”多爾瑪麗命令道。
“那您能只看我嗎?”他笑著討價還價,卻還是照做了。多爾瑪麗的腰沉在他的手臂上,她看向窗外的夜空,潔白的脖頸因為舞蹈的動作成了長弓似的曲線。在她身後,龐大多彩的煙花頻頻綻開,卻奪不走一點他的眼神。
也在此時,管樂到達了樂曲的頂峰,隨後便極快地衰弱了下去。人們在一場舞內飽脹的感情就像戳了氣的氣球那般消失了,又是短暫的休息,舞會的男女們再度互相交換起自己的舞伴。
這可能不妙。他想,多爾瑪麗鬆開了他的手臂,輕輕拍了拍他的胸前。他朝對方鞠了一躬,並吻了多爾瑪麗的手。隨後,他意識到有什麼自己的胸袋裡多了些什麼東西,他急忙將其和胸袋圈一同取了出來,卻看到意料外的東西。
那是一張名片,上面寫了一間衣帽店的地址,除此之外,就只有“多爾瑪麗”的署名。他呆呆地看了會兒那張名片,一抬頭卻看到那位神秘的太太已經走遠了。正當他愣神的時候,達德利用粗厚的手掌拍了拍他的後背,即便相隔不近也能聞到酒氣。
“蓋因,蓋因,來不來玩賭酒飛鏢?”
“當然。”
他坐上沙發,在一夥醉意盎然的紳士間笑著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隨後將空了的酒杯給了侍者。跟著一同脫手的還有達德利遞來的飛鏢。
那一擲正中靶心。
亞伯拉罕的腦袋被他打得碎爛。
人是死透了,一點呼吸都沒有了,用亞伯拉罕自己的話來說,死得不能再死。當然,亞伯拉罕現在也沒什麼話可說了。他低下頭去看著那具尸體,有些想發笑,但天氣太冷了,笑容在半途成了雙唇間一道扭曲的縫兒。
大街上冷冷清清,什麼人都沒有,夜色恰好成了塊骯髒的遮羞布。他在黑暗中看了一會兒那東西臉上的血窟窿,想起曾經還有人稱呼這東西為美男子——曼哈頓的太太小姐們似乎挺喜歡這張臉的,尤其是查普曼小姐。他常聽到有人稱讚這張臉有貴族氣質,可當一個人的五官上有個大洞的時候,再有氣質倒也看不出了,更何況亞伯拉罕的雙手不會再作畫了。這還不夠,他又用刀子破壞過了亞伯拉罕的五官才稍稍放了點心,這個行為並沒有給他什麼特殊的感覺,只讓他想起前幾天在晚餐前剁過的肉。
他甩了甩手套。晚冬讓尸體僵得很慢,可最初的血已經乾了。早些時候,他費了點力氣把他哥哥那頭被貴婦們讚賞的銀色長髮剃了下來,現在看著尸體光溜溜的腦袋,他開始覺得自己手藝不錯,或許可以考慮哪天去學學剪髮,畢竟理髮師永遠不會失業。他頗為幽默地為自己加上旁白。
他把石頭綁在曾是亞伯拉罕的肉塊身上,將之推入河流。隨著一聲激起浪花的巨響,尸體完全隱匿在夜晚奔騰的水流中,一如沉入黑暗本身,一同消失的還有他投在河上的倒影。
“晚安,做個噩夢。好好在地獄畫你的油畫吧,我的兄長。”
他又能睡個好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