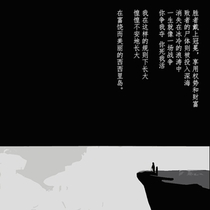1.埋火: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678/
2.残灰: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835/
想听BGM的话:http://music.163.com/#/m/song?id=16666729&userid;=79152045
手上黏糊糊的,沉甸甸的责任和恐惧压得奥瑞斯喘不上气,他既害怕这个经由己手的病人死去,又害怕她的死被怪罪在自己头上。
如果这个笑眯眯的女人死了,卡莱瓦和项远会怎么对自己?杀之用以泄愤吗?他开始浮想联翩,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腿上的血止住了,可是还是不行……不行!”奥瑞斯漏出一丝哭腔。
还有哪儿在流血?还有哪儿在流血?!他的手悬在半空犹豫着,不知众目睽睽下该不该脱掉风行衣服仔细检查,“腿骨也有问题,怎么回事,明明刚才还在走!”
项远把后备箱盖拆了,脸贴在玻璃上吼叫着,此刻忽然露出愤怒的表情,一拳捣碎玻璃,伸手揪住少年衣领!
“我操你妈的!骗老子?!”项远表情狰狞,血染在扭曲的五官上,如同恶鬼,“她死了你也别活了!!”
奥瑞斯无声地飚出泪来,心想自己真是委屈万分倒霉透顶,可又不能跟这些王八蛋讲道理,气得浑身发抖。
“哭!哭有个屁用!”轿车一路飞驰,连闯红灯,项远的吼声飘落在风里,两侧的行人投来诡异又好奇的目光,而车后是被抛下的刺耳鸣笛。
奥瑞斯一辈子没这么刺激过,也没这么被恐吓压榨过。一时间悲愤压过恐惧,他挥手推开项远,大声咆哮:“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她死啊!我为什么要害她?!我也想救她!我也想救她啊!”
我也想救她啊!奥瑞斯无声地呐喊,他想起母亲去世时悲苦无力的自己,那时他还是个因为什么也做不到谁也救不了而哭泣的孩子。之后很多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手上终于有了些力量,直到现在,他猛然发现自己依旧什么也做不了,他还是那个只会发抖的废物啊!
奥瑞斯暴怒起来,这怒火大多是因为自己的无力,他在愤怒中全力一击,把项远推了个趔趄,差点栽到车外。
项远跌坐在后备箱里,抬头看着那张满是泪痕又稚嫩的脸,愣了半晌,突然间勃然大怒。
“我操!”他几拳把挡风玻璃敲成撕烂,攥住奥瑞斯衣领,腾一下在疾驰的车上站起来。
“你敢推我?”他杀气腾腾提着奥瑞斯,眼里全是疯狂,“你也敢推我?!”
灯光投落下来,又随着呼啸的风逝去,光怪陆离的颜色在项远脸上变换着。奥瑞斯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项远在一个人死去的声音里无所事事,他既不恐惧也不慌乱,甚至没有卡莱瓦面对工作和生命时的肃穆。他只是不耐烦地望向门外,希望这段无聊的时光赶紧过去。
奥瑞斯想这个人根本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也不是那种能感同身受的人,他发愣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眼中的弱鸡敢推自己,而不是因为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他。他是个疯子,身上毫无人性。奥瑞斯觉得只要现在自己再多嘴一句嘴,就会被项远从车上抛出去。
轿车已经驶出了黑塔区,进入了空旷无人的大路,项远可以毫不犹豫丢下奥瑞斯,一丝顾忌都没有。
“有种你就试试。”奥瑞斯没敢这么说。他敢,他真的真敢,他的眼神这么说了。奥瑞斯好不容易鼓起的一丝勇气在冷风中吹散,半张着嘴,不知如何是好。
“放下他。”卡莱瓦说。
“你算老几?”项远瞪着搭档。
“我让你放下他。”
“要是我不……”
轿车猛地刹住了,项远骂人的话来不及出口就被惯性扔向前方,他抓了一下窗户边,破碎的玻璃上流下一道血痕。青年身子顿了下,还是被甩出去老远,维拉缇丝眼疾手快扑向后座,一只手抱住风行,又一只手接住从窗户里掉进来的奥瑞斯。
趴在地上的项远动了下,慢慢站起来,虽然灰头土脸,眼神却亮的吓人,像头发了凶性的狼。
“我……干……你……母……”他一步步走向驾驶座,砰地踹在门上,“给我滚下来!!!”
黑洞洞的枪口从车窗里探出,项远身子微微一僵。
卡莱瓦从车上下来,枪戳在他下巴上。
“我滚下来了。”壮汉仍旧严肃沉稳,“BOSS说了带上他,那么就要带上他。”
风行在寒风和冲击中悠悠转醒,费力地看了眼两人,有气无力骂了句脏话。
维拉缇丝叹了口气:“你们boss需要医生。”
“别惹事,别浪费时间,乖乖回后备箱。”卡莱瓦收回枪,“我们去医院。”
“求求你们用大脑做事。”风行轻声细语,这不是因为临死所以要展示一下不为人知的温柔,而是身体状况只允许这样。又不是拍肥皂剧,离她最近的维拉甚至能感受到少女语气里的仇恨。
“医院不能去,就那么几家医院,肯定都有叔叔的眼线了……你们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
“门诊和那些黑医肯定也被他盯着呢!你谁都别找了,等死吧!”项远咆哮着。
风行皱着眉偏过头,把脸埋进维拉肚子里,等他声音落下,才嗡嗡说了句真吵。
“去我家吧。”奥瑞斯抹了把眼泪,“我家有工具,我知道哪能联系到安全的医生。”
项远蹲进后备箱,车子又动起来,奥瑞斯跟终端那头的人说着什么,大惊小怪的声音从通讯中漏出。
“喂喂?奥瑞斯吗?!”
“是我……”
“你上哪去了!不是说好今晚来接我吗!”
“你声音小点!”奥瑞斯觉得头疼,“出了点意外。”
“哗!我这边出了很大意外好吗!我跟你讲刚才酒店里有黑帮火并,莫名其妙突然就打起来了!不行了这里一刻也不能多呆,你把地址发来我直接去你家躲躲……不是我怕啊!是我身边还有女士在,怎么能让女孩子处在危险中呢……”
好的好的,我正要你去。奥瑞斯在心底默默地说。
“记得把你身边的女医生也带着,有病人……钱?肯定不缺你钱啊。”奥瑞斯看了一眼这群人,“只要保证病人不死,绝对不会少你钱的。”
冷风从车窗破开的大洞里灌入,风行皱着眉,心里诅咒起项远,意识又开始模模糊糊飘走。
真冷。她想。啊对了,今天除夕,难免下雪啊……
“我劝你这次别睡过去了。”
流淌的风被阻了一下,她睁开眼,看见维拉接过项远递来的外套,盖在自己身上。项远背对自己,狠狠一个激灵,又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
“操,这么冷。”他小声咕哝着,紧紧咬着烟。
“我给他的。”维拉说,“稍微暖和一下。”
卡莱瓦开大空调,把自己的西服脱下,递给了项远。
“你他妈没有眼力见啊!刚才直接给大小姐不就是了!”项远骂骂咧咧的。
风行没力气再纠正“要叫老大”,她的新雇员搓了搓手,交叉双手在腋下暖了会,接着从衣摆下伸进手来,摸索着哪里还有伤口。
她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气,维拉了然地收回手。
“不是很严重,大概在肠子附近,打穿了,但是没伤到脏器才对,不然你坚持不了这么久。”维拉从腰包掏出随身带的止血凝胶,涂在手上,“因陋就简,将就下吧。”
“奥瑞斯。”风行忽然说。
“什么?”奥瑞斯惊了下,挂断了正在通讯中的终端。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车里是你。”
男孩没有接受道歉,而是沉默一会。
“如果不是我,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是吗?你不介意为了自己杀一个无辜的人。”他等了一会,都没有等到回答,抬头看去时,风行已经闭上眼,又一次陷入沉眠。
风行是被巨大的嘈杂声吵醒的。
一路上她都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维拉不停问话,她不知道自己回答了没有,如果有回答了哪些。只记得被带下车又进入温暖的房间,柔软的床铺让疼痛都不再清晰。其实她这辈子还真没怎么好好睡过床,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路上,仿佛大半人生都在旅行,在井都的山道中,在中心城的货机上,在尤金的风雪里。空艇列车风餐露宿轮换来,小时候跟着兄父颠沛,长大了一个人流离。
项远点起的烟味始终萦绕不去,可他只抽了一根,那味道早该散去了。
嘈杂的噪音越来越大,最后清晰地冲进耳朵里。
“你看什么看!我***,大小姐是你能看的吗!”项远和黑皮金发的男性对峙着,对方高了他一头,也壮了他一圈,笑嘻嘻地摸了摸青年头顶。
“我就看了,怎么着?”男人推开他,目光落到床上,“皮肤是挺白的啊。”
风行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自己,上身赤着,被血糊住的裤子右腿由剪刀拆开。放在平时,她不会在意这种挑衅,与其说大度,不如说没这个意识。小时候她跟着商队,总觉得自己和男孩没什么区别,夏天赤膊去水边乘凉也不是一次两次。但现在风行只觉得累,她盯着天花板,疲惫地开口:“卡莱瓦。”
卡莱瓦猛地站起,身边用来包扎的东西嘡嘡啷啷掉了一地,他也比黑皮高了一头,壮了一圈。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项远把枪上膛,双眼发红,黑色金属哒哒戳着对方脑门,“枪不响我喊你爹。”
“别、别……”奥瑞斯急得跳脚,在三人旁边举着手,不知所措,“古尔!你开玩笑不分场合么!”
“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古尔闭上眼,也不知是忌惮哪一位,“非礼勿视我懂我懂,放松兄弟……”
“这是古尔,医生就是他带来的!”奥瑞斯求救似的看向风行。
医生没有理会正在上演的闹剧,她在检查奥瑞斯给她的工具。
“要打去外面,不要妨碍我工作。”女医生说,“要是在我自己诊所,你们全都要被踢走。”
“滚出去。”风行精疲力尽,“枪放下。”
卡莱瓦勒着古尔脖子出去了,身后跟着项远,房间里顿时清净。
维拉看着风行:“子弹卡在你腿骨里了。”她顿了顿,让风行心里一阵不祥。
“这位医生叫阿朗。”
“别转移话题,想说什么就说吧。”
“但是奥瑞斯家里没有麻醉剂……”
那双蓝眼睛又闭上了,主人痛苦得想要嚎叫,最后却只能低声呻吟,“放我死吧!!”
“医生不会放弃病人。”阿朗拿着刀,低头看向风行,她皮肤本来就黑,此刻背着灯光,脸上像罩了层凶恶的黑气,“忍着。”
刀子镊子比话音更快地落了下来,维拉眼疾手快上前摁住,手下一股巨力弹起。
“放松!放松!”阿朗厉声说,“这样不行!”
维拉扭头看向风行,对方大张着嘴,却没有一丝声音,也不知道是忍住了,还是实在没力气,手倒是紧紧拧着床单,青筋暴起。
“长痛不如短痛。”阿朗深吸口气,“你是跑商队的吧,不想这条腿废了就忍着!”
“狗日的项远!!!!”剧痛让人回光返照,风行脖子上血管凸起,开始痛恨这个让自己脱离昏迷的手下。
阿朗手上用力,伤员忍了十几秒,再次嚎叫起来。
“不行不行松手!腿废了就废了!我去装义肢!”
“行了!”
“什么?”
“行了。”什么东西掉进垃圾桶的声音传来,阿朗拍了她肩膀一把,“已经取出来了,但你还是要去趟医院,这里条件太差了。”
风行惊魂未定,她用了三秒沉默:“维拉。”
“嗯?”
“门外安静好久了。”
“是啊。”有人推开门,客厅里林林总总站了十几个人,卡莱瓦趴在地上,项远抱着头蹲下,古尔高举双手开始嚷嚷“我是无辜的我不认识她”,奥瑞斯缩在古尔身后哆嗦。
阿朗知情识趣地退到窗边,举着手为自己辩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她们找来的医生。”
“很对,小姐,别找麻烦。”来人赞同了阿朗的举动。
维拉绷紧肌肉,可雇主悄悄扯了她衣服一下。
风行偏偏头,看着来人叹了口气:“高乐贝拉,你果然找来啦!”
“闻着你血的味道,我找来了。”
维拉缇斯上前一步,风行喝止了她。
“就是这样,女士。”高乐贝拉满意地笑,“轻举妄动不是上策,先生知道你是司烛,所以才会派我来。”
“是吗,生怕我还活着啊。”风行笑起来,“我今天才招募的猎人,你们立刻就知道啦!”
“在酒店追砍你们的头领派人来见先生,说‘有个司烛猎人在帮她’。”高乐贝拉抹着刀,“听说能力罕见又棘手,但凡被你泼出的液体触碰,立刻就会冰结。”
维拉缇斯愣了下。
“靠!给我根烟抽!”项远叫起来,被人一脚踢在肚子上。他跪了半天,吐出口血沫,低声嘀咕起来,“不给就不给,真他妈小气。”
项远又被踹了一脚,但他直愣愣的瞪着自己老大的新雇员,维拉缇斯心领神会地苦笑起来。
“我也想抽烟。”她说,“我一直有烟瘾。”
高乐贝拉点点头:“请便。”
打火机闪了一下,维拉取到了火种,她叼着烟退开,风行又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原来不是项远在抽烟。她想。是维拉缇斯啊。
“叔叔不是刚和尼科拉诺谈下一笔生意吗。”风行说,“今天两家人共进晚餐,你难道不去尽尽保镖的职责?”
“晚宴就在先生家中进行,安全且愉快。但是有人中途插入,说你命不久矣,先生听了忧心,让我来替他看望你。”
“看望我?”风行冷笑起来,“是不是要送送我?”
“你有这自觉最好了,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风行心想阿爷阿奶早就死了。
“你父亲死了,该成为领队的是他弟弟,不是一个任性疯癫的大小姐。”高乐贝拉从部下手里接过刀,向她走来,“为什么你不懂得自觉离开?”
风行死死盯着对方眼睛,眼珠随之转动,对那寒光闪烁的骇人钢刀却看也不看一眼。
“叔叔竟然没有亲自来,尼科拉诺的生意比我的生死更让他挂心吗。”
“我来就够了。”高乐贝拉说。
“可是只有你,有些事就不好办了。”
寒光在灯下一闪,钢刀深深斩进少女左臂里,这次她没喊叫,只是浑身发抖,落下大颗的汗。
“你让卡莱瓦弄死我兄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被剁得面目全非?”高乐贝拉看着那张脸变得煞白,露出仇恨的神色,又感到一丝痛苦。
“你父亲和哥哥都死了,你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提着刀站在床前,血顺着刀锋落在地上,“今天除夕,下雪,好日子。去陪陪他们吧,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圆。”
>>>
最开始是一片蝉鸣。
然后有雨声。
再后来便有了歌声。
>>>
绊踮着脚推开房间的窗,人群的熙攘声与阳光一并涌进她的怀里。
她呼出一口浊气,睁着眼等着一趟从远方疾驰而来、又向远方疾驰而去的风。她喜欢从风中听到各色的声音。
然而有东西在声音之前来了。那是一条极漂亮的方正型织物,红绸作底,上面的丝线在阳光下映出细碎的金光。不知是从哪家小姐的手中滑出,随着风直撞进绊的视线里。
绊睁大双眼,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只是风果然是朝远方去的,那织物在她眼前闪了一瞬,便被带去了更远的地方。
绊的手顿在半空中。眼还跟着那片红色走着。
她不是目力极好的九十九,那种忽然入目又转瞬即逝的美震慑了她,让她只是呆立着,睁大眼睛望着,最后那些精美绝伦的绣线在她眼里只剩下那片大红的布,迎着光吹成啪啦啪啦的风声。
过往也这样,粗略一看似乎都是崭新的,但只要微微呼一口气,就能嗅到模糊的尘埃味道。以为鲜明得如同正红的光景,经年之后细细看去,才猛然知晓那片美好在脑里也只剩下这个色块了。
红色。她看着那个色块施施然远去。可纵使它只模糊成了一个小点,那也是极其灿烂明艳的,张扬不羁地,纵横驰骋在一切暗影之上,连岁月也无法阻挡它的鲜明,再重的凡尘也无法将它熏染。
绊摸了摸自己的脸,她的脸上也有这样的色彩。
你为什么脸上留着红痕?
你为什么化形成人的样子?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人?
岁月在她心口模糊不清地呼啸而过。
>>>
绊知道“逝去”。像晶莹透亮的雪花本在空中盘旋,却在猛一刻落在了地面上,化成水,而后化成空气。
逝去是无奈且冰凉的。
它那时候已经习惯了雨水顺着膜具的弧度流下,也知晓了“逝去”的含义。老迈的人就如同过了花期的樱一样飘落而下,腐化成泥,再也不会归来。然而,当它第一次直面“逝去”所见的场面,却没有樱花坠地的柔软。
那是废弃的神社,和逃亡的武士,以及倾泄的雨。
冷铁之间相抵的声音令人心慌,寒光之下武士的表情模糊不清。他的双手颤抖着,胡子颤抖着,刀也和他一起颤抖着。
刀终于不堪重负般地碎裂了,那一声刺耳的锐响让面具悚然。孤狼临死前的鸣叫也不过如此,半似咆哮半似哀嚎,然则这声音都太过微弱了,听不清是否含有更多的不甘,悔恨,惊惧与茫然。 它只是碎裂了,并发出了相应的,最后的碎裂声。
面具听到那属于刀刃折断的声音,那一刻面具以为是自己碎了。
而后那个本握着刀刃的人就在她眼前倒下。
破碎了,就和他的刀一样。武士悄无声息地伏在草丛中,口鼻掩入泥中。刀碎之后他没有再发出一丝声音,好像他的刀最后的悲鸣便也是他最后的吼声。
人呵一口气都能变出雪花的天气里,器物与人一并悄然而去。刀本诞生于烈火中,匠人们悉心捶打他们,拿着铁锤的手臂流淌下汗珠。 这之后的刀身沐浴温热的鲜血,最终却葬送在了一夜冷雨之中。
这就是它直面“逝去”的场景了,不是顺应自然规律而凋落,而是血的热气在雪天中氤氲缭绕,最终冷却消逝的残酷。
而当它自身经历“逝去”时,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当刀碎裂之时,作为器物,同为器物,面具在那一刻几乎是怜悯起了这把刀,它碎裂得壮烈,也碎裂的难堪,尸身留与一地血水里,昔日的锐利被污泥浊水尽数抹消了。
可当她跌落的时候,只有属于泥土的一声轻缓的叹息。刀还曾经为人所用,面具只剩得一片空落,甚至连一声绝然的碎裂声也发不出来。
失去了俯视的视角,她仰望着这个她本该熟悉的神社。
黄铜铃铛不知所踪,再猛烈的风也摇不起清脆的声音。雨水从屋顶的缝隙中悄然潜入,半途被废弃的蛛网们拦截,挂在上边摇摇欲坠地映着惨淡的月光。
自神社衰败之后,她也终于掉落了下来。
雨又落了下来。一片冰凉之下,面具再也看不到任何事情。
意识机械地转动。
她想起了“诞生”。
>>>
“诞生”是温暖的,热闹的。
当匠人落下了第一笔时,面具拥有了第一缕意识。最开始只有触觉,柔软的触碰着她,环绕着她,包裹着她。紧接着是听觉,一开始满是树叶厮磨似的沙沙声,最后只有人绵长的呼吸声。然后是嗅觉,气味们在阳光与尘埃中与她窃窃私语,但它当时还不明白那些都是什么东西的味道。
最后是视觉。从一片黑暗之中先是透了一丝光进来,而后她就缓缓地看到了一切。
工匠放下了笔,朝着面具呼出一口气。他将成品小心地举起来,窗外的光透过面具上作眼的圆孔中直射过来,倒真像有人目光如炬地直视他一般,刺得他稍稍偏了偏头。匠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被自己逗得微笑起来。
他干脆就借着刚刚眨眼间产生的奇怪感觉,对着面具说:“请好好守护这里哦?”
那是新神社的建立。原本只是一尊供奉着狐狸雕像的小石桌,随着人们的汇集,对神明的托付如同新开垦的耕地一样多了起来。人们在树林里开辟出道路,竖起深红色的鸟居。
面具就这样伴着祝福与欢笑,从工匠的手里挂上了墙壁。
实际上,她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缓慢地熟悉了这一切。并不能说她不够聪慧,但最开始的她的确很笨拙。
她无法明白合掌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如此安定地闭上眼去,嘴角旁带着安定的笑意。可既然如此,又为何要祈祷呢?
她无法明白失去亲友的人们脸上流下的东西。这些如雨水一般的液体不分季节时间地在不同脸孔上划过,又和雨水一样消失在衣衫上与土壤中。
她无法明白前来修补她的匠人取下她时蹙起的眉头,无法明白他新生的白发,无法明白他渐渐皱成一团的脸为何在某一天突然又平整光滑,却又有着细微的不同。
她缓慢地了解着一切。
祭品不是神吃的,是晚上来的动物吃掉的,不要对着空盘子惊喜地狂呼。
当然也不是我吃的,请不要对着我拜。
今年的烟花也好看,谢谢你们。
又见面了,今年的我被保存得很好,不用皱眉。
挂在高处,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让面具有了一种俯视众生的神明的感觉。
它就这样高高在上地,仰首看着这个世界。
鸟居是新鲜的暗红色,钱币掉落碰撞的声音时时响起,湖光倒映着晨光,前来修补的匠人眼里倒映着湖光,柔软的画笔轻轻抚摸它。
>>>
面具重新“醒”过来的时候,雨声如同月光一般倾注在她身边。
可是为什么觉得那么安静呢,仿佛这整个世界都濒临死亡。或许是雨水不再击打在面具之上,失却了实感,单凭声音已唤不起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
神是真的存在的吗?
那么他俯视苍生时,会不会有欢喜,有怜悯?
会不会有悲伤,有向往?
假若神也会有这些情感,那么神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消磨掉这些情感的呢?
还是只是高高在上地亲眼目睹与见证着,却置身事外,从不发一语?
当时为我涂抹的那名工匠是叫什么来着?是本家的第几代?
五百年来那么多事情都作古,人们各自由命先后沉睡在春夏秋冬里,却不随新一年发芽的稻谷再次醒来。
那时候,好像有谁附在面具耳旁说:“人类是很脆弱的。”
曾经骄阳般的生命,曾经坚定不移的信仰,都是脆弱的。
粉尘一样,转瞬间便没入土中。
她记得一个人的离去。
那是年轻挺拔的身姿。是创造面具之人的孙辈的孙辈的孙辈……在寂寞到连野狐鸣叫都消失的夜晚里,他衣着笔挺地走进了神社里,却没有像他的父辈们那样带着笔,身上也没有太多属于颜料的气味。
他摇了摇铃,轻轻拍了拍掌。拴着铃的绳子一摇便簌簌地落下了尘,生了锈的黄铜铃铛艰难地呜咽了几声,掌声在空空荡荡的神社中游荡开来。
他的目光也在神社中游荡了一遍,最终定格在了面具之上。一片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了:“我要离开。”他轻声宣告,听上去是不奢求得到回应与认可的语气,并不掩藏他的坚定。
“……不回来了?”面具想问,问不出。
不回来了。它想。
年轻人收回了视线,脚踌躇地在神社的地面上摩擦了一下,最后扶了扶帽子,于是面具便只能看到他抿成直刀一般的唇线了。
面具熟悉这样的弧度,工匠们为它修补时的神情便是这样的。严肃的庄正的平和的。然后再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瞬间柔软下来,笑起来。
那次面具没有看到最后的神情。
年轻人最终又压了压他的帽子,连那僵硬的线条也看不见了。他转身,静默地站了良久。面具顺着那道背影朝外望去,树叶遮住了鸟居,与夜色一并织就了一层暗沉地网,落在长长的阶梯上。
背影走了出去。长久以来的痕迹再次被冲刷,只剩那最后决然坚硬得不容回头的线条留在了面具的记忆里。
修缮的人顺理成章地更换了,那是一张全然陌生的脸,从细纹来看约莫属于人类的中年,或许更加老一些。
像是一柄刀一般将面具的记忆斩出一个断层,曾经修缮她的那么多张脸在那一刻猛然模糊。像是顽童突发玩心,猛然朝清澈的湖岸扔下一颗巨石。霎那间河泥翻滚而上,叫人连最近的河畔浅水都看不清。
它竭力去想了。然而那些本以为清晰的眉目却蒙了霜般朦胧而不可即。充当回忆媒介的人已经离去了。
或许用山洪形容更为合适一些,泥水从山顶滚落,不容分说地将树木连根拔起,沉默蛰伏在山体的巨石也苏醒,咆哮着砸向一切。
纵然雨过天晴,往日的痕迹也随着那混浊一并而去了。水面会再次清澈如往昔,河堤会青草萋萋如往昔,仿佛一切如昨。
她看到在被雨打湿的月光里,有一个人背对着面具,静静地立着。
仿佛一切如昨。
>>>
几十个烟花一齐绽放的盛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造的光华将天色染了半边去,暗红色的鸟居也在黑夜被照得通亮。
面具的视线在鸟居上一闪而过。以前的鸟居颜色是这么暗的吗?这个念头和烟花一样,稍稍绽一下便消散了。
人声也像是烟花一样,沸腾片刻后便静默了下去。
静默是面具习以为常的事情,只是这次的静默太过于长久了。直到面具第一次被雨水砸中,它才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
歌舞的人们呢?闭眼许愿的人们呢?那些笑脸呢?
忽而仅剩雨声。
>>>
“哎呀,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面具吗?”
“很旧了呢,还没有坏掉啊?”
“看来有被好好修补呢。”
>>>
岁月啊,情感啊,不由分说地倾覆在人们的身上,带来的重压连器物们都躲闪不及。
然而,想去依附,想去靠近。
想去亲吻那柔软面颊上绽放出的笑容。
想要挽留。
你为什么脸上留着这些红痕呀?
因为红色是美好的色彩呀。
因为这是我认识的人为我一笔笔描绘的呀。
你为什么会化成人的样子呀?
因为我想成为人呀。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人呀?
……
>>>
那是一个年轻的匠人吧。
他似乎是沉浸在独好的月色之下了,面对着庭院,久久不曾作声。若非月色在他的衣衫上随着呼吸涨退,面具会觉得这是一尊石像。
不知过了多久,匠人终于转过身来。他背对着月色,面目在昏暗的光下模糊成一团,面具远远地望着他,用零碎的记忆拼出了一张清晰的脸。
只是当他背对着月光一步步走来,面对着烛光一步步接近,那张清晰的脸渐渐又隐去了,而取而代之的,另一张陌生的、清晰的面孔从雾气中浮现了出来。
他挽袖坐了下来,凝视着面具。他拿起了案几上的笔。
火光在他的眼中跳跃,他的唇抿成坚硬的线条,眉间皱起一道山川。他审视着这一个濒临损毁、灭亡的器物。
于过往中隐去的面孔与在眼前无比清晰的面孔于此刻重合起来。
由原来惨白的膜具,被匠人柔软的指腹摩擦,一笔一笔添置上墨黑与朱红的色彩。作为死物,她被这些艳丽的东西一点点打开,唤醒神识,如同新生儿缓慢地睁开眼睛。
眼里的亮光,那就是她第一眼看见的东西。
漫长得几近腐朽的岁月都是被这样的神情所斩开来的。如同画笔沾染了新的染料,不容分说地覆盖上了那些快要生霉的部分。
工匠细细地调了颜料,矿石在水中肖融后有独特的气味。笔在水中润泽,他们用口舌将笔尖吮细。朱红在面具上漫开,嵌入,沉积。
舞女们在脸上都扑了厚厚的粉,颈柔顺的垂着。稻草扎在一起,披在男人们的斗篷上。女人的手握着扇,风从扇下过,吹起颂唱的歌声。
多年的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模糊不清的笑脸在河的对岸,喊出的话被雨声柔和地抱住了。
月光依然不曾吝啬它的美。
>>>
神高高在上,不发一言。神赐予人间春夏秋冬,赐予人类喜怒哀乐,各人向神呈上答案,无法回避,无法作弊,独立而唯一。
如若向她发问,她无以为答。
她已经拥有了很长的岁月,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笑,什么是哭。她知道在不同的季节里会有不同的花盛开,也同样知道这些如阳光一般灿烂的东西在不久之后就会随着风归入虚无。
她尚未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熙攘的人声让她恍然觉得自己处身在人的洪流中,即将被汹涌的岁月与情感淹没。
因为那份过往,她渴望着人类那微妙而神奇的情感。在蝉声与雨声中醒来时,她用手拨弄红绸上的铜铃,再一次感叹起自己看过的岁月。然后就着酒味与烟气,在唇齿间轻轻叹一句:
“拥抱我吧。”
也不知是对谁说。
>>>
你为什么脸上会留着这些红痕呀?为什么会化形为人呀?为什么想成为人呀?
为什么呀?
她想作答。
=
End
=
想写出面具随着神社的建立到衰败过程中心境的变化,在混沌的意识中观察与学习人类,从旁观人类的“答案”到渴望自己能够“作答”,大概是想表达这样的感觉……包括那种想要守护什么的心情……
但是笔力太弱,拖拖拉拉写到现在也无法彻底写出那种想要写出的意境来……就连后记也说不清楚自己想要写啥,完了我估计是废了O<——<
总而言之辛苦看到这里啦!非常感谢阅读><
………………所以来找绊玩吧!!亲妈在这里给您磕头了(砰砰砰


女孩好像变成了一只氢气球。
轻飘飘,轻飘飘地,飘到了云上。
她想在云上做一个云房子。她用大朵大朵的云砌出了一个大方块。因为她不是很会做手工,所以这个房子没有尖屋顶也没有圆屋顶,就是一个大方块。女孩端详了这个大方块好一阵,才发现这个大方块根本不能叫房子,因为它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房子的里面塞满了云,根本不能住人。
怎么办呢?
先做个窗子吧。
女孩想着,伸手去剥方块外面的云,但手还没有伸到,身体却先沉了下来——就像漏气一样,女孩的身体慢悠悠慢悠悠地降到了地面,云房子在她头顶五六千米高的地方悠哉悠哉地飘着,但女孩却不能再飞上去给房子做窗子了。
女孩养成了动不动就看天的习惯,她努力地伸着脖子,寻找着那朵方形的云。而那朵方形的云也给足了她面子——不论刮过多大的风,她总能看到一朵方方的云在天上飘。
不知不觉地,女孩的身体又像气球一样飘了起来。
她迫不及待地飘上了那朵方形的云,想把那个方块变成一座真正的房子。但她飘到云层上之后,马上就傻眼了——云房子不见了,云房子变成了一颗巨大的棉花糖!
因为女孩在地上的时候只能看到云下面的那一面,所以她并不知道云朵的方形底座上发生了什么。
有谁到她的云房子上来做了恶作剧吗?
她伸手攒了一团棉花糖塞进嘴里,棉花糖马上就化成了一滩水。
这一点也奇怪。因为云就是水做的。水做的棉花糖就像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但女孩很高兴,因为她从来没有从别人那里收到过棉花糖。
她开心地吃啊吃,吃啊吃,但不管她怎么吃,她都吃不完这样一个实心房子大小棉花糖。
这个棉花糖实在太大了。就算女孩吃得直打嗝,眼前的棉花糖还是像小山一样。
这是女孩收到的第一朵棉花糖,她不想就这样丢掉。不只是浪不浪费的问题,要是让送礼物的人知道自己送的东西就这样被丢掉的话,那个人一定会很伤心的。
怎么办呢?
女孩想了好久,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她把剩下的棉花糖做成了一只小飞象。
虽然是小飞象,但这毕竟是象,小飞象就像其他的象一样非常大,就像吃剩的棉花糖小山一样大。
女孩最喜欢小飞象了。她枕边的小飞象就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要把她最喜欢的小飞象,送给那个送她棉花糖的人。
她的身体又开始缓缓下沉,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飘回到了地面。脚跟落在地面上,重量又回到了身体,但女孩的心却挂在云上,再也回不来了。
女孩一直以为她独占着整个世界,天空也好,地面也好,全都只属于她一个人。但现在却突然有一朵棉花糖跑来告诉她,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人,有人和她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着同一片云——这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女孩一直想着那个送她棉花糖的人。不知道她想了几天,几星期,还是几个月,总之她想着想着,她的身体又漂浮了起来。
女孩飘到天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小飞象。她找啊找,找啊找,不要说小飞象,就算是像小飞象大小一样的云,她都找不到了。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天上的云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可以是风,可以是雨,让一朵小飞象大小的云变成碎片的方法多得数也数不清。
女孩很伤心,她钻进云的废墟里,想找找有没有小飞象的鼻子或者耳朵的残渣。
女孩找啊找,找啊找,她找啊找啊找。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漏气,所以她也不敢休息。她把云朵翻了个底朝天,但却连小飞象的尾巴也没摸到——终于,她累得翻不动了,一屁股坐倒在云堆上。
“吱——”
女孩一惊,跳了起来。
这是云上,怎么也不该有这种声音啊。
女孩小心地检查着刚刚坐过的地方,尽管知道这里除了她,大概,大概不会有别人,但她还是小心地把刚才坐的地方又仔细地翻了一遍。
一只仓鼠。
女孩居然在她刚坐下的地方找到了一只云做的仓鼠!
不会像女孩留下最喜欢的小飞象一样,那个送她棉花糖的人也留下了那个人最喜欢的动物吧。女孩把云仓鼠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开始思考这次要留下什么,坐垫猫?短耳朵兔子?绵羊球?但就在女孩还没想好,身体就先一步沉了下去。
她没有时间去留下什么东西。她抬头望向那片高头顶几十米的云,然后发现它的形状已经和自己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因为在云里翻小象的关系,云团变得又蓬又松,好多云团甚至被翻到了半空中。
好多气球——女孩这样想着——一团团小云团飘在薄薄的大云团上,除了颜色,简直和广场上飘着的气球们一模一样。
女孩回到了地面,但她很揪心。那些气球其实只是被翻到半空的小云团,没有那个人会不会喜欢那些气球呢?很想把那个人找出来问个清楚。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一只白色的气球忽悠悠忽悠悠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不好意思哈,能帮我把那个气球拿过来吗,我现在手脚有点不方便,帮一下下,帮一下下就可以了。”
那个白色的气球并不是野生的气球,它是有主人的。
女孩捡起了那个气球,走到了那个浑身上下乱七八糟地缠满了气球线的主人那里。
“能帮我把那个气球系到我身上吗?虽然那个气球不太有气了,但还是帮我系上吧。”
“谢谢你啊,我跟你讲,我要用这些气球飞上天,大家都说我脑袋坏掉了,但脑袋坏掉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世界的进步都是由脑袋坏掉的人推动的,因为只有脑袋坏掉的人才看得到天马行空的未来,而且,也只有脑袋坏掉的人才能把世界向那个未来推动。我们能有今天,全都是托那些脑袋坏掉的人的福,而我,也将成为把世界往那个未来推动的人之一!”
女孩被这气势磅礴的宣言深深地吸引了。但吸引她的不是宣言中的壮志凌云,而是那个“飞上天”。
也许这个人就是那个送自己棉花糖和云仓鼠的人?
女孩想问个清楚,但不管怎么比划,对方都是一头雾水。她想拿出云做的棉花糖,但棉花糖已经被她吃掉了;她想拿出云做的小仓鼠,但仓鼠已经在口袋里变成了一滩水;她努力地扑腾着双臂,想做成一个飞的动作,但她越是扑腾,越是觉得自己就是只大蠢鹅。
“哈哈哈,你脑袋也出问题了吗?”
女孩又羞又臊,将通红的脸别向了一边。
“抱歉抱歉,你太可爱了,所以忍不住就——你也想飞到天上去吗?”
不,我本来就能飞到天上。但毕竟这话女孩是说不出口的,而且她的手里早就被硬塞了好多气球。
“来,把这些系到身上,不够的我可以再充。”
女孩照着他的话做了。
身上的气球越系越多,终于,多到了能让女孩的身体飘起来的程度。
女孩的身体飘上天空,飘得比云还高。
她俯瞰着云做的房子,看着它慢慢消解成棉花糖、小飞象、云仓鼠和白气球,然后飘到了看不到云的高度,然后又和白色的气球一起飘到了无限高的远方。
这些都是女孩的秘密。
一般人知道的只是氢气球爆炸导致两个小朋友遇难的事。大家都在为死了两个玩氢气的熊孩子而欢呼,丝毫没有被他们一个不会说话一个不会走路的事情转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