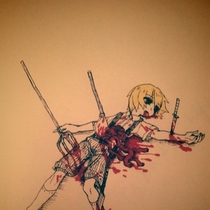
(本篇文章选录了几个世界各地比较有想象力的神秘生物的描述,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引用来源已不可考,或许本篇文章能像百科全书一样成为一个新来源,或许是这样。要看今年物理实验成绩的情况如何。)
前言
是的。曾经,曾经有很多姑娘喜欢过那个伟大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他是老大哥。他经营着一家农场和一家酒场,酒场只有星期六会开到半夜,桃子味的烧酒酒劲大得会让人看到二十三年前挂在针叶林边缘的云杉树上第二个高枝的缺腿的死鸟。大概进场得戴着防毒面具。那个时候,工人和学生在街上游行,然后姑娘们在地下跳舞。她是她们中的一个,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我能从她跳的舞里看到气球和彩色花炮,还有刚出炉的巧克力香蕉甜甜圈。
然后我约她出去,因为我看那地下的煤气灯感觉很受不了。
我买了两杯苹果酒跟她上街。——在这里,苹果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政治符号,但是我不想管那么多。她说我买东西掏钱时动作笨拙得像一只老猫,我纠正说是猫头鹰。其实只是我快没钱了,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数零钱做加法的尴尬境地。然后便说到跳舞,她说除了她以外,其他姑娘跳舞的姿势加上暗黄色的灯光就像一群大木偶。让我不自禁地觉得眼前图书馆的台阶上是一个大舞台,木偶们跳起舞来。最边上的那个,头上戴着一个苹果篮,神似我在历史书的哪一页上见过的画像。斯蒂芬说,历史是一场噩梦,我们挣扎着从中醒来。——它摔了一跤,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脊椎。然后她念着脏话,把只剩小半杯的苹果酒连杯丢在了路边。警察来了,游行的队伍开始混乱,场面失去了控制,我感觉我喝的不是酒而是橄榄油。
我想,我太高估我平衡街上和地下的环境的能力了。就算是历史书上的人也会跳很难看的舞。更何况我真的没钱了。没钱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让所有人都一样尴尬,痛苦起来。
土褐色的谢莉
土褐色的谢莉是一头体型偏小的,长着狐狸的身体和巨大的马的尾巴的白色犬科生物,耳和尾的末端颜色像泡过头的茶叶。在部分多愁善感的人看来,它是黑色的。
在这里,谢莉只是一个调侃性的假名,它可能叫夏洛特、劳伦西亚或者多洛雷丝。如果有陌生人在无意中发现了它的身影,那他马上失去参加省级化学竞赛的资格。
传言中谢莉有对旧炼金术和自然魔法的兴趣,虽然从来没有它使用魔法的记载。有些人坚定地相信它是女巫的化身,证据是曾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神秘学社将谢莉放在紫色的纹章图案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本科里选过材料学,毕业论文写了石墨烯。
在一些偏门的神秘书籍里,土褐色的谢莉被描述成一个脸色难看的女性,五官端正但不动人,拘谨有礼地坐在扶手椅上,望着桌上的三个圆形的话梅核。它看起来非常疲惫且不耐烦,并对浴缸里热水的温度大有怨言。在记载最为详尽的一则案例中,它把三倍浓缩的黑咖啡倒进瓷茶具里,谈及白磷火柴的绝迹与纯正氯化亚铁溶液的保存方法,并对市场上现行的家养观赏植物种植指南表现出不屑。
“不,他们不懂天门冬科。”它皱着眉头批评道,“他们在葡萄风信子的页面里插了张风信子的图,它们不是一个属的。”
此案例的作者称,谢莉脾性古怪且目中无人,对数学和装置艺术很不友好,有着泛滥的表演欲,且很喜欢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它高傲地向他要点心吃,并且指明了要石蒜花。
“石蒜花,红的,整个的。”这是他的引用。
此外,在一些桃红色封面的名流八卦文集里也可能有它惊异的出场。在那本书里它的态度变得激烈很多,并用非常苛刻的言辞批判了安娜·温特,称她是个长着数学老师脸的老魔头。
当然,大部分的记载中特地强调它是土褐色的,性格自我中心令人生厌,浑身上下又笼罩着巨大的忧伤。被它讨要点心的作者补充道,只要试图靠近它,就会被一种冰冷的,沉闷的悲伤填满,让他想起惨淡的未来和五岁时被风刮进江里的《大灰狼画报》。作为补偿,它在桌上留下了四盒盐酸米安色林片和一瓶碘化汞。
黑猫普路托
一只通体黑色的巨大动物。有着挪威森林猫的头,缅因猫的身体,土耳其猫的尾巴。它有苹果汁色的左眼,但没有右眼。因为它把它的右眼取出来抵了保险。
普路托的出现被认为是严重灾难的前兆,比如事故,心理创伤或接连三个月每天都在大街上遇到ChildFund的成员(如果你已经满了21岁的话)。它的本质是强烈反神圣的,就算它能让购物街边传教人数量爆炸性增长。
在最早的记录中,它被直接指明是死亡与绞死的尸体的象征。有的人觉得它是条野狗,尤其在英国中部地区。
它给人以梦魇。如果在睡前唱到“Volevo un gatto nero”会有更大几率召唤出它(而且它会不满地纠正不标准的意大利语发音)。不过在一些金属头心里它被认为是安心睡眠的象征,灵魂的保管人,并且出场自带着Enter Sandman。
当然这样认为的人通常没有真正见过它,因为它出场时放的是Freezing Moon。
有人声称它可以变成人形,套着黑长衫,且满头都是绷带,一时看不出脸的模样。
虽然是明确的凶兽,但普路托的性情并不算邪恶,只是忧郁又缺乏幽默感,且充斥着一种厌烦的可恶气氛。它能把世界变成黑白色且降温十三摄氏度,这可能由于它的毛发过于厚实。
普路托喜好麦片与家养鸟的心脏,以及看一些血腥的拟纪录片。曾经有个颓丧的吸毒者吵着要见到它,但看见它形容枯槁,无精打采。它对自己成为叶公好龙的消极小鬼们的精神偶像感到厌烦,并要求让它先回家听完Sterbend的专辑。
它会说话,但说的话含糊不清,而且大多不让人愉快。比如“……历史是一场噩梦,生命是一场噩梦,你们需要醒来……”。
深红国王
通常在神话里出现的生物。在十七世纪的文献中,它被描绘成一个披着天鹅绒窗帘的青年人,或一头人工养殖的狮虎兽。与深红国王类似的生物包括木星岛,一只背上长着棵小白桦树的豪猪,会编程,且想把眼前所有人送进流水病院。
它被认为是太阳与无星无月的黑夜的象征,至于是更接近光明(思考)还是黑暗(感官),应该是到过这里也去过那里,徘徊在两者之间的。此外它会让物体(以及不是物体的东西)凝固或往下掉落,或者让人变得精神分裂。
深红国王很少直接出现在人的眼前,因此关于它的记载并不多,但一些无关的学术著作里会有它神秘的出场。数学家希尔维曾称他曾经试图把一个柱坐标系比喻成深红国王的王宫,但这篇著作终究没有发表,因为冬天到了,他立刻忙着去酒馆然后睡得像条死猫。
它的好奇心很强,但性情高傲,发言又显得古怪,比如有位学生称看见它坐在自己的书桌上,说着“帕拉尼克是一个有趣的作者,不是吗?”并试图描述撕扯嘴唇表皮的痛感。由此看来它在审美方面是比较偏离的,如果让它讲述洛特雷阿蒙的美学或品钦的黑色幽默,它可能会自顾自地讲下一夜,夹着些毫无意义的丹麦语单词,顶多中间停下插播几则广告。
但无论如何,它都坚称自己是学院派。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它就拿出一份海德堡大学数学系的毕业证书。
再加九块钱的话,它会再出示一份帝国理工数学系的。不过虽然如此,它并不会给数学专业的人带来什么好运气(可能纯数学除外,只要愿意跟它愉快交流存在主义的分歧),顶多会教他们写泛函分析。
并没有人明确提到深红国王的出现是吉是凶,只有人说到在遇见它后,他看见的落日都变成了凶狠黑暗的血红色,好像掉进了贴图错误的游戏。夜里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这让他感到忧愁,然后他猛然想起自己的一项工作已经逼近最终期限。“如果你想要血,不要急,你总能得到它的。”它说,“反正你明天也会依然要哭出来。”
风雨使者
一只身长十七厘米左右的小鸟。称其为小鸟是因为它的身长里有一半是翅膀和尾羽的长度,而它自己的内核缩在厚实的内部,要用核桃钳才能挖出来。
风雨使者有着尖利的羽毛边缘。园丁实在找不到剪刀的时候,就抓住它的头把它当成剪刀用。
它会说话,但声音是一个成年男人,比较接近巴贝拉时代汤姆杰瑞里汤姆猫的音色,不过要更严肃一点。唱歌的时候会唐突地换成高音。
它的语气很有年代感,而且喜欢自称“他”。
风雨使者之名源于一些东欧文学作品中称它带来狂风暴雨,并让收音机自动运转播放起激流金属。有一次收音机里突然大声响起的地狱牛仔让一个心脏病老人不幸惊吓休克导致身亡,它因此吃到了官司。
它还有一个称号叫黄色弄臣,一般伦敦的中老年人这么称呼它。因为据传它与深红国王的传说有一些联系。它使物体上升,避开漩涡,但会不小心把物体撕裂或送进行为矫正中心。
发条虹
发条虹不是一种具体的生物,而是一种现象。第一个描述它的是一个曾经卓越的匠人(不是埃兹拉·庞德),他在一个下午走进他的工坊,发现所有的发条鸟都浮在空中,不停发着混乱的尖鸣。他对此感到好奇,然后其中一只布谷鸟偷了两个硬币,并一去不回。从此发条虹的形象通常等同于一群座钟里的发条鸟,或被想象成一只光鲜亮丽的重金属猛禽。
它看上去擅长力学,对光学与材料学缺乏兴致。如果要参加力学以外的物理考试,寻求它的帮助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发条虹通常是一个集合的总称。给它起了这种名字的匠人不知道曾经想过什么,至少不是想着七倍的发条橙。
它可以包括一群贴在冰箱上的鼹鼠冰箱贴,成簇的玻璃糖球,或一片处于量子谐振子模型中的分子。一般情况下,它是无法被人探测到的(按照隐形火龙的那种说法,它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的),但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手段可以,比如把它领进一个有钢琴或者电子琴的音乐教室,就能听到它狂刷琴键试图翻弹一整首Karn Evil 9 1st Impression。
因为难以直接交流,所以发条虹一直保持着无人格无喜恶的神秘形象。但它依然被认为是有人格的。据称,它喜欢一部名为《Labyrinth》的1986年的童话电影与一本名为《华氏451度》的书。它用圆珠笔特意划线强调了“It was a pleasure to burn”。
“去在断头台的刀刃上涂点凡士林。”该书的主人还在扉页上发现了这么一句话。
发条虹的住所与它的形象一样带有童话色彩。传说它住在巨大的发不出声音的八音盒城堡里,里面全是六种简单机械。没有人找得到具体地点,除了被它主动抓进去。因为发条虹是肉食性的。它对新鲜血液有所喜好,且比较喜欢酒精过量的。
青苹果先生
一位马人。不过不是人头马身的马人,是马头人身的。它是一头白色的马,并且它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它看不起红褐色的马和鹿。大部分时间,它在平流层漂浮。
青苹果先生有明辨是非的名声。只不过它的态度总是显得很刻薄,尤其在它得不到想要的报酬的时候。如果想不出付给它什么,建议送它一份会考成绩单的复印件。
它右眼的视力很差。与此同时左眼敏锐得能看到几公里外的烛光,或自动售货机下躺着的五分钱。
通常情况下青苹果先生不苟言笑,惜字如金,而且厌恶所有有明快性格的人。但如果领它去地下酒吧,它马上会变得非常健谈,一个劲向人讲解欧债危机。它擅长政治,但政治惹人厌烦。有一种名叫前言的生物与它在外观和习惯上很接近,不过前言长着两支角,而且它是红褐色的。
薇洛
薇洛是一只三米长的巨鸟,体重不到十五千克,飞起来像一张喜剧传单。它的羽毛上印着伍迪·艾伦的《库戈麦斯插曲》。它会说法语和西班牙语。
与它相近的生物是蓝星,既像水母又像童话里的公主,漂浮在天花板下面,能把空气变成柠檬水味。
大部分情况下薇洛被认为是友善而健谈的,并且所有生物系的学生会受到它的保护。只不过对植物系没什么用,因为它分不清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
除生物学的才能以外,薇洛爱好近景魔术,运动,默剧表演和新鲜的黄油饼干。有别于大部分鸟类的是几乎所有关于薇洛的记载都提到它是有魔法的,比如尖叫着把一对情侣变成一本《知觉之门》。
伤害薇洛会带来坏运气,通常是错过下一场作业的deadline。
曾有一个动物学专业的研究生通过实验得到了服用幻觉药物有更高几率看见薇洛的结论,几率由高到低大概是LSD,费洛塞宾,麦斯卡灵,只不过那里的薇洛一直在聒噪地唱着歌,拍打一只海狸,并不停地向外拨电话。几年后另一个学生试图效仿,连续吃下了三十四剂麦斯卡灵,然后开始疯狂喝威士忌并一遍遍地高唱山羊皮的Pantomime Horse,最后倒地身亡。
克里姆林薄暮
一只乌鸦。就算它通常看上去不像乌鸦,而像一棵红石蒜。它通常在黄昏和入夜之间的时间出现,可能是为了避人耳目,因为它很容易被人用弹弓从树上打下来,尤其是它看天看得太出神的时候。
通常它是安全的,当然更有可能是它总懒得理会别人。如果试图和它搭话,会发现它很会说话,而且比你想象中的要自我陶醉。在凯尔特传说里,它是个气色不太好的爱抖机灵的知识分子,穿着黑色的棉布外套,并真心实意地对一个常函数说“你真的很漂亮”。苏格兰有的民间传说也会提到它,不过那里它的幽默感变得有些黑暗,不仅说自己不认识Nevermore这个词,还经常问“你们杀掉我的话奖金够不够买一架100英寸反射望远镜?”
由此看来,至少克里姆林薄暮是喜欢望远镜的。虽然它擅长数学(准确一点,应用数学),但因此它也兼职关爱着天文系的人们。最近他似乎考虑着转正,那样他就不用理会中学生们的恶毒诅咒了。
此外,它喜欢诗歌,比如《元音》。还有少数几部题材很奇怪的电影,一般最后男主角都遍体鳞伤,然后被突然掉下来的墙砖砸死。
作为少数不蔑视爱情的生物,它理想的爱情好像是一朵大秋水仙。
对酒精和药有很强的耐受性。尤其是巴比妥类的。不过它实在喝多了或者嗑多了的时候就会抱着一个玩具犰狳在角落疯狂走神,自称是个幻想家,短暂住在平面国(死荫幽谷)里,虽然是个五边形但却畸变成了五角星。它不得不做出一个更大的五边形把自己藏起来。
“不过我依然是异教徒。”它说,“我要像这样缩在角落里才能保全我的角和我的黑眼圈。”
当然,这些关于克里姆林薄暮的材料有一个共识,就是它是一个天生的艺人。虽然它不表演,但它所有的发言都像在演情景剧,就差那一阵笑声。每当有好事的人问它是不是内心很伤感时,它就翻着白眼说“希望是一种长羽毛的东西”。
Z-Drugs
一只长着玻璃眼球的柔软的白色家兔,眼睛是甜蜜的糖果色。它和其他小白兔混在一起时很难被认出来,但用手指敲击它的脊椎的话,它会发出钢琴一样的声音。
它的成分包括(左或右)佐匹克隆,佐匹德姆与扎来普隆。它给人以长期的安心的睡眠,——不一定像死猫,至少要像地底下的鼹鼠。当然,在睡觉之前要先上好闹钟。
因为这一项特长,Z-Drugs被认为是带来梦魇的普路托的对头。
没有人指出它擅长什么,但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表示过自己对它的喜爱。他称它为“魔鬼的奶奶”。由此看来,它可能被看作学术的核心(心理学。一定要选出一个的话)。一个证据是如果向谢莉提起Z-Drugs,它会立刻摆出亨伯特看向洛丽塔一般的神情。
它支持交流,但它说话从来不加标点。
相比各路危险的动物,Z-Drugs是非常温和的。它喜欢给人讲睡前故事,虽然讲来讲去都是同一套365夜故事里的。有人在它眼里看见了七重林和拜占庭的玫瑰,或者是一个静止的地球。它自顾自讲了很多内容,从对立统一到儿童读物。有时它还会重复着说“吃下去,像吃糖一样吃下去”。这是它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



我不懂音乐,相比某人(那种随便给首歌都能说出该歌曲流派的特点还有典型例曲的),我对音乐的分辨能力大概是两种:“好听”和“不咋好听”。
某一天,我捡到了这根笛子……
所以我第一反应是上交给领导。
“呃,我们能用它干什么?”我问。
“吹。”
“我不会,你会吗?”
“所以你为什么要捡回来?”
我无言以对,跑过去把笛子洗了。
“我觉得,这笛子挺好看的,是不?”我讨好地说。他只是淡淡地看过来,然后把视线转回去。
我试着把笛子塞进嘴里,装模作样地按着上边的孔,吹出了一听就知道是新手吹出的调子。
“还能用嘛!”我说,“笛子也长得够好看,不如就收藏了呗?”
他想了想,“也行,”说,“反正不差这一个。”
晚上,我们吃完饭之后趴在沙发上唠嗑打屁。
这时候我就想起那根笛子了。我们觉得风景不错,电视节目说得也够诙谐,干脆来映风景来几首。当然,我是音痴,我不会吹。他就算是懂音乐的,对笛子也不够熟悉。但是两个人傻呵呵地轮流把笛子吹了两个小时。
“我这时候要偷偷把笛子偷过来!”我看着他手里的笛子想起这个梗,不由得一震。“然后偷偷舔……”
“恶,你在想什么?!”
“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幽默的说法吗?!”
“幽默在哪里?”
“在其低俗。”
我们这时候才注意到,门外有些躁动。
“呃。”我看了看笛子,看了看窗外。满月升起,一片心平气和的味道。我和他偷偷摸摸走到窗前(好吧,只有我是偷偷摸摸的),然后伸头——
“喔。”
我们对视三秒,又看回窗外。
“…………”
“原来是这个梗?”他说。
我举着笛子瞎吹一波,门外一大波老鼠又给跑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发现花园里全是洞。明天要是填估计得死了。我说:“能不能吹笛子叫老鼠给填了?”他一脸无语地看过来。
“又不是童话故事,还有小老鼠给你搬铲子给你填坑?”
“论破!哈梅尔是不是童话故事!”
“我更倾向于——民间传说。”
我想了想,好像也是。
“我们他妈吹笛子找童工吧。”
“醒醒,故事里的儿童基本是被催眠的无意识状态,估计不能填坑。”
“请使用控制他们无意识的能力。”
“我没有。”
我们扒拉扒拉花园,发现还好根什么的都还好,花花草草活得都好好的,还是有点感动的。但是这根笛子是个大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大新闻,我们决定就此事严肃地讨论一下。
“有了这个笛子,我们可以做灭鼠达人,一夜暴富哇。”
“在暴富之前先被抓走了吧。”
“拿去做拐卖儿童行业。”
“听上去有点赚。”
“你吹我套袋,找个叶子咯做中介,浩仔是司机,我两和他两分5比3比2,咋样?数字拐卖团,现成的!”
“为什么是我吹?”
“你吹的比我吹的好听。”
他没有否认。“咯咯怎么联系买家呢?”
“她可是社交花大现充,人际关系数字团第一,宇宙爆棚,找个山沟沟随便卖了。”
“陈浩哪来的车?”
“我们先租一辆,赚第一笔就买个大点的。实在不行用自行车吧,还可以体验山地越野的感觉。”
“听上去屁股很痛啊。”
“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啊。”
“赞同。”
我们达成共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吹。毕竟我也不敢真的套孩子拿去卖了。硬要说,咯咯也要先联系山沟沟里啊。
“笛子,要怎么办呢?”
“不知道。”
我们两无力地坐在花园里,看着被扒拉的草和坑坑洼洼的地,浑身都是一股疲惫感。累了。很困。我猛地发现他已经屁股着地,可能沾了无数泥巴(被老鼠刨过的),失声惨叫。短暂的绝望里,我还是平静下来了。“我想拿点牛奶喝。”我说。
他说:“也行,你顺便帮我拿酒来。”
“床底下那瓶?”
“沙发柜子底的。”
我说好,回厨房去煮牛奶喝。一时兴起,又跑去煮茶。煮得很仓促,有点苦,但是还算是成功弄了一锅奶茶来。我又失手多丢了半罐糖,我觉得大概苦味已经不会有了吧。我拿过去的时候他明显不高兴了。我才想起来忘了拿酒,而且拖了老长时间。
我问:“你坐这里屁股不冷吗?”
“有点,但是不想动。”他回答。
我心惊胆战地和他干杯,我们一边坐在破烂的花园草坪上(屁股有点冷,还有点湿,可能是露什么的,或者泥土本身就是湿润的),一边喝奶茶(客观来说可能太甜了,但我觉得不是很甜,至少不腻),然后看着月亮。
我想看另一边的样子。
笛子就放着吧,要不然明天泄愤埋土里去。我说。
他说,也行。
“就是拐卖不了小孩了。”
“你说不定还破了人生生财之路。”
我们还是拿起笛子,傻呵呵地轮流吹起来。起码在这种气氛下,吹什么都觉得好听了。可能也是我们吹得变好听了一些,老鼠什么的,小孩之类的,统统没有来。一定要说,就是风吹了,很凉快。
我们看着月亮,觉得这个气氛又土又俗。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又灌了奶茶,太甜了,又暖和,容易催眠。我祈祷不要等会喝得忘我直接在草坪上睡着,不然双双感冒,还可能半夜被良心发现回来的老鼠啃了耳朵。
是这样。
我们看月亮,我们喝奶茶,我们吹着笛子,我们吹着风。我们数着风,去听风。然后,夜幕降临。


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兔子,非常不可爱。
如果在路上见到了不开心的海兔,她就会把自己的两只耳朵各掰下来一半拼成一个耳朵团给不开心的海兔吃。
“我的耳朵一定能让你开心起来的!”
帕罗西汀拍着胸脯保证道。
但吃了她耳朵的海兔一点也不开心,反而觉得想睡觉起来了,鱼也不想吃,萝卜也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吃了。
帕罗西汀说没关系,开始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帕罗西汀把不开心的海兔扛回了家,无微不至地照顾起它来。
不开心的海兔很快和帕罗西汀的耳朵同化了,它突然间发现生命中充满了光。
下次混沌海兔再来风之海的话,就把自己喂给它吃吧!
就算是混沌海兔,吃了帕罗西汀的耳朵也会变得讨厌吃东西的吧,不开心的海兔很快就开心了起来,兔生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我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眼睛是棕色的,绿色的眼睛能看到真实的东西,棕色的那只能看到更多。
我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曾经我也有一对一模一样的绿眼睛,就和其他人一样,有一对一模一样,只能看到真实的东西的眼睛。
五年前,我卷入了一场交通事故。公车的车窗爆炸,飞溅的玻璃刮了我的眼睛。那时候我的眼睛不停地流血,红色和绿色混在一起,我的绿眼睛就这样被染成了棕色。
之后我过了一段缠着眼睛生活的日子。那时候用来看东西的眼睛是绿色的眼睛,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看到其他东西的特殊能力——即使照镜子,那只变了异的眼睛也藏在绷带下面,我看不到它的任何变化。
“玛琳,你好好听我说,医生马上就要把你的绷带拆下来了,你的另一只眼睛会变得有点不一样,不过你不要慌,那只眼睛只是能看到更多东西了,比你原来能看到更多东西了,开始你肯定不会适应的,不过过会,过会拆了绷带以后无论你看到什么都要冷静,然后慢慢听我说,好吗?”
我点点头。妈妈说的我都懂。我知道那只眼睛流了多少血,要是拆了绷带以后和以前一模一样我才会觉得奇怪呢。
医生拆掉了我头上的扣子,一圈一圈地解绷带,我会看到什么呢?整个世界会像后街的围墙一样被各种凌乱的线条画得面目全非吗?
绷带全部解下来了,我慢慢地睁开那只许久不见光的眼睛,然后世界,什么变化都没有。
是不是眼睛的打开方式有问题呢?我把那只眼睛闭上,又打开,闭上,又打开,但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玛琳,现在你还没发现,那些东西不是你张开那只眼睛就能看到的,你不只要张开那只眼睛,还要把你好的眼睛闭上。”
我妈妈的话,闭上了双眼,然后再把坏了的那只眼睛睁开。
什么都看不到。
“你什么都看不到是不是?”
我点点头。
“不,不是你什么都看不到,是你看到的太多,太多东西重叠在一起了。你再仔细看看,你眼前并不是全黑的,是不是?”
是的,我眼前并不是全黑的,除了黑暗,我还能看到别的东西,是有点发红的光,但光里有什么我还是一点都看不清。
“好了,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我睁开了好的眼睛,世界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妈妈的手里多了红色、黄色、蓝色,三种颜色的圆盘——我知道这是三原色,以前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过。
“红色加黄色是什么颜色?”
“橙色。”
“黄色加蓝色呢?”
“绿色。”
“那红加蓝呢?”
“紫色。”
妈妈把三个圆盘两个两个交叉起来,这些我都懂,红色黄色和蓝色三种颜色相互配合,能调出白色以外所有的颜色。
“中间的这个地方,是什么颜色?”
“黑色。”
“对,所有的颜色重合,就变成了黑色。玛琳,你的另一只眼睛比原来那只能看到更多东西,但它能看到的东西太多,各种颜色交叠在一起,最后变成了黑色。你的眼睛已经变成了这样,变不回去了,如果你只用那只眼睛看东西的话,就只能看到黑色的一片。不过如果你不想看那些东西的话,只要把另外一只眼睛睁开就行了。”
妈妈给我配了隐形眼镜。就像我开始说的,我那只能看到其他东西的眼睛因为流血,被染成了棕色,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话,就会被人发现我另一只眼睛的秘密。有特殊能力的人会被邪恶组织抓去做很可怕的人体实验,这个我在漫画书上看到过——隐藏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妈妈想得十分周到。
在隐形眼镜的帮助下,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奇怪的组织来找过我的麻烦,我的中学生活可以说是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得连一点小波浪都没有。
因为担心邪恶组织,我没有交朋友,社团活动只是挂名,就连平时和同学老师的交往也仅仅维持在最低的限度。虽然妈妈说有隐形眼镜的话就没关系,但我还是怕穿着黑大衣的坏人突然从直升机上挂下来把我朋友绑走,然后留下一封写着“想救她就交出眼睛”的信。
因为孤身一人,我拥有了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我没有虚度,我把它们拿来读书,学外语——我还是很在意我那只眼睛,为了解开眼睛的谜,我必须拥有渊博的知识,最好能够通晓八国语言,饱读国内外文献。
在往巨人的肩膀上攀爬的时候,我也没有荒废自己的思考。
用妈妈的话来说,那只眼睛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太多,各种颜色重复堆叠,最后变成了黑色。也就是说,原本我看到的应该是有各种颜色,能分得清什么是什么的东西,它们只是因为堆在一起,所以混成了黑色。我知道,如果把三原色的色盘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地分开,那中间的黑色圆三角、还有交界处的橙绿紫都会被分离,变回最初的红色黄色和蓝色。
如果我的眼睛和三原色有一样的原理,那只要好好地把重叠的颜色分离,我就能一睹异世界的神奇风貌。
之后我开始思考如何分离棕色眼睛里的颜色。
在化学实验里,我们可以往混合了各种离子的试剂里倒入另一种试剂,把有颜色的离子沉淀,得到颜色干净的溶液。但我的眼睛毕竟不是试管,不能往里面滴眼药水以外的东西。而且我总共只有两只眼睛,要是试剂把我的一只眼睛弄瞎了可不好,而且,就算不会瞎,眼睛受伤的感觉真的不好,我一点也不想再来第二次。
用化学反应分离世界的方法被我否决了,我最后还是使用了分离三原色色盘的方法,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
如果三张大小一样的色盘完全重叠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黑色的色盘。这和我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要分解这样的一个黑色的色盘非常简单,用指面在色盘的圆上轻轻一拨,摸出色盘的缝隙,然后把缝隙扩大到能伸进手指的宽度,就能轻松分离色盘了。
这个方法的重点在于缝隙——没有缝隙,黑色的圆盘就没有三个圆盘重叠一说,只能说是一整个黑色的圆盘,也没有分解一说了;有了缝隙才可以说它是三个圆盘重叠而成的,才有分解的可能性。
要分离我眼中的世界,必须找到世界的缝隙。
这很难。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一块无限大的黑色,没有缝,连一条线都没有。
黑色的圆盘从正面看,也就是一个黑色的圆。如果不从侧面看的话,是看不到缝的。我就对着异世界和现实世界重叠面的正面,至于它的侧面,在我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地方。
我没有因此放弃寻找异世界。
我每天晚上都扭着头,在黑暗中寻找世界的缝隙。
选择晚上,归功于我的灵光一闪。
我无论什么时候使用棕色眼睛,看到的都是以黑色为主。这很奇怪。拿我绿色眼睛看到的现实世界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运动着的,绿色眼睛里的颜色无时不刻都在变化。就算看到的东西再多,如果所有的色彩都在变化,那总会有光和光叠在一起呈现出亮色的几率。但几年来,我都没有看到过亮的异世界。棕色眼睛里的世界偶尔会有点红光,但那点红光不能打破黑暗,顶多算是“有点昏暗”——在现实世界的晚上,也会有这种情况,我想这是因为有光亮世界存在的结果。
在我们这边的晚上,异世界有光,就像地球的这面和那面,一面是白天,一面是黑夜。
“妈妈妈妈!我想去留学!去世界的另一边留学!”
“好啊好啊,你要去哪个国家呢?”
“呃……”
为了决定我留学的方向,我必须更加了解那个异世界才行。那个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有时差。我们这边是晚上的时候,那边有光,很可能是白天。
我躺在床上,闭上绿色的眼睛。棕色的眼睛里,只有一点蒙蒙的红——这边和那边并不是12个小时满打满的时差,眼前全黑的时候,就是两边都是晚上的时候。我静静地等待真夜的降临,那个世界变成黑暗的时候就是那个世界的黄昏,只要记下那个时间,就能靠日落时间推算出那个世界的时区,推算出时区,国家也就能确定下来了。
我等啊等,等啊等,因为看不见钟,我也不知道我等了多久,等我回过神来,眼前的已经不是“有点昏暗”的光,而是——一条缝隙!
缝隙里伸出一根指头。
指头截面的圆嵌在被戳开的缝隙里,就像蚌壳里的珍珠,眼睑里的眼球。
我拨开缝隙,伸进了一条腿。
我掉了进去。
我在一片红光之中。
周围什么也没有。
“你的眼睛很好看。”
我的眼睛好看吗?
“一只红一只蓝很好看。”
“不是一只红一只蓝,是一只棕一只绿!”
我抗议着,但她并没有听我的。
“我有些蛋糕你要吃吗?”
她拿出一只白色的盒子,里面有一些咖啡色的蛋糕碎屑。
我拿指头蘸了一点,吃了一口。
是巧克力的,还有樱桃果酱。
“我在里面加了毒药,你没什么舒服吧?”
“没有。”
我又蘸了一点,我喜欢蛋糕。
然后我就倒了下去。
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自己的卧室了。天已经大亮,我拨开闹钟上的便签,看了看时间——还好今天是周末,不然就死定了。
“早饭在碗柜里,记得加热。爱你,别忘了关灯。”
家里没有人,我热了妈妈留下的鸡蛋火腿三明治,一边吃,一边回想昨天另一个世界的光景。一片红的,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其他景物,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只记得自己在一片红雾里。给我蛋糕的人我也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也不记得她穿什么衣服,话我听得懂,但我一点也不记得他用的什么语言了——到头来我只记得我在一片红雾里吃了两口加了毒的巧克力樱桃果酱蛋糕,根本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我脑子里一整天都是加了毒的巧克力樱桃蛋糕,结果作业写得很慢,写到很晚。躺到床上后,我闭上绿色的眼睛,世界立刻黑了下来,只剩下一点红光——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红雾,这我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眼前的是这个蛋糕世界的红雾、别的世界的黑暗,还有这个世界的灯光。
“爱你,别忘了关灯。”
我想起了妈妈早上贴在我闹钟上的留言,起身关掉了房间的灯——昨天在异世界被毒倒了,也忘记了在睡前关灯,浪费了很多电,我很惭愧,今天不能再重蹈覆辙。
刚关灯的时候还没感觉,四周都暗下来以后,我再单开棕色的眼睛的时候,原本能看到的红光都不见了!
我眨了下棕色的眼睛,又眨了下绿色的眼睛,一点变化也没有,眼前一片漆黑。
真是个大发现!
我马上按下闹钟的夜光灯,已经十二点了,这就是那边天黑的时间!日落的时间不管是哪个时区,都是当地的下午五点到六点,我们这里和那里应该有五到七小时的时差,那个地方应该是亚洲,接近上海或者东京。
上海,也就是中国那边,因为工业发展长期伴有毒雾,就和十九世纪的伦敦一样;东京,日本那边,因为地震导致核泄漏,曾经也一度被标成红色的辐射气体笼罩。两个地方的人都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在毒气里对毒产生抗性,就算拿加了毒药的蛋糕当饭吃都不会有事。
我想再去一次那个世界,之后我也的确去了好多次。
我看到一张张亚洲脸孔,他们都不在地上走路,总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我看到商店里穿成串的球形面包,被不同的毒素染得五颜六色。
我看到长得和人一样大的兔子,看到我大喊了一声“要被吃啦”后就逃之夭夭。
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使用方形文字,穿着浴袍上街……
异世界在我的视界里越发清晰,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分清那里是中国还是日本——中国人会轻功,会做绿色的点心,四只脚的除了桌子什么都吃;日本有忍者,会做粉色的点心,受辐射变异的动物到处都是——虽说中国和日本的语言和服装风格有差异,但这差异实在太小,一觉醒来后我根本不记得这些语言服装的细节,根本不能分辨那些方块是汉语还是日语,是汉服还是和服。
最后我没有办法,只能通过丢硬币来决定留学的方向了。
反正日本和中国都在亚洲,离得也近,去哪里都一样。
我硬币丢了个日本,所以我就到日本来了。
(完)
宇佐见莲子翻完了长长一摞入社申请。写得不错,使用了这么多成语,在留学生里已经算出类拔萃的了。就是一股子中二气,让人不忍直视,不过莲子本人也没有资格去说别人中二什么的就是了。
“嗯?怎么样?可以吗?”
“呃……怎么说呢……呃……这个……这个……”
“尽管说吧,我听得懂。”
“日本没有什么染红的核辐射烟,也没有什么变异的动物,现在也没有忍者了,大家都是在地上走路的……”
“我看到了,所以我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说实话很失望……”
“还有明明是异世界,为什么要用地球的时差来推算它在哪啊?如果是你看见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有交叉,那你看到的东西应该和你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那个世界是平行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差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我倒是没有考虑过……”
“而且就算是时差啊!日本的时差是早你们那里七小时吧!你们半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天亮不是天黑!你该去的地方是米国!米国才对啊!”
“啊……你发现了啊哈哈哈哈……”
“切……”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殊能力,我这只眼睛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被戳穿了的少女干笑着取下了一只眼睛上的隐形眼镜,“不过‘一只眼睛因为车祸变成了棕色’是事实啦。其实这只眼睛是瞎掉了,虽然不是全盲,但最多只能分辨光照,具体的东西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啦。”
“我就知道……”
“三原色的色盘也是真的。我妈妈不想我因为失去一只眼睛而难过,特地编了那样的谎言。我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就是五年前左右,你懂的,就是那种年龄,把它当真的,真的去找异世界了,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眼睛是瞎了,直到我高中时得了点小病,看到了自己的病历,不过那时我已经习惯了一只眼睛的生活了,就算知道了也就是小小地失望了一下,虽然说起失望,还是知道日本没有哥斯拉那会要失望多了……”
“你多大了还信哥斯拉……”
“幻想并不是坏事,这些年来我做的那些梦都是我今生宝贵的回忆。”
“我就说,怎么在异世界会有人看得到你两只眼睛不一样。如果你在异世界的话,绿色的眼睛应该闭着,根本不会有人看得出你另一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不过如果你都是做梦的话,这就好解释了。之后的飞来飞去是你看了太多杂书或者玩了太多游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哈哈哈,就是这样!全部被看穿了呢!这些事情我一直想找个人说的,但我已经这个年龄了,和别人说这些怪不好意思的,正巧这个时候看到你们的纳新广告,嗯,你应该也是和我一样脑洞大开的人,所以……”
“我不要你。”
“哈哈哈哈!要不要无所谓啦,让我把这些说出来就好啦。我有一个超酷的好妈妈,我就是想说这些。”
“的确是个好妈妈。”
“那我先走啦,接下去还有科幻协会、电影协会、漫画协会、现代视觉研究协会……你也要加油啊!”
送走了奇怪的留学生,莲子一口气干完了桌上已经凉掉的红茶。刚看到申请里“能看到更多”的时候莲子还小兴奋了一下,最后知道这只是个谎以后,虽然对不起那位母亲,但莲子真的很失望,比那个留学生知道日本没有哥斯拉的时候失望多了。
活动室的门又被敲响了。
又是一位留学生。
又是啊……
“我叫玛艾露贝莉·哈恩。”
“嗯。”
-1-
“柳妹”,這個可愛到甜腻的外號,是她起的。
雖然柳妹的大名是Leon Bechstein(对,他是男人),被冠上了一個“柳”字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因為她,——他的女友,——喜歡瑪莎斯圖爾特。她喜歡那明日之城,那高大的塑料條做的假柳樹。而她第一眼見到他,就自顧自地說他像棵假塑料樹。因為他高大,且帶著一股沒有生機的塑料氣味。呵!她也聽Radiohead啊!——他的第一反應倒是這個,并自豪地回去把Fake Plastic Trees循環了五十遍。
除此之外,她還稱過他為“蜻蜓”。
因為他的網名是一種石炭紀的巨型蜻蜓。潮濕的雨林,節肢動物的天國。雖說他起的id名為Eidoleon只是因為裡面有一段他的本名。他慶幸自己起名叫Eidoleon而不是Charmeleon,不然他可能就會身體力行變成契訶夫筆下的丑角。
“晚安,我的柳妹,我可愛的小蜻蜓!”
聊天聊到最後她就會來這麼一句親切又略顯曖昧的告別。年輕的小蜻蜓就得迅速摸出杯子喝一口汽水(冰的更好,無關季節)來平穩一下心情。當然,他們並沒有在網戀。他們是實打實的純潔的同學關係,只有放學之後能順路一起坐公車,然後在不同的車站下。
蜻蜓迷戀甜食,但他不喜歡杏仁巧克力。因為甜里的苦合不上他的口味,他喜歡虛假醜惡的甜,熱量越高越好,因此他熱愛著白巧克力。
雖然巧克力原教旨主義者會覺得白巧克力這種油脂的塊簡直是對巧克力之名的一種侮辱,——他還是喜歡。至少它把讓他愉悅的齁甜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了。像是德芙禮盒里那種夾著草莓味糖精的白巧克力,能把他甜出嚴重的內傷,扶著墻暗自反胃起來。
但這是不可避免的!苦杏仁的味道只能讓他想起他苦澀的沒有結果的愛情,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
他是個可憎的享樂主義者。且一有機會就想大喊帶我去那甜蜜的花花世界。
-2-
碎仔與柳妹一樣嚮往著甜蜜。但是碎仔可健康多了。他只是吃什麼都甜,像是用奇異果做了舌頭,包括舔自己的鼻血。雖說他的危險就是源自他對甜食的熱愛,即使他的愛好健康一點,不至於讓人得糖尿病。
而櫻桃早在第一次新概念出道就自詡巧克力原教旨主義者了。百分之九十八黑,這便是成熟的靠谱的人。雖然他說自己靠譜時葉子在身後狠狠地嘔了一聲。
-3-
偶爾,蜻蜓會滄桑地追思自己的校園生活,——尤其是高中。除了會追思一下假塑料樹,還會順帶追思一下那時的忙碌。他畢業了(也失業了),天天只能打遊戲或在油管上看些低級趣味的疼痛視頻,稍微停下來就要懷疑自己身在何方。他不由自主地懷念忙碌的生活。
(當然這只是一種裝模作樣的消遣。是個學生都不會喜歡這些的。)
有些東西偶爾思念一下會讓人心痛。與許多人一樣,蜻蜓懷念校園生活倒不是因為那時候的天真無邪心無旁騖,而只是因為那時的友誼。雖然他上了高中就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空長了一米八七而不會打籃球。他只能懷念到更遠的地方去。
有一個朋友自幼兒園時就和他交好(那時候他還是很開朗的,哪像現在!),並且是互留電話互相串門的交好。在那個年代,在座機前面打出一個電話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從幼兒園直到小學畢業,他們相處了七八年,也逐漸從每天打電話逐漸減到了一年打不到一次。到了五年級之後,他們便不再交往了(即便身處同一個教室)。
好朋友終究不是永遠的好朋友,總會因為各種原因逐漸疏遠開來的。
聽上去很乏味。小時候要好的朋友是那些被邀請著參加生日聚會的,週末一起組團去自然公園的,能夠成立一個小團體并玩各種匪夷所思的角色扮演遊戲的,——在別人緊閉的車庫門前。當然蜻蜓早就不記得這些說好一輩子的朋友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了(呃,可能最早的那個他還記得。但他不該早就搬家了嗎?)。直到近日無意間翻到幼兒園舊友的社媒,才想起自己加過他的關注。
他看不懂他朋友的世界。那些笑臉都模糊了,怎麼也記不起來。
其他人早已沒有聯繫。想到這里天性多愁善感的蜻蜓就有些傷感。白菊花茶一樣的傷感,清淡如水,卻的確飽含苦澀。
-4-
高中同學奔現的例子也不是沒有。極端的例子那就是小透和滿金,雖然此奔現非彼奔現,他們只是友谊地久天长二人组。
曾經做同桌的時候他们關係還是挺正常的。畢業之後關係反倒突飛猛進一發不可收拾起來,畢業多年了兩人還能保持著隔幾天出去吃一次香香雞的親密關係。他們經常經常經常鬧彆扭,但彆扭鬧太多了反倒友誼堅固。唉。這是男人。
其實很不合理。
-5-
而靜物……是指現在租著蜻蜓房子的那個美少年,他似乎從來不知道還有友情這種東西的存在。反正他只知道盯著夏夏發呆,偶爾轉頭對付一下線性代數。他落進了又一個沼澤,蜻蜓知道。這傢伙就是個愛情怪獸,美學恐怖分子。他們曾經坐在同一張桌子的兩邊吃晚飯,他臉上的亮粉還沒洗乾淨,在不亮的日光燈下閃得像一條銀河。他懨懨地吃著生培根。
他沒有朋友但起早貪黑地很少回家。幾乎足不出戶的蜻蜓,對他唯一的住客的作息還是很敏感的。“我就是感覺很困惑。”他抽著虛偽的電子煙。即便是戲劇部的年輕人也還是演不出那種成年人的滄桑,“我腳下什麼也沒有。就像拔了希望的花所以只能在暗室里痛哭。”
靜物是個未來的狗男星。蜻蜓在心裡揶揄。他一早便注意到這人頸上的半道紅痕,不過他懶得問那是什麼的印記。也不會離開感情問題吧?葉海龍的熟人,不是性變態他已經很慶幸了。
-6-
不過蜻蜓很喜歡葉海龍。這邊的“喜歡”概念比較模糊,只是單純的有好感而已。世紀級異性戀蜻蜓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水準的好感。他跟葉海龍認識十年,足夠螞蟻一場馬拉松了。十年不長不短,不夠天荒地老海枯石爛,不過足夠讓一個幻想中的朋友徹底消失,把一些人和事永遠遺忘。
葉海龍不是幻想中的朋友。雖然蜻蜓已經長大了十歲,從一個剛上國中的小孩變成了一個頹廢的失業成年人,他卻還是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甚至看上去比蜻蜓年輕了。這該死的逆生長。
他一直十年如一日地把蜻蜓單方面地當作朋友,這讓蜻蜓很是感激。即便他是個可疑人物,還是個持有餅臉書櫃大會員的宇宙毀滅性變態,蜻蜓也忍了。長久以來他聽葉海龍講述或吹噓那些光輝歲月,比如戰場挖尸,他地下室的人體農場,曾經他象征性地害怕一下,但自從他上過醫學院,見過了海濱浴場一樣的深黃色防腐大體池,他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不過那些十有八九會是真的。——蜻蜓相信這點,畢竟對方是葉海龍,獨立城最恐怖的人之一。也許他動動手指就能給正常人留下任意面積的心理陰影,不過蜻蜓也不是什麼正常人。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看著葉海龍給他展示的封在膠塊里的漂亮眼球,蜻蜓說。
只希望以後少分享些超重fanfic。求求您。
-7-
蜻蜓不討厭尸體,這是職業病。畢竟他醫學院的,雖然現在宅在家裡。他從小就喜歡看些奇怪的科幻書,人工智能,模擬生命。他想知道人類的生命之源,除了腦子電波的模擬外還有什麼?作為靈魂論拒否的人,腦就是一切。——“好像把一個人體弄得支離破碎然後尋找生命。”他說。
與之類似的場面,一個死去的女人,美麗的,反正看上去很美麗。然後尋找美麗的時候,就得用刀切開她的胸腔,剝開她的臉皮,美麗在哪裡?取出她的臟器,她的頭腦,數她的肋骨,她無神的眼球,美麗在哪裡?在肉堆尋找的時候美麗就逃跑了,什麼也沒有。
很不幸蜻蜓以前經常做這樣的夢。一開始他以為這裡頭蘊含著什麼深刻的血淋淋的隱喻,後來他意識到這種夢老是出現在做完閱讀理解題後。
要理解生命,首先理解死。蜻蜓深信這一點,因為死比活著單純多了。從中學一個令人難忘的黃昏開始,他就決定去調戲一下各種各樣的死。他報法醫課。
順便學法醫很髒的。光是去挖泥就很髒了,他永遠記得組隊實踐大雨瓢潑的上午,他手指僵冷到無法活動。對學習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是要吃苦頭的。
-8-
死對大白來說只是一場遙遙無期的戰役,她就是戰鬥狂,別想了。鬼知道她是出於什麼心態把那個紅髮小孩撿回來的。——肯定不是出於同情!這個詞早被她丟出好望角了。
也許是有什麼秘而不宣的趣味和一些更深遠點的原因。至少那個紅髮小孩長大了,長成了秋天的魔法師(人類),即便他狂躁,自閉,神經過敏,還是個愛上口紅軍八卦論壇的緋聞男孩,她還是愛他。畢竟她的那點性格已經模因遺傳過去了,多麼溫馨美好。
狗屎,她的性格是正常人能遺傳的嗎?
-9-
死對小透來說就是個必然會上演的節目。他現在已經不關心它的出場順序了,或者他這年齡的人本就不應該關心。還是端起爆米花看好戲吧。他開始用美好的事物說服自己,至少暫時麻醉五分鐘。他不打算複診他的雙相了,也不打算規劃未來。他現在只想在自己的破房子里住到厭了為止(其實早就厭了)。不就是個玩嗎。
自殺未遂的人總是想著去搞第二次。不過不包括他,倒不是他看到了什麼生命的美好,而是他變懶了。他開始玩金魚,并拍攝金魚的各個角度,試圖理解那個喜歡田名網敬一的高中同學的心態。這個世界對他或者對他都太不方便了,無論是死了還是活著都只有麻煩,於是他也三年沒有再用那麼大的力氣割手了。割手根本不可能死,奶奶的。
-10-
香草也三年沒死了。不過香子蘭女巫的腦子里一直電波橫行,鬼知道他在想什麼。自從脫離迫真藥效后他就變得盲目樂觀,快樂得好像被陽光迷了眼睛,看不清眼前的信號燈是紅是綠。Nothing but Sunshine!本質上他還是蠻積極向上的。香子蘭女巫的傳統藝能便是自給自足,泡在他自己的快樂麻藥海里漂流。他是這麼一個幻想家。滿金?算了吧。
-11-
人生便是戀愛和革命,然後再通向死。蜻蜓這樣說。
他的愛終究還是要給純潔的同學關係的。雖然中學生了,是時候早戀一下了。蜻蜓並不知道他喜歡她的哪一點,只是喜歡她。如同他夢中那個說不清美在何處的美人。
不過她就坐他鄰座。這個理由還是足夠單純。他無差別犯案。
她低血糖,所以口袋里總是裝杏仁巧克力。從前她遞一塊給了蜻蜓,蜻蜓在自己口袋裡捂了一天,回家時化得像水一樣,讓他感覺自己的骨頭都化了,變成柔媚的深褐色。還好那是塊糖,沒有滲到他的身上去。放進冰箱里,還可以再凝固回來。
雖然那口感實在很不怎麼樣。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愛的柳妹。
有的時候,她生病住院。蜻蜓自費買一大包杏仁巧克力送到她床頭,她會很開心,隨後說:
“我喜歡白巧克力。”
儘管如此蜻蜓依然認為她是杏仁巧克力味的。不過他不喜歡吃,除了苦,還可能因為馬爾克斯。一種悲哀,像白菊花茶。從一個讓人難忘的黃昏開始,她就去世五年了。
我的寶貝得了潛水病。
-12-
睡鼠深愛那個女孩,不知多長時間。和蜻蜓一樣,“睡鼠”只是一個可愛的一時興起的愛好,但她不想拋棄這個名字。她愛的人都死了,渾身是血,奄奄一息。她除了做她該做的,沒有任何選擇,沒有。在她患病的雛菊星球上,致命的陽光在燃燒,白色的光和火炫目地跳動著,夏天要到了。
差點就是末日了。她長出一口氣。
-13-
淺神保證自己和那個不幸的小女孩無關。他在公園里做他的自由江湖騙子,負責從他絢麗的帽子里變鴿子(然後扔掉它們)。作為一個精神的高危動物,他異常受小孩歡迎,也許因為他張開臂膀就好像一個稻草人,他樂意接受這一點。永遠的時間流逝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心是什麼。向日葵?一片蕎麥?針葉林?他不像睡鼠,專注地種雛菊。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個稻草人,無聲無息,眼睛不在這裡。偶爾他的身體里長出新芽,在垂死的凌晨五點。他是單純的快樂人,披著烏鴉皮毛的百靈鳥。——還有調色工,那個月之暗面人。狂氣從腦損傷里淌出來,祝有病人終成眷屬。
-14-
“人死後會是什麼樣的?”
她這樣問過。蜻蜓無法解答(和活著的人一樣),只好以唯物主義信徒的姿態說什麼也沒有。不會有天堂不會有地獄不會有下輩子,什麼也沒有,“我”只是大腦的工具,腦是操縱身體的那方。
“是電波。”
——也許我會變成電磁波,在交通頻道和音樂頻道之間的某個頻率上。她這樣說,好似深信不疑。蜻蜓當然不會相信,但他還是試了,不知出於哪個位面的僥幸心理。當然,這兩個頻道間什麼也沒有。
-15-
櫻桃就是那個冷漠地觀望世界劇場的傢伙,或許他早就買好爆米花了,雖然他拒絕吃玉米。他是個苦難的二十世紀少年,和葉子一樣,但比起葉子他更加適合去創造傳奇。放在五十年前,也許他會因為他的瘋狂而名垂青史,但現在瘋狂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有精神病,他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數。後現代已經不吃香了,是時候開發後後現代一類的東西了。
就算他是個理科人,還對軍機一類的東西頭頭是道,這廝還是有嚴重的藝術家氣質,像一種纏身重病。死對他來說像個小姑娘,像很多小姑娘一樣跟在他身後卻追不到,不管是金髮的瑪格麗特還是灰髪的舒拉密茲。他深有自信。
葉子,葉子葉子。你是秋水仙。你是被賣花姑娘放在籃子里賣的東西,劇毒不幸的藍紫色。它能讓人存活好幾天,充滿痛苦地死去,且保持清醒。
-16-
蜻蜓敗了。他沒勁去做追思校園生活的事情了,到了半夜,他該打菲特了。他清醒地躺在床上,關掉燈。在黑暗裡醒著,就好像在對黑夜里補作業和寫怪話的時光的悼念。——也許沒有這麼酸,總之這是一種習慣。長期的夜間工作讓他早睡就犯困,他遷就自己的身體。他晝夜顛倒,且無人想管。在失去她之後地球依然轉動,太陽照常升起,夏天早冬天晚。這或許也是快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