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日
“你妈妈的脑电波,不太稳定喔♪”
Evariste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此。他面对坐在月光下的窗前拿着不知是几年前买就一直放置着的吉他唱着歌的Akinly一阵错愕。吉他没调准音,他唱的也走调。Evariste选择了静观其变,但对方除了唱歌没有别的行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你妈妈的不正常,就是脑电波♪”Akinly唱,“你的妈妈不正常,你的妈妈脑电波,你的妈妈是脑电波妈妈♪”
先不说这个词的品味如何,调子也太难听了。Evariste爬起来,稍微靠近一些Akinly作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对方闭着眼。“难不成是梦游吗”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涌上来,但是那么怪异的梦游的举动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
就这么放着也不太妙,况且唱的歌也太难听了。但——应该说是兴趣使然,他没有叫醒Akinly,但也不打算继续让他唱下去。他走到Akinly身前,拉过后者的手(幸好他没有把吉他挂在身上,Evariste轻松地引着他把吉他放下),把他领回床上躺下。过了半个小时,Evariste意识到Akinly确确实实不会继续梦游了,望着天花板发呆了二十分钟后,闭上眼睛。
第二日
当Evariste睁开眼的时候对方的确不在身边。他不动声色地摸了摸床单,有点冷。Akinly不在房间里。他走出房间,餐厅亮着灯。Akinly坐在餐桌前,用一种极其休闲的姿势翻着书,桌上还放着一杯酒。
Evariste慢慢靠近他,走到他面前。他发现Akinly闭着眼,但还是用一种不平稳的频率(也就是时不时)翻一翻书,不过酒是没有喝。他蹲下身,看了眼Akinly的书。《安娜·卡列尼娜》。之前看上去很新,但什么时候买的就不清楚了。Evariste静静地看着Akinly静静地看了(梦游着)五分钟的书,最后把书从他手上抽出来,合上,盖好在餐桌前。Akinly没有醒。Evariste把脸凑到他面前,小心翼翼地闻了闻。一股黄桃牙膏味。对于就算是梦游也安安静静的Akinly,他满意地牵起对方的手,把他领回去。在床上,Evariste放了几首摇篮曲就睡着了。
第三日
Akinly还在看《安娜·卡列尼娜》。
今晚也没有喝酒。
第四日
Evariste认为,直到他看完都不会做下一个梦游行动了。
第五日
Akinly合上书,走到书房放好。然后他回到客厅,没开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想些什么。Evariste想他终于是看完了。Akinly靠在沙发上,然后站起来,走到Evariste坐着的沙发前(Evariste对他的如此准确的判断开始怀疑他梦游的真实性),什么也没有(气氛十分纯粹地)地半分钟后,他开始脱衣服。他松开睡衣扣子,就这么让睡衣滑到地上,头发乱七八糟地散着。在延伸到客厅的月光(或者是白色的路灯)的照耀下,Evariste无言地看着Akinly的脚背,受光铺满的位置像爬满了细细小小的萤火虫。晶莹的,纯白色的。Akinly站在光下,什么也没有做。Evariste盯着他的脸,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的路灯难道是该打这个光的吗?
随后,Akinly缓缓蹲下身,坐在地上。Evariste翻起他的刘海,看了看他的眼睛,把他拖回房间里去。睡衣的事就交给明天的Akinly来办吧,Evariste坚决地想。
第六日
在早晨还在使劲躲着的家伙到了晚上还是那么镇静。今晚的Akinly坐在窗前,十分偏执地为吉他写上了“胡桃木”。之后跑到浴室,放了一盆热水(Evariste再次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真的在梦游),没脱衣服就躺下去。想到昨晚上和今晚上的反差,Evariste觉得一阵莫名的笑意。他走过去把Akinly的刘海翻起来,湿漉漉地黏着。Evariste突然觉得有点像两只猫(不,Akinly是兔子。他纠正。)在舔毛。不过水是温的,他总觉得这个气氛有些像什么诗里写的那样,一时没想起来是什么诗。他颇有耐心地把Akinly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整理好,然后看着Akinly的侧脸。等到水温降下来,他再把Akinly扯出水,把衣服脱下来,让他在毛巾上滚了两圈,扔进了床底。一切都像往常一样,Evariste欣慰地想,明天Akinly又要嚷嚷了。不过被子很厚,他还不会感冒。
第七日
Akinly醒了。
他看着Evariste撑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顿时毛骨悚然外加不知所措。“怎、怎么了?”他问,“难道是我牙膏太好吃你给吃完了吗?”
Evariste摇摇头。
“那你是要对我夜袭吗!”Akinly警觉起来,“你好下流呀!前两天我醒了都是光的,我都不知道Eri还有这种兴趣,真是大变态!虽然我觉得睡奸本的确蛮有趣的……”
“别说话。”Evariste突然说。
Akinly眨了眨眼,转过头一本正经地和Evariste对视着。“唔,”他含含糊糊地说,“要以一个冲击性的结尾作为结束。”他说着,把半个头缩进被子里。Evariste伸出手把他的头发顺到耳后,眼底十分平静。
“一切都结束了。”Evariste说,“好歹,在一切结束之前活了下来。虽然活不活都无所谓。”
Akinly说:“什么?”
“没什么。”
Evariste用一种轻得不可思议的口吻说,“你还在,真好。”
Akinly继续缩进被子里,不过两只眼睛瞪得很大。
“黄桃味的牙膏很不错。”Evariste话锋急转。
“你果然是吃了!”
“我没有。”
“Eri好下流啊!”
Evariste躺下来,枕头比任何时候都让他觉得舒服。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不一会传来了平稳的呼吸声。Akinly看着Evariste的睡脸,悄悄地深呼吸,随后小心翼翼地爬下了床。
——
一个狂欢,一个庆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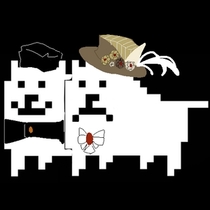

在她向我露出那个薄荷味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成了一对狼狈又自由的难民,在一个离熟悉的城市几十几百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沿着火车线,步行街,还有护城河堤的石灰栏杆上明灭的彩灯,向前向前。艺术家与难民这两个意象总是联结得那么紧密,我们大概属于后者,在地图上四处流窜。她和我都没有艺术细胞,没法从这流窜里得到什么灵邪的乐趣,除了她偶尔会说这彩灯的电缆在栏杆上画了一片片巨大的开口朝上的二次函数。我叫她数学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你是第一个叫我数学家的人,虽然有些过奖,我只不过是天生擅长解题而已。”认识她的第六天,她请我去了夜市的甜品店,点了一碗芒果雪花冰放在我面前。这是她第一次与我说超过四个字的句子。“因为一些老毛病,我更习惯被人叫有病的家伙。毕竟我着实是个奇怪的人。”
我觉得你哪里都好。我说,把碗推到桌中央。就算你把雨衣当成常服穿,还总是拉起眼前的纽扣,我也觉得你是一个正常又有趣的人。
那是因为我总该需要一个东西去隔开。每个人都把世界分成我与非我的两个部分,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划出这条分割世界的线。她说。对我而言便是这层雨衣,里面的东西,大约是与∑非我一样的重量。在我看来的话。——虽然一般理解起来,里面该是一个大脑,一个患病的身体,数式,字母,无法理解的语言与灰色的逻辑混合在一起,一并盛在这层黑色的塑胶壳里。
而且可以挡住这世界上倾泻的热雨。我说。
热雨。我和她便是在这样的时节相遇的,那时候她还对我没兴趣所以她很闷。六月的南风天是湿淋淋的,带着和了水的死灰的气息。她坐在四楼走廊的栏杆上看着刚刷过的,带着肥皂水味道的瓷砖,因为是在布置高考考场,所以清理比周末前的大扫除更加卖力。天上的乌云有一大片,阴森森地压着。她还穿着雨衣。尽管暂且没有下雨,只是穿着黑色的干燥的塑胶雨衣,拉着帽子遮住脸。正常的朝气的学生们已经急不可耐地拖着书包奔向期末前最后一个假期了,这层楼上一个人也没有。那时她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被丢在栏杆角落的黑色垃圾袋。我对她说过那一刻我心中闪过的比喻,做好了她生气的准备,但她只是说:
“其实哪里都没错。”
虽然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依然留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眼前是学校的大门。她没有穿她那身著名的雨衣。
我依稀记得我在里面跑过两千米,推过我的自行车,丢掉过三张饭卡。站在校门口,突然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个正要进门上课的学生的角色。门卫经常忘记查胸牌,我便无比自然地摆着年轻人的姿态踱了进去。就算我没有背书包。不背书包在校门间进进出出,对以前的我而言其实是有些尴尬的,所以从前我就算只是出去买点储备粮也会背着书包。现在我并不在意这个便是了。反正接下来,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学校把胸牌换成手环了。”在操场的跑道上,她像想起什么不算重要的事一样仰头说道,“所以这不是我们的学校。就算你戴着胸牌来也没有用的。”
“就算这样,难道你不是高二三班的吗?我不是高二五班的吗?我们的教室不是还是在西区向阳楼四楼楼梯口右拐的同一道走廊里吗?”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她又笑出声来。“是的。”她说,“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出来散步。而且我没记错的话,明天是高考的日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道。它和我印象里的样子相比几乎毫无变化,只是几栋混凝土砌的小楼忽然糊上了红砖,走廊上名人的挂画也换成了塑料黑框,看上去有些崭新得不伦不类。是的,崭新的不伦不类。如果要说我总感到哪里有些陌生的话,大概归功于这些东西。
“我想我们走进了一个共同的噩梦。它是那么怀旧的,熟悉到几乎流泪的,但是有时又让我感觉到它彻头彻尾都是错的,相似的东西从来就不曾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在操场的绿化带前,她又开口道。我很了解她所说的“噩梦”的感想是什么,因为我瞄了一眼,绿化带里原本那有着深红色叶子的灌木不见了。
“这要看你能记住哪些东西。”我说。
“记住的东西都错了。回来看一看,其实什么东西都和我印象里的有一点差别。果然现实是现实,我认为的现实是我认为的现实。”
大概你所记住的现实都已经被加工过一遍了。
毕竟曾经是穿着雨衣的天才,可能可以被叫做雨人吧。这听上去像一个冷笑话。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她跟我解释过什么叫一个患病的身体。计算强化的学者症候群。其中的一半会有脑损伤与脑疾病,而另一半有一种自闭症系列的障碍。我是后者。她说。我知道,我们都是先天性的病人。
“一件旧事。在我家门口的幼儿园里,我多少也做过一个让所有老师挨个抱着的乖宝宝,让我格外地喜欢那里,和一上幼儿园便吵闹哭泣的小孩不同。我叫得出每个阿姨的名字,她们说喜欢我。后来我上了小学,回来想告诉她们的时候我被她们挡在了外面。——你是几班的?小学一五班!——那你现在不是幼儿园的啦,请你回去!我最喜欢的阿姨和我说。我回家把枕巾都哭湿了。很久之后我才想通她们其实是不会记得听话的孩子叫什么的。”
她同情,或者说共勉地地拍拍我的肩。
“上学让我联想起灾难。和许多人一样。”她说。
“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我与所有人都不在一个频率上,像一头五十二赫兹的鲸鱼。这种感觉,大概类似老师把你拦在门外不让你进教室。”我们路过西区的向阳楼,它带着新刷油漆的味道,让我想起在街头问过路的那个女人的笑容。“我就经常做这么一个梦,被锁在我熟悉的教室的门外时候。我拍着门喊着让我进去请让我进去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还能上课我还能考试我还在全国数学竞赛拿过一等奖的!但里面什么也听不到。里面在读下一课的单词,每个都和我印象里的一模一样,我都能把它们按顺序背下来了。但这就和我没有关系。
“我醒来就想,我是该落荒而逃,还是干脆死皮赖脸一点在外面读起书来呢?想一想我的风格是后者——我对单词倒是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自作多情地想杠他们而已,我总是摆出一副硬派脸和各种各样的人杠上。不过每次这梦做到我意识到‘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时候就结束了。实际上如果成为现实,首先我就不会去敲门的。”
她仰头望着四楼,我跟着她望过去,不小心看见了楼顶上露出的一大片乌云。
“我知道你本来就很闷。”
“我没兴趣的人看我才觉得我闷。”
“所以说实际上你可以开朗起来啦?”
“我不介意在我喜欢的人面前开朗。”她说,“只是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喜欢的人。”
一瞬间我觉得她才适合去撩妹。
“自闭的人无论过多少年也依然是自闭的人。这条界限是刻在眼前的,所以我只能是我,非我只能是非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学一学一种新的语言系统,我与我之间,用这种语言交流。自变量是主语,因变量是宾语,谓语划出了函数图象,用语言的性质去描述它的性质。我能熟练地用这种私人的语言去抒情,去对着雨天歌唱,只有当它不被任何其他人理解的时候,我才感到安全。”
她说。
“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乐意做出开朗的引导者的姿态,把这个机会给你。”
“如果用一种动物去形容你的话,大概是海龟。
“绿海龟的心脏九分钟才会跳一次,一本名著里说,它的心脏离开了身体还可以跳动几个小时。它沉迷于生活在自己的密室里,生活上几十上百年,被全世界的时间抛下。我觉得听上去有一点你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听上去能量都很低吧。按照你那样的说法,导数等于零一样的平稳又沉郁。低能量的人通常比较长寿,不是吗?”
“可能吧。”
“我的心脏是不会停止跳动的,无论我试了多少次,它也还在连绵不断的阴雨天里不断地跳着。”
高二五班的牌子变成了高三五班,地砖倒还是同一片,假期前大扫除时他们热情地用刷子和肥皂水刷过的米色地砖。教室里谁也不在。她轻快地翻上栏杆俯视着我。今天她没有穿着雨衣,尽管暂且,马上大概就要下雨了。我总感觉她这么坐相当危险,但我不想阻拦。
“那样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吧。”她说,“像那天一样,再来一次。”
“啊,像那样吗?”
“嗯。”
“你是三班的吗?”
“是。”
“高三的吗?”
我把高二改成了高三。
“是。”
“那你,明天便高考了吧?”
“是。”
“你不在家里复习吗?”
“不。”
“啊,我知道你。
莫非你是我们数学老师说过的,三班那个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的保送生?”
早就知道数学好是一门强势的干货。班主任在班会课上会充满憧憬地念那些竞赛优胜的好学生们是多么的认真,是多么的严谨,是多么的自觉,既不认真也不严谨更不自觉的我们听到这些不仅没有如他所想一样羞愧地低下头,反倒更麻木不仁地偷吃起早点来。你去过竞赛吗?——我们互相问。没有,真可怕。——拿奖的家伙一定都长着兔子耳朵和四只爪,不然怎么听着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物种。——说得好像驯兽马戏团一样(大笑)。是的是的,还有三班的那个有病的家伙啊。
“是。”她平静地回答,“该你了。”
我低下头,因为我看到闪电在黑云里划过。雷声响了起来。
“我没有保送。也没有足够自信,我只是头脑空空想出来走一走而已。”
她偏过头,好像要说些什么。不过还是什么也没有说,把没有温度的眼光从我身上转到肥皂水味的地砖上。我忽然紧张起来,好像刚才那一刻我和她之间的关系真真切切地变回了陌生人。她刚刚才给了我那样一个机会的。我连忙想拉点话题,但是的确是头脑空空。
空气黏成一片。
忽然,她跳到走廊上来,几滴水珠洒在栏杆上。下雨了,大概只需要十秒钟就会下成一片狂热的大暴雨,在这种季节。我以为是她主动结束了这角色扮演,但她向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指去,那里走出了值班老师。——三班的班主任。他那有点治不好的皮炎的脸曾经是我们班私下的笑话。我怕他隔这么远也能一眼认出来她是那个让他受了不少赞誉的数学竞赛一等奖。
你们是哪里来的?他边朝我们走来边问道。我觉得此时解释比不解释更麻烦,只是他看见了她的脸,一时满脸都是迟疑。“我好像认识你,”他说,“你是不是曾经三班的学……”
“不是,我是六班的。”她轻描淡写地扯起谎来。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她没有穿雨衣。
他偏过头看着我们,感觉像是有一个什么道理苦思冥想也想不透。他伸手摸起口袋来,大约是想打电话给办公室里坐着的六班的班主任了。在那一刻她拉起我的手飞跑起来,和她刚才说的一样,落荒而逃。值班老师的喊声被甩在身后,尽管它秒速三百四十米,我跟着她飞奔而下,跑过楼梯跑过大厅跑过操场的跑道,一直跑到进来的东校门。雨越下越猛,迎头砸在她的身上我的身上我们的手上,踩过一片水洼我的鞋和袜子大概也湿透了。虽然跑相比较狼狈,但是我并不紧张。大概这是我第一次气定神闲地逃亡,从老师的手里逃亡,却镇定到不需要喘气。在校门前回过神来,我感觉刚才大概是飞过来的。从四楼的教室,用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轻飘飘地飞了过来。虽然在暴雨天里飞行听上去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不过每次厌倦爬楼梯的时候,我就会站在门口这样想。
灰白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在不锈钢的校门上,折叠门只开了一条缝。传达室里是黄色的灯光——像是到了晚饭点一样,虽然刚刚上下午课,只是天色昏暗极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这句刚才闪现的话又回来了。至少不该去这里,虽然我对它无比熟悉,跑过两千米,推过我的自行车,丢过三张饭卡。
但现在我没有在这里的理由,大概我早就不是个学生了。
我们钻过那条窄缝,不管门卫有没有看到我们——大概是看到了——踩着已经漫到脚踝的水,穿过学校门口那条马路,差点撞上一辆车,我与司机的目光短暂地交接了一下便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们跑进了校门口的小吃店里。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买晚饭,里面是一股熟悉的酱味。最大强度的电风扇把风冲到我湿透的身上,让我感觉自己掉进了冰箱。
“胡椒面。”她伸出两根手指对店主说。我们坐在角落的双人座,想起刚才飞一样的奔跑,不禁笑起来。
“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学校里没命地逃跑啊。”
“我说过吧,这不是我们的学校啊。”
她没有穿雨衣,像个普通人一样湿成一团。她用手指划着盖在眼前的长发,雨水从上面滑下来,淅淅沥沥地掉在白瓷砖的地上,变成灰黑色的污水。
“我很讨厌下雨天后的白瓷砖。每次雨天都会很难清理。”我说。
“也是。但我便是生在下雨天的魔头,说不定我是一只青蛙吧。”
“不,你比较像一只海龟。”
她愉快地看向我。
“这是一个有趣的印象,和当时你称我为数学家一样。”
面来了。
“接下来去哪里呢?”
“没有想好。”
我望向窗外。全世界模糊在一片银灰色的雨幕里。从学校里逃出来时,我们已经对这里有些陌生了,连那个灰色的路口叫什么我和她都说不上来。我能心算七位数乘法,但却记不住我的过去是在哪里生活的。她自嘲道。前路和未来一样茫然不定。
“去我家吗?”
“随意。”
“那里并没有人,看一下午电视大概也可以。”
“要不要离开这里?”
“怎样的?”
“去几十几百几千里以外。那里有护城河与石灰栏杆上的彩灯,还有雨后充满水的味道的空气。”
“可以啊。”
她露出了笑容。我说过,那是个薄荷味的笑容。我没有问她怎么去,就算听上去并不靠谱,好像我们两个难民样的家伙终究会饿昏到街头。只是当我隔着胡椒面的热气,看见罩着水珠的,她那张清爽的笑脸时,我感到了一种深沉而轻快的幸福。虽然前路与未来一样茫然不定,但不管接下来所向何方,还是无路可去,我也终究不会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