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冷啊。”
大府的宅子建在半山腰,每到冬天就冷得格外快一些。彼时的大夫人才刚有一些学习兄长做侠客的念头,每天拿着一柄木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再有几个月她便要及笄,不过她已和她的郎君说好,她要去做大侠。
那时候的老爷也还是少年,还没去沉于秦楼楚馆,整日里不是找别的公子哥骑马射箭,就是来大府翻墙头。
“山上本来就冷的快,你还穿这么少,大哥见了一定要训你。”甄少爷踩着梯子从墙外翻进院里,一边打量着对方的打扮。
“才不会呢,”姑娘停下练剑的动作,炫耀似的挥挥手,她眼珠一转好像发现了什么,几步跑到少年面前伸出手“你是不是给我带东西了?”
“这都瞒不过你。”甄少爷把背在身后的手伸出来,动作一晃就把一根簪子钗到大小姐发髻间。
那是一支木制的簪子,但是被手艺极巧的匠人雕琢过,上面还缀了几根蓝色的翎羽。
“好看么?”
大小姐的手还悬在身前,准备去摸簪子的时候又被甄少爷止住。
“你的手好冷啊。”略带嗔怪的语气,甄少爷指尖摸索着姑娘的手握紧,细细抚过人手心的掌纹,弯着眉眼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口胡诌着:
“姑娘,你的命纹很好嘛,一生顺遂平安幸福。”
“然后呢?”
似乎确实觉得冷了,又或者身边人肉火炉的温度够高,大小姐钻进甄少爷的斗篷里,扬起脸催促着问他。而少年则仿佛故意吊人胃口似的停顿几秒,几秒的寂静又显得那样漫长,只把斗篷下的姑娘抱得紧些。
。
甄老爷动作轻柔地将毫无知觉的人搂抱在怀中,拿起掉落在床铺上的蓝翎发簪,斜着插到怀中人散乱的发中。她长长的睫毛掩住了灵动骄傲的目光,苍白惨淡的脸颊没有了当初害羞的神情,她的嘴紧闭着,再也说不出话。
就连那柔软温热的手,也变得冰凉。
。
“真暖和。”
大小姐小声说着再向甄少爷怀里靠靠,贴近了面颊等着他的下半句话。
“……就算死,也会死在爱你的人面前。”
——说来你兴许不信,我瞧你几分眼熟。是欠你一杯酒,还是欠你一只镯子?
惠太后是行来无声,青石板里碎刀兵,划破双雪里白,金丝脱了纹路再染淤泥,哪里瞧得见风雅。先踏长街,再上雀桥。月色借美人一寸光,好教她往断壁中寻条路,莫往无间去,身存阴阳界。
幽冥帛,纸铜钱。
往那桥上信手撒,魍魉拾去替她买路。
醴都困不住这厉鬼,要那修罗显形。
瞧一身破袍烂甲没了人皮,骑的分明是凶角夜叉,业火燃身,烧个孤魂野鬼。恶煞持人骨,往生台都容不得这般冤孽。
可桥下黄泉忘川水,映的却是凤袍贵妃,抱杆沥血枪斜倚匹桃花骠,桃花眼里尚且含着情。
“我来祭你。”
胭脂骨,玉露香,替你画皮。剜块心头肉,渡口生人气,捏个有血有肉。
要你重回阳间做个金贵人家子。
“我认得你,惠贵妃。”
“我还你一杯酒。”
“笑话,阎罗太岁来讨你命,你就还我一杯酒?”

唐川是会用剑的,他在芒玉并非以毒术称奇,真正称奇的是他的剑法。只不过他并没在影表露过这件事。
尹雪再见唐川的时候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往事温柔早在杀戮中消磨殆尽,唯有唐川还是那副笑嘻嘻的模样,和尹雪仅存的儿时记忆约约重叠。
“你做的事,能置喙不是我,乃是道义。”
唐川轻叹宛似叹息,孤零随唇迹笑意抿去。只可惜伊红颜绝艳,却落不得最美句章。
白玉剑鞘,剑就已无声而出,以臂使剑,并不直击剑锋,向后一掠。待扫过颈侧,然后才向她喉间抹去。
“乃是世间道义。”
“哈?”
尹雪难得沉声,道出疑虑,声色清寒,却是听不出什么喜恶。但凝滞的气氛,及其快成一线的皎洁寒光,却已昭显出持剑者内心的狂怒。
“道义?”
尹雪的剑势回转,向左微挫,格住唐川的杀招,仿若春日里断了线的飞鸢,轻身若凭风,凌空向后掠去。身后便是入天古木,珠履在木中一踏,才振袖而起,黑衣如影,比不得白鹤戾空。
“从我落为遗孤开始,我就知道——谁是胜利者,谁就掌握了道义。”
稚女年岁虽轻,但身法步眼,力道声势,一毫不差。
“世事一场冰雪,却不知你将之只看得这般浅薄。”
唐川身姿灵巧,剑越腾兔,追形超影,虚晃一剑,就和尹雪拉开了距离。木叶萧萧而落,他的神情不愤激也不过于洒然,掌中把剑,便将此生护持的信义高擎剑中,肆意挥斩。
“小姑娘,你会使剑,却不会用剑。”
素手转腕,似放撷花,长剑一收,漫天剑气顿时消散,连同白雾,也一并随风去绕远山,做了山中神女的鬓上雾花。
“世人常说,说不可为之。前辈,领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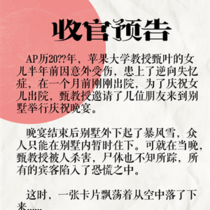
——你若能在夜风吟诉中听得马蹄声。
晨昏荣朽都已奈何不了她。许是红墙青瓦,天家宝顶方才困得住她,不若说是成全她盛名。这恶鬼生前不可一世,如今还得如何放肆:所幸添进堂前燕窠,剔剔透透一截指骨,架住雏鸟横梁。
她顶着镇国将军的名字,着皇后的凤袍,以长公主的礼制入葬。
——你听得这马蹄声顿在何处。
檐下贴红褪墨,一双石头狮哪里镇得住太岁,水磨青石踏上一双白粉绣鞋。那恶鬼以马代步,横行街上,但却舍不得踩碎一瓣梨透白。
你在此地作甚?
照旧斜倚门栏,勒停马。眼底盛桃花。
——你竟看得见我。
莲峰清静,白日青树,铜炉雕铸瑞兽,檀灰细碎,线香燃半,陶壶水沸。恍有清苦涩鼻的气息扑面,贾夫人敛袖替来客沏茶,语带三分笑意。
“你的伤基本痊愈了。”
“都是夫人妙手回春嘛,”唐川背着手走过来,也不客气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不知夫人家中可有宝剑,某在此愿给恩公谢礼。”
“你要舞剑?”
唐川没做回应,贾夫人还是命贴身侍女去金武阁中取来一柄剑,一并取来的还有一把琴,夫人袍袖一翻,悠悠一句。
“请。”
一声落时,唐川起身。
广袖拂开,云纹飒然,带几分风流意味。
或许是因饮的那杯茶,又或者是因他本身对旁余无所谓。
“借夫人家的剑一用。 ”
唐川那时已站在树顶,自高处落下时,引来家丁不小的骚乱。他自旁侧侍女手中,抽来那柄长剑在手。清影悬若一线,指按寒水刃面。光映落他眼底,照那笑意也凌厉。
薄唇翕动,他未出声,目光遥遥落树影之中。
——夫人,今为你一舞,可看好了。
似是漫天星辰落他剑尖,寒光白亮如雪如银链,在翻飞绛色,奏乐里连成一线。
昔有魏晋南山子,弹剑作狂歌。
严格来说,唐川的剑并不成章法,说舞又失了柔美。可贵在舞剑人写意自然,又合着韵律节拍,由他做来,反有几分名士的狂放。
剑尖遥指时,舞乐声停,墨发衣袖旋,一点花瓣拂唐川唇畔。冲冲剑气拂乱院中花草,一片朱红,幽幽吻剑尖。
他却将长剑收的利落,归还时,于夸赞于调笑,皆温温道一句过奖。还身落座时,若非气息尚有不稳,便好似不曾,做这一曲剑歌。
“尽兴。”
贾夫人抱琴颔首,唐川眉眼间温煦犹在,好似方才剑影,无声言语,皆由另一个人做成。唐川似乎天生有这般本事,任是杀人也罢,舞剑也罢,总教人知,皆是他无心作为。
“唐川,我的名讳。”
日渐西沉,茶水全凉的时候,唐川突然开口。顷刻里红霞里烧灼遍穹绯烟缭雾,丝络游走,两人短暂的对视,然后墨色就撞上墨色,极尽一种机缘巧合,奇异又精微。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良人的名讳。”
大甜甜和小蜗牛似乎吵架了,原于小蜗牛要给大甜甜的口红切个斜面,结果切多了。小雪糕和寿小司拎着菜来到大甜甜家里,得知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见姐姐在厨房里忙碌,小雪糕只得和寿小司一起帮这个姐夫想办法,但卫大龙不会有这么作死的举动,小雪糕也没谈过恋爱,三人还没讨论出结果,大甜甜就喊着几个人开饭了。
是竹林野雉鸡,一斤二两重,褪毛去肠收拾干净,炖个熟烂。
端上桌是陶盆儿,还沸着热气,浮层鸡油撵着葱粒往边上挤,并些时鲜嫩菜芯,绿得冒芽,正巧是烫得将熟未熟。
白面的大圆桌,大甜甜就势占了上方位,一盏白釉碟,一只缠枝青花碗,手中拿着竹箸,探入陶盆内一夹,软烂鲜香。
两只翅尖儿被分与寿小司和小雪糕,大甜甜扯了鸡腿先搁置在碗中,方才捡了剩下那只搁自己面前。
“甜甜,我也想吃鸡腿。”
小蜗牛看了眼自个尽是白饭的碗,憋着张脸,硬生生非给憋点委屈样出来,学个不伦不类。
大甜甜指尖捻着那鸡爪子轻轻一扭,凑过去塞到人掌心之中。
自然一如往常的温煦。
“这也是鸡腿的一部分,爱吃吃,不吃就喝汤。”
应该是新年篇,但我不知道写什么了,所以占个篇幅,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恭喜发财,新的一年能够开心顺利。
春节跳过了两个不详数字。
坤道X新郎(安泉/贾姑娘),双性转注意
安泉蔻丹拢着道袍,白袍滚海纹。
她是一枝含苞菡萏,婷婷道人身侧,眼里是城中茫茫雾水和他。微风牵上衣角,桃花绢与太极袍,粉的白的缠在一处,映了湖水湄边恰好春光。
她嗓里像酿着蜜,清朗朗地开口:
“道长从这经过,不知引了多少好姑娘,但偏偏赠伞于我。”
“是不是瞧着我眼熟啊,道长?”
安泉掩了笑,五指攥着桃花绢儿,那身仙骨贴得她更近了一些,一身胭脂红尘都染在他身上。
“我修了千年身,只为在你身旁站一会儿。”
她眉眼里又是清纯又是狡黠,眸子里能唱一出戏,缠缠绵绵,尽是水波春好。
“就一小会。”
“好不好呀?”
那道士折了片火红海棠,这艳物在人低温的指端陡出一丝突兀,他伸手簪与她耳边时,有风拂过。
“贾姑娘,今天有人告诉我。”花瓣悠悠吻在湖面上,一吻也落在姑娘唇角。“替你别了花,就是我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