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少主失踪的消息传出已过了两日,在此期间,城中要道和出入口均设下了不少卫兵盘查过往行人。江湖各处来的侠客也仍然活跃各处探查着蛛丝马迹,而百姓也如往日一般继续日常劳碌。
这日,沈平依然坐在客栈大堂里吃着炒菜,整合着这几日他在矿场和村落探听到的线索和消息。
说来也奇怪,少主被绑架了,那歹人竟毫无作为,究竟是何意呢?为钱?为人?连个信也不传。城主虽是着急,但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也只是守住城内各类要道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罢了。
饭后他打算再探矿场,却不想外头竟传来一声马嘶。
沈平马上抽着剑跟上那马上卫兵,那人行至城主府门口方才勒住马,他翻身越下,自怀中掏出块玉佩,高声喊道。
“于家的伙计传来消息,说是在矿场一处洞里捡到了少主的随身玉坠,瞧着是往深处去了!”
听闻此言,聚在城主府周围的人群瞬间起了骚动。有的已经马不停蹄赶往矿场,有人仍觉得疑点重重,有的赶忙上前盘问中那马上卫兵,企图再捞点其他的消息。
沈平是没有时间管这些了,他也立马赶往矿洞。里头已经有几位侠士进去了,他点着火折子燃着火把也孤身一人往洞口中去。
矿场地形复杂,伸手也不见五指,沈平只听见看见自己的脚步,还有水滴声以及凌乱的脚印和散落在洞旁的各种器具和推车。
这里似乎并不仅为一处矿洞,而是由多个洞窟连在一起,内部曲折,蜿蜒岔路众多。如今眼下已无退路,他只得往前一探究竟。
寻着面前的一条路,沈平踏入了一个洞窟,此处洞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古怪符咒。同时他也感受到有侵入骨髓的凉意沿着洞深处蔓延开来。
这很不对劲,再往前走,洞里竟突然起了雾。也不浓厚,只是肉眼可见,随着一阵雾起,沈平意识到此处为一处幻阵,顿时大感不妙。轻功立马运起又要跳出这古怪幻阵,但也已经为时已晚。只见周遭烟雾已盘旋在脚下,逐渐攀升而上,而周围的景色也逐渐变得模糊扭曲。
雨,很大的雨。
沈平睁开眼。
不远处,站着两个人。
天地间仿佛挂了几层珠帘,冰冷的雨水冲刷着长街的青石板,溅起细碎的水花,街灯在雨幕中晕开一团,昏黄的光勉强照亮巷口对峙的二人。
左边的人一袭白衣,却已在雨中早已湿透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挺拔的身形,他手中只有一柄合拢的折扇,白玉为骨,苏绢为面。在这杀机四伏的雨夜里显得格外的雅致,右边的人身着玄色劲装,几乎要与这浓稠的夜色融为一体,他手中握着一柄剑,剑未出鞘,却能感受到那股迫人的锋锐。
雨水顺着剑鞘滑落,如同泪痕,两人就这样站着,任凭雨水浇淋,谁也没有先动。
“你不该来。”沈平的声音比这雨更冷。
“但是我已经来了。”白衣男子微微一笑,手中的折扇轻轻敲打着掌心,“江湖上,道理往往需要用血来写,正因如此,我才来。”白衣男子笑容不变,眼神却锐利了起来。
话音未落,沈平的剑已经到了跟前。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光,如同黑夜中的闪电,悄无声息划破雨幕,只取白衣男子的咽喉,快到极致。
雨水似乎都已经被这一剑斩断,也就是在这同一刹那白衣男子手中的折扇唰的一声展开,上面并非寻常的花鸟山水或是书画字句,而是一片泼墨般的浓黑,又将几点金纳入其中。在这雨夜中,那扇面仿佛骤然展开了一个吞噬光线的洞口。
沈平的剑尖点在扇面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火星一闪而逝。那看似轻薄的绢面竟不知是何材质,硬生生抵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剑。
沈平瞳孔微缩,但剑势不收,翻紧手腕一抖,长剑化作点点寒星如大雨倾盆笼罩向白衣男子周身命穴,剑光在这一刻织成了一张死亡之网!
却只见白衣男子身形飘忽,如同风中柳絮在密集的剑光中穿梭,他手中的折扇打开,动作优雅从容,仿佛不是在生死相博,而是在雨中独舞。扇骨与剑身不时碰撞发出或清脆或沉闷的响声,在哗哗的雨声中交织成一首诡异的曲。
沈平的剑意越来越快,让周遭的雨水都避开三尺,他的剑法凌厉每一招都力求毙命。
而白衣男子的扇法更为诡异,往往于不可能的角度用带着一股阴柔的力化解掉刚猛的剑势。
突然,沈平一个急刺穿透雨幕,直指白衣男子心口,这一剑凝聚他全部的功力,气势一往无前。
白衣男子似乎避无可避,但他却没有躲。原本张开着的折扇猛然合拢,如同白玉打造的短棍,不偏不倚,擦过了那剑尖。
两人再次站定,隔着雨幕相望,经过方才电光火石般的交锋,彼此的眼神中都多了几份凝重。
沈平深吸一口气,压下胸中翻涌的气血,他握剑的手因着刚刚的一击和大雨带来的失温,指关节已然发白。而白衣男子依旧从容,但眼底闪过的一抹凝重和微微震颤的手腕显示他刚刚也并未轻松。
没有预兆,两个人同时动了。
沈平人随剑走,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预图刺破这雨幕和眼前的一切,这一剑摒弃了所有变化,只有速度与力量一往无前。
眼看剑锋将至,白衣男子猛的吸气收腹,身体没有骨头般向后弯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剑锋堪堪贴着他的鼻尖掠过。同时,他点向沈平命穴的折扇,方向不变却骤然加速。
噗!
扇骨敲击的声音与剑锋划破衣襟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两个人交错而过背对背站立一动不动。
雨声似乎又在这一刻消失了。
滴答。
一声清响打破了死寂,不是雨滴,是血滴落在积水中的声音。
沈平缓缓低头看向自己的衣衫,那处已被点破,一个小孔透出一股阴柔的尽力让他半身酸麻,几乎握不住剑。他知道对方在最后关头收了力,否则碎的不是衣衫,而是他的肋骨和内脏。
白衣男子也缓缓直起身,胸前的衣襟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渗出的水珠迅速被雨刷冲淡。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沈平剑锋上的杀意,也在最后化斩为扫,否则他已被开膛破肚。
沈平还剑入鞘发出一声清响。他没有回头,声音中带着一丝复杂和未尽的颤抖。
“……为何收力?”
白衣男子轻轻抖了抖折扇上的雨水再将其合拢。
“我想要的本就不是命。”
“那你想要什么?”
“一个答案。”白衣男子转过身看着沈平的背影。
“三年前,孤枫林外,你是否救过一个垂死的少年?”沈平身体猛的一抖,豁然转身,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死死盯住白衣男子那张被雨水打湿却又依旧带笑的脸。
“那是我师弟。”那是白衣男子的笑容淡去,眼神变得锐利如刀,他死前。只说了雨剑二字……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到底发生了什么?”
雨渐渐小了。
沈平默然。
长街之上两个浑身湿透的男人。一场生死搏杀之后,开启了一段关乎真相恩怨与救主的对话,而这场雨仿佛只是为了洗去掩盖往事的尘埃。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沈平站在洞中,也只是站在那里。
他在借着这道烟,看向过去的某个人,也看见过往的某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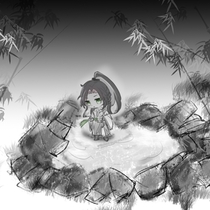
福源客栈。
沈平刚从二楼窗户处翻回自己的房间——别多想,他只是踩着城内的房檐几息之间便回到了白天瞧见朝廷神鹰阁鹰犬几众出现过的地方......
百花坊?沈平率先在脑中排除了此地,此地人多眼杂,浑水摸鱼的人犹如过江之鲫,偶尔问点什么就被有心人抢先一步套了话,人流量如此之多不便再细细查问了。
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跑着江湖,兜里没几个方圆兄,万不能在此地就给歹人摸了去,虽然沈平自己也有这番手艺,但此举断不是江湖侠义之举。
这么想着,沈平来到了商肆市井。
石板路泛着水光,柔和的月色如上好的缎子一般和水巧妙地糅合在一处,周遭灰黄的纸灯笼烛火未熄,也悄无声息汇入这月色河流之中。
沈平说不清楚自己怎么就在此处放慢了脚步,但白天里客栈大堂的那一桌人说的话还犹在耳边回响。
——————————————————————
【喂,于家最近那活儿,你们去不去?】
【你敢去?我可不敢!】
【你们没听说?于家主给的钱是多一一可前些天我同乡去了,本来以为是个好活计,结果刚于没两天,有天回来了在屋头躺着等饭,等热好饭去叫人,才发现人都死透了!】
【当时整条腿肿得那个高哟,牛边身子都紫了,眼珠子瞪得老大,合都合不上,他婆娘当场就吓晕了!】
【他婆娘说他那几天老念叨着什么'洞里边有怪味'之类....我听人说,城东那边的矿里是挖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去那儿干活,晓不得什么时候你就犯了忌讳,就要了命了!之前不是没了好几个...都那边出的事儿!】
【唉,要我说,哥几个都拖家带口的,为眼前这几个钱丢了小命,不值当!昨晚上我还见个有人那般大的黑布包从矿上运出来,沉甸甸的,保不准又是哪个倒霉蛋栽里头了......】
————————————————————
按理来说,他该去矿场那块的,但大晚上出城去一个出过人命的地方也太引人注目了,这并非沈平期望之内的。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调查未果,沈平原路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却不曾想,今夜是城中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来了。
天光微亮,雾薄未散,沈平轻车熟路来到前几日招亲仪式的地方,擂台的喜绸红纸还落在原地尚未收拾,台前零零散散点着几个人了,一丝疑虑忽然浮上心头。
只见前面几人凑在一起寒暄了几句,城主府的方向几声炸响传来,不同寻常的声响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力,沈平一个腾身直接运起轻功往城主府而去。
城主府前很快便围了一圈人,个个引颈张望,窃窃私语声如同潮水般涌动。朱漆大门豁然洞开,一队铁甲卫兵扛着沉重的告示栏冲出,重重砸在石墙前。
人群霎时涌上,将那朱红围得水泄不通。
告示上,墨迹未干。
季灵泽的画像栩栩如生,眉目间还带着招亲那日惊鸿一瞥的疏朗风华。可旁边那行字,却透着刺骨的寒意:“昨夜玉城少主疑遭贼人所掳,不知所踪。”
人群哗然,惊叹与猜测如同沸水般翻腾。白银千两已是寻常人家几世都挣不来的财富,而后两条……更是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沈平就挤在这片喧嚣鼎沸之中,却瞥见一个身影悄然自人群外围掠过。
那人并未像旁人那般拼命向前拥挤,只是隔着人海,淡淡地瞥了一眼那画像。
目光触及画像上那双熟悉又陌生的眉眼时,他眼底似有寒潭微澜,但瞬间便归于死寂,快得仿佛从未发生过,似是撞见沈平的目光,他不再多留转身便走,毫不留恋。
“喂!那谁!你撞到人了!”一个粗鲁的汉子被他肩头轻轻一带,竟踉跄几步,不由怒喝道。
青衫客脚步未停,仿佛未曾听闻。
那汉子自觉折了面子,骂骂咧咧地伸手欲抓他肩膀:“老子跟你说话呢!”
就在那粗厚手掌即将触碰到青衫的刹那——也不见那人如何动作,仿佛只是随意地侧了侧身,那汉子便觉得一股诡异的大力扯得他下盘一空,整个人“噗通”一声栽倒在地,摔了个结实的嘴啃泥,周围瞬间一静,所有目光唰地集中过来。
短短几息之间,沈平对此人动作尽收眼底,那诡异的步法对他来说甚至有些可怕的熟悉。
目光再度转回告示一栏,沈平唇角勾起一丝无人察觉的冷峭。
寻人?
这江湖,从来就不是找人的地方。
是杀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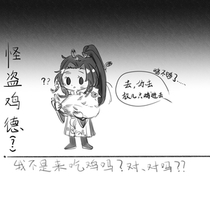
“比武招亲?”沈平挤在人群外,对着嘈杂的人群提炼出来这么一句。
“那可不!”隔壁健谈的大哥马上就过来搭话,自觉承担了接下来的解说“当年这季城主武功非凡,与人在西子湖畔切磋比试,那一手刀使得出神入化......”
"刀法?"闻言,沈平来了兴趣,忙不迭接上一句,怕得大哥不说了;“这城主大人如何?”
大哥这不有人听就来劲了,唾沫花子不要钱似地往外蹦;“湖水涟漪,放眼望去只余残荷,可咱们城主竟是生生连着这湖水和残荷一起,劈成了两半!”大哥怕不是说书出身的,语气给人兴致吊得老高了。
“那这次比武招亲是和城主千金打还是......”讲到这里,沈平的语气带上了点他自己都未察觉到的兴奋:“还是和她爹啊?”
“小伙子想啥呢!当然是和各路英雄豪杰进行切磋武艺了!”大哥扬声摁灭了沈平已经飘远的思绪,“要是个个都和城主大人或是少主打,那不得是车轮战吗?”
“哈哈,那倒也是,大哥说得对哈。”沈平跟着笑,心思却又不自觉飘远了。
次日,武斗台前盛况虽不比昨日,但是满眼的刀剑兵器将周遭氛围闹得热火朝天,沈平吃过早饭才懒懒地抱着剑到地,窝着个地就先坐下开始消化肚子里的白面烧饼了。
“文......算了吧,我会写我的名字和三字经已经算是对得起我一年的书塾日子了......”沈平漫无边际地想着。
对,他就是纯来看热闹,顺带手痒想切磋两把的。
台上大汉抡着自己的银环刀挥得步步生风,那边的江湖郎中摸出一把银针使得出神入化让沈平有些来不及看清,只见那人手腕一翻银光一闪对面的刀就“叮当”两声挡了下来。
这大汉也不赖,粗中有细,步法扎实,看样子不是半路出家的。
但是,沈平撇了眼同样靠在场边的官袍之人,如此场面昨日沈平就已经知晓了这几人,来此是意欲何为,这难道不是什么普通的比武招亲?
算了,沈平不去细想了,总该是有什么机密要务在身,合该都是与他毫无干系的。
这么想着,沈平跳上了比试武台,冲着刚刚获胜的江湖郎中一拱手:“敢为兄台姓名,有无师承啊?”
青年只是皱皱眉,但还是回答到:“一介郎中,跑江湖四处行医偶尔锻炼拳脚罢了,让兄台见笑了。”
沈平黑衣如墨,手中的剑泛着光,像一段被遗忘的月色,青年手中空无一物,沈平却不敢大意。
剑光乍起!仿佛一道闪电毫不留情撕裂了雨幕,快到极致。剑锋迅速弹开飞来的银针,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决绝自取青年咽喉。
一定要快!这是沈平看清对方甩出武器的一瞬间就意识到的事实,事实上他也足够快了,但还是有漏网之鱼擦者耳边过。台下的看客还在惊讶,台上的二人手上已经过了一回合。
沈平也还有心思说起了烂话:“兄台飞针确实难得,平常医治病人想必也是迅如闪电吧?不过......”
"你还不够!"
快是其一,但力量沈平也不是等闲之辈。
这一剑,已练过数万次。
青年不再说话,他手腕翻转,但沈平剑花一挽便轻松化解,剑光不再是一点,而是化作无数寒星,迅速又精准地弹开青年每一次的攻势,剑的每一次颤动都准确无误落入沈平的掌心,然后化作雨声席卷着从青年而来。
沈平赢了。
“多谢兄台不吝赐教。”沈平收回了架在青年颈侧的剑背,待到宣布他胜出时,只听霖霖雨声,剑便入了鞘。
沈平跳下台,往着人潮外走去。
中午该吃什么好呢?

作者:不落虚
要求:随意
白日很快到来,分局的人动作迅速高效,仅是一夜便把他的表面身份做好了。覃在拿到资料的时候不过扫了几眼便些惊讶,甚至小小了一下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这层天衣无缝的身份过往时,向总局申请调取了自己的档案——这是一个暴发户的跋扈儿子。这简直……简直是他的本色出演!
上午十点,一队人马在青歌大剧院的侧门停下了车,一车人先下了车把周围给围得严严实实,打着把厚重的黑伞开了车门。一位挂表戴帽少爷做派的人落了地,带着人背手走了进去。
今天是吴家三少出来和彪爷约定好面谈的日子,两边商量着把位置定在了青歌大剧院——他们那一出《雪车》可是相当经典。吴少爷跟着来接的人入了最上层的包厢,这可是绝佳的好位置。旁边有一厚帘隔绝了他的视线,吴少爷这下可有些恼了,指着旁边擦汗的老板问道:“这帘可挡着我了!你们怎么做的事?存心和我过不去是吧!我看你生意也别做了,趁早滚蛋!”
老板差点给这位爷跪下,他哆哆嗦嗦走近少爷想说些什么,却给旁边凶神恶煞的打手给拦下了,只得大声了点:“吴大少爷,其实这……”
“这戏还没开场呢,吴少爷就要离场不成?”一道声音从厚帘那传来出来,给在场的人都打一愣儿。还是跟在吴少爷身边的人反应过来,他赶忙伸手拉了一下少爷的袖口然后对着那帘拱手道:“可是……彪老板?”
对方没应,只是那手中摆弄着的两大珠子一响一响的。吴少爷拽着剧院老板领口的手,就那么一松一推,理着袖口又坐下了。
“让彪老板看笑话了,惭愧。”吴少爷在一旁放着的果盘里捞了个葡萄丢进了嘴,陷在软椅里没个正形。
“哪里。”对面客客气气的听不出什么毛病,此外就无更多交流了。
包厢下,买票赶来的人们正在陆续进场入座,台上那厚重的幕帘还拉着,偶尔抖动几下还有踏在木板上的响声。吴少爷好歹也是被他老爹塞去国外沾了点洋墨水的人,学业倒是请别人完成得漂漂亮亮,但那外国戏吴少爷可是不假他人,他可亲力亲为地“苦心钻研”——说白了就是这戏他可看不上,甚至也隐隐有点看不起隔壁约着他来这谈生意的彪爷。想到这,他不由地轻嗤了一声。
观众落座完毕,幕帘拉开,好戏开场。借着台上慷慨激昂的台词,彪老板终于说话了:“说实话,我看不懂。不过久闻吴大公子对此颇有研究,可否为我这个老人家讲解讲解啊?”
“吴大公子”——覃抬起了头,这颗被塞万提斯熏陶过的“外国戏”脑袋终于有了它的用武之处,覃模仿着塞万提斯平常和他聊天的调调开始侃侃而谈:“那您这可就问对人了,我虽然没承到我爹的商业头脑,这点不入眼的小玩意还是略知一二的。”
覃呷了口茶,开始了他的“表演”:“雪车的故事很简单,一出复仇记。故事只是讲雪夜列车上发生的惨剧……喏,彪老板看现在,”覃伸出手指了下台上,“现在就是刚刚开始行驶了。
覃还在脑子回忆着,他边摇头边道:“不过这剧的最后倒显得莫名其妙,像是幅画最后收尾草草划拉了两笔,一个搞机械动力的还是别来这行业混饭罢。但话说回来……”这时的“吴大少爷”终于沉不住气了,他迫切想进入正题:“这……”
“欸,这正头上呢,不急那一时。”彪老板打断了他,搓了下左手上的翠绿扳指,一挥手示意属下:“可以先看看货咯!”
下一秒,“吴少爷”的包厢便响起了敲门声,开门便是两人一前一后,为首的中年人一袭黑色长衫,脸上挂着微笑。见人来开门立刻拱手道:“我是老板差来带样货给少爷验验的,规矩咱可都懂,也就不多说了。”
吴少爷听见后面响动,也不扭头,就等着人上前来再看,后头的人跟着验货的人走了过来。那人见吴大少爷一副不爱搭理人的模样也没落了笑,一侧头示意后面端着盒子的人上前来。
“吴少爷,这就是这次要做的生意了。”那人已经从兜里掏出了——一副手套戴上,轻轻拉开了锁扣。
吴少爷颌首示意:“那就有劳……”
“我姓宋,吴少爷。”
“哦,那就有劳宋先生了。”
平平无奇的木匣拉开锁扣后露出了一漆黑的小盒,那盒泛着光,但总感觉有层浮灰。吴少爷离得近,随着那盒子的开启,他忽然闻见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像百花盛开时聚集在一起的芳香,却在其中含了一分苦意。那一刻他感觉世界都安静了,没有台下观众的窃窃私语和掌声,没有台上人枯燥无聊的台词,也没有那些怪模怪样的西洋乐器发出的嘈杂声响。他好像回到了多年以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没有嬉闹,只有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安静地看书,还有那时不时才会响起的翻页声。阳光透着绢布蒙着的窗格溜了进来,落在那宽大漆红的书桌上,照在了小小的发顶上。
书房里的人,不是他。
那会是谁?
回忆还在继续,下一刻,一个稚嫩但熟悉的声音由远而近,伴随着书房大门被推开的吱呀声,那个声音说道:“……”
吴少爷……不,是覃听不到了。
这段“虚假”的记忆,是什么时候植入他脑内的?
“快点!快快快!跟上跟上!”站在门边的人对着里面的人大声催促:“小心你们脑袋!动作再快点!欸欸欸那边的,搬好了!里面东西把你们全部卖了都赔不起!”
这边管事的还在催促着工人们尽快装货,那边穿着粗布外套的记账来拿着厚厚的大册子一路小跑过来:“宋叔你给看看?这数目我刚叫外头的伙计一一对过了一样不差。”
被叫宋叔的人这一下笑得牙不见眼,他搭着记账的肩膀往外走寻了个没什么人的角落,从怀里摸出了个小布袋,里头叮铃咣啷的,记账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什么。
他连忙推阻诶:“这、这我可不能收!大伙都是给人干事儿的,哪里讲得了这些?”说罢,手又往宋叔那推了推,“我先走了啊,那边还等着咱呢!”
时隔多年,覃又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船上虽然好,但任谁坐了半个月的船多少还是有些不适的。码头的人都穿着粗麻布的外褂,人人都着长衫大袍,倒显得他一身西装风衣还拄着手杖的模样像是个在外国喝了几年洋墨水的。不过真要较起真来,非说他在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倒也不假。
出发前,X难得找了一次他。会议室里没有其他人了,X就坐在长桌的尽头,而他的位置上放着一沓牛皮纸封着的文件,覃刚刚想拆开,X终于说话了。毫无机质的声音透过黑冷的蒸汽面具总是叫人有些听不清。
“……快到了再开,是回收任务,其他部门不会对此次任务进行留档记录。”
“那好歹告诉我去哪里吧代言人小姐?”覃见X要离开了,站起身喊了一句。
但她的脚步未停:“你会知道的。”
他现在确实知道了,当年他就是离开了这个地方才活下来有了后面的一切。
覃迈着一瘸一拐的步子,在路边招了个黄包车,从口袋里摸出个纸条给车夫:“去这。”
可他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动,他往前探:“怎么了?”
车夫挠挠头,他把纸条递回来,语气是说不出的无奈和羞愧:“俺不识字几个,不知道这写的……”闻言覃才回过神来,这不比纽兰特的出租车司机,上车递纸条就可以闭上眼等着了,海都的人还是这么……他笑了笑,开了口:“抱歉,我刚刚来海都不太熟悉,您带我去霍氏商行门口就行了。”
“得嘞!”
覃闭上眼,在脑中把任务文件一一分析。
海都繁茂这么多年,什么新鲜玩意这里都有,覃离开之前这里就是全国最大的贸易点。而什么都有底部的根基支持,在海都这庞然大物之下,有一根支撑着繁华奢靡一切的支柱。说得这么玄乎,其实它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黑市。
就像海都人民都知道海都商会大王是谁一样,黑市的人也都知道黑市的大王是谁,但——调香师是谁,其实谁也不知道。只听说他活了很多年,是黑市的幕后之手,又听闻他调的香千金难换,有医死人肉白骨的作用。每年总是有新入黑市的人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传闻嗤之以鼻,但这时上了年纪的人就会告诉这些人调香师的诡秘之处。这一来二去的,总局终于注意到海都有什么东西在酝酿了,便派了从这离开的覃来执行任务。
霍氏商行离得近,没一会儿就到了,覃感受着停下的黄包车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张面额比较小的纸钞塞给了车夫,他也不管车夫在后面叫着“先生不用这么多!”的响声,支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踏进了门。覃略过大厅里的人山人海,径直上了楼转入一个小隔间站定,用手杖敲了敲墙。那听上去……像是空心的。
墙倒是没开,不过另一边墙倒是发出了声音,他听着倒像是从那幅仿得挺好的山水画后面传来的。
“您好,我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我是纽兰特外差来的,叫你们负责对接的人来吧。”
“那么请问阁下是……”
“上阁院,覃。”
“原来是覃先生,我们已经知道总局的命令了。请走出这隔间,出去后往右手边走六步推一下那盆兰……”里间的人还没说完,他便看见覃站在了自己眼前。
“你们也该换一下了。这东西的年纪应该比我还……算了。”覃掸了一下肩上落下的灰——那都是机关启动的时候顺着墙面缝隙漏出来的。
覃自来熟地往椅子上一坐,从包里拿出已经拆封的文件。这里很暗,没点几盏灯,借着微弱的灯光还能看见黑木漆的桌上留着已经干涸的水痕,看来这里确实不怎么用了。
“……覃先生,我们将会为您提供一切助力,总局发来的文件在这之前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任务内容为追捕‘调香师’,请问有什么异议吗?”负责对接的人笑眯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在他眼前打开了锁扣。
里面只是一张地图,还有一张小字条。对接人把木盒推向覃,笑道:“这是地图,上面已经标明了各个地点和机关,我们的人员现在已经在入口处等候了。”这时他伸手虚点了字条,“这是有人留给您的,请在无其他人在场时打开。”
覃微不可查地皱了下眉,他实在想不到这个字条是谁塞的,X?她可不是会给“温馨提示”的好人。
夜晚很快来临,覃躺在旅所的床铺上,从怀里掏出了字条。很短,他阅读得很快,也很迅速地坐了起来。覃沉吟片刻后,从口袋里摸出了打火机“咔嚓”一声将字条点着。
那字条的笔迹很熟悉,但他想不起来执行局内谁是这种字体,四四方方的汉字让他感到有点陌生。那字条上赫然写道:“欢迎回来。”
作者:不落虚
要求:随意
又是一年一次的元夕到了,宗门每在这个时候就露出自己人性化的一面——即元宵宴。
修仙路漫,待人身怀一身他人所不能及的修为回乡时,可能看到的只是两座无人打理的荒坟,而自己还是青年模样,叫人不由唏嘘。所以,修仙即是斩断尘缘。但大多是弟子对于人世间多有留恋,但宗门门规第一条便是不得私自下山,不知有多少人望着山下零星点点的灯火黯然回首。
于是便有了元宵宴,元夕时节全宗门上下不分品阶,不看出身,只为热热闹闹吃一顿“宗宴”。这一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课业都会比平常轻松许多,大大小小的烦琐事都会在这一天偷摸着躲到无人的地方去。弟子们借着这宴席,总会沾上一点微乎其微的烟火气,告诉自己并未无情。
不过这些都与谢涣没什么关系。他常年独自一人住在不云峰上,宗门里平日无什么大事都不会去打扰他,他也总与师尊没什么联系——其实只是双方没什么要紧事就懒得说,谢涣又身为体修,元青师尊除了剑术也没什么好指导他的。但就是因为这师徒二人总是见不到几面,宗门里时有时会传出元青长老和其徒弟不和的谣言来。
不过这一切都在小师弟严崇来了之后有所改善——啊,跑远了题。
谢涣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记事起就是在宗门内长大的。又加之早慧,师尊也着重强调修道不应与世俗情感为之固化,他便也不怎么与人交际。待人接物总是隔着什么,叫人多少有些不自在,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他这般性子。
但他不修无情道,竟是令人意外地讲究在“随心”一词上。这一点多少偏了向来宣扬“修行就该随心所欲,端着样子有什么好”的魔道之人。
不云峰上除了他再无任何人,连猛兽都没有,谢涣推开竹舍的门,倒是惊起了院外不知名的鸟雀们。他抬头望去,如同蘸了饱饱的墨汁在天幕上画了一道又一道的夜空映入眼帘,皎月散着柔柔的光芒,借着月光可以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一切。月朗星稀,偶尔几颗零星的星子缀在空中,倒让白月显得不是那么孤单。
满月啊……他想,今天已经十五了吗?嗅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冷梅香气,他忽然想起来今天已经是元夕了。院子里有棵两丈高的桃树,谢涣将上面细小的花苞看得真切,忽而感叹又是一年过去了。今日既然是元夕,想必宗宴已经办起来了吧?以往的宗宴总是那么热闹,不过在谢涣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搬到了不云峰上,再也没去过了。
元夕佳节,人间那是一等一的热闹。花灯在河里你推我搡,街上是人山人海,街边的小摊上有各式各样的面具,又或者是形态各异颜色鲜艳的提灯。有巧聚心思的圈一大块地,挂上各样的字谜供人思索,猜对了就可以把灯提回去。蜜渍的果脯,小巧的风车,颜色讨喜的糖果,无一不叫小谢涣看花了眼。
“涣儿可有什么看中的啊?为师给你买。”元青剑尊伸着自己的小拇指让小谢涣牵着,弯着腰笑眯眯的:“涣儿这是头一回下山过节吧,为师带你好好玩!”彼时谢涣还是个可以被人抱在怀里的软糯团子,粉雕玉琢的瓷娃娃是人见人爱,完全不知道后来怎么一副生人莫近的冷淡样。
小谢涣牢牢拽着元青剑尊的指头,只恨自己一双眼不够看,亮晶晶的觉着什么都新奇。偶然间路过一个买提灯的摊,小谢涣就地站住不走了,一个劲盯着人家的摊上看。小贩是个憨厚的大汉,他注意到小谢涣闪闪发光的眼睛,咧嘴一笑:“诶!小公子看上俺们家哪盏灯啊?叫你爹买一个不?都是自家扎的,算不上巧,倒也好看。”
元青剑尊先是一愣,但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他低头看着小谢涣,柔声道:“涣儿看上什么了?直说便是。”小谢涣的眼光在摊上流连,似乎在仔细挑选。不一会儿,小谢涣抬起手指着一个花灯,抬头望向元青剑尊,说话声也是软软糯糯的:“师尊,我想要那个。”元青剑尊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个小巧的兔子花灯。
不多时,那盏兔子花灯就被小团子提在了手中,小团子眼睛亮亮的,看样子是对这新奇玩意儿喜欢得紧。而这时候空中有细微的雪花,开始轻轻地飘落,就好像什么白色的星子,突然降临在这个人间。
明明已经是元宵,但是这雪却依旧下了下来,似乎是老天也赶着这人间的热闹。元青师剑尊弯下腰把小团子抱在怀里笑着问他:“今天还是你出生自以来,师父第一次带你下山过元宵,以后如果涣儿还想来的话师父肯定还带你玩的啊。”小团子窝在元青剑尊怀里笑得可开心了,平常总是板着一张小脸的他这次没有丝毫的掩饰,终于有了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几分样子。
小团子这样今天过的很开心,最后和师父一起在河边放了花灯,开开心心地趴在师父的背上睡着了。
思绪转回,林中低低的几声虫鸣把他的思绪完全拉回,一个人住久了,总是会模糊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借着月光,他看见地上有着薄薄一层、要化不化的雪,轻轻踩上去也没有什么声响。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回走,看见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小亭,准备去坐一会儿。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布置在外的灵阵有人碰到了,于是他坐在了竹林前的小亭里,等着那个人来。
不一会儿,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谢涣抬眼望去,原来是小师弟提了个小木盒上来。他一眼就看到了亭子里的谢涣,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斟酌着自己的词句:“师、师兄……今日是元夕了。师父,师父叫我莫忘记了师兄,宗门里的宴会你总是不来,然后我就赶紧吃完宗宴,去厨房那端了点吃食送给师兄,师父说你一个人喜静总是会独处一个人,于是我就来悄悄打扰一下师兄……”
谢涣没说什么,只是偏头对亭子里另外一个位置说了一句坐。等到严崇走进来谢涣才发现,原来他手上提着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灯笼,那应该是盏……花灯?也许是它的外表并不像一个花灯该有的样子,做工多多少少有些粗糙。
严崇提着盒子放在了石桌上,赶紧打开后端出了一小碗元宵和一小碟点心一样的东西递给他 还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因为我也不知道师兄喜欢吃什么,就端了一碗元宵和一碟梅花酥上来。望师兄不要嫌弃。”说罢,像是逃跑似的,严崇提着小木盒就急匆匆地走了。
还留下了那盏小花灯。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还是回头叮嘱了一句:“师兄,元宵莫要凉了再吃啊!”只留下了谢涣一个人坐在小亭里,看着那碗冒着丝丝热气的元宵。
他沉默了半响,慢慢拿起了勺子,一口一口,把那碗元宵吃完了。又收起了碗,提起那个花灯回了竹舍,还把它挂在了门外。
元宵很甜,那碟梅花酥也很甜。
严崇其实一直没告诉谢涣,那碗元宵,那碟梅花酥,那盏小花灯,其实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为此他还挨了师父的责罚,师父说他不好好修炼,净干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于是这些东西都是他在修炼的时候,练剑的时候,偷偷背着师父挤出时间来做的。他还偷偷去找了负责厨房的小师姐请教,一个人练习了很久。
上一世,严崇有很多话,很多事都未曾对谢涣出之于口。
于是就这么错过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