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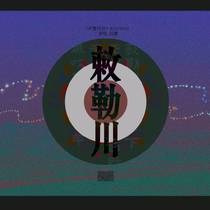







—
—
—
—
—
—
时雨第一次抽烟是在医院的天台。
她浑身扎着绷带、右手石膏挂在脖颈,止痛药的药效没过。同事的烟盒就像他尸体一样被断梁压得皱巴巴,里面完好的还剩四根半,她边抽边咳,边咳边流眼泪。
队里的人都喜欢叫她哑巴,常开玩笑说要是你没瞎只眼说不定有警花的潜力,你这样很难找对象云云。除了上工的必要查问,她不常与人聊天,有些梗不太听得懂,倒也没生气。大家都知道她话少、性子又孤僻,每次吃宵夜都会喊上她。有时听懂了大家互相调侃的玩笑话,把酒杯送到嘴边会忍不住浅笑一下,都会被起哄说“天天板着个脸,这不是会笑嘛!”
会的事久了不做也会遗忘,只有抽烟越来越熟练。没有要紧事就去天台上一根接一根抽。她对着那几个皱巴巴的盒子上印的牌子买,只买那几种,反正抽不出好坏,只贪图肺部在工作时大脑能稍做偷懒。
“有新男友了?”时雨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干净。
“才没啊。前男友问我要不要复合,我拒绝了嘛!”阿姨拿过碗又给填满递回去。
“他欺负你啊?”
“没啊,本来就因为他花心所以分手,现在又觉得还是我好,说在反省,这种鬼话谁信啊!?”
“他要是欺负你,我就去把他腿打断。”
“哎呀,都说没啦!不用麻烦我们阿sir啦!”
阿姨总劝她戒烟,说抽烟对身体不好。她勉强答应了。
她试过去跑步、去靶场、去拳击场分散注意力,最后只落得手麻到换不了弹夹,或者对手因为一句“矮子”喜提住院三个月。最后从肺里重新呼出来的才稍好点,家里的狗都能闻出来她身上的烟味。
重新回局里上工那会直接被分配到文职,交流对象大部分是白纸黑字和牛皮纸袋、电脑和黑色文件夹,日子又淡又闲。她发觉投入进工作,有时能忍住不去想抽烟的事,后来干脆不带打火机只带烟盒。
“我觉得你很有能力,只是没发挥出来而已嘛!”上司总这样讲,时雨也总是站直了敬礼,然后该干嘛干嘛,没有任何改变。
夜深人静时她在家里阳台角落抽烟,没把自己吹清醒的夜风就着烟一起吞进肚里,再吐出一部分,在极力克制下依然有两三根下肚。
她经历过车祸,得过脑震荡,忘了很多事情,但又重新记得很多事情。这些事像吸进肺里的烟,拧成黑块,无论怎么吐都吐不出来,然后刻在肺里,刻在脑子里,最后这座抽烟机像一具行走的空壳,灵魂随烟都吐出去,一滴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