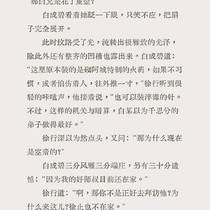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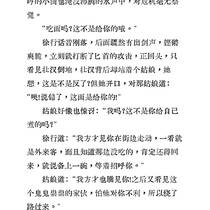


要过年了么,仲秋提前准备些腊肉。晚上队正说要来看流浪猫……幸好住处虽然狭小但胜在整洁,但还是得和奉离说一声。
做吃的她其实不算擅长,照顾大小姐的时候全靠厨娘。但非要和赶制冬衣比起来,那还是做吃的容易些。
如果有自己的小院子就好了,不用这样和衣服们挤在一起晾晒。她这样想道。但回头看看,正是因为镇安司的官服遮挡,麻雀们看不到自己来了,所以才心安理得地继续偷啄腊肉。腊肉本就是多做了一块给他们的,白天是鸟雀,夜晚是野猫,分配合理,如果多拿,就被暴打。
被谁暴打,仲秋不知道,只奇怪怎么大家如此有序,一次一口,彬彬有礼。
前阵子回温,来的小鸟更多了,乍一看以为春至,其实还有得熬。仲秋把官服抽出来,灰色的外衫不庇佑麻雀,该去守护百姓了。她看一看天,鸟雀呼晴,觉得阳光很好,实在适合晒被褥。
她路上买了两个烧饼,真正到镇安司时,还没到她换班的点,但听到门口有吵闹。她走过去看,见曹石拎起个小孩,正摩挲下巴那没刮干净的胡茬,难保不是昨晚又通宵了:“小徐兄弟为什么喜欢来镇安司摘桂花?”
徐止挣开曹石,猫一样蹲在墙头,振振有词:“此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德俱尊,四季平安,没人来偷,无人敢抢,连桂花都开得很茂盛。”他停一停,回头看到仲秋,问:“镇安司的绿树是对公众开放的吧?”
仲秋愣一下,却看向曹石:“仲秋不知,要问前辈。”
前辈。徐止嚼一嚼,这老家伙要是着急点,年纪可以做你爹。仲秋思考了一下,说,可是小白你好像只比我大一年。曹石问,要红包吗?徐止尾巴上的毛竖起来:……给多少啊让我多个长辈。曹石认真想想,塞给他二十一文。
这边长亭出来了,看到仲秋分自己一半午餐,刚闻着味道就说,长乐坊的?仲秋点点头。长亭说,有劳你绕路。仲秋摆摆手,没有的事,我刚好去找连珠。
两个人换班,没让徐止蹲到要蹲到人,出来个小狗头。小狗头问:“金离今日不当值,小白你找他什么事?”
徐止说,我想让他给我画个年年有鱼贴家里。曹石说,我也可以写个“快长快大”给你。徐止想了想,把纸递给他。
既然守株待鱼失败了,徐止和拾肆一路往回走。还没到一半呢,天降暴雨,他们看到两条长辫脑袋往前跑,头上扎得凌乱但结实,居然没给晃散。至于袖子,长得能唱戏,抱着木盒又抱着猫,往上一盖,自成雨伞。
徐止在屋檐底下,看拾肆想也不想冲过去送伞,又淋着雨跑回来,道:“我可没说要让你蹭我的伞。”
拾肆愣了愣,小怯而大勇:“要不你现在说一下……?”
他也是难得能把徐止说无语的狗。
“有些时候也不用非得路见不平。”徐止道。“我有一次见宫里的奇珍异兽跑出来,是条大虫,城里不多见,都到朱雀街了才被人发现。”
拾肆问,后来呢?徐止说,被一个身有奇力的女子路过拍晕带回去了,我建议你们镇安司去给这位姓罗的女子安排一份工作。拾肆说,你怎么知道的?徐止说,刚才你去送伞的纸无书说的。
狗想了想,交换些自己的生活:“喔,小白,我最近和雨哥学刀,上次他教了我一招保命的,很好用。”徐止道:“时雨啊,时雨也上次教我,说,短刀特别短,长刀特别长。”
拾肆听得愣了一下,问,雨哥真这么说?徐止说,我骗你的。
但时雨人如其名,刀急如快弦,弦上雨翻飞,见马作的卢,斩夜中恶鬼,谁临了被那双眼瞧一下,阎罗殿也来得近一些。镇安司不少这种人,但也十分正常,毕竟打击罪恶,有些时候自己也要长得足够罪恶,分出外勤内务。
你就不适合出外勤。徐止笃定。拾肆问,那谁适合?周貅兄?徐止说,出外勤也不是每次都要这样用力,我看不如蒋平吧。
“蒋平赌术也许不太好,但刀特别快,酒也特别能喝。上次她被人出老千吧,还把店里喝了个空,老板要她赔钱,扣了她的刀。”
拾肆听到这里,心居然提到嗓子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徐止说,是啊,店都给人砸了。拾肆抿了抿嘴,问,呃,蒋平姐不会被镇安司给踢出去吧。徐止说,当然不会,因为那店里的酒馋了水,否则她怎么口齿清晰,反客为主,倒过来威胁店主每月给她送一坛,否则小店不保。
徐止过一会儿又想,要真是好酒,怕那老板才是真的性命不保。
蒋平抽刀时猝不及防,那一手起式比剑眉英目更漂亮,谁着了道,会后知后觉其实若是拿坛酒和她交朋友,并不算贵。徐止念及此,转头对拾肆正色道:你还小,不要学她。
拾肆就说,我学不来。但任平哥也许可以和蒋平姐喝个酒。徐止说,双平局是吧,俩月俸禄,一决高下。
雨还在下,说是立春,却没有任何回温的气息,凉意一层一层的,催得脖颈寒风漏,雨帘如瀑落。徐止的伞和他的店差不多,里面黑来外面黑,但好在足够大。他说,还是和你打伞好啊,曹公那个头跟我打伞,迎面就是大雨洗脸。
拾肆一时间分不清到底是在说自己矮,还是在说他俩关系不错,但既然徐止说和自己打伞好,那就是后者。他尾巴甩了甩,又和小猫凑得近了一点。
徐止问,你没伞么?拾肆说,这不是刚送出去,而且我没有和小白一起打过伞呀。徐止那缺德嘴终于打算闭一会儿,还没琢磨出什么好话,拾肆又说,明年也想和小白一起打伞。徐止憋了半天,耳朵都憋红了,说,行。
他又说,我要买点儿水果,今晚去仲秋那儿很热闹,你去吗?拾肆想起来有好吃的,但很犹豫,又问,小白去吗?小白说不去,停了一会儿,听见雨声在风里滚过一圈又一圈,又开了口:“但你下次可以来我家。”
他居然放狗回猫窝!拾肆立刻答应,摇摇尾巴,说,那下次我也带你去见我们老大。徐止想着那个凶神恶煞的脑袋,说,不了吧,除了太和观在任何地方见到他都不太平安的样子。
“你还去太和观啦?”
徐止说,去了的,半路碰到些熟人,那地方也很适合开摊问诊,请初一大夫和迟兄,初一坐到初七,横幅一决高下,看谁开的药最多最准。拾肆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明白这家伙居然没有被人套麻袋打一顿。正想着呢,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卢坊主店里,徐止说,你一会儿跟小红姐去仲秋家吃饭吧,我也要回去了。
拾肆问,那你回哪里啊?徐止想了想,觉得年夜饭要吃顿大的,说可能回一个姓海的贼窝吧,约了人喝酒来着。拾肆很认真地担心,问,你不会约通缉犯吃饭吧。徐止也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没约。
=
蜘蛛鬼市,天罗地网,百无禁忌,蛇鼠一窝,虫蚁作祟。从踏入开始,路边摊位像肠子滚地,满眼望下去看不清边界,全靠萤火点灯,切割这场噩梦。
其中一个摊位摆竹篓,装鸡头,又两尾鱼,布几颗破烂怪石,造型奇异,形同怪目妖容。
徐止抬一抬下巴:老头你坐着的,什么东西?
那不过是个破布盖矮凳,谁知道什么东西?独眼老人烟嗓烫,笑一声,低如铁砂听不清,理都不理徐止。徐止听明白了,又说,一坛『饮山崩』,让我看看。
小铁公鸡,长点眼睛。但老人掏耳朵,伸出两根手指冲着徐止,都懒得瞧他。
老铁公鸡!徐止嘀咕。怀里摸出两小瓶竹筒瘦的酒,土色红纸封旧泥,扔他身上,忍不住又说一次:老铁公鸡。
酒方入手,手应声抽布——几乎同时,那底下坐着的矮凳被抽起来竖着,竟是个剑匣!老人单手推酒盖,仰头倒陈酿,另一头半扶半靠,看机关稳送六把剑依次错开:白虹、紫电、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剑身自有暗纹叠光华,流转杀机隐其鞘,结果徐止挑个眉:假的吧。老头刚喝两口,咂咂嘴:我就教你这么杀价?徐止又道,那让我试试。
老头酒没喝完,只送个手掌:自便。
试就试!
徐止抽把寸宽不足的窄剑,两指不到,重一斤三两,身如冰骨呈玉色,不见头顶月清辉。他手中甩个剑花,只尖回肘转时在虚空中略一停顿,又猛的施力,立刻就抽出寒风松声破空响。
白成碧在一旁摇扇子:趁手?徐止点头:趁手。白成碧又道:来把?徐止摇头:太穷。
这扇子轻点,目送流星剑回鞘,微笑道:我看倒不是小白太穷,而是剑卖得太贵。
徐止耸肩,把剑掂一掂:“可能吧,我不懂这个。”他顿了顿,问:“你懂?”白成碧道:“随便懂懂,大概也就能看出这剑值不值钱。”
老铁公鸡可听不得这话:“什么意思?不识货就给我放回来!”
放便放。徐止把剑抛入匣中,正嵌合,闻铁器声响,他对着老头说,你再喝另一瓶试试呢?
老头刚喝尽一罐,又拇指平推,卸去另一罐的瓶口,鼻子都不稍动就发现:普通白水!
“好你个徐止,学会骗人了!”
铁公鸡一手猛拍古匣,迫那六把好剑乘机关颤动,正平稳回收,另一手立刻泼向徐止。徐止立刻抽伞来挡,瞬如黑鹰展翅,以翼蔽之,那水只洒出个花,滴滴答答落在地上,剑匣几乎同时,轻轻“嗒”了一声,收入六把剑,合满。
徐止收起伞,露出个猫笑:“老头,再慢些,这水泼上去,你的剑便要遭殃了。”
眼看这暴风骤雨的怒斥就要杀来,他立刻戳戳白成碧,背后顶着老铁公鸡慷慨激昂的骂骂咧咧:“白兄,白兄,速走,速走。”
白成碧被他拉拉扯扯,只拐弯一个普通地方,霎时灯火通明。徐止忽然站住,低头愣神,几乎不敢置信:将黑伞再次撑开,里头居然真有方才自己试过的那把剑!
他抬头,眼里写满震惊,好像凭空多了两斤肉作猫粮:“……你刚搞的?就我开伞那一下?……难道你是啄木鸟?”
白成碧用扇子把那耳朵压下去:“白某教你,夸人可以用‘眼疾手快’。”
徐止哦了一声,把这剑拎起来,只见光华流转玉生烟,轻如薄纱也似纸,吹毛立断可斩风:“这把好像确实是唯一的真货。”
他再看白成碧,欲言又止。白成碧就道,在下也不是多想要这把剑。徐止不懂这家伙什么毛病,难道艺高人胆大,只是偷来玩玩?还是因为不喜欢老头真假参半地卖,要他跳脚……罢了,好像都是他做得出来的事,无端猜测,没什么用处,既然给自己了,那就拿着。
他俩分而行之,各自寻路。这鬼市各分区域,纵深往后,逐渐嘈杂:华贵衣衫有血衬,明亮矿石半真假,更见前朝禁书与宝图。徐止持剑,正寻思留作己用,还是即刻出手,就听见有人脚步尾随,只在暗处。
徐止不动声色,假意挑挑拣拣,只靠余光瞥见:跟踪者藏身之处这样暗,瞧得清楚么。
他摸几文钱,买了个青蛙脑袋的面糕,结果一嘴下去,全是苹果味,苦得他咧嘴:谁拿瓜果生烤啊?!
正是同时,有风声横来,他立刻猫身躲过这横劈,便要再躲个竖砍,青蛙脑袋被徐止拿来挡刀,一刀两半落在地上,他说,我的钱。对面听到了,眨眨眼,但刀不停,只说,那赔你一个。徐止无言,问,你若是要害我,就让我再吃一个。可是对面没回答,是刀比嘴快:短刃削雪光,玲珑碎几片,来去快如雨!
雨声暴烈,铁马冰河,也如玉珠,落盘声声。徐止力不及他,抽剑格挡,卸不全这刚猛狠劲,只走偏锋,如个捉不住的泥鳅,千百纠缠,难杀要害。几个来回,他自己嘀嘀咕咕:镇安司也多管闲事?
对面刀客默然停招,负手持刀,刀不入鞘:……你不问自取。
徐止正色道:我捡的。时雨哪见过这样没脸没皮的,一时间被这无赖说得沉默,换了个问的:你怎么认出来?
“绝佳偷袭时候,不行杀招;力可斩刀,只求击落,如此光明磊落,就差把我‘我不伤人’写在脸上了。”
时雨没得反驳,又眨一下眼:“那你把剑还了。”
猫龇牙:“我不。你这狗头,太过正直,很不好骗。”
时雨思来想去:难道还有好骗的狗头?那拾肆的脑袋刚浮现脑海,就见徐止扛着伞,无声无息凑过来——他个子太矮,这样抬头,总有一种要把时雨当树爬的错觉:“小狗,做个交易,我嗅觉不好,什么都闻不见,咱俩合作,寻个食魂散——你们镇安司也不希望这种迷香流散入民间吧?找到之后,我立刻去还这把剑。”
那头时雨还没想清楚为什么是“小狗”,但是记得一码还一码,严词拒绝。徐止又换个说法:“那你帮帮良民小百姓,一会儿我就迷途知返把剑送回去。”
这居然很轻易说动他,只见时雨把短刃收回鞘里,闷声应了:好。
徐止想,真这是另一种好骗啊。
=
拾肆今儿不巡街,被徐止拎出来。
他俩脸上都跟坏了一样,面无表情,能不动就不动。猫眼狗眼,都只转一转。拾肆说,你其实很适合来镇安司,坏人一看你,容易吓得不敢跑。徐止有来有往,说,你也适合收破烂,客人看了你,通常会不要钱,放下就走。拾肆很少听这样的话,居然老实问,为什么?
徐止想了想,从善如流,说,因为你可爱。
他俩还没走,仍在镇安司门口。曹石路过了,问,吃饭啊?徐止说,捡破烂。曹石说,那在下先告辞了。徐止叫他别走,曹石不解,这猫说:我捡捡你。曹石给他扛起来放墙上去。
拾肆哒哒哒跟过去,又问,你捡破烂还捡人啊?徐止说,有些话本来有趣,你如此认真,显得我十分缺德。我只是捡曹石,但曹石不让我捡。拾肆说,哦,那他毕竟不是破烂。徐止说,你真可爱。拾肆说,你也是。徐止叹一口气。
吃烧鸡吗?徐止拍拍灰尘,边走边问。拾肆眼睛一亮:吃。但转念一想,很担心:捡破烂的钱,够不够吃饭?徐止说,比之镇安司,实在差很多。拾肆说,难怪曹石每每问我,都是叫我请客。徐止说,要不咱俩去摸他的钱包。
拾肆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这如何可以?
徐止头头是道:我若是摸到了,咱俩吃一顿,你将我抓起来。我若是没摸到,就躺在地上,讹他一顿。
拾肆说,你开玩笑的吧。徐止说,是啊。拾肆说,你真可爱。
徐止说,你是故意的吧,拾肆说,是啊。
=
要过年了么,仲秋提前准备些腊肉。
做吃的她其实不算擅长,照顾大小姐的时候全靠厨娘。但非要和赶制冬衣比起来,那还是做吃的容易些。
如果有自己的小院子就好了,不用这样和衣服们挤在一起晾晒。她这样想道。但回头看看,正是因为镇安司的官服遮挡,麻雀们看不到自己来了,所以才心安理得地继续偷啄腊肉。腊肉本就是多做了一块给他们的,白天是鸟雀,夜晚是野猫,分配合理,如果多拿,就被暴打。
被谁暴打,仲秋不知道,只奇怪怎么大家如此有序,一次一口,彬彬有礼。
前阵子回温,来的小鸟更多了,乍一看以为春至,其实还有得熬。仲秋把官服抽出来,灰色的外衫不庇佑麻雀,该去守护百姓了。她看一看天,鸟雀呼晴,觉得阳光很好,实在适合晒被褥。
真正到镇安司时,还没到她换班的点,但听到门口有吵闹。她走过去看,见曹石拎起个小孩,正摩挲下巴那没刮干净的胡茬,难保不是昨晚又通宵了:“小徐兄弟为什么喜欢来镇安司摘桂花?”
徐止挣开曹石,猫一样蹲在墙头,振振有词:“此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德俱尊,四季平安,没人来偷,无人敢抢,连桂花都开得很茂盛。”他停一停,回头看到仲秋,问:“镇安司的绿树是对公众开放的吧?”
仲秋愣一下,却看向曹石:“仲秋不知,要问前辈。”
前辈。徐止嚼一嚼,这老家伙要是着急点,年纪可以做你爹。仲秋思考了一下,说,可是小白你好像只比我大一年。曹石问,要红包吗?徐止尾巴上的毛竖起来:……给多少啊让我多个长辈。曹石认真想想,塞给他二十一文。
=
1
=
“卖糖葫芦咯!”
卖糖葫芦咯。徐止跟着他嘀嘀咕咕,被赵弘义听到了,一转头,可是那猫耳朵躲在草垛子后面,什么都看不到。赵弘义不信邪,把草垛子往左,猫也往左,赵弘义把草垛子往右,再往右,咚一下,看见猫头,击中猫头,猫头蹲下。
“……哎哟徐兄,不好意思,我以为见鬼了。”
猫头捂着脑袋蹲半天,面无表情爬起来,手里居然有一串掉了的糖葫芦,他说,你不要了吧。赵弘义说,呃,可以不要。你头没事吧?徐止说,还能用。赵弘义说,我给你点药?徐止高看他一眼,问,你还随身带药?赵弘义说,万一呢,总有人用得着。徐止说,你倒是随时助人为乐。赵弘义道,人活着么,是这样的。
徐止偷偷把糖葫芦吃了,说,我随时准备入土为安,你路过可以帮我埋一下吗?赵弘义若有所思,说,赵某拄拐杖不太好挖坑,坟头放一把糖葫芦算吗?
=
2
=
有个小孩买糖葫芦,一路往北跑,结果铜板掉地上了。赵弘义看得见够不着,正要喊,也不知道去他去哪里,只瞧个猫耳朵,鬼一样窜下来捡了。
“小徐兄弟!来得好。”
——好个屁,他还没说话,那猫把铜板揣自己兜里了。
赵弘义扶额,说,小徐兄弟,你腿脚快,能不能把这铜板给刚才买糖葫芦的孩子送过去?徐止面露不舍,说,都掉地上了。赵弘义劝道,那也是人家的,我请你一串,你帮他一把。
十分划算。徐止露出点笑:好啊。
这厮居然起身就走,目标明确,三两步消失巷口,没多久便跳回来,抬着他的伞,说,给他了。赵弘义想,是不是又被这贼猫坑了。
贼猫还在笑,心情很好,挑了串小的。赵弘义问,你今日不开店?徐止道,开不了,朱雀大街死了人。赵宏说,难怪旧日同僚如此忙碌。徐止道,我也忙碌,如何不见你称赞我。赵弘义看着他吃第一口糖葫芦,说,你本可以不忙碌。
他俩慢慢往前,话题东倒西歪,徐止吃到第二颗,居然又看到那小孩跑回来,他指了指,说,街头李家奶奶的宝贝孙子。
赵弘义大惊:“她哪来的宝贝孙子?”
徐止道:“我也觉得奇怪,但你上个月说二狗媳妇丢了娃,死活找不着,鼻歪,眼斜,家里人也不在乎,官都不报,只有孩子娘哭天喊地。”
赵弘义听出弦外之音,说,我们去看看。徐止吃完第三颗,转了转眼珠:“我帮你把他抬过来,你再给我一串?”
这是什么缺德买卖。赵弘义问。徐止说,你看,这镇安司要是看见了,我是说我捡垃圾,还是说我拐卖人口啊?赵弘义说,你想说你拿串糖葫芦过去是送爱心吗?猫说,那先谢谢赵老板的爱。
“蒋平!你的酒钱!”
不知道谁喊的,从馆里递出来,到这街上也只剩个尾巴。被喊的那个更不在乎:是多了还是少了,若是少了自会有人追出来,若是多了,便算今日的心情钱。
心情好啊!哪里是这样容易买出来。她掏掏耳朵,好像真的没听到有人跟来,只剩风声了。今日风也好,风急,天高,自有飞白过耳,蒋平眯着眼,眼中世界左右倾斜,却觉着树里不太对劲:你也不见她有半分严肃,步子仍是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左踏时如虚凭风,要跌不倒,下一秒居然飞身便起,再回头已在树上,捉了条黑猫尾巴。
“又是你。”
这醉汉却用个笃定语气——她穿圆领,不系好,内衫居然还有百花楼带出来的墨痕,字迹妩媚,另有些风情,一笔歪了,连同口脂吻在她怀里。
被捉的人叹口气,说,我以为你醉个半死,怎么清醒成这样。
蒋平只问,找我作甚?徐止便答,找你酒钱。
黑猫一头乱毛,没睡醒的样子,掌心里摊着铜板,递给她。蒋平松了那尾巴,又落到地上,兴趣缺缺:只是跑腿?那不必了,你这小孩,留些钱买件冬衣去吧。
那长辫甩一甩,更像条漂亮的尾巴。徐止看着发呆,又不动声色移开目光,说,冬衣我有。
蒋平又问,找我作甚?徐止不答,仍在墙上。
这种流落小猫,蒋平也不太放在心上,兀自往前去了,哼一首曲子,调也歪了几句,随风吹得很远。
=
蒋平便是梦中杀人也并不奇怪。
她醉起酒来清醒得像鬼,平日里收住的拳脚打全一套,是排山倒海破竹来,烈风过野摧枯朽,更莫要提使刀:她也使刀,使刀更行云流水,千钧得怪异,好像压抑山洪一日起,恶鬼门关百年通,大开大合,只取首级,不屑手足。
手足?蒋平不信手足,手足不如刀,刀在手中,如天地间任我行,行路难时任我平。刀要挥去哪里,便可挥去哪里,手足却不可以!手足说不明白,是血肉魂骨,是梦中折钉,醒来又握着刀,忽然不知道挥去哪里!
于是真就醒了,那刀已入树中三分,再难抽出。她原先真要劈这树么?我看不尽然。那树是蛮力破土,生长在村口,生长在心口,教会自己原来有力气,便可挥刀拦路,斩断别人的生活。
蒋平看着手里的刀,心想,我便也要如此么?我便也该杀死谁么?
她又喝一口,要醉个痛快:谁也杀不死我。
=
徐止问,喝茶么?金离说,不了,谢谢。徐止对着那条尾巴说,你喝么?金离愣了愣,很配合地甩一下,说,不了,谢谢。
徐止说,那你喝茶,这尾岂不是不知道茶香?金离就笑,说,那徐兄见花开,有风过,却嗅不到味道,是否寂寞?
这猫耳朵动了动,眼睛游到一旁,说,啊,知道了。
镇安司其他人早同金离说过,这捡破烂的,脚步轻又快,到处乱窜,不知道怎么神出鬼没,而且邋里邋遢,哪都有他。尤其那百礼还说,这徐止是条猫,怕是看上你这条鱼,嘴痒了,要吃两口。金离就笑,真的假的?
他其实也感到奇怪,公务繁忙,每每清闲换岗时,徐止却总能蹲在这里等到他,就像算好时辰,特地来的。
那猫有时候困了,就在树上睡觉。有一次他半路忽然跳下来,金离好像终于有些好奇,就问,小白老板,不去做些生意?
徐止就说:“捡破烂的生意,做与不做,都是那样。今天困了,就不做,明天没死,那就做。”
金离接下来便不问了,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是需要些缘分,缘分说出口来,便是破了的河水泡沫,他十分清楚,于是只微笑:“在下还有一刻便……”
徐止就打断他——这猫是挺没礼貌的,也只有金离不介意:“我知道,你要换岗,从这条街寻起。我是来告诉你,那边桂花开了一树,很漂亮。”
=
=
捡破烂的猫终于醒来,雨停,霜重时,他抱伞出门,去护城河边。百礼眼睛尖,早早看见他,于是鬼影一样踏夜风,游墙沿,跟过来说,小白老板,亲自来捡破烂啊?他就闷一声,说,嗯,我通常还亲自去死。
徐止旁若无人,在水沟飞檐走壁。百礼觉得好玩,同样是猫,有这样不怕脏的,吃好喝好,还掏垃圾:见他伸手扒两下,困得那脑袋几乎掉进去,居然爪子还带起来一个钱袋子。百礼又说,哟,小白老板,开张了啊?他翻了翻,污水水稀里哗啦的,从他手上流下去。说:“官爷,这儿有官银,上游死人了,您闲得无聊,不如去巡逻吧。”
百礼歪一下头,说,你捡到了官银,我再把你捡回去,是不是官银换赏银,赏银换酒吃?
徐止面无表情把钱袋子扔沟里,泥水飞溅:“徐某乱讲的,徐某没有官银,徐某只是想打发官爷。”
官爷却拿着一种笑意,说,大家都是猫,我看你嗅觉灵敏,咱们互帮互助过个年嘛。徐止说,不巧,徐某嗅无味,倒是可以帮官爷捡捡垃圾。百礼说,是吗,我看你嗅觉挺灵的,昨晚百花楼失窃案,戌时三刻你在哪里?
夜风凛凛,乱长街灯,破月底云,人影昧。徐止抬头看她,甩了一下尾巴。
=
一个时辰后,天光破,百花楼歇业,窗启,扑面漫出欢靡酒气,徐止翻进来,尾巴上拴着的骨头把瓦片砸出点动静,他本来懒得管,想了想,有个女人好像换了新的琉璃瓦,于是木然地回头看一眼,雁过无痕,鸦雀无声。
屋子里有个男人,衣衫不整,未醒,估计楼下的马车就是来接他的。屋子里还有个女人,梳洗打扮,清醒,抬眼看徐止,对那少年脸庞似有不屑,却转了转眼睛,并不明显,以为是穷酸小子。
只说:“小公子,来错地方了吧?不过脚下功夫了得,下次从正门带银子来。”
那捡破烂的小儿毫不在乎,好像来这房间只是借道,轻车熟路。边走边说:“徐某嘴上功夫更好,姑娘试试?”
那姑娘是新来的,自然不认识他,还没回话,就看徐止已经出门。门外不知什么人,袅袅身姿,皓腕霜雪,伸手过来掐他的耳朵:“再欺负我们新来的妹妹,我把这玩意儿穿咯。”
徐止就啧一声,给她捏得头都歪到一边,说,好好,多个洞也是多个招牌,给姐姐的百花楼添砖加瓦。
那老板娘微微眯了眼,笑意温和,却刀一样抵在他脖子上:“添砖加瓦?要死快哉莫摔我瓦,以为刚才进来我不晓得?”
徐止说,我看姐姐玩的买卖学的。茉莉笑得更深了,那猫耳还在她手里呢,刚要开口,徐止从善如流,说,茉姐,来打听点儿事儿。被叫做茉姐的女人挑一眼瞧他,发间流苏轻晃,如春风生,养万物情,声如脆玉:“小畜生,自说塞话,先去刷碗!”
和尚没了,讨不到功夫。符逸没了——符逸的刀没了,讨不到金子。生意很不划算,加之海霁出现,这树多少就显得有些过分拥挤。一座庙小,妖风太大,事已至此,不如及时止损,打道回府。
徐止说,徐某经营小当铺,符老板经营大当铺,要典当通缉犯,理应由符老板出手。符逸微笑:我等正经生意,此物太过破烂,店家不收,不若小白老板术业专攻,一并带走。
海霁道:“你俩在这谦让什么。”
徐止道:“谦让一些镇安司的官爷才能做的事。”
这话说者不知有意无意,听者多少不能无心,那百礼若是来了,海霁和白成碧都跑不了,于是前者十分潇洒,从容告辞,道山高水远,有缘再会。后者移形换步,扇子轻飘飘搭在徐止肩膀上:“那徐老板一会儿要去哪里。”
徐止猫毛倒竖,觉得不太对劲,生怕他跟来,说我去积德。白成碧说,在下现在榜上有名,招摇过市多少有些不太合适,还是有个人同行比较好,不若我与徐兄一道。符逸附议:你俩是该积点儿。
猫把那扇子往旁边挪一寸,说:“想来白兄光明磊落,一定不会使挟良民这种下三滥的市井手段。”
白成碧道:“我只是邀请徐兄去逛逛西市。”
徐止说,那你为什么不邀请你师叔。白成碧道,你看到他手上那张纸了吗?
符逸道:“在下乐善好施,只是来捐香火积功德的。”
至于这位大老板,是否用真金白银换得扫地曾高开贵口,暂且不得而知,那白成碧的扇子摇一摇,真把风吹到西市去了。
西市独有一家泥塑坊,坊中也独有一位工匠,工匠名为卢晨肇,手艺了得,捏人绝不像鬼,捏鬼绝无活路,上通灵兽精怪,下通吃喝饭菜,手中总生出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他二人至坊中,见四周散落个中成品,左青龙,右绵羊,地上炮仗如辣椒,约摸是失败了,还有些碎块淤土。杂物中间端坐一人,不修边幅,泥点作墨,正低头捏碗,碗中一条锦鲤,若空游,无所依,盛茶盛酒,都是极好。
白成碧合扇,问:卢坊主也做器皿?卢晨肇知道来者是谁,于是他头也不抬,先把那尾巴补全,回道:“偶尔做做,如果需要,捏个面团也是行的。”
徐止问,包子也能捏成元宝的样子吗?
这回卢晨肇反而抬头了:“哟,小徐老板。”
至于那白成碧,是因前几天才来过一转,看中个小泥塑,说请卢坊主上个颜色,之后来取。登记时正巧瞥到那名字一栏有个徐止。 徐止却为什么同他相识?
猫眼尖,看到新漆鲜亮,居然落在一对雕上:左边那只收翅合翼,目光炯炯,颇为神气,右边那只振翅未成,神情微妙,好像撞了树,又像跑了兔。
徐止只高柜台一些,他趴在这茶壶大小的新泥塑面前,歪着脑袋看了半天,问:你的?白成碧道,我的。
徐止向来少管闲事,此时此刻也忍不住想问:你买这很像卢老板捏歪的泥塑,图的什么?保留他生意上的污点做个纪念?
白成碧只笑,垂眼把玩其中一只,不答反问:白某什么时候是这种人。不如问问徐兄要了什么?
徐止倒是老实:要了只猫。白成碧道,哦?徐止继续说,长得像我的。白成碧道,哦。
本来话说到这里,徐止已经想停住,可是看一眼白成碧,发现他居然好像洗耳恭听,还在等徐止继续说下去。其实也不奇怪,白成碧这样眼高手不低,挑好刀争魁首,向来只对猜不到的事更感兴趣,何况从他了解的徐止来看,断不可能花平白无故之钱,做对镜自赏之事。
可惜那猫垂眼又垂耳,说,没了,就这样。
卢老板从帘子后出来了:他托来一只手掌大的泥人,这泥人果然猫耳猫尾,貌同徐止。并且未经处理,莫谈火烧,更无颜色,天然素寡,却面容精致,表情鲜活。最怪的在它姿态曼妙,是个少女模样。
白成碧轻轻合扇:若非十分熟悉容貌,捏不出这样神似,看这架势,真是熟客。
这几年铜钱不值钱,卢晨肇却和第一年开张时一样,收同样价格,徐止从兜里仔细点了钱——想说什么,还是没多一句话,只说声“谢了”,转身便走。
白成碧收扇收雕,亦步亦趋,继续跟猫。
猫还是太小只,一步不如白成碧两步,甩是甩不掉了,见他悠哉,神态自如,徐止问:“你怎么还跟着我?”白成碧好像发自内心地困惑:“白某方才不是邀请徐兄逛逛么?”
徐止道:“我以为你要拿我当镇安司的挡箭牌,人来了就挟持我。”
白成碧豁然开朗,说,好主意,但白某诚然不是这样的人。徐止说,我是,我小人之心。白成碧就笑,又道,但徐兄明知白某没有挟持你的情况下,还是共同白某走了一路,能否理解成徐兄其实并非小人之心,而是给出一种提议?徐止不吭声了。白成碧对着那猫头笑道,可惜白某也不是谁说留就能留下的,心意就领了。徐止说,哼,你清高……哎哟,别摇你那破扇子!
白成碧问,那么徐兄现在这是要去哪里呢?
去放生池。
放生池并无太多游人,却盛满许多愿望。人总想交换,以为给出便该有回报。其实在谁身上亏欠的,就该从谁身上讨,发现到许多事无可回转,才求神明完成这种弥补。
你说功德,若真能掐指一算,求个明白,又何必先捉后放,人生空阔,才许真心。
徐止不带鱼,不带龟,只带手中一把泥人来,往池中化了烟云去。那张酷似自己的脸,本来就没有颜色,现在沉入池里,散个明白,一幅水墨,说扔便扔。
徐止忽然笑一下:镇安司不管放生池干净不干净吧?
白成碧问,你要放生谁呢?徐止说,我不知道。过了一阵,他低头对池,池中仍是自己的脸:毕竟我已经不记得她的样子了。
那少女年纪尚轻,不过十四五六,难说是徐止妹妹,或是姐姐。白成碧说,放生池本是放生灵,还业障,徐兄是觉得她没走出去,还是你没走出去?
夜至,河灯点点,送游人往朱雀大街散。说寂寥如何寂寥,说热闹哪里热闹。徐止说,老白,我不知道谁欠我,也不知道我欠谁,我举目见日,却不见长安。
徐止耳朵一动,听见风声远远传来些动静,不知河上船道运的什么人,传的什么事端。只托着腮,道,听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不过我饿了,要去吃面,白兄一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