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醒的比其他孩子早一些。
某个夜晚,年幼的殳川忽然醒来,迷迷糊糊和漂浮在空中的水母大眼瞪小眼,单方面对峙了十几秒后噔噔噔噔跑去摇醒睡着的妈妈:“妈妈,有水母!”妈妈醒了但没看到任何东西,只得安慰孩子说是他做梦了。
之后的某个白天,这次小川千真万确的看到了水母,噔噔噔攥着妈妈衣角指着精神体:“妈妈你看!真的有水母!”普通人看不到精神体,妈妈以为孩子撞邪了有点害怕,去了医院咨询未果,之后和同事提起这事被提醒才想起有可能是精神体。
她不太懂这些。两辈几十年间家里没有特殊人群,接触的也不多,孩子的父母和(外)祖父母辈都是普通人,平静过了几十年普通人的生活,潜意识认为这个孩子也会是普通人。总之还是带了孩子去机构检测,检查报告结果显示——是哨兵。
小川看到的水母是他的精神体,只是觉醒的比较早,还不能自由控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精神体。
力气意外的很大。小时候便出现一丝端倪,父母也没有太过在意,只觉得孩子身体很健康有力量。没想到是哨兵身份的预示。
父母因感情不和离婚,他跟着妈妈。父亲有按时给扶养费用,偶尔也会来看他。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节能状态,呆呆的,看起来比很多哨兵好说话,所以时不时会被叫去帮忙,一来二去人缘还不错。
和平时呆呆的样子完全不同,出任务时冲的很猛,万幸的事还算听指挥,因为只是想赚钱,并不是不要命的类型。出任务很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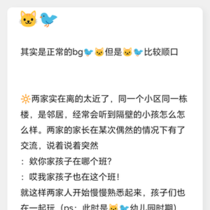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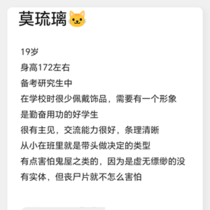
这是一桩发生在艾弗利领地,不,应该说是柏夫涅家族的“丑闻”。
那是帝制时期的事情了。
按照惯例,家主之位常由下一代的长子继承,在尼德霍格这一代,作为长子,他也从小接受继承人的教育。
这位小小的主人在任何方面都做的无可挑剔,唯有一点,脾气古怪,执拗且暴躁,宅邸内的侍从工作时愈发小心,生怕做错了事引火烧身。
尼德霍格十岁那年,他的父亲——也是当时的领主,挑了个晴朗的日子,带他巡视领地,顺便练习骑马。二人并不准备大张旗鼓,点了几名护卫便出发了。
两旁的景象飞速倒退,尼德霍格本该策马继续向前,却鬼使神差地勒住缰绳,像是被什么攫住了一样回头,他看到不远处的人影,是个正在编草叶子的年幼女孩,辫子歪歪扭扭的搭在肩膀,阳光给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毛边,像随时会消散的幻觉。一旁拉着她的是个成年男人,女孩头发上的杰作大概就是出自他手。走近了些才注意到旁边有几只羊,大概是附近的农户,借着牧羊的机会带着孩子出来玩耍。
牧羊的男人明显有些紧张,这一行人虽然穿着并不华丽,但走在最前面的两人,他估摸着应该是什么大人物。在牧羊人的注视下,尼德霍格简单介绍了自己和父亲的对外身份,紧接着指向拉着牧羊人衣角的小女孩,直奔主题:“我想要这个孩子,她会有比现在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
牧羊人愣了,半晌没说出话来。一旁尼德霍格的父亲也惊讶了一瞬,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明明对侍从不感兴趣也从不在意,但…想想这孩子的性格,就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
牧羊人支支吾吾——要把孩子交给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作为一个父亲,这怎么可能答应?可眼前的人显然不是普通农户能抗衡的。他只是个放羊的,妻子是裁缝,如果拒绝,对方会不会报复?纵然这是在艾弗利领地、在正直的柏夫涅家族的管理下,仍然有他们不能管辖到的范围、不能完美处理的事情。
尼德霍格的父亲走上前去和牧羊人交谈,表示歉意,并隐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对方拒绝,他们也不会纠缠。按住还想说话的尼德霍格,他希望对方再认真考虑一下,毕竟在领主宅邸内工作得来的生活要比做农户好得多。领主对这对父女露出稍显僵硬的笑容,严肃,但没有恶意。牧羊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时,一行人已经走远了,自己手里还攥着对方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愿意,可以向这个地址寄去消息。
回到家后的牧羊人急忙拉住妻子,告诉她这个消息,两人又忧又喜,抱着年幼的女儿,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选择。过了半个多月,在尼德霍格不知道第多少次想要发作时,宅邸内终于收到了消息,他们同意了。
尼德霍格如愿以偿的得到了这个女孩,也听到了她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赛伊。
这一年,尼德霍格十岁,赛伊八岁。
刚到宅邸的赛伊看起来可怜又无助,虽说父母和她商量过,说是为她好才把她送到这里,也保证以后会来看她,但小孩子理解不了这么多。每个晚上赛伊都在茫然地哭泣,但由于特殊的原因,没有人责怪她。
因为是尼德霍格亲自指定的人,自然而然的,赛伊作为侍从被安排在他身边,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学习如何工作。面对赛伊时,尼德霍格的态度明显比对其他侍从缓和很多,所以在某些工作方面的小事上,他们会拜托赛伊帮忙。赛伊是个善良的孩子,对于她们的请求,她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尼德霍格察觉后训斥了赛伊,也惩罚了其他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同时,因为有“特权”在身,赛伊和大多同事的关系不坏也不好,好在有那么一两个侍女愿意同她亲近。生活方面也比普通人要好的多,和外界的传闻一样,只要安安分分地工作,柏夫涅向来对人不差。
一年又一年过去,尼德霍格对赛伊的占有欲愈发明显。希望赛伊开心,又不希望她和别人走的太近,不允许其他人使唤,俨然成了自己的专属。惹她伤心也不会哄,只会皱着眉塞各式各样的礼物,从珍品宝石到鲜花发卡。赛伊不敢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隐约感知到自己对侍奉的主人有了不一样的情感,但她没有体验、不敢想象、也害怕可能会发生的任何情况。在焦灼和矛盾之下,她选择了逃避。
关于尼德霍格的婚事,领主和领主夫人很是忧愁,和他年龄相近的孩子大多已经定好了婚约。讨论过几次,也介绍过其他家族的合适女性,无一例外都被尼德霍格无情拒绝了。直到某次他终于松口:我要娶赛伊作为我的妻子,要么不结婚,其他免谈。
领主和夫人虽然知道儿子对那位叫赛伊的侍女非常在意,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想法。柏夫涅家向来以正面形象示人,并引以为傲,自然也不会太在意对方的身份,但比起平民,柏夫涅更倾向于得到其他家族的助力。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尼德霍格打个招呼便离开了。
深知儿子的性格,领主夫妻俩苦恼地商讨了好一段日子,之后再和尼德霍格提起婚事,不管是说起对家族的好处,还是进入另一阶层对赛伊的为难,还是假意威胁,尼德霍格都不为所动。直到最后,他的父亲问出:那赛伊也一样喜欢你吗。尼德霍格看向旁边没有回答,半晌终于望向父母,斩钉截铁地说:那不重要,我说了,如果一定要我结婚,妻子只能是赛伊。
领主少见的发怒了。尼德霍格也比往常更难接近,侍从们工作时不敢多一丝动作,宅邸里空气僵硬凝滞的仿佛实质。前往主人书房送信的赛伊心情和其他人一样忐忑,并不否认,尼德霍格对她很好,没有惩罚过她,也没有随意惩罚过其他侍从。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只是性格急躁一些,她想。但她还是控制不住的害怕对方,既想靠近又想逃离。
忙于处理公务的尼德霍格听到熟悉的脚步声抬起头,不动声色地听着赛伊工作上的汇报。女孩在说完后久久得不到回应,疑惑地看向他,然后听到了来自对方的请求,或者说是要求更为合适:做我的妻子,和我结婚。
赛伊心如擂鼓,脑内也止不住嗡鸣,尼德霍格就那样坐在桌后看着她,没有其他动作和话语。赛伊紧张地绞着衣角,说话自己都听不清,磕磕绊绊、连不成完整的句子。尼德霍格无意识地捻着书页一角,听的倒是很清楚,只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虽然猜到可能会是这种回答,但真正听到了还是不免恼火。忍着火气把赛伊支走,尼德霍格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重新拾起未完成的工作,只是没有安静多久,他还是攥紧拳头,狠狠地砸在桌面上。
无视父亲的反对,母亲的阻拦,赛伊的为难,他人的劝说,婚事最终还是按照尼德霍格所希望的那样举行了。
从见到女孩的第一面起,他就像是被命运施下了魔咒,渴求她、抓住她,这种念头像藤蔓一样,最初只是不起眼的幼苗,再次看去时已经缠绕的密不透风。握住女孩有些僵硬的手指,朦胧的头纱后,他未来的妻子正按照流程宣读的那样露出笑脸,但眉眼中带着忧愁。没关系,不论是因为什么,他都会去道歉的,只要她想要,只要他能做到,他都会献给她。之前的相处的时间仿佛都是虚幻,穿着婚纱走来的赛伊在这一刻才真实走进了他的命运。
成为准领主夫人的赛伊突然忙碌起来,有很多东西等着她去学习。尼德霍格告诉她不要着急,一切可以慢慢来,不想去的聚会、不想交往的人,他都可以推掉。赛伊明白他的好意,但她不敢那样,也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对于新身份,她也不能很好适应,纵使尼德霍格花了一整天时间和她道歉、解释、保证未来,她很少见他一次性说那么多话,但下次面对他时,赛伊还是会不自觉的紧张。
丈夫?自己侍奉多年的主人?她又为什么会变成领主夫人?无法否认,自己对尼德霍格有恋人般的情感,但她还没确定自己的心意,一切就这样仓促裹挟着她走向那个已经定好的结果。为了让自己没有闲暇去想这些令人困扰的事,赛伊整天的扑在书堆和课程里,希望时间能告诉她答案。
尼德霍格送她礼物的情况已经成为常态,从鲜花风铃到裙子项链,感觉什么好看、她会喜欢,全都带回来,卧室和衣帽间放不下,以至于赛伊不得不另开了一座房间,专门存放来自尼德霍格的礼物。看着满满当当的饰品,她总觉得尼德霍格似乎有把她打扮成洋娃娃的爱好。
然而,世间没有无十全十美之事。尽管艾弗利领地在柏夫涅家族写管理下风评甚佳,仍有些阴影是他们无法触及的。即使要求宅邸内的侍从都遵守规矩,依然会有令人不适的闲话传来。总有无法拒绝的邀请,聚会人多眼杂,就算没有错也会被人挑出毛病,更不要说本就是平民的赛伊,连带着尼德霍格也被明里暗里讽刺。赛伊又控制不住地想起最近她去送茶点时,领主大人熬夜处理公务,揉着太阳穴的样子。
在各种无形的压力之下,赛伊发觉自己好像病了。
尼德霍格察觉到了什么,心中隐约不安,他本就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有逐渐增加次数的拥抱,以及越发频繁地把搜罗到的好东西献给她。
赛伊不想添麻烦,或许只是错觉,自己其实并没有生病。她沉默着,不提要求,而尼德霍格也小心翼翼地不敢点破,日子便这样一天天流逝。
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尼德霍格二十六岁那年继任了家主,如果不是前家主身体不济,也不会这么快就让长子接手这个位置,只可惜除去性格执拗,在其他方面尼德霍格做的实在让人无可挑剔。也是在这一年,赛伊的病终于隐瞒不下去了,连带着身体一同虚弱下来,医生诊断后告诉他,夫人思虑过重,可能是常处于忧虑状态,如果不能好好调养,情况将会变得非常棘手。送走医生后,尼德霍格定定站在房门外,脑海里回荡着医生的忠告,突然控制不住地弯腰干呕起来。
尼德霍格带着赛伊搬至原宅邸不远处的新住处,只带上了少数亲信。又向赛伊的几位好友送去信件,恳请她们空闲时来陪她说说话。新住处完完全全改造成了赛伊喜欢的风格,少了许多似有若无的视线,不用考虑在意别人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赛伊对这里表现出明显的喜爱。尼德霍格暗中松了一口气,或许在这里,赛伊可以心情好一些,安心调理身体。
天气晴朗的下午,空气中飘来有些苦涩的、自由的青草气息,赛伊坐在草坪上,手指无意识摆弄着刚编好的草环,草环歪歪扭扭,看起来并不是成熟的作品。搬进新宅邸的喜悦没过多久就被冲散了,一切都很好,什么都没发生,她也按照医嘱说的那样做了,虽然明白自己的病并非一天两天就能治愈,但毫无好转迹象的现状让她感到焦躁与茫然。赛伊很快便又消沉下去。
某个午后,侍从捧着信笺进来时,赛伊正对着窗外发呆。原来是来自旧日友人的邀约,邀请她和几位好友一同前往马场散心。去吧,赛伊想,好久没骑马了。次日清晨,尼德霍格亲手为她系上骑装腰带。当他指尖碰到她后腰时,两人都僵了一瞬。曾几何时这个动作意味着亲密,现在却像在触摸一件濒临破碎的易碎品。“草场风大。”他生硬又温柔地塞给她一双手套。
在护卫的跟随下,赛伊抵达马场,却仍有些出神,她摇摇头试图甩开杂念,前去加入好友们的话题。经过一片野草地时,赛伊突然勒住缰绳。风把她的发带吹落到草丛里,她却盯着那些摇曳的草叶不动。“要帮您捡回来吗?”侍女问道。“不,”她轻声说,“就这样吧。”
意外总是来的突然。赛伊骑乘的马匹突然受到惊吓失去控制,赛伊也因此摔下马背,当场昏迷。踉踉跄跄赶到的尼德霍格看到满是伤痕的爱人,脑中忽然一片空白,所有的声音全都消失了,过了半晌才缓过神来。他跪在床边,死死虚握住爱人的手抵在额前,求求你,求求你…快点醒来。
赛伊昏迷不醒,紧接着反复发起了高烧,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后终于稳定下来,宅邸的侍从们为这位和善的女主人感到担忧,也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风雨”而提心吊胆。终于,在昏迷后的第六天,赛伊醒来了。
三天了,尼德霍格还是没有完全适应。醒来后的赛伊失去了婚前大部分记忆,对大多数之前亲近的人感到紧张,唯独对自己的丈夫表现出全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这让尼德霍格慌乱又窃喜,像是被抢夺来的公主终于完全接纳了恶龙。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爱人相处,尼德霍格极力压缩了处理公务的时间,这不免让某些同僚和属下感到不满和埋怨,并试图把这些言论传到领主夫人的耳朵里去,而尼德霍格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宅邸内没出现的暴风雨全都降临到那些人的头上,尼德霍格头一次对领主的责任产生了抗拒。
丢失了部分记忆的赛伊身体比原来弱了很多,总是断断续续的生小病,但相比之前开朗了一些,对未知的东西感到好奇,同时异常听从尼德霍格的话,自此之后尼德霍格恨不得将赛伊的大小事情全都包揽,几乎每日亲手打扮自己的爱人,装饰洋娃娃一般,每每二人一同出现,衣着打扮总是带着极大的反差感。就这样又过了四年,赛伊断断续续恢复了一些从前的记忆,两人的关系也在相处中比以往更加紧密。
在赛伊二十八岁这年的秋天,没有任何预兆,又或许是早有预兆,从一场令人头痛欲裂的午睡中醒来后,她的身体开始迅速凋零,没过两天就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又过了两天,赛伊已经无法自由走动了,她只能无力地依靠在床上,看着床头友人送来的一小束野花,看着窗外晴朗的天空,看着侍从不小心投过来的不忍眼神,看着每日向祈祷的雕塑一样坐在身旁的尼德霍格。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她大概已经清楚了。
长时间不进食导致赛伊肉眼可见的消瘦下来,前面的几天里赛伊还能微笑着安慰男人,到后来,连说话都变得艰难起来。无数个医生来过,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尼德霍格从刚开始的暴怒到后来的平静,现在他只能一遍遍对虚空作无谓的祈祷。
生命无可挽回地流逝着。病重的第二十三天,赛伊忽然微微一动,缓缓望向尼德霍格,挣扎着抬手想触碰他的脸。尼德霍格慌乱地凑过去,身体不住地颤抖,双手紧紧包裹住爱人的手。他面色灰败,泪水模糊了充满血丝的眼睛,顺着爱人消瘦到硌人的手腕流淌下来,浸没到衣袖里,晕成一片小小的灰色。耳边传来赛伊很轻,又断断续续的声音。
“对不起……一直以来都…谢谢你…以后要……好好生活……不要太…伤心………你是……很好的领主…”赛伊的声音越来越轻,直到尾音消散在空气中,唇边还挂着微笑,手却无力的落下。无论尼德霍格怎样呼唤她的名字,再也没有人给予回应。
尼德霍格平静的令人害怕,他不允许任何人踏足那个房间,也不能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现实,不论是宅邸的侍从,还是前来探望的来访者,全都被赶了出去。把自己闷在房间三天后,门终于打开了,尼德霍格目标明确的奔向书房,又在里面闷了五天,每日送餐的侍从不敢多问,只敢打开一条门缝,小心地把食物放在地上,然后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去。第六天,领主久违的把自己打理个干净,特意梳洗打扮了一番。宅邸中侍从的去处已经安排好,准备好的信件也会在明早送达,文件协议都在书房,一切都很好,差一点点就完美。
把提前准备好的鲜花插进房间的花瓶中,调整到最合适的角度,和衣躺在爱人身边,调整了好一会儿才十指交握,尼德霍格有些高兴。赛伊,我很快就能去见你了。
艾弗利领地的深秋,枯叶卷着霜气簌簌落下,印着柏夫涅家族的纹章旗帜在风中沉默地翻飞。
前领主——如今不得不重新协助次子执掌家族的老人——站在宅邸的走廊尽头,望着仆人们进进出出。他们搬运文件、清点遗产、低声交谈,偶尔有人抬头瞥向二楼那扇紧闭的房门,又迅速低下头去。那间卧室的门锁已经被撬开,但无人敢擅自踏入,仿佛那里仍盘踞着某种不可触碰的阴影。
直到黄昏时分,前领主才终于推开那扇门。
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照进来,床上的两人仿佛只是睡着了。赛伊面容平静,唇角甚至带着一丝微笑,仿佛只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而尼德霍格,他的儿子,侧卧在她身旁,手腕上的伤口已经干涸成暗红色,另一只手却仍紧紧扣着她的手指,像是生怕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与她走散。
多年后,他们曾短暂居住过的宅邸,被改建成了一座花园,园中种满了各式各样赛伊生前喜爱的花,而在花园正中央,立着一尊没有铭文的石碑,石碑的基座上,缠绕着一圈早已枯死的荆棘。
仿佛仍在固执地守护着什么。
——END——
联姻对象是个比兄弟俩聪明的,但更会伪装
弟被联姻的那个坏家伙(好家伙)吃的死死的,希望哥把把关
联姻对象对弟有点兴趣,但更多以利益为先,不是纯粹的好或坏,如果能把他们(弟家里)吞并就更好了
联姻对象家规模比弟家大,属于地头蛇
弟还没有接管,处于正在学习和听从命令的时期,总之以后会是他的
明明也有亲生的继承人
弟也在等对方(联姻对象)的支持,比较险
弟现在还没现在当家的手段,也没有被人看得起
他主要还是在听命令做事,可以看作是(保安)小组长,还要管其他人吃喝拉撒小矛盾
手下不全都是大汉,也有身板不行的(马仔)至少这些人他必须得管得住
弟的竞争对手(亲生的继承人)拉拢人心方面更胜一筹
弟办事比较利索,下手也狠
如果弟不成功,一个选择是他被对方针对排挤或者直接拉到某个地方做了。另一个是当对方手下,但会被当驴,还会被惦记,被纯苦力打压,总之目的是降低其他人对他的支持信任,让人不敢支持也不敢出手帮助,不管关系多好。
就算不成功,弟这个“小队长”的身份也会留着,还要他做事,需要有身份